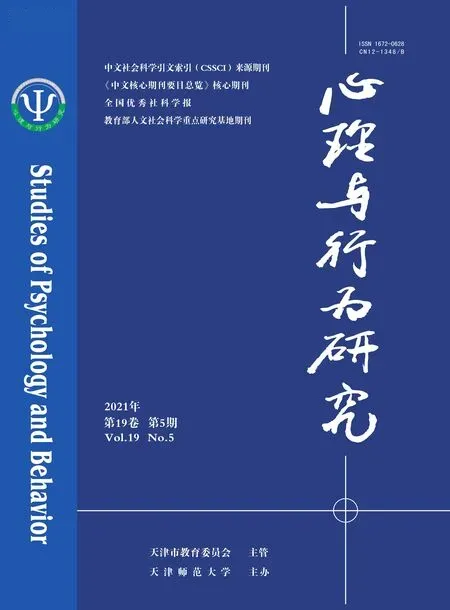同伴關系與兒童的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交叉滯后分析*
周廣東 周廣敏
(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天津師范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院,天津 300387) (2 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天津300387) (3 學生心理發展與學習天津市高校社會科學實驗室,天津 3003871) (4 天津師范學校附屬小學,天津 300131)
1 引言
同伴關系(peer relationship)是指同齡人之間或心理發展水平相當的個體間,在交往過程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人際關系,這種關系里包含了在一系列互動中產生的意義、期望和情緒(Rubin, Bukowski, & Parker, 2007)。同伴關系既是兒童社會性發展的重要背景,也是兒童社會性發展的主要內容。進入小學以后,同伴關系在兒童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影響其心理和行為的諸多方面,比如攻擊(Parker, Rubin, Erath,Wojslawowicz, & Buskirk, 2015)。
攻擊(aggression)是指故意做出的傷害他人的行為(Dollard, Miller, Doob, Mowrer, & Sears,1939)。兒童的攻擊行為因其功能的不同可以分為“反應性攻擊”和“主動性攻擊”:反應性攻擊(reactive aggression)是指個體在感受到威脅后做出的傷害他人的行為;主動性攻擊(proactive aggression)是指個體為了預期利益或某種精神主導而故意傷害他人的行為(Dodge & Coie, 1987)。
研究顯示,反應性攻擊兒童容易被同伴拒絕,但主動性攻擊兒童卻可以得到同伴的接納(Stoltz, Cillessen, van den Berg, & Gommans,2016)。反應性攻擊兒童對同伴的行為意圖判斷有偏差,往往誤將同伴在模糊情境下的意圖歸因為有敵意的(Evans, Fite, Hendrickson, Rubens, &Mages, 2015);另外,反應性攻擊兒童人際交往技能較差,行為反應沖動且過激,負性情緒較多(Moore, Hubbard, Bookhout, & Mlawer, 2019)。這些特點往往導致反應性攻擊兒童不被同伴接納。相反,主動性攻擊兒童往往具有領導力和幽默感(Price & Dodge, 1989),他們在同伴關系里經常占據主導地位,因而容易被同伴喜歡。
雖然兒童同伴關系和攻擊行為的關系已經被大量研究證實(Guimond, Brendgen, Correia,Turgeon, & Vitaro, 2018; Price & Dodge, 1989),但對二者關系的方向性問題存在三種不同觀點。
第一,有研究者認為,同伴拒絕導致被拒絕兒童使用攻擊行為(Jiang & Chen, 2020)。Vitaro,Boivin和Poulin(2018)總結了三種理論來說明同伴關系是如何影響兒童的攻擊行為的:(1)行為缺陷機制認為同伴拒絕使得兒童不得不獨處,或跟年齡更小、社交技能更差的兒童相處,從而減少了其練習解決社交問題的機會,進而使用攻擊這種沖動的行為來解決同伴問題(Ladd, 1983);(2)社會?認知機制認為來自同伴群體的拒絕會使兒童產生憤怒情緒,加劇其對敵意信息的敏感程度,進而用攻擊來回應同伴的“敵意”(Lansford,Malone, Dodge, Pettit, & Bates, 2010);(3)社會歸屬機制認為人類有天然的建立和保持正性而持久人際關系的需求,同伴拒絕會使得兒童加入其他被拒絕者的隊伍,從而使他們接觸到了更多攻擊性情景,而“同道朋友”的攻擊行為也會為兒童的攻擊行為提供“榜樣”作用(Vitaro, Pedersen, &Brendgen, 2007)。綜合以上三種理論觀點和先前研究可知,行為缺陷機制和社會?認知機制中對同伴拒絕導致兒童獨處和敵意的觀點更適用于解釋反應性攻擊兒童(Evans et al., 2015; Moore et al.,2019),而社會歸屬機制中對同伴拒絕導致兒童加入攻擊者的隊伍更適用于解釋主動性攻擊兒童(Stoltz et al., 2016; Vitaro et al., 2007)。
第二,也有研究者認為,兒童的攻擊行為導致其同伴關系變差(Evans & Fite, 2019; Lansford et al., 2010)。在早年的一個綜述中,兒童的攻擊行為被認為是預測同伴拒絕最顯著的指標(Coie,Dodge, & Kupersmidt, 1990)。一個關于同伴拒絕的進化觀點(Schaller, Simpson, & Kenrick, 2006)認為,人類進化出的心理適應性旨在形成關系,以便更好地生活在社會群體中,那些違反社會規范的人(比如攻擊性強的人)往往會被群體拒絕,因為社會規范可以簡化和促進人際交往,有利于人類更好地生存和進化。在兒童群體里,攻擊行為往往不被群體規范認可,因此那些攻擊行為較多的兒童容易被同伴拒絕。
第三,兒童的攻擊行為與同伴關系二者相互影響(紀林芹, 潘斌, 郭菲, 陳亮, 張文新, 2017;Kamper-DeMarco & Ostrov, 2019),這一結果符合“轉換模型”(Sameroff, 2009)的理論主張。該理論認為,兒童與其所處環境是相互影響、動態發展的,兒童的先天特性在后天環境中得以發展和展示,環境反過來也會影響兒童特性的變化程度。具體到本研究的主題,該理論認為兒童的攻擊行為與同伴關系是可以相互影響、相互預測的。
對兒童同伴關系與攻擊行為關系方向性的爭論可能來自以下兩點:(1)以上三種觀點的實證支持大都來自橫斷研究的結果,而橫斷研究從方法學上并不能解決這一爭論。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縱向追蹤的方法,探討同伴關系與兒童的攻擊行為的關系方向性。雖然以往有關于兒童同伴關系和攻擊的縱向研究(紀林芹, 高敏, 張良, 潘斌, 張文新, 2020; Chen, Huang, Wang, & Chang, 2012; Rohlf,Busching, & Krahé, 2017),卻沒有區分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2)以往的理論往往把攻擊行為作為一個整體而非異質性的不同類型來看待。事實上,兒童的攻擊行為有不同的亞類,比如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這些不同亞類攻擊性兒童被證實有不同的同伴關系(Evans, Fraxer, Blossom, & Fite,2019)。
在實際研究操作中,衡量兒童同伴關系的常用指標是“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它反映了群體中的同伴對某一個體的喜歡程度(Coie,Dodge, & Coppotelli, 1982)。社會偏好得分越高代表被同伴接納的程度越高,得分越低代表被同伴拒絕的程度越高。低社會偏好常被視為兒童發展中的壓力事件(Lansford et al., 2010),因為同伴群體是兒童發展社交技能的重要領域,來自同伴的拒絕則剝奪了兒童參與社交互動的機會,因而無法有效發展良好的社交技能,進而使其更多地卷入到攻擊性的社交活動中(He, Koot, Buil, & van Lier, 2018)。
由于以往研究顯示,反應性攻擊兒童有較多的敵意歸因偏差(Evans et al., 2015)、較差的人際交往技能和易怒的情緒反應特點等(Moore et al.,2019),往往導致其在同伴群體中的社會偏好較低。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兒童的反應性攻擊負向預測其社會偏好。此外,較低的同伴地位對兒童是一種挫折體驗,挫折會直接導致攻擊或為攻擊的發起做好準備。來自同伴的拒絕往往損害兒童的自尊,為了捍衛自尊,被拒絕的兒童也更有可能表現出反應性攻擊行為(Wong & Raine,2019)。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社會偏好負向預測其反應性攻擊行為。
主動性攻擊兒童常被認為是有領導力的、幽默的(Price & Dodge, 1989),因而容易被同伴所接納(多為與其有相同不良行為的兒童),但同時又被受其侵害的同伴厭惡(Crick, Murray-Close,Marks, & Mohajeri-Nelson, 2011)。所以,主動性攻擊兒童的同伴關系可能存在兩極分化的現象:一方面在有不良行為的同伴里受到擁護和喜歡,另一方面又在被攻擊的同伴里受到拒絕和厭惡。基于這種情況,在整體考慮兒童群體時,主動性攻擊兒童的社會偏好可能會因為兩部分群體的相反態度而相互抵消。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社會偏好與兒童的主動性攻擊無顯著預測關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整群抽樣法,以天津市南開區某小學一到五年級兒童為研究對象,于2017年4月(T1)和2018年1月(T2)分別進行了兩次施測。第一次調查時被試總人數為1409人,由于轉學的原因,在第二次調查時缺失了29人。采用在兩次調查中提供完整數據的1380人,其中男生729人(占比53%),女生651人(占比47%)。第一次施測時一到五年級的平均年齡和標準差分別是6.89±0.76,7.88±0.71,8.71±0.63,9.75±0.64,10.67±0.60。其中,一到五年級的人數分別是274人(占比20%)、325人(占比24%)、327人(占比24%)、223人(占比16%)、231人(占比17%);獨生子女占總人數的41%,非獨生子女占總人數的59%;父母婚姻狀況中,已婚狀態占96%,離婚狀態占3%,其他占1%;家庭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占8%,3000~4999元的占16%,5000~9999元的占52%,1萬元及以上的占24%。
2.2 研究工具
2.2.1 反應性?主動性攻擊問卷
采用反應性?主動性攻擊問卷(Dodge & Coie,1987)測量兒童的攻擊行為,由班主任依據此量表對自己班級內的每個學生做出評價。該問卷由6個題目組成,其中前3個題目評價反應性攻擊,如“對意外事件的憤怒反應過于激烈”;后3個題目評價主動性攻擊,如“威脅或欺負別人”。量表采用Likert 5點計分,對題目中描述的行為發生在該兒童身上的頻率進行評價,1代表“從來沒有”,5代表“總是有”。這一問卷是測量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被使用最為廣泛的量表。在本研究中,反應性攻擊分量表在T1和T2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是0.87和0.80,主動性攻擊分量表在T1 和 T2 的 Cronbach’s α 系數均為 0.87。
2.2.2 同伴提名
同伴提名(peer nomination)是Coie等(1982)用來測量同伴關系的一種方法,具體做法為:在教室里,發放給每一位同學一份自己所在班級的人員名單,要求每個人選擇至少三個“最喜歡”(積極提名)和“最不喜歡”(消極提名)的同學。統計分析時,首先,計算每位同學得到的積極提名(like most,以下簡稱LM)和消極提名(like least,以下簡稱LL)數量,每得一票即累加一分;其次,將積極提名和消極提名的分數在其所在的班內進行標準化,得到標準化的積極提名(ZLM)和消極提名分數(ZLL);最后,計算社會偏好分數,即用積極提名標準分數減去消極提名標準分數(ZLM?ZLL)。
2.3 研究過程
本研究由經過專業培訓的研究生和班主任擔任主試。在施測前,對主試進行集中培訓,確保被試充分了解整個測試的操作流程和明確注意事項。在征得父母、學校和老師的同意后統一施測。首先,班主任填寫反應性?主動性攻擊問卷,對班級里的每個同學進行評定;其次,班主任作為主試發放同伴提名量表,介紹統一指導語,以班級為單位集體施測;最后,每班班主任按班級收齊問卷并上交。
3 結果
3.1 主要變量的相關分析
各變量間的兩兩相關結果見表1,人口學量表中的父母婚姻狀態和家庭月收入與其他所有變量之間均無顯著相關,因此,在后續的交叉滯后分析中不再考慮兩個變量。而性別、年級和父母受教育水平與攻擊行為和同伴關系的指標之間大多相關顯著,因此在后續的交叉滯后分析中將其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

表1 人口學變量、社會偏好、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的相關分析
T1和T2的社會偏好與兩次的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均呈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在?0.32至?0.22之間,屬于中等相關,符合進一步進行交叉滯后分析的要求。
3.2 重復測量的差異檢驗
為了檢驗重復測量的差異性,對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及同伴關系的指標分別進行了單因素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兩次反應性攻擊之間存在顯著差異(F=30.64,p<0.001,=0.024),T2的反應性攻擊顯著低于T1(MT1=2.03,MT2=1.85);兩次主動性攻擊之間存在顯著差異(F=20.23,p<0.001,0.016),T2 的主動性攻擊顯著低于T1(MT1=1.40,MT2=1.30)。
由于社會偏好是對同伴提名標準化結果的計算,而標準化后的平均分數皆為0,所以,對同伴關系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以同伴提名的實際分數而非標準分數作為指標。結果顯示,兩次同伴積極提名的分數之間存在顯著差異(F=2140.89,p<0.001,=0.642),第二次的同伴積極提名分數顯著高于第一次(MT1=11.64,MT2=21.69);兩次同伴消極提名的分數之間存在顯著差異(F=1287.17,p<0.001,=0.489),第二次的同伴消極提名分數顯著高于第一次(MT1=6.60,MT2=13.40)。
3.3 交叉滯后分析
采用交叉滯后模型來分別檢驗兒童的反應性/主動性攻擊與社會偏好之間的縱向關系(見圖1)。將性別、年級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作為控制變量;同時出于基本的邏輯考慮,將性別與年級、父母受教育水平之間的相關固定為0。
在兒童的反應性/主動性攻擊與社會偏好的交叉滯后分析中(見圖1),模型擬合良好:CFI=1,TLI=1,RMSEA=0.005,90%CI[0, 0.038],SRMR=0.009。結果顯示,各個變量的縱向穩定性較好,尤其是社會偏好的穩定性最高,β=0.74,p<0.001,95%CI[0.71, 0.77]。另外,T1的反應性攻擊顯著預測T2的反應性攻擊,β=0.18,p<0.001,95%CI[0.13, 0.23];T1的主動性攻擊顯著預測T2的主動性攻擊,β=0.16,p<0.001,95%CI[0.10, 0.22]。

圖1 社會偏好與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的交叉滯后模型圖
在交叉滯后路徑中,T1的社會偏好顯著預測T2的反應性攻擊行為(β=?0.17,p<0.001,95%CI[?0.23, ?0.11])和主動性攻擊(β=?0.18,p<0.001, 95%CI[?0.25, ?0.11]),T1 的反應性攻擊也可以顯著預測T2的社會偏好(β=?0.05,p=0.020,95%CI[?0.10, ?0.01]),但 T1 的主動性攻擊對T2社會偏好的預測不顯著。
4 討論
同伴關系和攻擊行為對兒童的社會性發展均有較大影響,但對于二者之間關系的方向性卻并未得到一致結論。本研究基于這一研究問題,采用縱向追蹤的方法探討二者關系的方向性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區分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結果顯示,社會偏好與兒童的反應性攻擊相互負向預測,即較低的社會偏好導致較高的反應性攻擊,而較高的反應性攻擊也會降低其社會偏好;社會偏好可以負向預測兒童的主動性攻擊行為,但主動性攻擊并不預測社會偏好,即較低的社會偏好導致較高的主動性攻擊,但較高的主動性攻擊并不一定會損害兒童的社會偏好。
4.1 同伴關系和攻擊行為的縱向變化
本研究發現,兒童在T2的積極和消極提名均顯著高于T1,這可能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兒童對本班同學的熟悉度越來越大,因此在T2的測量中都有了更多的提名。但教師對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行為報告顯示,T2比T1均有顯著下降。關于兩類攻擊行為的發展變化,不同的研究結果不盡相同。比如Fite,Colder,Lochman和Wells(2008)對245名高攻擊性兒童為期6年(從4年級末到9年級)的追蹤研究發現,兒童的反應性攻擊及主動性攻擊在6年級達到頂峰,之后兩種攻擊行為的發生頻率都開始下降。
4.2 社會偏好與反應性攻擊
本研究中,社會偏好與反應性攻擊相互預測,這一結果符合“轉換模型”(transactional model)(Sameroff, 2009)的理論主張。該理論認為,兒童與其所處環境是相互影響、動態發展的,即兒童較低的社會偏好可能會導致較高的反應性攻擊,而具有較高反應性攻擊的兒童會被其他兒童進一步排斥,導致更低的社會偏好。這一結果與Chen等(2012)的縱向研究結果一致,只不過該研究并未區分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
雖然社會偏好與反應性攻擊相互預測,但具體到每條單一的路徑,其內在機制可能不同。就反應性攻擊負向預測社會偏好這一路徑來說,可能是攻擊行為在中國文化下不受歡迎,攻擊行為被認為是對群體規則的違反。在兒童群體里,攻擊行為往往不被其他兒童認可,因此那些攻擊行為較多的兒童容易被其他同伴拒絕。從同伴拒絕的進化觀點(Schaller et al., 2006)來看,那些違反社會規范的人(比如攻擊性強的兒童)被群體拒絕可以看作是對違反群體規范的懲罰,以便群體成員更好地遵守群體規范。兒童的反應性攻擊顯著負向預測其社會偏好,證實了假設1,這一結果也與Evans和Fite(2019)的研究結果一致。該研究發現,幼兒園時期的反應性攻擊可以預測小學1~3年級的同伴拒絕。這說明,反應性攻擊預測社會偏好具有中外一致性。
另外,社會偏好顯著負向預測兒童的反應性攻擊,證實了假設2,相同的結果也在很多中外研究中得到驗證(Gagnon & Rochat, 2017; Yao et al.,2019)。對兒童而言,較低的社會偏好意味著他們不被同伴群體接納,進而缺少了與同齡兒童進行社交互動和有效解決社交問題的機會,導致其使用簡單粗暴的攻擊行為來解決同伴沖突(Ladd,1983)。來自同伴群體的拒絕會使反應性攻擊兒童對社交信息產生判斷偏差,比如他們習慣把很多模糊情境下的同伴意圖判定為是“有敵意的”,進而被這種錯誤的“敵意”判斷驅使著做出更多的反應性攻擊行為(Lansford et al., 2010)。
4.3 社會偏好與主動性攻擊
本研究中,社會偏好負向預測兒童的主動性攻擊行為,與假設3不符,這一結果也與西方的主流研究結果不同(Card & Little, 2006)。這一結果與一項針對香港8~14歲青少年的研究結果一致(Wong & Raine, 2019),該研究發現主動性攻擊較多的青少年其同伴關系問題也較多。出現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來自同伴較低的社會偏好降低了兒童的自尊水平,為了維護被損害的自尊,兒童傾向于使用主動性攻擊來挽回“顏面”和“控制力”。
社會偏好對主動性攻擊的單向預測符合社會歸屬機制的預測(Vitaro et al., 2018),即兒童也有天然的建立和保持正性而持久同伴關系的需求,同伴的拒絕會使得其加入其他被拒絕者的隊伍(Fite, Colder, Lochman, & Wells, 2007),進而接觸到了更多攻擊性情景,而“同道朋友”的攻擊行為也會為兒童的主動性攻擊行為提供“榜樣”作用,使得這些被拒絕的兒童學習到使用主動性攻擊行為來解決同伴關系問題。也就是說,主動性攻擊兒童的攻擊行為可能是其在同伴群體里學習而得到的,用來應對同伴拒絕帶來的壓力。當他們意識到攻擊帶來的“好處”,便會在認知上形成“攻擊能達到正向結果”的預期(Marsee &Frick, 2007),這會讓他們以后更多地使用攻擊行為。
同時,兒童的主動性攻擊并不預測社會偏好,可能的原因是,主動性攻擊兒童往往具有“幽默感”和“領導力”(Price & Dodge, 1989),這些特性是他們受到一部分兒童喜歡的原因(Stoltz et al., 2016);另一方面,其主動性攻擊行為又會讓被攻擊者排斥他們。也就是說,主動性攻擊兒童的社會偏好可能會因為這兩個群體的相反態度而被折中,進而無法體現出主動性攻擊預測社會偏好的關系。
4.4 區分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的重要性
西方研究中,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兒童的同伴關系截然不同,反應性攻擊兒童的同伴關系較差,而主動性攻擊兒童被同伴接納的程度較高(Stoltz et al., 2016)。基于此,本研究推斷反應性攻擊和社會偏好相互影響,主動性攻擊與社會偏好無顯著相關,但結果只有部分支持這一推斷:社會偏好與反應性攻擊互相預測,但社會偏好對主動性攻擊則是單向預測。這一結果為解決不同理論的爭論提供了實證依據,比如,社會偏好與反應性攻擊的關系符合“轉換模型”的預測,而與主動性攻擊的關系更符合社會歸屬機制的預測。同時也說明,在討論同伴關系與攻擊行為關系的方向性時應區分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
4.5 研究的創新與局限
本研究的創新性有以下幾點:(1)采用了縱向追蹤的研究方法,利用交叉滯后模型,考察了這兩種攻擊行為與社會偏好的關系,對解決同伴關系與兒童攻擊行為關系方向性的爭論有重要貢獻;(2)區分了攻擊行為的不同亞類,發現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與社會偏好的關系方向性是不同的,這些結果有助于在實踐中去更有針對性地預防兒童的攻擊行為和改善同伴關系。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被試樣本來源欠缺多樣性,僅選取了一所學校的被試,樣本的代表性不夠好。第二,追蹤時間較短,前后僅8個月的時間間隔。第三,數據采集次數較少。雖然采用縱向研究,但只有兩個時間點,因而同伴關系與兩類攻擊行為之間關系的考察仍然不夠豐富。第四,攻擊行為的評價來源不夠多樣化。兒童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行為由班主任評價。但兒童的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在家庭里的表現如何,兒童撫養者如父親和母親對兒童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行為的評價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5 結論
本研究通過對兒童同伴關系及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兩次追蹤,運用交叉滯后統計分析方法,探討了兒童的社會偏好與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關系的方向性問題,得到以下結論:(1)社會偏好與兒童的反應性攻擊相互負向預測,即較低的社會偏好導致較高的反應性攻擊,而較高的反應性攻擊也會降低其社會偏好;(2)社會偏好可以負向預測兒童的主動性攻擊行為,但主動性攻擊并不預測社會偏好,即較低的社會偏好導致較高的主動性攻擊,但較高主動性攻擊并不一定會損害兒童的社會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