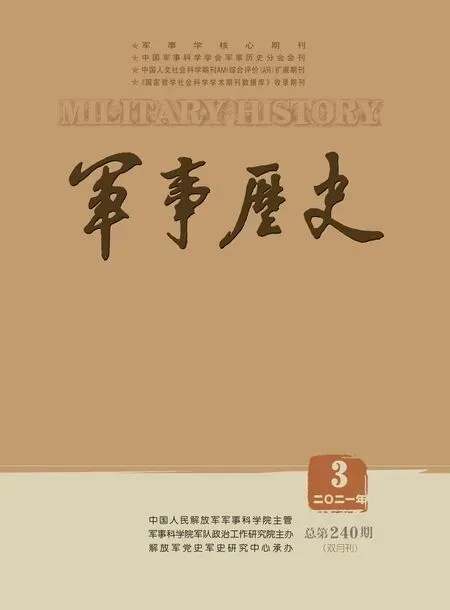試論日本對美提供軍事技術的開啟*
★ 吳懷中
日本對美提供軍事技術,是從20世紀80年代正式開啟的。之前,日本由于產業技術水平與美國相比顯著低下、國內政治因素及相關政策的嚴格限制,①在“和平憲法”“武器出口三原則”等法規之下,日本對外軍事合作在二戰后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此外,在20世紀80年代前的政黨及議會政治競爭中,被貼上“反憲”“違憲”的標簽等于政治自殺,所以作為執政黨的自民黨對軍事裝備及相關技術的出口實施了較為嚴格的自我控制。尚不具備對美開展此種合作的條件。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日趨激烈的美蘇戰略及軍事競爭使得美國亟須盟國提供包括軍事在內的全方位支持,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已成為公認的世界經濟大國并在軍民兩用即通用技術領域擁有先進實力,以中曾根為代表的保守集團主導日本安全防衛政策的制定并竭力放寬對外軍事合作限制,以上這三個條件使得日本對美提供軍事技術成為可能。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美國的高科技武器中,日本的技術及器件已是重要的組成要素。日本向美提供軍事技術,對美國加強軍事綜合力量與掌握世界霸權發揮了相應作用。同時,從其后的發展可知,日本通過這種合作,也在不斷突破對外軍事交流的限制和層級,加速防衛政策的調整與改造。
從中國知網(CNKI)的數據看,以“日美”+“軍事技術”為關鍵詞檢索,所得相關論文僅有5 篇左右,可見目前中國學界研究本主題的論文仍顯薄弱。馮昭奎著《美國要日本提供哪些軍事技術》為1983年發表的文章,且主要是對美國可能要日本提供的十種技術或材料“進行粗略的介紹”,基本沒有涉及日本實際是否以及如何對美提供的政策過程。李友申著《日美軍事技術合作新進展》為1992年發表的短文,也幾乎沒有涉及產品、材料等技術細節,只是簡略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日美雙方的相關“考慮”。①參見馮昭奎:《美國要日本提供哪些軍事技術》,《系統工程與電子技術》1984年第3 期;李友申:《日美軍事技術合作新進展》,《世界經濟與政治》1992年第9 期。以上兩篇均無注釋,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其他研究日美同盟及日美關系的論文數量眾多,但對此主題均一筆帶過,缺乏詳細論述。有鑒于此,本文擬分析20世紀80年代日本對美提供軍事技術合作的緣起、背景、演變過程、關鍵突破與持續進展,尤其從政策過程和技術內容兩個方面,對20世紀80年代日本對美提供軍事技術進行系統梳理和論述。在此基礎上,梳理其特點與趨勢,從而揭示80年代日美軍事技術合作是已進入日本能夠成為“提供方”的雙向時代,這在其后的日美軍事合作及同盟轉型脈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和作用。②實際上,要對日美軍事技術合作做到詳細、系統的論述,是很困難的。雙方就日本對美提供武器技術而締結的是“一攬子”協定,并不就日本提供的每項技術交換公文,且規定原則上不公布所提供的技術內容。這給外界和研究者了解這個問題的全貌增加了很大難度。
一、歷史背景與緣起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軍事技術”作為支撐美國軍事力量的因素開始發揮作用。③此處的“日本軍事技術”,泛指日本對美提供而被美方用作軍事用途的軍事技術以及民用技術,后者一般也被稱為Dual-use technology(簡稱為DUT)。其原因,一是美國的戰略需求和客觀形勢所迫,二是日本能夠提供美國所需的部分技術及產品。
(一)美國為應對冷戰新階段形勢,需要日本軍事技術的支撐。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美蘇冷戰進入更趨激烈的新階段。1981年1月,里根即否決前任卡特政府的對蘇“緩和”戰略,大幅增強軍事實力,試圖以“以實力促和平”,即建立軍事優勢來壓倒蘇聯。當時,美國在關鍵戰略武器的開發、生產等領域,具有足夠的儲備力量,但在兩用技術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卻面臨著國防產業競爭力下降的局面。也就是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長期重視軍品的設計與生產技術,卻導致兩用技術及產品的開發被推遲延誤,使得美國在軍工基礎的一般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力多有下降——而這對生產尖端武器裝備是不可欠缺的。
現代國防生產中需要很多民用或通用技術的支撐,這增加了非傳統的軍事供應商通過技術及零部件生產進入國防市場的機會。最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主要的國防裝備愈發變得以技術為中心并且非常復雜,因此,后來者很難在沒有大量前期投資與技術儲備的情況下趕超上來并進入這種制造系統。實際上,美國在武器系統配件采購上也日益依賴于海外供應商,其中依賴性較大的產品和零部件有以下幾種:(1)用于高速數據處理的新一代砷化鎵合成半導體;(2)使用砷化鎵的激光半導體發射器等多種光纖光學器件;(3)隨機存取半導體;(4)計算機終端;(5)用于計算機數字讀取裝置的液晶顯示板;(6)精密玻璃;(7)用于高電壓開關切換裝置的特殊硅;等等。④參見[日]松村昌廣『日米同盟と軍事技術』、勁草書房、1999年、35~45 頁。很明顯,這些在當時很多是日本的領先項目或獨門技藝。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正式開始關注同盟國的軍事及軍民兩用技術。里根政府就職后,立即表現出對日本軍事及兩用技術的濃厚興趣,希望將其轉用到美國,使其成為本國技術力量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在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開始認為日本的軍事及兩用技術對于增強自身的軍事技術是必不可少的。⑤參見[日]花井等·淺川公紀編著『戦後日米関係の軌跡』、勁草書房、1995年、172~181 頁。從這一點看,日本技術可以說是里根政府應對冷戰的力量元素之一,雖然它可能只是眾多變量中的一個有限成分,但卻是必要的組成部分。
(二)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期尤其80年代,日本產業高度發達化,軍民兩用技術先進,可以為美提供軍事技術援助。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軍事技術或兩用技術通常都是由民企研發使用的。實際上,武器生產也是由廣泛產業領域的眾多民企生產的零部件組裝融合而成。軍事技術原本很多是作為民用技術而用于生產的,性能或功能等進行改變或改善后也可用于軍事,日本在這方面無疑具有突出的優勢和吸引力。①例如,80年代的“東芝事件”就說明了這一點。該事件的基本脈絡為,日本東芝機械公司因違反“巴統”出口限制向蘇聯出口大型數控機床而在1987年5月遭到日美政府的懲處。
在日本,軍事及軍民兩用相關技術與產品的關鍵處理中樞,是防衛廳技術研究本部和大型民間防衛產業企業。防衛省技術研究本部總管龐大的預算,將預算撥付于民間防衛產業企業——例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島播磨重工業、日立、日本電氣等進行訂貨,開展軍事技術及軍事產品的委托研發與生產。此外,經濟產業省作為監管防衛產業的行政機關,在軍事技術及軍事產品的規劃與發展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②參見[日]久保田ゆかり「日本の防衛調達の制度疲労と日米関係」、『國際安全保障』2010年第38 巻第2 號、47~66 頁。
總的來說,20世紀80年代,就國際比較而言,美國在對國防工業基礎來說愈顯重要的兩用技術方面并不領先。形成對照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民間制造部門持續得到投資,其一般制造技術得到高速發展,結果是軍民兩用技術的進步也日新月異。到了20世紀80年代,在原材料、零部件、子系統設備等領域,日本開始生產性能、價格均優于美國制造的產品。如此,日本的大型企業集團在開發民用技術的過程中,實質性地開發出了高度的兩用技術或軍事技術,某些領域的水平已經領先于美國,例如半導體技術等。③李友申《日美軍事技術合作新進展》,《世界經濟與政治》1992年第9 期,第36 頁。此外,日本的國防產業界在依賴美國技術的同時不忘消化吸收,由此也得以快速發展起來。例如,在軍用飛機領域,通過特許生產美國F-4 和F-15 戰斗機,日本積累了發動機與機身制造、空氣動力技術和其他工程技術等研發經驗和能力,其后,更是達到了追求國產下一代戰斗機(Fighter support x,簡稱FSX)的水準。④參見[日]久保田由香里·佐藤丙午「日米防衛裝備·技術協力」、竹內俊隆編著『日米同盟論』、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年、213~221 頁。以上兩種作用力的結果是,日本在私營企業部門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工業基礎”。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急速精密化的軍品生產體系需要無數的高科技零部件,而這不可能由美國國內產業制造部門全部承擔。于是,日本的兩用技術或軍事技術被美軍引進,形成了彌補美國軍事產業基礎欠缺部分的現象。特別是,日本在光學和電子等高科技領域中開始擁有比美國更好的技術及產品,美國因此迫切希望進行引進和利用。在此過程中,包括聯合研發FSX 等,日美軍事技術交流合作新動向也不斷顯現。
二、美國明確要求日本提供軍事技術與日本初步回應
美國對日啟動軍事技術政策調整,是以設立雙方定期磋商機制為標志的。1980年9月,日美兩國政府在華盛頓舉行了“第一屆日美裝備與技術定期磋商(S&TF)”。磋商會主要是由當時的日本防衛廳次官原徹與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佩里推動建立的政策溝通機制,以兩國防務部門負責武器研發和采購的副部級高官擔任聯合議長,每年在東京或華盛頓交替舉行1—2次,以加強兩國在軍事裝備和技術方面合作。⑤其后,可以看到,以磋商會機制為契機,便攜式地對空導彈(SAM)相關技術、美國海軍造船及改裝技術、FSX 相關技術、P-3C 機載數字飛行控制系統相關技術等眾多日本技術陸續提供給了美國。此外,以該機制為背景,日美之間還開展了固體沖壓火箭發動機、毫米波及紅外復合導引頭、人眼安全激光等方面的聯合技術研發。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總統后,任命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為國防部部長,大力推動加強美國的綜合軍事力量,同時明顯加快調整對日軍事技術政策的步伐。里根政府在成立初期就表示“美國向日本提供武器及技術,但日本卻不向作為同盟國的美國進行這種合作,這很奇怪”,因而不斷要求日本提供相關武器技術。⑥[日]小泉親司『日米軍事同盟史研究』、新日本出版社、2002年、250 頁。
1981年6月,溫伯格與日本防衛廳長官大村襄治舉行了日美防衛首腦會談。溫伯格表示:日本的一些技術處于最前沿,尤其是在電子和通信技術領域,希望日方積極考慮向美國提供相關軍事技術,并將這一做法作為例外舉措排除在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適用范圍之外,大村對此亦做出了原則上希望加強雙向交流的意向。①參見[日]小泉親司『日米軍事同盟史研究』、246~250 頁。所謂“武器出口三原則”是1967年4月佐藤內閣明確作出的規定,禁止面向以下三類國家和地區出口武器:共產主義國家、根據聯合國決議禁止出口武器的國家、國際爭端當事國或有其他危險的國家。1976年2月,三木內閣發布“關于武器出口的政府統一見解”,規定:對“三原則”禁止對象以外的區域,也要根據憲法和外匯法的精神,謹慎出口武器。這兩個規定后來被統稱為“武器出口三原則等”,事實上全面禁止日本對外出口武器及相關技術是美國從日本獲得軍事技術及相關零部件時的最大障礙。②[日]竹內俊隆編著『日米同盟論』、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年、244 頁。
此時,美國特別關注的是日本的電子、通信、陶瓷、材料、飛機操控裝置等相關技術的發展。美國需要日本的尖端技術來提高其武器的高精尖水準。美國國防部曾評價說,日本尖端技術將為美軍武器小型化、消音化、隱形化、高性能化作出貢獻。例如,日本的電子、半導體等技術使美國導彈系統的精度更高,并且對其他常規武器的精確打擊能力提升也發揮了重要作用。③Takahashi.Sugio,“Transformation of Japan’s DefenceIndustry?”,Security Challenges,Vol.4,No.4,Summer 2008,pp.101-115.
從1981年開始,面對冷戰新形勢,日本政府強化“西方一員”立場,積極配合里根政府對蘇采取強硬對抗戰略。為此,1981年5月,鈴木首相與里根總統發表了“日美首腦聯合聲明”,提出了總體安全合作目標。但是,當涉及防衛領域的具體措施時,因國內因素的限制,日本無法完全響應美方的要求——例如仍然只得繼續拒絕公開向美國提供武器技術。④參見[日]川上高司『米國の対日政策』、同文館出版、1996年、138~145 頁。對此,美國對日本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1981年6月,“第二屆日美裝備與技術定期磋商”召開,美國要求日本考慮提供以下技術:(1)日本政府及防衛廳技術研究本部擁有的試驗技術;(2)日方對“美國技術”進行改良后的技術,包括生產現場的工程管理、焊接要領等制造技術等;(3)日本民間開發的技術,例如弱電激光、光電子等通信技術,紅外線夜視技術,高密度集成電路(VLSI)和超小型計算機等電子技術,機器人等精密機械技術等。⑤參見[日]西原正·土山実男『日米同盟Q&A100』、亜紀書房、1998年、142~153 頁。也就是從此開始,美國國防部的相關官員在訪日之際,屢屢特意視察日本的各大半導體和計算機企業,并不時抗議日方對美實行技術保密。⑥馮昭奎:《美國要日本提供哪些軍事技術》,《系統工程與電子技術》1984年第3 期,第3 頁。1981年12月,“第三屆日美裝備與技術定期磋商”舉行,美方再次對日提出了就以下武器研發和系統對接進行合作的要求:(1)技術人員的相互交流;(2)相互開設研究設施;(3)關于下一代裝備品研發的信息與技術交流;(4)全面聯合研發軍事技術及武器;(5)日本盡早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⑦參見[日]西原正·土山実男『日米同盟Q&A100』、142~153 頁。
總體上,對于以上美方的提議或要求,囿于“武器出口三原則”,日本政府難于做出正面響應。這種情況的改變,是在中曾根康弘上臺執政之后。1982年11月,中曾根就任日本首相。作為鷹派政治家,中曾根就任不久即承諾,將努力實現此前鈴木與里根達成的“日美首腦聯合聲明”中提出的合作目標,同時將從維護《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立場出發,調整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與對美武器技術合作之間的關系。中曾根決定盡快將美國從防衛技術出口禁令中單獨剔除并表示:“如果僅限于技術提供的范圍內,這是正常業務中的技術與知識交換,并非日制武器裝備本身的轉讓。向盟友美國提供技術,沒有任何問題”,“迄今,我國從美國得到了包括技術提供在內的各種合作,考慮到近年我國技術水準提升等新情況,我國謀求與美國在防衛領域的技術交流,對確保日美安保體制的有效運用是極其重要的。”⑧小泉親司『日米軍事同盟史研究』、250 頁。可以說,隨著美國對日壓力的加大與中曾根政權相關政策的調整,“武器出口三原則”被架空和失效只是時間的問題。
三、日本松動政策,解禁對美提供軍事技術
1983年,日本對美提供武器技術的政策出現大幅調整,該年也成為日本武器技術出口政策首次發生重大變動的標志性年份。1983年1月14日,中曾根政府通過“對美提供武器技術”的內閣決議并發表“關于對美提供武器技術的內閣官房長官談話”,對外宣布:“自去年6月以來,美國政府要求日美兩國在防衛領域的相互技術交流,作為其中一環,日本政府部門內部認真考慮了向美國提供武器技術的問題,其結果是達到如下結論,并在今天的內閣會議上獲得批準”。①參見[日]「対米武器技術供與について內閣官房長官談話」、『外交青書』27 號、1983年1月14日、428~429 頁。“如下結論”的具體內容是:
(1)在日美安保體制下,日美兩國通過相互合作來維持和發展各自的防衛力量,此前,日本為了構建防衛力量,從美國得到了包括技術提供在內的各種合作。考慮到近年來日本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等新情況,在防衛領域謀求與美國的技術交流,對確保日美安全體制的有效運用至關重要。這符合《日美安全條約》及相關規定的宗旨,也有利于日本及遠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全。(2)日本政府一直按照“武器出口三原則”處理武器出口等問題(包括政府于1976年2月頒布的武器出口政策)。但鑒于上述理由,根據美方要求,作為相互交流的一環,政府將開辟一條向美國提供武器技術的途徑,此提供途徑將不拘泥于“三原則”的規定。此種情形下,技術提供應在《日美相互防衛援助協定》有關規定的框架下實施,以確保基于“武器出口三原則”的和平國家理念,避免助長國際沖突。再者,作為政府,今后也將基本上堅持“武器出口三原則”,當然也會尊重1971年3月公布的有關武器出口問題等的國會決議。②參見[日]「対米武器技術供與について內閣官房長官談話」、428~429 頁。
由于“武器出口三原則”等沒有公開被否定且表面上仍然起著約束作用,日本實質上禁止向國外出口武器及技術,所以中曾根政府上述決議的邏輯是:對美提供軍事技術此事本身并不是明確的武器出口行為,而是按照《日美安全條約》第3 條規定以及《日美相互防衛援助協定》而實施的日美互助義務。即,通過將此舉作為“武器出口三原則等”的例外事項(特例)進行處理。這標志著日本打開了向美國提供武器技術的通道。實際上,此時開始提供的日本軍事技術,為提高美軍先進技術和武器水準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而日本企業在尚未全面意識到此舉意義的情況下,就開始被納入美國軍事技術和全球規模武器制造的宏大生產體系中。
1983年1月18—19日,中曾根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談,將“對美提供武器技術”作為“對美支援政策”的重大成果加以展示,并在會談中對里根表示:“日美是命運共同體,應在太平洋兩岸為世界和平與亞太的繁榮穩定進行合作”③「ロン·ヤス初會談、防衛強化で蜜月へ外交文書公開」、『朝日新聞』、2017年1月12日。。這一表態得到了美方的認可和贊賞,美國1983年第74 號國家安全會議(NSC)指令指出:我們對最近日本重新制定防衛技術出口政策表示滿意,并對促進和簡化對美技術轉移感興趣。④[日]細谷千博、有賀貞、石井修等『日米関係資料集1945—1997』、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1023 頁。
1983年7月,在“第四屆日美裝備與技術定期磋商”中,美方就日本對美提供軍事技術提出了根據互惠性、總體框架對相關程序進行簡化的要求。為了使日本民企擁有的技術能夠順利進入美國,美國要求日本加強相關措施以保障美日企業之間的協作、保密以及軍事技術全面交流的順利實施。⑤Rubinstein.Gregg,“Emerging Bonds of U.S.-Japanese Defense Technology Cooperation,”Strategic Review,1987,p.45-48.也就是從此時起,為更好地了解日本軍事及兩用技術的發展情況,在日本政府的許可下,由美國政府和企業的軍事技術專家組成的技術評估團開始頻繁訪日、實施調查。1983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美國向日本派遣“凱利調查團”,實地勘察并分析日本的技術能否以及如何具體應用于美國的安全保障。調查團對日本外務省、通產省與防衛廳的政府官員,隸屬于國會防衛、外交、科學、國際貿易和技術等各委員會的議員政治家,富士通、日立、三菱電機、日本電氣、東芝、石川島播磨、川崎重工、三菱重工等日企及經濟團體聯合會的員工等進行了訪談。通過調查,美方開始重點關注日本的16 個尖端技術領域,其中特別高度評價了砷化鎵化合物裝置、精密陶瓷和其他復合材料以及耐熱材料等,認為這些將會對美國國防作出重要貢獻。①“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OUSDRE)”,1984,Report of Den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Industry-to-Industry International Armaments Cooperation:PhaseⅡ-Japa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June,P.60.
1983年11月,日本與美國簽署了“關于根據日美相互防衛援助協定對美提供武器技術的備忘錄”(簡稱“關于對美提供武器技術的備忘錄”),據此構建了對美提供武器技術的制度。該備忘錄的概要如下:(1)日本政府遵照為實施該備忘錄而締結的細則,根據有關法令承認對美提供為了提高美國防衛能力的必要武器技術。(2)作為實施該備忘錄的兩國政府間的協商機構,特設立“日美武器技術聯合委員會”(JMTC)。日方根據從美方得到的情報及JMTC 的討論,決定提供由日本政府授權的適當的武器技術。(3)為了實施這一備忘錄,雙方政府的職能部門將進一步規劃細則。(4)該備忘錄是根據《日美相互防衛援助協定》等來實施的,該協定規定:禁止與聯合國憲章相矛盾的使用,禁止目的之外的使用,禁止未經事先同意向第三國政府轉讓等。(5)美國政府同意采取與日本國規定的秘密保護等級同等的保密措施,并在美國免除與提供武器技術有關的征稅等。
根據備忘錄,日美雙方還明確了以下事項。第一,對美提供的武器技術的含義是指專用于武器的生產技術和設計圖、武器的試制品等。第二,“武器技術以外的防衛領域的技術”是指電子部件等通用產品和可能轉用于武器的通用生產技術。第三,伴隨武器技術提供,逐步構建日美之間聯合研發武器技術的基礎。第四,日美共同開發的武器,被允許在日本自衛隊使用。②日本防衛省「対米武器技術供與に関する交換公文」、1983年11月8日、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87/w1987_9146.html2020-11-28.中曾根政府的“對美提供武器技術”決議即通過上述備忘錄所構建的制度來落實。
四、日美展開積極互動及落實舉措
有了1983年的日本政策松綁和日美政策共振,到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美武器技術合作加速發展。1984年7月,美國派出“麥卡倫調查團”訪日,重點調查了光電工學、毫米微波這兩個領域,并視察了相關的研發和生產狀況。基于這次調查,美方于1984年8月在“第六屆日美裝備與技術定期磋商”上向日方通報了雙方可以在光電工學、毫米微波等展開合作的相關技術領域。隨之,美國國防部就向三菱電機、富士通等企業提出訂購電荷耦合器件(CCD)等光電子器件技術。③馮昭奎:《美國要日本提供哪些軍事技術》,《系統工程與電子技術》1984年第3 期,第6 頁。之后,美國基本每年派出一個技術調查團赴日進行相關考察。④Lorell Mark,Troubled Partnership:A History of U.S.-Japan Collaboration on the FSX Fighter,Transaction Publisher,1996,pp.33-38.同年11月,為促進日本對美積極提供武器技術,雙方正式成立了JMTC,作為日美政府之間的常設磋商與協調機構。
1985年初,美國開始呼吁日本參與“戰略防衛構想”(SDI)即俗稱“星球大戰計劃”的研究工程。1985年1月,中曾根和里根舉行會談,雙方就SDI 進行了溝通。3月,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代表美國正式邀請日本參加SDI 計劃,但中曾根內閣沒有給與直接答復而只是表示理解。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星球大戰”:對美蘇太空爭奪的剖析》,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358 頁。4月,“麥卡倫調查團”再次訪日調查。5月,“第七屆日美裝備技術定期磋商”舉行。在以上這些溝通和磋商的基礎上,12月,日美簽署了《對美武器技術提供的實施細則協定》,該細則協定規定,日美之間的武器技術轉讓僅限于技術及技術轉讓所需的物品,禁止日本利用相關技術對外出口美國生產的武器。①[日]秦重義「日米防衛技術協力の過去と將來」、『防衛技術ジャーナル』1999年10月號、19~21 頁。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一方面要求日本提供武器技術,另一方面也在竭力壓制日本自主武器裝備及技術的研發,這種情況從日美武器技術合作的起始階段就得到了體現。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關于FSX,中曾根內閣當初曾考慮以下三種選擇方案:(1)研發國產飛機;(2)改良航空自衛隊當時使用的主力戰斗機F-4EJ;(3)引進外國飛機,進行國產化。當時,在日本,負責防衛產業政策的通產省和負責國防政策的防衛廳是FSX 國產化推進派,以維持日美同盟為優先的外務省和意圖抑制防衛產業政策支出的大藏省是FSX日美聯合開發推進派。1986年12月,里根政府開始明確表明美國對日本發展FSX的立場,國防部部長溫伯格和國防部副部長助理阿米蒂奇對日發出購買美機而非“自力更生”的暗示。溫伯格接受日本記者采訪時表示,為了提高美國在亞洲對蘇聯的遏制力,美日的技術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其時,美方還將此與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問題聯系在一起。實質上,日美同盟是美國占有優勢的非對稱同盟,美國政府考慮的是,通過在同盟框架內行使影響力,直接讓日本從美國購買下一代戰斗機,以便維持美國的軍事霸權。②以上參見:グレッグ·ルービンスタイン「日米武器協力」、『日米同盟――米國の戦略』、勁草書房、1999年、158~175 頁;大月信次·本田優『日米FSX 戦爭――日米同盟を揺るがす技術摩擦』、論創社、1991年、50~80 頁。
1986年7月的日本大選中,中曾根領導的自民黨取得壓倒性勝利,確立了在眾參兩院的絕對優勢。根據選舉結果,中曾根新內閣決定取消美國一再要求取消的日本防衛費占GNP 1%比例的限制,并參與SDI 的研究開發。同年9月,日本政府圍繞日美SDI 合作正式做出了對美提供武器技術的第一號決定。1987年7月,日美兩國政府在華盛頓簽署了《關于日本參與SDI 研究計劃的協定》,旨在讓日本企業參與美國的SDI 計劃。對美國而言,繼1986年美蘇舉行歷史性的雷克雅未克會談后,1987年可謂里根政府實施對蘇戰略的關鍵階段——為了壓倒蘇聯,美國需要發出所有能發出的強烈信號,包括簽署美日SDI 合作協定在內等。日本對美提供武器技術被美國視為聯合對蘇施壓總體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同年10月,國防部部長溫伯格和防衛廳長官栗原祐幸舉行日美防衛首腦會談,決定以美國F-16 為基礎,兩國聯合研發FSX。③[日]今野秀洋「日米FSX 摩擦とはなんだったのか—検証と教訓」、2011年10月7日、https://www.rieti.go.jp/jp/events/11100701/pdf/konno_jp.pdf [2020-12-27]。
在FSX 的聯合研發中,美方看重的是日本的復合材料技術和雷達技術。首先,日本的復合材料技術(例如碳纖維增強塑料,即CFRP)在當時已達到世界最高水準,例如東麗公司通過相關民用產品研制已獲得復合材料的高級應用技術。此類復合材料技術發展成為日本獨有的專利,可以由碳纖維和環氧樹脂制成戰斗機的機翼主體并一體形成大梁和外殼,并在耐熱性、抗振性和抗沖擊性方面開始滿足武器研發所需的嚴格條件。
其次,關于日本雷達技術,美國關注的是有源相控陣雷達(APAR)。APAR 的特征在于,可以通過電子掃描來改變無線電波的方向,而無需機械地移動圓形天線。以防衛廳技術研究本部為中心,日本從1970年開始研發APAR,1981年技術研究本部委托三菱電機進行實際開發,1986年完成了試制品。相控陣雷達構成的最重要技術及部件,是雷達天線部分用于收發的模塊的制造技術,有了這種技術,雷達天線可以被制成約90 厘米的圓形結構,能夠完全裝進戰斗機的前端部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考察團曾多次訪問富士通、住友電工、防衛廳技術研究本部、三菱電機等,目的即在于察驗構成APAR的收發模塊。④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Office of Japan Affairs(NRC)(1995),Maximizing U.S.Interes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ations with Japan”,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pp.8-10.并且,其中用作收發模塊元件及高速集成電路制造材料的鎵砷化合物半導體尤為重要。1988年,日本電器、富士通、三菱這三大公司占據了鎵砷化合物半導體市場的50%以上,而全部日本企業則更占據了約2/3 的市場。1985年,住友電氣一家就占了供應給西方國家鎵砷化合物的75%。特別是在鎵砷化合物半導體的原料——鎵砷化合物晶體方面,日本企業幾乎獨占了市場份額。同時,在FSX聯合研發中,日本方面所需要的美國技術,是系統集成所需的軟件技術和數據。①參見[日]山崎文徳「対日依存問題と米國の技術収奪」、大阪市立大學商學部·大學院経営學研究科『経営研究』第57 巻第3 號、2006年、56~60 頁。
日美雙方還注意到,為了使武器技術交流更加便利化和制度化,需要使《日美防衛專利協定》的功能更加健全。該協定是日美兩國政府于1956年締結的,是一個關于軍事專利的保密條約,旨在促進出于國防目的的專利權和技術知識的交流。該協定既沒有制定“實施程序細則”,也未有長期持續的行動落實。1988年3月,應美國政府的要求,日美成立了專利協定第6 條規定設置的技術財產委員會。以該委員會的成立為契機,兩國決定激活第3 條的“程序細則”。通過如此操作,在美國被認為是秘密專利的技術,包括日美聯合開發的技術在內,其秘密在日本也能保證得到有效保護。1988年11月,日美兩國政府簽署了《關于共同開發FSX 的諒解備忘錄》,該備忘錄明確規定,日方研發的相關成果應適當地提供給美方。事實上也是如此,例如,其后,三菱重工的機翼整體成型技術提供給了通用動力公司,三菱電機的雷達技術提供給了美國國防部——這最終加強了西屋電氣等企業的技術發展以及相應的美國軍事技術實力。②參見[日]薬師寺泰蔵「日本が握るポスト冷戦のハイテク·カード」、『世界週報(特集號)経済文化摩擦の真相』、時事出版社、1990年、35~42 頁。美國國防部從1988年開始對日本的高技術進行過多次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在構成美國安全保障的20 種基礎高技術領域中,日本有5 種技術全面領先于美國,這5 種技術是光學技術、半導體、智能機器、生物技術、超導技術,而且在復合材料、高性能雷達等領域也處于部分領先地位。③轉引自:李友申:《日美軍事技術合作新進展》,《世界經濟與政治》1992年第9 期,第37 頁。
1990年2月,日美召開JMTC 會議,決定“日本的FSX 相關武器技術”一攬子提供給美國。同時,APAR 被認定為與一體成形技術不同的、屬于日方的獨有技術。3月,日美FSX 聯合開發小組成立,12月決定采用通用公司制造的發動機。特別是,在日美FSX 聯合開發中,日本提供了美國極其關注的“主翼一體成形技術”和“雷達技術”,對美國加強軍事技術力量起到很大作用。除了以上這幾種技術,到冷戰結束為止,日本已決定的提供給美國的武器技術,大概有以下幾種:用于個人便攜式地對空導彈的跟蹤制導技術,補給艦建造技術,航空母艦改裝技術,FSX 相關技術,反潛巡邏機P-3C 的飛行控制技術等。④參見[日]村山裕三『米國のハイテク兵器と日本の両用技術』、平和·安全保障県有所、1992年、22~28 頁;劉世龍《美日關系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579 頁。囿于資料所限,圍繞這幾種技術提供的具體內容不詳。
五、結語
綜上可見,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尤其1983年實現了對美武器技術合作的初步突破,沒有這一步的邁開,其后相關政策進一步松綁及解禁將是難以想象和缺乏基礎的。例如,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日美導彈防御聯合技術研究,到2004年小泉內閣發表關于“日美導彈防御聯合開發生產”的談話,2006年與美國簽署“對美武器及技術提供協定”,再到2011年民主黨野田內閣發表“防衛裝備品等的海外轉移基準”談話,⑤以上的相關內閣談話均以官房長官的名義發表。2006年的“對美武器及技術提供協定”簽署后,即替代了1983年的“關于對美提供武器技術的備忘錄”。形式上仍然是通過沿用80年代的“中曾根方式”——即根據“例外措施”進一步放松而不是完全修改政策來允許相關合作。⑥一直到2014年4月安倍政府宣布新的“防衛裝備和技術轉讓三原則”,才實現不根據“例外措施”而是根據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的審議結果,在國家安全戰略的總體框架下,決定防衛設備和技術的轉讓。通過上述案例分析,可以看到以下有關80年代日本對美提供軍事技術的幾個主要特點。
(一)日本對美提供武器技術,從戰術與戰略兩個層面對美國增強軍力起到重要作用。自從自衛隊成立以來,日本和美國一直在進行著防衛裝備和技術合作,當然,一開始這主要是美國對日本的單向輸出。從20世紀80年代尤其里根政府時期起,經濟全球化和產業跨國化加速開啟,美國再像之前那樣包攬全部軍事技術及產品的工作,則難免效率低下且日益不現實。因此,日本的產品、技術開始迫切被需要納入美國全球軍事生產體系。軍事力量是美國維持世界霸權的核心要素,為此美國軍工產業有必要在規模、技術、生產力等所有方面保持壓倒其他國家的優勢,其中的關鍵要件之一就是軍事技術的領先與運用。從里根政府時期起,如本文所見,日本就以其卓越的工業技術及產品能力,開始為美國國防工業和軍事力量稱霸全球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日本的半導體與電子技術、高新復合材料、高質量生產工藝等,通過SDI 計劃推進、尖端導彈、先進戰斗機及艦船制造等,在為維系美國的軍事霸權不斷提供支持。某種程度上,美國“贏得”冷戰、拖垮蘇聯,與得到日本在內的盟友的經濟與技術支持是分不開的。
(二)日本對美提供軍事技術是一個不斷深化與拓展的過程,并連帶撬動國家安全防衛政策以及日美同盟范式的改變與轉型。首先,日本在對美軍事技術合作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從20世紀80年代起步至今,已連續發布了多項政府聲明以及官方文件,為防衛裝備和技術的更大程度的對外合作放寬條件、鋪平道路。同時,日本還逐漸從對美合作擴大到不涉及美國的武器和技術轉讓。這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國家安全防衛政策的轉變——突破了專守防衛及和平發展的基本路線。其次,日本對美提供軍事技術,改變了80年代以前美國單向對日提供技術的局面,在幫助強化日美同盟的同時,預示著同盟在軟硬件兩方面都開始轉入雙向交流和合作的時代。再次,此種“提供”,也為日本對外安全防衛合作、參與大國博弈并提升地位提供了新杠桿和工具。因為,日本的軍民兩用技術和產品在不少領域具有其他國家所不具有的獨特優勢,以對美提供技術為突破口,日本可進一步展開武器及技術出口,加入國際軍品貿易競爭。
(三)通過對日技術交流,美國使日本在軍事技術乃至武器發展體系上處于被主導和控制的局面。日本承擔了美國許多重要的軍事技術和產品的分工責任,日本的國防產業企業,作為轉包、零部件供應、局部技術開發等的一種從屬地位,被編入具有壓倒性規模的美國全球軍事產業結構體系當中。即,核心功能由美國掌握,零部件、散裝技術等廣泛的輔助功能在全球化、跨國化的過程中由日本及美國的其他同盟國承擔。這種結構造成的結果就是,雖然日本防衛廳早在1970年就宣布了防衛產業本土化的方針,但嚴峻的現實是日本國防制造商無法完全基于其自有技術生產國防設備,其防衛生產技術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國提供的特許使用或直接從美國進口。20世紀80年代圍繞FSX 的內外辯論和博弈,證明了日本在相當程度上不得不依賴美國的國防技術,日本制造商可以生產一部分甚至主要部分裝備,但其無法承攬包括發動機和應用軟件等在內的完整生產鏈條。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日本對美提供軍事技術仍始終面臨著諸多的制約因素。首先,雖然日本政府一再放寬相關政策,在與美、英、法、澳等國的防務技術合作方面采取了迅速行動,但也一再面臨更加困難和微妙的政策案例及限制。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日本政府往往缺乏足夠的能力做出大膽的、一步到位的突破和決定。其次,日本并沒有一個政府總體層面的協調機構——例如在國家安全會議或首相官邸內設立一個常設委員會,以便就武器及技術貿易的方向做出統一的決定。在這方面,日本政府還需避免相關政府機構之間的內部權斗,例如,國家安全會議、外務省、經濟產業省和防衛省等部門之間就需要進一步的部際聯系和協調機制。再次,日本國內仍有很強烈的聲音,反對參與軍事技術出口及軍火貿易的政府政策行為。日本公眾普遍認為,與國防技術開發和裝備生產相關的任何商業活動都意味著“死亡生意”。公眾也擔心民企參與國防生產時會產生溢出效應,破壞國家政治生活。因此,不解決公眾對這些問題的擔憂,日本政府和行業實際上就很難放手推進國防技術貿易的發展和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