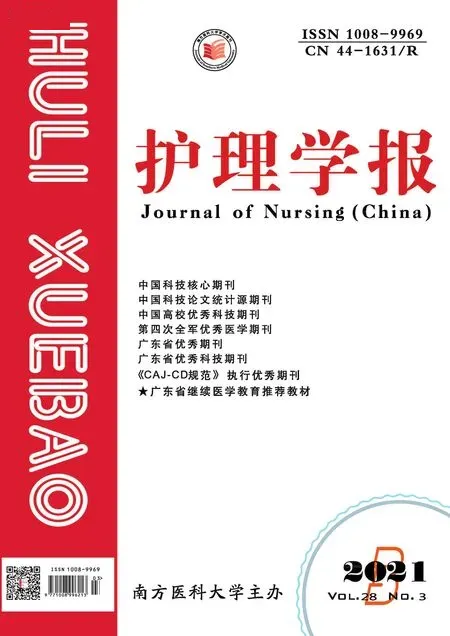醫療不良事件對第二受害者影響的研究進展
張蕊馨,謝暉,汪晨晨,蔡維維
(蚌埠醫學院 護理學院,安徽 蚌埠233000)
醫療不良事件是指與疾病及其并發癥無關,僅由醫療活動所導致的傷害事件,是繼心臟病和癌癥之后的第三大死因[1]。研究顯示,其發生率約為10.4%~46.8%[2],造成的患者傷害所產生的經濟負擔占全球疾病負擔的第14 位,與結核病、瘧疾等疾病負擔相當。醫療不良事件在損害患者健康的同時,也對涉及其中的人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傷害, 這些人員稱為“第二受害者”。 2009 年,Scott 等首次明確了第二受害者的定義, 指參與預期外不良事件、 醫療差錯和(或)患者相關損害,并因此身心受創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包括醫護人員及醫療機構中一切參與患者服務的其他人員),他們往往感到自身對患者的救治結局負有責任,并懷疑自己的執業能力。 其中,護士是第二受害者的高危人群, 醫療不良事件可能會引起護士悲傷內疚、喪失信心、抑郁焦慮,甚至產生自殺意念和創傷后應激障礙[3]。 國外第二受害者研究起步較早,對第二受害者現象、復蘇規律、管理干預的研究相對成熟[4-6]。 而我國的醫療機構對第二受害者還未有充分的認識, 缺乏對第二受害者身心體驗的關注和支持。因此,本研究通過介紹醫療不良事件對第二受害者的影響現狀及組織支持, 以期為第二受害者的干預提供科學依據, 為推動國內第二受害者研究提供參考。
1 醫療不良事件對第二受害者影響的現狀
美國、芬蘭、希臘、瑞士、西班牙、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對于醫療不良事件中的第二受害者現象均有研究, 亞洲國家中開展第二受害者研究的僅有以色列、韓國和新加坡[7-8]。 查閱文獻發現,醫療機構中第二受害者現象普遍存在[9]。
1.1 不同國家醫療不良事件中第二受害者的基本情況現狀 西班牙對1 087 名醫務人員的研究表明[10],近3/4 的醫務人員在過去5 年內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過醫療不良事件,有過第二受害者經歷。荷蘭1 項針對4 369 名醫療保健者的橫斷面研究發現[11],10%受訪者表示僅在過去6 個月內就曾涉及醫療不良事件,且患者受傷害程度越深,第二受害者癥狀持續時間越長。Joesten 等[12]指出,30%~60%的第二受害者無法獲得醫療不良事件后的相關支持。Mira 等[10]指出,約70%調查對象表示: 機構內沒有針對第二受害者的管理預案,也沒有提供任何指導、咨詢、支持和幫助的項目。Harrison 等[13]調查顯示,約67%醫生認為,醫療機構沒有充分支持醫生應對不良事件的壓力。McDaniel等[14]認為,相關機構應在不良事件發生的4~24 h 內給予支持, 因為這段時間對參與不良事件衛生專業人員的影響尤為重要。我國學者陳貴儒等對518名三級甲等醫院護士進行調查,發現258 名護士經歷過醫療不良事件,第二受害者比例高達49.8%[15]。
1.2 醫療不良事件中第二受害者受到的傷害現狀1 項針對意大利33 名護士的訪談顯示[16],護士第二受害者在身體和心理上均遭受痛苦, 并試圖通過各種方式獲得情緒支持來克服事后情緒壓力。 徐晶等[17]對10 名醫療不良事件中護士第二受害者進行深入訪談,發現護士在成為第二受害者后,會出現一系列類似于創傷后應激壓力癥候群的表現, 這些問題給醫護人員身心健康、 職業安全感和認同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 金玉梅等[18]對17 名在兒科護理中發生過護理不良事件的在職護士進行訪談后, 發現護士作為第二受害者普遍經歷了自責、 后悔等負性體驗,這種負性體驗會持續幾個月到幾年,有的護士甚至無法完全解脫。 楊巧等[19]認為由于醫務人員個體應對患者安全事件能力有限, 難以迅速或根本無法從負向心理或生理表現中復原, 從而影響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
1.3 針對第二受害者的評估工具 對于第二受害者影響因素的研究, 大多數國外學者采用第二受害者經驗及支持量表(the Second Victim Experience and Support Tool, SVEST)進行調查,該量表包括7 個維度和2 個結局變量,共29 個條目[20]。7 個維度分別測評心理困擾、生理困擾、同事支持、上級支持、機構支持、親友支持和職業自我認知;2 個結局變量測量離職/轉行意愿、暫時性離崗。 每個維度都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每個條目分值為1~5 分,1 分為非常不同意,5 分為非常同意。 總分范圍為29~145 分,SVEST評分越高,表明第二受害者現象越普遍,提供的支持資源越不足, 第二受害者相關的負面工作結局越嚴重。 我國的陳貴儒等[15]對SEVST 量表進行漢化,采用便利抽樣法對258 名綜合性三級甲等醫院臨床執業護士進行問卷調查, 漢化后第二受害者經驗及支持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數為0.892。陳嬌嬌等[9]對第二受害者經驗及支持量表進行跨文化調試, 形成中文版,并測量382 名護士的心理學特征,得到的總量表Cronbach α 系數為0.824。
1.4 醫療不良事件中第二受害者現象逐漸被關注2012 年,Pratt 等基于第二次受害者體驗的現有最佳證據開發了一個工具包, 旨在幫助醫療機構實施支持計劃。 醫療誘導性T-rauma 支持服務(Medically Induced T-rauma Support Services, MITSS)為患者、家庭、 發生不良事件后的臨床醫生提供了一個可預測的支持網絡, 為構建第二受害者支持計劃奠定了基礎。 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制定了“RISE”計劃,該計劃的一個長期目標是使所有醫務人員在不良事件發生的前、中、后都能相互支持[21]。 MISE (Mitigating Impact in Second Victims)計劃著重研究第二種受害者現象的預防方面, 它的目的是設計一款針對一線醫院和基層醫療專業人員的在線程序, 以提高意識并提供有關第二受害者現象的信息[22]。密蘇里大學組建了一個由同儕支持者組成的快速反應小組-“For You”,從臨床醫生和醫院的雙重視角,提高第二受害者的恢復力和能力[3]。 雇員援助計劃(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23]作為支持臨床醫生的一種手段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甚至有時作為醫院支持需求的唯一手段,但具有感知效能低的缺點。
2 醫療不良事件中第二受害者的組織支持
研究表明, 醫療不良事件中的第二受害者渴望得到外界的支持和幫助[8],但他們并未獲得足夠且有效的支持[24]。 目前,我國護理人員的支持現狀處于中低水平[17-19]。 多項研究表明[25-27],支持是第二受害者恢復的關鍵, 為第二受害者提供組織支持及營造支持性氛圍,可減輕其心理、身體、職業困擾,使其更快地恢復到工作狀態中。
2.1 醫院管理者制定相關制度
2.1.1 構建醫院患者安全文化 研究顯示[28],第二受害者痛苦和支持受到多因素影響, 其中醫院患者安全文化被認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良好的患者安全文化被認為是一種環境催化劑, 能增加對第二受害者的支持,減輕其創傷,從而成為重要的第二受害者保護屏障[26]。 對醫院患者安全文化的積極認識,可以通過培養一種促進有效應對醫療不良事件的環境,來減少第二受害者的痛苦,在醫院內部建立關心第二受害者幸福的患者安全文化。 研究表明[6],教育可以為更健康的醫療環境提供基礎。 通過針對醫護人員的宣傳活動和教育計劃, 來提高對第二個受害者現象的認識。對于有意愿發揮更積極作用的個人,可以接受相關培訓, 以在需要時提供同儕支持和心理急救。
2.1.2 構建醫院“公正”文化 政策制定者可要求醫療機構在醫院內部成立第二受害者支持小組, 并通過及時識別、 匯報和實施適當的支持項目來減少第二個受害者的心理痛苦,以創造一種公正的文化[29]。醫療機構、政策制定者、監管機構和專業機構也有責任開發相關系統,支持這些受影響的醫務人員,將不良事件報告變成一種開放、透明的文化,確保其成為一項學習活動,而不是恥辱、羞愧的行為[13]。 此外,組織機構還應保障第二個受害者的權利, 包括: 治療權、尊重權、理解權、同情權、支持性護理和透明度,以及加強實踐的機會[5],真正為醫療不良事件中的第二受害者構建支持性體系。 在管理制度和文化方面,應建立非懲罰性管理體系,加強對第二受害者心理、情感等方面的關注。
2.2 醫療事件中第二受害者的干預手段 對醫療事件中第二受害者進行的干預, 相當于使其身心情況復蘇到正常狀態的過程。 2009 年,Scott 提出了經典理論模型,包括以下6 個階段,即:混亂及事故反應期;侵入性思維期;恢復完整期;忍受調查期;情感急救期; 結局。 且這個復蘇過程包括3 個潛在的路徑,即:離職/逃避;生存伴隨困擾/壓抑;積極成長/蛻變。 2016 年,Koehn 等[30]通過對重癥監護室30 名護士進行訪談提出了“錯誤中學習”五階段模型,包括:自身狀態失衡;認識錯誤;報告/講述錯誤;反思;記憶。 2018 年,Chard 等[31]通過圍術期護士經歷的術中錯誤提出了將手術室相關的環境-人的本質-發展相結合的理論模型,該模型包含環境、人類、發展3個主題, 旨在提高護理質量和培養安全文化。 2019年,韓國學者Lee 等[32]基于Anselm 和Juliet 的扎根理論提出了5 個階段的恢復路徑,包括:糾纏階段、攪動階段、斗爭階段、管理階段、誘導階段。 同年,瑞典學者Wahlberg 等[33]根據建構主義理論提出了產科不良事件后的復蘇概念模型,包括外在自我和內在自我兩大方面, 它構建并解釋了一個核心類別“重新獲得職業自我形象”,該模型的重點是經驗、策略和事件后的行為。 我國學者李潔莉等[34]抽取近6 個月內經歷不良事件的護士46 名,進行4 個課程模塊的正念冥想干預,包括正念冥想介紹、正念冥想框架、縱向引導冥想計劃、正念冥想詢問和反思,持續8周。
2.3 醫療事件中第二受害者的干預效果 國外學者El 等[35]對外科醫生實行第二受害者支持計劃后,大多數參與者對該計劃表示滿意,81%的人認為該計劃對醫院的 “安全與支持” 文化具有積極影響。Marmon 等[36]認為努力改善醫院文化并開發個人支持系統,對增強醫務人員心理彈性,提供更高質量的患者護理具有顯著影響。 我國學者采用便利抽樣法對護士第二受害者進行正念干預, 發現正念冥想干預適用于護士第二受害者人群, 能有效降低其經歷不良事件后的痛苦體驗,提高其支持及希望水平[34]。
3 展望
目前, 我國醫療機構對醫療事件中的第二受害者現象逐漸關注, 但對第二受害者還未有充分的認識,醫療不良事件發生后,第二受害者也不知該如何尋求指導和幫助。認識第二受害者現象,以及強有力的組織支持, 對減輕事后影響及在意外錯誤發生后幫助醫務人員恢復至關重要。因此,未來我國醫院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應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支持體系,以滿足第二受害者的需求、提高護理質量、促進醫療事業可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