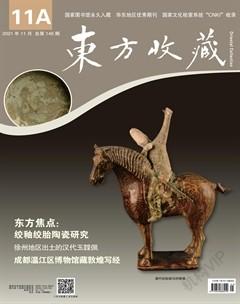盛唐遺珍



摘要:本文由日本正倉院藏唐傳密陀繪漆器引發對密陀繪技藝的思考,經過實踐考察、尋訪匠人、查閱資料,對失傳技藝密陀繪有了初步的理論認識,梳理了密陀繪工藝與我國傳統技藝描油漆器之間的聯系,對密陀繪工藝在國內存在的證據進行了大膽的推測,確定了對其進行后續實踐研究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關鍵詞:正倉院;密陀繪;漆器;描油
日本東大寺正倉院內,藏有多件我國盛唐時期傳到日本的工藝珍品,其精美程度遠勝于國內博物館藏品,更有甚者,如今在國內已無跡可尋,如著名的紫檀螺鈿五弦琵琶,再如神秘感十足的幾件密陀繪漆器作品(圖1),在國內已被列入失傳技藝的范疇。隨著展出的機會越來越多,密陀繪技藝引起更多漆藝愛好者和專家學者的關注。多方資料表明:密陀繪工藝源自中國,但目前世界已知為數不多的幾件密陀繪漆器均藏于日本正倉院,并被奉為國寶。是國內密陀繪漆器已于歷史長河中消失殆盡,還是由于國人對密陀繪工藝沒有深入了解而忽略了身邊的寶物?這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研究與探討。
一、密陀繪的定義及現存狀況
密陀繪,又稱密陀彩繪,或密陀僧繪,是我國三國至隋唐時期盛行的一種漆藝技法,因在色料中加入密陀僧而得名。密陀僧,化學成分為一氧化鉛,東漢時期由波斯傳入中國,名字也源自波斯語音譯,將其加入漆或植物油中能起到促干作用。唐以后漆器的地位逐漸被高性價比的瓷器取而代之,轉而成為少數權貴享用的奢侈用品,漆器審美也隨之日趨繁復、華麗、奢侈,至宋元以后,雕漆、百寶嵌等順其自然成為我國漆器的主要品種,于是一部分盛極一時的漆藝技法相繼失傳,其中就包括密陀繪。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我國對天然大漆的應用最早可追溯到8000年前,極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應用大漆的國家(有資料稱日本發現9000年前的漆器,中國最早用漆的地位受到挑戰,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是最早熟練并大規模使用漆的國家)。西漢時期,我國漆藝發展達到頂峰,三國至隋唐在繼承前代成就的基礎上,受到西域外來文化的影響,又有了新的發展:金銀平脫、螺鈿、脫胎造像以及密陀彩繪技法風靡一時,在全球范圍內處于領先地位。在此幾種工藝技法中,金銀平脫、螺鈿、脫胎造像工藝均有流傳至今,也吸引了不少學者的關注,既有實物可考,又有資料可查。相比之下,外來語得名的密陀繪就顯得神秘莫測,因為在我國目前出土或傳世的文物之中,沒有任何一件明確是密陀繪技法制作,而諸多史料或者學術著作中,對密陀繪的描述也僅限于蜻蜓點水般一筆帶過。
自鑒真東渡日本以后,輝煌的唐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奈良時期,日本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來中國,把當時最先進的髹漆工藝帶回去。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里的珍貴藏品,無疑是對當時中日文化交流情況的最真實的體現。正是這一時期,金銀平脫、螺鈿、密陀繪等優秀技藝相繼傳入日本。正倉院內最為人熟知的紫檀螺鈿琵琶、阮咸、古琴等唐代宮廷樂器,均系唐代宮廷贈與日本圣武天皇,工藝精湛,無與倫比。同時期藏于正倉院的密陀繪皮箱、密陀彩繪唐花紋小柜、密陀彩繪忍冬紋小柜等十余件密陀繪作品,做工精美,彩繪部分色彩豐富而飽滿,圖案紋樣唐風猶存。日本人間國寶室瀨和美曾肯定:“中國制造漆器工藝品的方法,在唐代亦即日本的天平時代,幾乎全部傳入日本。目前日本使用的漆藝技法有蒔繪、螺鈿、平紋、漆繪、密陀繪、箔繪、沉金、醬、存星、雕漆、雕木彩漆等幾乎全是從中國大陸傳播到日本的。”日本學者山崎一雄在《法隆寺壁畫顏料》一文中說:“利用油和顏料混合繪畫的技法在古代就很發達,從文獻可知在漢代以前此種技法就有記載。日本正倉院的藏品中這種技法顯而易見。有名的琵琶和阮咸的畫全部使用了油和顏料混合繪畫的技法。當然這是從大陸傳來的技法。”這里的“大陸”當然指中國,他所說的“文獻”暫時無從考證,因此我們不能確定漢代以前就應用密陀僧入油,但可以肯定的是漢代以前油和顏料混合繪畫的技法已經產生,正倉院內唐代藏品使用油和顏料混合的技法無疑就是我們所說的密陀繪。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尚不能確定是否存有古代密陀繪工藝作品,因此我們無從對比、考證。
二、密陀繪工藝初探
大漆是從漆樹干上采集的天然樹脂,因此也叫生漆、天然漆,它的組成成分為水、蛋白質、漆酚、漆霉和微量元素。接觸空氣后,與空氣中的水分子結合,由乳白色氧化為深褐色,經過去水分提煉,可制成深褐色半透明漆。古法與礦物顏料和植物油研磨制成色漆,可用于器物上描繪圖畫或素髹單色漆。由于大漆的干燥過程獨特,需要溫濕的環境,因此大漆干燥一般在陰房內完成,并且色漆干燥以后,顏色明亮度會降低,變得比較灰暗,這便是漆畫中難見鮮艷明亮色彩的原因,也是蛋殼的白色作為漆畫中白色顏料使用的蛋殼鑲嵌技法形成的主要原因。
筆者認為,大漆顏色晦暗不明也是密陀繪技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前文已述,西漢前后是我國漆藝發展的巔峰時期,特別是南方代表性的楚文化地區,出土漆器數量可觀,很多學者用“無器不髹”來形容當時的社會,十分貼切。漢代的漆器用途廣泛、做工精美、器型多樣、彩繪紋飾精巧華麗而不失大氣磅礴,不愧為巔峰之作。但統攬當時的漆藝作品,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的工藝技法僅以描繪刻劃為多數,雖然早在戰國時期金銀片就開始運用到漆器的制作中,但畢竟是不算成熟的早期階段。對比后世,先秦到西漢的漆文化巔峰時期在對彩繪刻劃之外的漆藝技法的探索方面無疑略顯不足。相比之下,巔峰過后的三國至隋唐時期,雖然漆藝的輝煌將逝,但漆藝技法的多樣性卻是前所未有的,前邊提到的金銀平脫、螺鈿、脫胎造像,以及宋代流行的素漆,明清推崇的雕漆等工藝技法皆產生于這個時期。不僅如此,在色彩方面,走到各大博物館的漢代漆器區域,視野之內,無出紅、黑、金三色,搭配少量的灰、黃、象牙等顏色,漆器色彩略顯單調與晦暗,幾乎不見豐富而鮮明的色彩,這固然與當時社會條件和主流審美有一定關系,但大漆自身干燥變色的特性,無疑也是當時漆器顏色暗淡的內在原因。在顏色方面的探索,后代的三國至隋唐時期,同樣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密陀彩繪的產生。
鄭師許《漆器考》中提道:“及三國時,曹魏已有言密陀繪漆畫之事,其法即以氧化鉛傾入油中而煮沸之,然后以繪具髹飾,以為色漆之代用品,與今日油畫無異。于油漆中另辟蹊徑,實則為‘油之演進,非‘漆之演進也。吾國油漆本分二途:漆器以漆液為主,密陀繪則不以漆而以油……然此等用料殊不易干,于是有天聰者,創為加以促干料之法……自是以后,油與漆分道揚鑣,雖當時漆工家付以密陀漆之名,然吾人一經研究,不得不謂為‘油一系統之演進。”
鄭先生對密陀繪的描述已是諸多學者中最詳盡的一位,由此結合前文中所述漆色易變暗的特性,我們可知當時的漆藝工作者為了避免或者減輕色漆變色,開始嘗試減少色漆中漆的比例,或僅以植物油調色,但植物油不易干燥,于是有“天聰者”將油中加入密陀僧作為促干料,由此得到與礦物顏料本身更接近的鮮艷色彩,這大體便是密陀繪產生的過程,從工藝特征來看,甚至可以稱之為是油畫的雛形。但歷史學家的角度仍免不了重史料而輕實踐,如鄭先生把密陀繪從漆器中分離出來只講繪畫,雖邏輯清晰,但仍缺少實驗以及實物證據,可能由于當時正倉院中密陀繪藏品還未進入鄭先生的視野,正倉院密陀繪漆器的存在使漆油分道揚鑣之說不攻自破,二者并未分離。另一方面,由于漆的變色,自古以來我國漆工調色漆都會與植物油混合,以減少變色。據王世襄先生推測,我國自春秋時代起,漆與油便開始結合,起初使用的油主要為荏油,即蘇子油。宋代以后,桐油取代了荏油,成為漆工藝調色的重要材料。其中油為溶色劑,質軟不牢,起干燥固化作用的是漆,結膜后堅硬牢固。因此控制色漆顏色、干燥速度以及堅硬牢固程度的是油和漆的比例:油多,干燥慢,變色少,軟而不牢;漆多,干燥快,變色多,硬而牢固。如鄭先生所言,純油中加入促干料調色,固然可行,但若想要干燥速度、顏色明度、硬度和牢固程度等因素達到平衡,漆與油缺一不可。王世襄先生在《中國古代漆工雜述》中提到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木板屏風(圖2)時說:“幾乎可以肯定其中的白色等鮮明的淺色均為油所調配,但淺色容易脫落,正是油色不及漆色堅牢的應有現象。”這樣的做法在湖北出土的戰國彩繪鎮墓獸漆底座(圖3,黑色發亮處為淺色脫落痕跡)和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雙層長方形油彩漆奩(圖4)以及辛追夫人彩繪漆棺(圖5)都有所體現。不難發現,這些實例的共同點都是以油為主的彩繪裝飾于大漆表面。由此我們也可以推論:經過時間的考驗而沒有脫落的淺色是不是有可能在以油為主調配的顏料中含有適量的大漆?當然,這個結論需要進一步的實踐研究來證實。
通過以上論述,似乎可以把密陀繪定義擴展為:凡是以油加入促干劑和礦物顏料調色作為漆器彩繪顏料的工藝做法,均可稱為密陀繪工藝。王世襄先生在《髹飾錄解說》中提道:“正倉院藏有彩描花鳥紋的密陀繪箱,畫黃色山水花鳥人物的密陀繪盆等,它們可能是中國運往日本的描油漆器。”由此,王世襄先生也給我們研究密陀繪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描油,顧名思義,就是用油進行描繪,即在漆器的繪畫部分運用油和顏料混合描繪的方法,用到的油同樣是桐油、荏油之類,因此必然需要用到促干料,密陀僧一類就必不可少。到明清時期,描油漆器仍然存在。倘若將唐時的中國描油漆器與正倉院藏密陀繪漆器進行成分對比,發現成分一致,便可斷定描油就是密陀繪。因此,對描油漆器和疑似密陀繪漆器作進一步檢測分析比對也是必要的研究工作。
三、研究密陀繪的意義
即便一項在當今社會已無價值可言的失傳技藝,我們對于技法的深入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在文物保護與修復乃至考古與歷史研究領域內,假設我們對密陀繪的工藝技法有非常全面的了解,那在面對疑似密陀繪作品的文物時,也可以避免只能形容為“疑似”的尷尬。極其特別的是密陀繪作品的現存狀況,已知確定為此技法的作品全部藏于日本正倉院,而中日專家學者通過文獻資料研究均得出此法來自中國唐代的結論。因此我們更需要努力揭開它神秘的面紗,找到它在中國流傳的證據,這樣不僅對類似文物的保護與修復有很大幫助,同時會為研究當時的工藝、繪畫、生活以及科技發展的歷史提供佐證。
我們當今對密陀繪研究的意義絕不僅限于對過去的了解。自漆畫從漆藝中獨立出來成為一種以漆材料的特性為語言的繪畫品種以后,漆畫顏色晦暗的問題始終是眾多漆畫家回避不了的大問題,因此也經常有人會誤認為漆畫就是黑乎乎的畫面,但是漆的語言絕不僅限于黑。而據筆者推斷,古代密陀繪的產生也正是為了解決漆色單調晦暗的問題,于是對這一工藝進行深入研究無疑會為現代漆畫的創作與創新注入新的力量。
對于失傳技藝密陀繪的研究,于歷史、于當代都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制定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理論結合實踐,用實驗以及實地考察結果來作為最終的研究結論,逐步揭開密陀繪神秘的面紗,找到國內密陀繪漆器遺存的證據。
參考文獻:
1.王世襄.髹飾錄解說——中國傳統漆工藝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鄭師許.漆器考.上海市博物館叢書.
3.王世襄.中國古代漆工雜述,1979(03).
4.日本山崎一雄.法隆寺壁畫的顏料(段修業譯).敦煌研究,1988(3).
5.日本小野勝年.日唐文化關系中的諸問題.1964年10月9日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演講.
6.滕軍.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與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作者簡介:
吳勝杰,單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碩士,研究方向:工藝美術、傳統工藝美術文物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