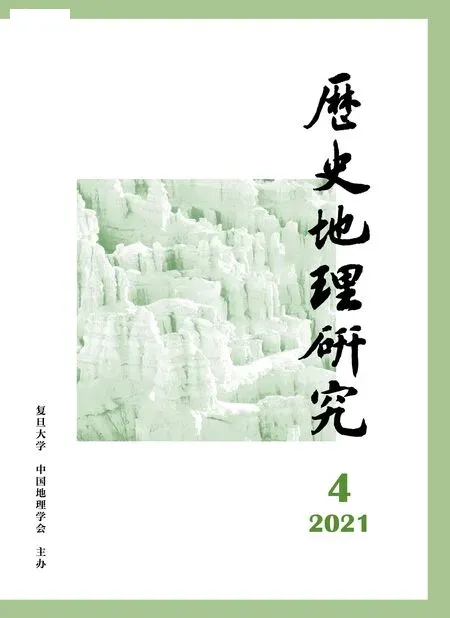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楚縣公的多重身份屬性
鄭伊凡
(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美國(guó)加利福尼亞州 94720)
縣制,作為中國(guó)歷史上歷時(shí)最久又最穩(wěn)定的政治與行政制度之一,大約于春秋早中期創(chuàng)制于楚、秦和晉。(1)關(guān)于縣的起源地,學(xué)界一直存在爭(zhēng)論,主要有楚、秦和晉國(guó)三種看法。清人洪亮吉曾說(shuō):“創(chuàng)始于楚,而秦與晉繼之。”見〔清〕 洪亮吉撰,劉德權(quán)點(diǎn)校: 《洪亮吉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983—984頁(yè)。近代學(xué)者顧頡剛亦以楚權(quán)縣為春秋第一縣,張正明、何浩、羅運(yùn)環(huán)等從之,參看顧頡剛: 《春秋時(shí)代的縣》,《禹貢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6、7合期,第169—189頁(yè)。也有學(xué)者主張秦和晉為縣制起源地,如虞云國(guó): 《春秋縣制新探》,《晉陽(yáng)學(xué)刊》1986年第6期。有關(guān)先秦縣制的綜合性研究,可參考周振鶴: 《縣制起源三階段說(shuō)》,《中國(guó)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3輯;魯鑫: 《東周郡縣制度研究》,南開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8年;陳劍: 《先秦時(shí)期縣制的起源與轉(zhuǎn)變》,吉林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9年;周振鶴主編,李曉杰著: 《中國(guó)行政區(qū)劃通史·先秦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245頁(yè)。國(guó)外學(xué)者的代表性論著有H. G. Creel, The Beginnings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the Hsi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4, Vol.23, No.2, pp.155-184; [日] 増淵龍夫: 《先秦時(shí)代の封建與郡県》,《中國(guó)古代の社會(huì)と國(guó)家》,巖波書店1996年版,該書的中譯本請(qǐng)參看[日] 增淵龍夫著,呂靜譯: 《中國(guó)古代的社會(huì)與國(guó)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87—366頁(yè)。縣公,一般認(rèn)為是對(duì)楚縣長(zhǎng)官的稱呼,也是研究楚縣乃至先秦時(shí)期縣制的重點(diǎn)之一。(2)有關(guān)楚縣公的研究,可參看楊寬: 《春秋時(shí)期楚國(guó)縣制的性質(zhì)問(wèn)題》,《中國(guó)史研究》1981年第4期,后收入《楊寬古史論文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83頁(yè)。[日] 平隆郎: 《楚王と県君》,《史學(xué)雜誌》第90編第2號(hào),1981年;中譯本參見[日] 平勢(shì)隆郎著,徐世虹譯: 《楚王和縣君》,劉俊文主編: 《日本中青年學(xué)者論中國(guó)史(上古秦漢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45頁(yè)。[日] 安倍道子: 《春秋後期の楚の「公」について——戰(zhàn)國(guó)封君出現(xiàn)へ向けての一試論》,《東洋史研究》第45卷第2號(hào),1986年,第187—204頁(yè)。徐少華: 《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291頁(yè)。春秋戰(zhàn)國(guó)之際的楚國(guó)先后出現(xiàn)一批地位顯赫的縣公群體,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影響甚至主導(dǎo)了楚國(guó)歷史的發(fā)展進(jìn)程及其與周邊國(guó)家的關(guān)系。本文擬充分吸收前人對(duì)先秦楚縣性質(zhì)的探索及相關(guān)理論方法的反思,結(jié)合出土文獻(xiàn)與新近考古發(fā)現(xiàn),以魯陽(yáng)公的身份為切入點(diǎn),對(duì)春秋戰(zhàn)國(guó)之際的若干縣公群體作出勾勒和描摹。在此基礎(chǔ)上理解先秦時(shí)期楚“縣公”與秦漢以后作為地方行政長(zhǎng)官的縣令(長(zhǎng))的異同,重視既有研究對(duì)縣制發(fā)展過(guò)程中不同階段的性質(zhì)作出區(qū)分認(rèn)識(shí)的貢獻(xiàn)。(3)如楊寬曾指出:“春秋時(shí)代的縣制與戰(zhàn)國(guó)秦漢以后的縣制,根本性質(zhì)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楊寬: 《春秋時(shí)代楚國(guó)縣制的性質(zhì)問(wèn)題》,《中國(guó)史研究》1981年第4期)徐少華也曾指出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政治經(jīng)濟(jì)制度不是一朝一夕產(chǎn)生的,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不可避免地帶有舊體制的成分和因素(徐少華: 《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第291頁(yè))。周振鶴在《縣制起源三階段說(shuō)》一文中更具體地把縣制的起源發(fā)展歸納為三個(gè)階段,加深了學(xué)界對(duì)縣制從先秦到秦漢發(fā)展歷程的認(rèn)識(shí)。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楚縣公具有明顯的爵稱特征、分封屬性和超越地方長(zhǎng)官的中央影響力,對(duì)先秦縣邑和縣制的理解不應(yīng)受限于職官名號(hào)(如“君”與“公”之別)上的二分框架,而應(yīng)更注重考察其實(shí)相及所處的具體歷史環(huán)境。
一、 魯陽(yáng)公的身份再探討
魯陽(yáng)公可能是楚縣公群體中最為顯赫和引人注目的,有關(guān)魯陽(yáng)公的材料在傳世和出土文獻(xiàn)中曾多次出現(xiàn),并一再引起學(xué)界的關(guān)注和討論。本節(jié)以清華簡(jiǎn)《系年》的記載及最新研究成果為突破口,重新探討魯陽(yáng)公的身份,在“尋找”魯陽(yáng)公的過(guò)程中,暫時(shí)拋開對(duì)其頭銜的所謂“君”與“公”的框架束縛,先以史事考證為主。清華簡(jiǎn)《系年》中兩次出現(xiàn)“魯陽(yáng)公”,其中第134—136簡(jiǎn)記載了楚悼王時(shí)期魯陽(yáng)公與晉師的戰(zhàn)事,釋文如下:
魯陽(yáng)公率師救武陽(yáng),與晉師戰(zhàn)于武陽(yáng)之城下,楚師大敗,魯陽(yáng)公、平夜悼武君、陽(yáng)城桓定君,三執(zhí)珪之君與右尹昭之俟死焉,楚人盡棄其旃、幕、車、兵,犬逸而還。(4)清華大學(xué)出土文獻(xiàn)研究與保護(hù)中心編,李學(xué)勤主編: 《清華大學(xué)藏戰(zhàn)國(guó)竹簡(jiǎn)(貳)》,中西書局2011年版,第196頁(yè)。
從《系年》的這段記載可以看出魯陽(yáng)公在楚國(guó)地位之尊崇。他率楚師北上征戰(zhàn),很有可能是此次戰(zhàn)役的主帥,地位排在平夜悼武君、陽(yáng)城桓定君和楚國(guó)的右尹之前。《系年》還明確稱前三者為“執(zhí)珪之君”。《戰(zhàn)國(guó)策·東周策》曾記載趙累與周君的對(duì)話:“公爵為執(zhí)圭,官為柱國(guó),戰(zhàn)而勝,則無(wú)加焉矣;不勝則死。”(5)繆文遠(yuǎn): 《戰(zhàn)國(guó)策新校注》(修訂本),巴蜀書社1998年版,第4頁(yè)。可知執(zhí)圭已經(jīng)是楚的最高爵位。新近研究表明,此次武陽(yáng)之役的主戰(zhàn)場(chǎng)在今河南原陽(yáng)至中牟一帶(6)張馳、鄭伊凡: 《清華簡(jiǎn)〈系年〉第二十三章與〈史記·六國(guó)年表〉對(duì)讀——戰(zhàn)國(guó)早中期相關(guān)史事、年代與地理問(wèn)題芻議》,《出土文獻(xiàn)》2021年第1期。,武陽(yáng)到魯陽(yáng)公的封邑或任職地魯陽(yáng)(今河南魯山縣城南關(guān))直線距離約兩百千米。此戰(zhàn)在楚國(guó)歷史上意義重大,包山簡(jiǎn)中被作為七條大事紀(jì)年之一的“魯陽(yáng)公以楚師后城鄭之歲”即源于此,關(guān)于其年代曾有過(guò)楚懷王與楚悼王兩種說(shuō)法。《系年》公布以來(lái),學(xué)界對(duì)于戰(zhàn)國(guó)早中期的年代認(rèn)識(shí)有了較大推進(jìn),認(rèn)為該事件的主體發(fā)生在公元前395年,根據(jù)最新的戰(zhàn)國(guó)紀(jì)年研究對(duì)應(yīng)于楚悼王五年末,作為大事紀(jì)年被選為下一年的年代標(biāo)識(shí)。(7)相關(guān)研究成果見李學(xué)勤: 《論包山簡(jiǎn)魯陽(yáng)公城鄭》,《清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4年第3期;鄭伊凡: 《再論包山簡(jiǎn)魯陽(yáng)公以楚師后城鄭之歲——兼談楚簡(jiǎn)大事紀(jì)年的性質(zhì)》,《江漢考古》2015年第2期。魯陽(yáng)公率楚師與三晉(主要是韓)及鄭的交戰(zhàn),亦見于傳世文獻(xiàn)《淮南子》等的記載,如《淮南子·覽冥訓(xùn)》云:
高誘注:“魯陽(yáng),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guó)語(yǔ)》所稱魯陽(yáng)文子也。”《國(guó)語(yǔ)·楚語(yǔ)下》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yáng)公也。”(9)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zhǎng)云點(diǎn)校: 《國(guó)語(yǔ)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527—528頁(yè)。孫詒讓在《墨子間詁》中轉(zhuǎn)引賈逵注《國(guó)語(yǔ)》曰:“魯陽(yáng)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yáng)公。”(10)〔清〕 孫詒讓撰,孫啟治點(diǎn)校: 《墨子間詁》卷一一《耕柱第四十六》,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431頁(yè)。可見舊注家皆以為初代魯陽(yáng)公為司馬子期之子、平王之孫公孫寬,又稱魯陽(yáng)文子。公孫寬生年雖不詳,但其父司馬子期死于楚惠王十年(前479)的白公之亂,楚惠王十一年(前478)即出任楚司馬,此時(shí)當(dāng)已成年。史籍所見公孫寬生活年代下距《系年》所見的魯陽(yáng)公前后相距80余年,二者不可能是同一人。因此錢穆曾對(duì)高誘注作分析指出:“高氏此注,以魯陽(yáng)公即魯陽(yáng)文子是也,顧謂即司馬子期之子,則非。”(11)錢穆: 《墨子游魯陽(yáng)考》,《先秦諸子系年(外一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頁(yè)。也就是說(shuō)錢穆認(rèn)為《淮南子》中的魯陽(yáng)公可能被稱為“魯陽(yáng)文子”,但不會(huì)早至楚惠王時(shí)期,從年代看只能是公孫寬之后的某代魯陽(yáng)公。這種解讀沒(méi)有考慮“公”與“子”或“君”的稱呼之別,主要以年代和史事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為考量,而清華簡(jiǎn)《系年》中的魯陽(yáng)公與《墨子·魯問(wèn)》中的一段記載恰好可以對(duì)讀:
魯陽(yáng)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魯陽(yáng)文君曰:“魯四境之內(nèi),皆寡人之臣也……我攻鄭,順于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12)〔清〕 孫詒讓撰,孫啟治點(diǎn)校: 《墨子間詁》卷一三《魯問(wèn)第四十九》,第467—468頁(yè)。
《墨子》這段記載引起聚訟之處在于“鄭人三世殺其父”及“三年不全”,清代學(xué)者蘇時(shí)學(xué)認(rèn)為是鄭幽公、鄭哀公、鄭公三世,孫詒讓則懷疑三為二之誤。鄭威曾做過(guò)排比分析,指出幽公為韓武子所殺,應(yīng)當(dāng)排除,進(jìn)而提出昭公、靈公、哀公三鄭君的說(shuō)法。(13)鄭威: 《墨子游楚魯陽(yáng)年代考》,《江漢考古》2012年第3期。但對(duì)于“三年不全”,尚未見有學(xué)者提出恰切的解釋。清華簡(jiǎn)的公布對(duì)于戰(zhàn)國(guó)早期的鄭國(guó)歷史研究有較大推進(jìn)。(14)程浩: 《困獸猶斗: 新史料所見戰(zhàn)國(guó)前期的鄭國(guó)》,《殷都學(xué)刊》2018年第1期。《系年》的內(nèi)容補(bǔ)充了《六國(guó)年表》中所未見的細(xì)節(jié),可知鄭國(guó)在楚聲王被殺、悼王即位之初曾叛楚而結(jié)盟三晉,甚至一度敗楚師于桂陵并奪回榆關(guān)。但隨后即招致楚的報(bào)復(fù),大敗鄭并俘獲了鄭之四將軍。外部壓力導(dǎo)致鄭國(guó)內(nèi)部也出現(xiàn)了動(dòng)蕩,《系年》一方面揭示了傳世文獻(xiàn)所未見的信息,也證實(shí)了《史記》等傳世文獻(xiàn)關(guān)于此段歷史的齟齬之處其實(shí)另有隱情:
鄭太宰欣亦起禍于鄭,鄭子陽(yáng)用滅,無(wú)后于鄭。明歲,楚人歸鄭之四將軍與其萬(wàn)民于鄭。(15)清華大學(xué)出土文獻(xiàn)研究與保護(hù)中心編,李學(xué)勤主編: 《清華大學(xué)藏戰(zhàn)國(guó)竹簡(jiǎn)(貳)》,第196頁(yè)。
若以上考證可以成立,則《墨子·魯問(wèn)》中“鄭人三世殺其父”可能是指哀公、公、子陽(yáng),而這一方案可以很好地解釋“三年不全”的問(wèn)題,其具體所指正是《韓非子》中的“鄭子陽(yáng)身殺,國(guó)分為三”的現(xiàn)狀。子陽(yáng)被殺是在楚悼王三年(前398),而魯陽(yáng)公伐鄭是在楚悼王六年(前395),中間恰好間隔三年。至于“不全”,周勛初曾指出《韓非子》中的“國(guó)分為三”是說(shuō)鄭國(guó)在子陽(yáng)身死之后分裂為負(fù)黍、陽(yáng)城和鄭三部分。(22)周勛初: 《〈韓非子〉札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頁(yè)。這應(yīng)當(dāng)就是《墨子·魯問(wèn)》中“魯陽(yáng)文君”攻鄭的背景,也印證了傳世文獻(xiàn)中的“魯陽(yáng)文君”在清華簡(jiǎn)《系年》中被記作魯陽(yáng)公,這與錢穆和李學(xué)勤的認(rèn)識(shí)是一致的。(23)值得注意的是,錢穆和李學(xué)勤的考證都沒(méi)有考慮魯陽(yáng)公與魯陽(yáng)文君/子在稱呼上的區(qū)分,但他們的立場(chǎng)與賈逵、韋昭等舊注家不完全一致,因后者未考慮年代差異而把幾個(gè)文獻(xiàn)中的魯陽(yáng)公系于公孫寬一人身上。需要再次指明的是,這里的魯陽(yáng)公不是指初代魯陽(yáng)君公孫寬而應(yīng)當(dāng)是其后繼者。
如果把目光轉(zhuǎn)向其他文獻(xiàn)和考古材料,魯陽(yáng)公還曾多次見于曾侯乙墓竹簡(jiǎn),王鑫分析了向曾侯乙助喪赗贈(zèng)路車的七人,分別是楚王、太子、平夜君、羕君、陽(yáng)城君、君和旅(魯)陽(yáng)公,考察他們赗贈(zèng)路車所用的馬匹規(guī)格與數(shù)量,陽(yáng)城君、君與魯陽(yáng)公皆是三屯麗,高于羕君和平夜君。(24)王鑫: 《戰(zhàn)國(guó)封君形態(tài)及領(lǐng)地治理探研》,武漢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20年。說(shuō)明魯陽(yáng)公和陽(yáng)城君、君處于同一等級(jí)的地位,這和《系年》中的情況類似。同時(shí)也反映了在封君內(nèi)部也存在爵位和地位的差異,這當(dāng)是由其他因素(如職官、資歷、出身、封邑規(guī)模等)決定的,不是所有稱“公”或“君”的貴族地位都完全同等。王鑫還分析了目前所見的楚簡(jiǎn)大事紀(jì)年的所有人物,發(fā)現(xiàn)只有楚王和魯陽(yáng)公不稱名姓,其他所有封君和客卿都無(wú)一例外稱呼姓名,更見魯陽(yáng)公地位之尊崇,出土文獻(xiàn)中的這些信息和《墨子》中反映的魯陽(yáng)公、君在其封邑或任職地內(nèi)的支配地位是一致的。(25)如《墨子·魯問(wèn)》篇中魯陽(yáng)文君聲稱“魯四境之內(nèi),皆寡人之臣”,見〔清〕 孫詒讓撰,孫啟治點(diǎn)校: 《墨子間詁》卷一三《魯問(wèn)第四十九》,第467—468頁(yè)。
二、對(duì)封建與郡縣的理論框架在先秦縣
制研究中的回顧與思考
魯陽(yáng)公對(duì)應(yīng)傳世文獻(xiàn)中的魯陽(yáng)君一說(shuō)首先會(huì)面臨的挑戰(zhàn)和質(zhì)疑是: 魯陽(yáng)公有沒(méi)有可能被稱為魯陽(yáng)君。畢竟在現(xiàn)行學(xué)術(shù)史框架下“公”和“君”一般被認(rèn)為是分屬于郡縣與封建兩種政治體制下的官稱和爵稱。(26)持這種觀點(diǎn)的學(xué)者以何浩先生為代表,可參看何浩: 《魯陽(yáng)君、魯陽(yáng)公及魯陽(yáng)設(shè)縣的問(wèn)題》,《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要回答這一問(wèn)題,首先要對(duì)這一認(rèn)知框架被建立起來(lái)的過(guò)程作一學(xué)術(shù)史的回顧,并考察它在具體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沈?qū)毾檎J(rèn)為,從建設(shè)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歷史長(zhǎng)時(shí)期的角度看,鄧小平理論、“三個(gè)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今后形成的理論,都是圍繞著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這一歷史主題而展開的,綜合起來(lái)看,將構(gòu)成一個(gè)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理論的體系。研究這個(gè)理論體系,是歷史的需要。我們要以歷史的眼光來(lái)認(rèn)識(shí)這個(gè)問(wèn)題,對(duì)待這個(gè)問(wèn)題[19]。
楚邑的管領(lǐng)者和長(zhǎng)官的稱呼常見有公、尹、君和大夫等,其中《左傳》明確記載楚有“縣公”和“縣尹”,分別見于宣公十一年(前598)和襄公二十六年(前547)。但應(yīng)注意《左傳》中并沒(méi)有出現(xiàn)過(guò)具體“地名+縣”的記載,只有一般讀作動(dòng)詞的“縣陳”“縣申、息”等少數(shù)幾例,把它們理所當(dāng)然地讀為“設(shè)縣”其實(shí)是加入了學(xué)術(shù)預(yù)設(shè)。畢竟這里的“縣”在大部分語(yǔ)境下是取“懸”“系”之本義,即以之為縣鄙或縣邑,“懸”于國(guó)都或中心城邑,作為其屬邑的含義。正如土口史記所指出的,學(xué)界現(xiàn)行判定楚縣的方法多以職官名稱的“某公”“某尹”“某大夫”來(lái)反向判定存在“某縣”。(27)[日] 土口史記: 《先秦時(shí)代の領(lǐng)域支配》,京都大學(xué)學(xué)術(shù)出版會(huì)2011年版,第178頁(yè)。而學(xué)界之所以對(duì)“縣”特加關(guān)注,自然是受到秦漢以后成為主流的郡縣制的影響,將后世的情況回溯而加之于早期,這是一種“輝格史學(xué)”的認(rèn)知方式。(28)有關(guān)“輝格史學(xué)”的相關(guān)論著,可參讀[英]赫伯特·巴特菲爾德著,張?jiān)烂鳌⒈背勺g: 《歷史的輝格解釋》,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版。從邏輯推理來(lái)講,這一過(guò)程包含了“默證”和“循環(huán)論證”的風(fēng)險(xiǎn): 因?yàn)榇嬖凇暗孛?公”的記載,所以認(rèn)為該地應(yīng)當(dāng)是某縣;反過(guò)來(lái),因?yàn)椤耙阎庇小澳晨h”,所以“某公”應(yīng)當(dāng)是該縣之地方長(zhǎng)官,這樣的思考過(guò)程默認(rèn)了需要論證的前提和預(yù)設(shè)。大量出土文獻(xiàn)雖然帶來(lái)了更豐富的個(gè)案例證,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這一格局,比如包山簡(jiǎn)中大量出現(xiàn)的“公”,其中就包含各類不同層級(jí)的管理機(jī)構(gòu)的職官名,很多名稱根本與地域無(wú)關(guān)(29)比如土口史記曾分析“”,認(rèn)為它更像地方的附屬機(jī)構(gòu)而非行政單位,參看[日] 土口史記: 《先秦時(shí)代の領(lǐng)域支配》,第107—116頁(yè);另參[日] 柏倉(cāng)優(yōu)一: 《包山文書簡(jiǎn)よりみる戰(zhàn)國(guó)中期楚國(guó)の縣制》,《中國(guó)出土資料研究(第二十四號(hào))》,2020年,第70—72頁(yè)。,反而使得楚縣的判定更復(fù)雜了。
“地名+大夫”的情況與此類似,傳世文獻(xiàn)中比較多見晉國(guó)的縣大夫或邑大夫,包山簡(jiǎn)中則多次出現(xiàn)楚的“(縣)大夫”,學(xué)界早先認(rèn)為可能是縣的長(zhǎng)官。游逸飛在系統(tǒng)梳理和比較之后指出,包山簡(jiǎn)所見的楚“縣大夫”具有較強(qiáng)的個(gè)人屬性和爵位性質(zhì),應(yīng)當(dāng)被視為爵稱而非官稱。(30)游逸飛: 《試論戰(zhàn)國(guó)楚國(guó)的“大夫”為爵》,《出土文獻(xiàn)》第5輯,中西書局2014年版,第75—85頁(yè)。爭(zhēng)議較大的還是縣公、縣尹和縣君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封君制作為西周以來(lái)的分封體系的一部分,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雖然有發(fā)展和流變,但封君作為封邑領(lǐng)主的性質(zhì)基本沒(méi)有改變。(31)有關(guān)楚國(guó)封君制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發(fā)展,以鄭威的研究集其大成,可參看鄭威: 《楚國(guó)封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作者在書中曾總結(jié)道:“‘縣君’僅可能是偶見的對(duì)縣長(zhǎng)官的尊稱,而非常見的正式稱呼。”又說(shuō):“春秋后期‘邑名+君’可能指的是封君,也可能是對(duì)縣尹的尊稱,但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封君大量出現(xiàn)后,一般專指封君。”筆者認(rèn)為這一認(rèn)識(shí)大體上是中肯的,至少把原先看似截然二分的性質(zhì)界定的問(wèn)題變成了一個(gè)“定量”的程度問(wèn)題,為進(jìn)一步探究這種二分格局預(yù)留了空間。根據(jù)既有研究,縣君一般指封君。問(wèn)題的關(guān)鍵還是在于縣公的性質(zhì)及其與縣尹之間的關(guān)系,而有一條核心材料始終是無(wú)法繞開的。
《左傳》宣公十一年記:“諸侯、縣公皆慶寡人”,這是《左傳》中唯一一次出現(xiàn)“縣公”的記載。杜預(yù)注曰:“楚縣大夫皆僭稱‘公’”(32)〔晉〕 杜預(yù)注,〔唐〕 孔穎達(dá)正義: 《春秋左傳正義》,〔清〕 阮元校刻: 《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76頁(yè)。,認(rèn)為縣公是楚國(guó)縣大夫的一種僭稱。高誘注《淮南子·覽冥訓(xùn)》也持類似看法:“楚僭號(hào)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33)〔漢〕 劉安編,何寧撰: 《淮南子集釋》卷六《覽冥訓(xùn)》,第447頁(yè)。高誘和杜預(yù)的注其實(shí)是把縣公等同于縣大夫,并默認(rèn)縣大夫相當(dāng)于秦漢以后縣的長(zhǎng)官(守)。至于“僭稱”的說(shuō)法,當(dāng)是因?yàn)椤肮痹谙惹氐恼Z(yǔ)境下首先讓人想到的是作為內(nèi)爵的“三公”或五等爵分封體系下的“公”,這樣的“公”自然難以和“縣守”聯(lián)系在一起,于是便用“僭稱”來(lái)解釋。但正如上節(jié)分析“魯陽(yáng)公”時(shí)所顯示的,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魯陽(yáng)公的身份本就是僅次于楚王之下的高等級(jí)貴族,不需要“僭”稱。問(wèn)題不在于稱“公”,而在于這里的“縣”不能簡(jiǎn)單地等同于秦漢以后基層地方政府的縣。
清人王引之不同意“僭稱”的說(shuō)法,他認(rèn)為“縣公,猶言縣尹也,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王,其臣僭稱公,則楚之貴者,無(wú)如令尹、司馬,何以令尹、司馬不稱公,而稱公者反在縣大夫乎?……公為縣大夫之通稱,非僭擬于公侯也”(34)〔清〕 王引之: 《經(jīng)義述聞·春秋左傳中》卷一八“縣公”條,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第689—690頁(yè)。。王引之首先把縣尹也放進(jìn)來(lái)一起討論,認(rèn)為縣尹、縣公、縣大夫三者是等同的。接著指出了重點(diǎn),認(rèn)為縣公的“公”根本不是爵制體系中作為高爵的“公侯”之“公”,他的理由是楚國(guó)的中央長(zhǎng)官令尹、司馬才更有資格稱公。然而正如第三節(jié)將要展示的,楚國(guó)的縣公就不是類似于秦漢以后的“地方長(zhǎng)官”,有些楚縣公在擔(dān)任“縣公”后即任令尹、司馬等中央職官(35)如子西在僖公二十六年(前634)時(shí)以司馬的身份出現(xiàn),《左傳》文公十年(前617)則提到他“為商公”;楚公子棄疾在昭公十一年(前531)時(shí)為“蔡公”,昭公十三年(前529)為司馬;葉公子高更是以葉公身份匡正楚王室,兼任令尹、司馬。楊寬曾論及楚縣尹的地位僅次于令尹和司馬,縣尹常常升任左右司馬,參見《楊寬古史論文選集》,第71頁(yè)。,其權(quán)力直接影響到楚國(guó)的政局走向。如果說(shuō)高誘、杜預(yù)的“僭稱說(shuō)”是為了調(diào)和作為高等級(jí)爵稱的“公”與“基層地方長(zhǎng)官”之間的違和之處,王引之的方法是更為直接地拒絕了“公”在任何爵制意涵方面的暗示。
顧頡剛是現(xiàn)代學(xué)者中最早集中討論春秋時(shí)代縣制的,他對(duì)于楚縣長(zhǎng)官稱公的解釋是:“君”與“尹”本是一字;而“君”與“公”音近相通。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沒(méi)有區(qū)分后來(lái)學(xué)者以為涇渭分明的封君與縣大夫,比如他認(rèn)為棠君和棠邑大夫是一回事。顧頡剛還認(rèn)為,楚縣是直隸于君主的,“沒(méi)有封建的成分在內(nèi)”,因而是秦始皇建立郡縣制的先聲。(36)顧頡剛: 《春秋時(shí)代的縣》,第171—172頁(yè)。平勢(shì)隆郎認(rèn)為“公”和“君”并用的可能性較高,而“君”與“尹”本質(zhì)上是一樣的,因形近被混用,只不過(guò)“尹”多用于中央官職,而“君”用于縣統(tǒng)治者,“公”則是其特殊稱號(hào)。(37)[日] 平勢(shì)隆郎著,徐世虹譯: 《楚王和縣君》,劉俊文主編: 《日本中青年學(xué)者論中國(guó)史(上古秦漢卷)》,第217—218頁(yè)。楊寬繼承了顧頡剛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春秋時(shí)期的楚縣“是直屬于國(guó)君的別都的性質(zhì)”。他還區(qū)分了縣公與封君的差別,認(rèn)為“楚縣設(shè)有長(zhǎng)官,叫做縣尹,又尊稱為縣公,由國(guó)君任命派遣”。“春秋時(shí)代楚國(guó)縣尹沒(méi)有稱‘君’的,稱‘君’的當(dāng)是封君性質(zhì),例如魯陽(yáng)文君就是如此。”“在一般場(chǎng)合下都尊稱縣尹為縣公,只有在正式場(chǎng)合才使用正式的官名成為縣尹。”(38)楊寬: 《春秋時(shí)代楚國(guó)縣制的性質(zhì)問(wèn)題》,《中國(guó)史研究》1981年第4期。楊寬所確立的縣公與封君的二分框架成為此后學(xué)界主流認(rèn)識(shí)并為后來(lái)學(xué)者所繼承(39)比如何浩堅(jiān)持認(rèn)為,縣公是一縣長(zhǎng)官,不能與爵稱混為一談。并認(rèn)為封君對(duì)所屬封邑有直接的統(tǒng)治權(quán)力,是一種完全的分封制度。這種分封制分散了楚國(guó)的力量,甚至導(dǎo)致了楚國(guó)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衰落。參見何浩: 《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楚封君初探》,《歷史研究》1984年第5期。,但他認(rèn)為縣尹才是正式官名而縣公只是尊稱的提法可能并不準(zhǔn)確,此后隨著更多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學(xué)界對(duì)縣公和縣尹的關(guān)系作出了更細(xì)密的區(qū)分。
顧久幸認(rèn)為,“凡是遷離故國(guó)所設(shè)的縣,其長(zhǎng)官稱‘尹’……凡是就故國(guó)舊地所設(shè)的縣,其縣官稱公”,即縣公是一種職官名而非尊稱。(40)顧久幸: 《沈縣和沈尹——兼論楚縣的性質(zhì)》,張正明主編: 《楚史論叢·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135頁(yè)。沈縣的地望在今安徽臨泉縣,考證過(guò)程可參見徐少華: 《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第280—281頁(yè)。陳偉推測(cè),楚國(guó)大縣稱公而小縣稱尹,類似后世的縣令與縣長(zhǎng)之別,都屬于職官名。(41)陳偉: 《楚“東國(guó)”地理研究》,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頁(yè)。徐少華根據(jù)襄陽(yáng)山灣墓地同時(shí)出土的“鄧公乘鼎”與“鄧尹疾鼎”指出,縣尹與縣公是可以同時(shí)設(shè)于楚縣之中的。(42)徐少華: 《論近年來(lái)出土的幾件春秋有銘鄧器》,《古文字研究》第25輯,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94—198頁(yè)。如徐少華所論,“鄧公”與“鄧命(令)尹”也同時(shí)見于包山簡(jiǎn)的記載,說(shuō)明鄧邑同時(shí)有“公”與“尹(令尹)”。包山簡(jiǎn)中還同時(shí)有“郯路公”與“郯路尹”,如果“路”是楚國(guó)一種特殊的縣級(jí)政區(qū)的說(shuō)法可以成立(43)鄭威: 《“夏州”小考——兼談包山楚簡(jiǎn)“路”的性質(zhì)》,《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那么公和尹并用的現(xiàn)象可能更為普遍。而“公”大量出現(xiàn)于法律文獻(xiàn)及官方文書中的事實(shí),也說(shuō)明它不只是一種“非正式的尊稱”而已。
在這種主流的二分框架之外,也并非沒(méi)有不同的聲音。比如虞云國(guó)認(rèn)為,史料中“縣+地名”的記載不足以反映早期縣制的建立,這里的縣不過(guò)是縣鄙、縣邑之義,表示把相關(guān)地方作為一國(guó)的屬邑而已。具體到楚縣“縣尹”的稱呼,虞云國(guó)一方面認(rèn)同顧頡剛、童書業(yè)的考證,認(rèn)為尹通公、君,具有裂土封賜的性質(zhì),他還批評(píng)了杜預(yù)等以“僭稱”解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中的“縣公”。他的解釋是,楚國(guó)大夫因?yàn)榻杂蟹庖兀@些邑為縣邑,也可僅以“縣”稱之,所以楚大夫其實(shí)都是縣大夫,都“尹”(作動(dòng)詞用)縣,自然也都可以稱縣公。在楚國(guó),大夫即縣大夫或縣公(縣君),三者本就是一回事,并不存在僭稱的問(wèn)題。(44)虞云國(guó): 《春秋縣制新探》,《晉陽(yáng)學(xué)刊》1986年第6期。這一解讀的特別之處在于,他認(rèn)為“縣大夫”中的“大夫”應(yīng)該放在先秦諸侯國(guó)內(nèi)“卿-大夫-士”這一官爵體系中理解,而不是把它等同于秦漢以來(lái)的“縣令”或“縣長(zhǎng)”。
在上述針鋒相對(duì)的立場(chǎng)之外,居于中間的聲音也一直存在,可能更接近歷史的復(fù)雜實(shí)際。增淵龍夫在20世紀(jì)50—60年代即已對(duì)顧頡剛提出的秦楚之縣屬于君主直轄地性質(zhì)的認(rèn)識(shí)作了批判。他認(rèn)為春秋時(shí)期縣的設(shè)立打破了舊有的氏族秩序,建立了一種新的支配方式,也指出楚縣(乃至春秋時(shí)期各國(guó)的縣)兼具公、私的性格。他總結(jié)道:“通常在理解采邑的諸關(guān)系、與縣的各種具體關(guān)系時(shí),至少在春秋時(shí)代,就將私邑和公邑用那樣明確的相互對(duì)立概念區(qū)別開來(lái),未必合適。”(45)參看[日] 增淵龍夫著,呂靜譯: 《中國(guó)古代的社會(huì)與國(guó)家》,第340頁(yè)。另參閱同書第287—290、333—355頁(yè)。安倍道子也分析了《左傳》《國(guó)語(yǔ)》中的用語(yǔ),發(fā)現(xiàn)“封”和“為縣大夫”的用法其實(shí)是一致的,并不能區(qū)分出分封制和郡縣制的差別(46)[日] 安倍道子: 《春秋後期の楚の「公」について——戰(zhàn)國(guó)封君出現(xiàn)へ向けての一試論》,《東洋史研究》第45卷第2號(hào),第197頁(yè)。,因而提出“公”可以分為“封邑公”與“官邑公”兩類,前者具有封邑的性質(zhì),后者在本質(zhì)上屬于爵號(hào),雖然一般并不世襲。
這里還涉及一個(gè)關(guān)鍵問(wèn)題,即學(xué)界在判定某邑屬于封邑還是中央直轄的縣的性質(zhì)時(shí),往往用其統(tǒng)治者是否能夠世襲作為標(biāo)準(zhǔn)。事實(shí)上,同樣稱為縣,有的屬于君主直轄地,有的不是;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同樣屬于君主直轄地的邑,有的稱縣,而有的不稱縣。(47)參看[日] 增淵龍夫著,索介然譯: 《說(shuō)春秋時(shí)代的縣》,劉俊文主編,黃金山、孔繁敏等譯: 《日本學(xué)者研究中國(guó)史論著選譯(上古秦漢卷)》,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96頁(yè)。增淵龍夫認(rèn)為春秋時(shí)期的縣有時(shí)可以世襲,平勢(shì)隆郎分析了楚申公的情況,認(rèn)為楚國(guó)一般否定縣的世襲。(48)[日] 平勢(shì)隆郎著,徐世虹譯: 《楚王和縣君》,劉俊文主編: 《日本中青年學(xué)者論中國(guó)史(上古秦漢卷)》,第212—245頁(yè)。現(xiàn)有材料下楚縣公序列較為完整的申公有申公斗班與斗克,是父子相繼。田成方結(jié)合一批息國(guó)銅器的銘文分析,發(fā)現(xiàn)春秋早中期的楚息公也長(zhǎng)期被屈氏家族成員把持,呈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采邑化”傾向。(49)田成方、陳鑫遠(yuǎn): 《息器與周代息國(guó)、楚息縣》,《出土文獻(xiàn)》第15輯,中西書局2019年版,第69—85頁(yè)。土口史記考察了春秋晉縣的情況,認(rèn)為否定世襲并不是設(shè)置縣的結(jié)果,而往往是縣的長(zhǎng)官出奔、被殺、族滅等特殊外部原因造成的。晉縣之所以沒(méi)有世襲,更多是由于繼承者出缺造成的,屬于外在、偶然的政治狀況,而非制度化的縣的設(shè)置導(dǎo)致的體質(zhì)性改變。(50)[日] 土口史記: 《先秦時(shí)代の領(lǐng)域支配》,第176頁(yè)。他的這一看法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楚。吉本道雅認(rèn)為,春秋時(shí)期楚國(guó)國(guó)君的權(quán)力較大,能夠阻止特定氏族的世族化。(51)[日] 吉本道雅: 《中國(guó)先秦史の研究》,京都大學(xué)學(xué)術(shù)出版會(huì),2005年,第365—366頁(yè)。可見,縣邑長(zhǎng)官的非世襲性不足以否定它的封邑性質(zhì)或認(rèn)定它屬于秦漢以后流官體制下的“地方政府”。
無(wú)論是典籍舊注對(duì)于縣管領(lǐng)者稱“公”的解釋,還是顧頡剛認(rèn)為的楚縣“沒(méi)有封建的成分”,都建立在封建與郡縣這一二元理論框架的認(rèn)可基礎(chǔ)上,但這一看似涇渭分明的二元格局也有其時(shí)效性和局限性。(52)需要說(shuō)明,本文未重新界定文中所使用的“封建”一詞,而是隨目前學(xué)術(shù)界一般的用法。有關(guān)“封建”的概念在中國(guó)歷史學(xué)界的植入與應(yīng)用,及其所帶來(lái)的學(xué)術(shù)問(wèn)題的反思,可分別參考馮天瑜: 《“封建”考論》,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Barry B. Blakeley, On the “feudal” interpretation of Chou China, Early China, 1976, Vol.2, pp.35-37; Li Feng, “Feudalism” and Western Zhou China: a critic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03, Vol.63(1), pp.115-144.它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人們基于所熟悉的秦漢以后確立的與周代“封建”相對(duì)的“郡縣”體系下的認(rèn)知,是一種反向投射,不一定完全符合早期歷史的實(shí)際。顧炎武曾說(shuō)“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53)〔清〕 顧炎武: 《郡縣論》,收入華忱之點(diǎn)校: 《顧亭林詩(shī)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頁(yè)。,對(duì)春秋時(shí)期的縣邑區(qū)分出公邑或是私邑的性質(zhì),從而設(shè)立標(biāo)準(zhǔn)的做法本就應(yīng)當(dāng)更謹(jǐn)慎周全(54)[日] 增淵龍夫著,呂靜譯: 《中國(guó)古代的社會(huì)與國(guó)家》,第347頁(yè)。。郡縣制的早期發(fā)展進(jìn)程,正如孫聞博曾說(shuō)的,“并非線性的簡(jiǎn)單演進(jìn),而呈現(xiàn)出復(fù)合性特征”(55)孫聞博: 《秦君名號(hào)變更與“皇帝”的出現(xiàn)——以戰(zhàn)國(guó)至秦統(tǒng)一政治秩序的演進(jìn)為中心》,《“中研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集刊》第91本第3分,2020年,第335頁(yè)。。游逸飛也提醒“追溯秦漢郡縣制的淵源,固然意義重大,但也容易陷入線性史觀的窠臼,忽略歷史多元發(fā)展的可能性”(56)游逸飛: 《制造“地方政府”: 從“郡縣城邦”到“共治天下”》,復(fù)旦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中國(guó)中古史研究》編委會(huì)編: 《中國(guó)中古史研究·第七卷》,中西書局2019年版,第329頁(yè)。。具體到“公”的問(wèn)題,閻步克曾引用顧炎武考證晉文公亦稱文君、魯昭公稱昭君等事例,顯示“君”“公”兩名有時(shí)可通用,周秦漢時(shí)代“公”曾普遍作為爵號(hào)和尊稱。他還進(jìn)一步指出“歷史早期官、爵不分,若把它看成官號(hào),也沒(méi)問(wèn)題”(57)閻步克: 《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jié)構(gòu)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7年版,第46—47頁(yè)。。正如包山簡(jiǎn)中的“(縣)大夫”所反映的身份的個(gè)人性特征更像是爵位而非官位,游逸飛基于此指出“戰(zhàn)國(guó)爵位不只是身份等級(jí)制的一部分,更是行政制度的一部分”(58)游逸飛: 《試論戰(zhàn)國(guó)楚國(guó)的“大夫”為爵》,《出土文獻(xiàn)》第5輯,第85頁(yè)。。具體到中國(guó)縣制的發(fā)展歷史,增淵龍夫認(rèn)為:“作為君主直轄地的縣制的形成,不光是要求被支配的邑的氏族重新組織,也要求國(guó)本身的權(quán)力組織進(jìn)行改組,也就是說(shuō)支配者的諸氏族重新組織,并經(jīng)過(guò)官僚化的進(jìn)程。”春秋時(shí)代的縣不是直接和秦漢時(shí)代的縣銜接起來(lái)的,它們的性質(zhì)有時(shí)甚至是矛盾的。從春秋到秦漢的郡縣制過(guò)渡須經(jīng)過(guò)一次社會(huì)重組的重大變革,打破過(guò)去的氏族秩序。而這不僅僅是對(duì)被支配者的要求,也是對(duì)支配者的要求,君主必須建立起一個(gè)有效的權(quán)力基礎(chǔ)。統(tǒng)一完整的郡縣制是專制君主權(quán)力的基礎(chǔ),但在其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中,一方面要排除各種抵抗和阻力,另一方面還需要有一個(gè)較強(qiáng)的君主權(quán)力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59)[日] 增淵龍夫著,索介然譯: 《說(shuō)春秋時(shí)代的縣》,劉俊文主編,黃金山、孔繁敏等譯: 《日本學(xué)者研究中國(guó)史論著選譯(上古秦漢卷)》,第207頁(yè)。
游逸飛曾以“制造地方政府”為題,概括楊寬、嚴(yán)耕望等近代學(xué)者建構(gòu)的地方行政圖景。這一圖景中的郡縣制以西方現(xiàn)代概念的“地方政府”為模板,其主體內(nèi)涵則是成熟的官僚體系和集權(quán)的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延伸與復(fù)制。在近現(xiàn)代史學(xué)研究的實(shí)踐和話語(yǔ)中,學(xué)者所熟知和慣常使用的其實(shí)是西漢中期以后建立起來(lái)的所謂“漢式郡縣”,而對(duì)它在此前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經(jīng)歷的其他可能性未多措意。(60)游逸飛: 《制造“地方政府”: 從“郡縣城邦”到“共治天下”》,復(fù)旦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中國(guó)中古史研究》編委會(huì)編: 《中國(guó)中古史研究·第七卷》,第321—337頁(yè)。具體到先秦楚縣的研究領(lǐng)域,土口史記討論了學(xué)界現(xiàn)行研究多從郡縣制形成與發(fā)展這一單線條的路徑角度來(lái)理解包山簡(jiǎn)司法文書中所見的楚國(guó)的“邑”,不加辨析地把“邑”看作“郡縣”體系下的一級(jí)行政單位,他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從領(lǐng)域支配的多樣性的角度來(lái)看待“邑”等統(tǒng)治單位。從嚴(yán)格的史料批判角度看,包山簡(jiǎn)中甚至并未出現(xiàn)確證的楚縣,更不要說(shuō)把“地名+公”直接等同于秦漢以后的縣令、縣長(zhǎng)那種行政長(zhǎng)官了。(61)[日] 土口史記: 《先秦時(shí)代の領(lǐng)域支配》,第99—101頁(yè)。土口進(jìn)一步指出,從先秦到秦漢郡縣制形成的系譜建立在“西周—春秋晉國(guó)—三晉—秦—漢”這一發(fā)展脈絡(luò)基礎(chǔ)上,而楚國(guó)的“邑”甚至都不在這條發(fā)展線上,屬于主流之外的“潛流”。也就是說(shuō),學(xué)界根據(jù)秦漢以后或是先秦其他地區(qū)的郡縣制發(fā)展的一般模式所總結(jié)的規(guī)律,未必適用于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楚縣。
對(duì)于先秦縣制的認(rèn)識(shí)應(yīng)當(dāng)植根于對(duì)整個(gè)早期國(guó)家結(jié)構(gòu)和官僚制的形成與建立過(guò)程的深入理解當(dāng)中,對(duì)縣公性質(zhì)的理解也不應(yīng)受限于名義的區(qū)分,而應(yīng)考察其實(shí)相。而對(duì)縣公性質(zhì)的把握不能脫離具體時(shí)代背景下縣的特征,筆者認(rèn)為“縣尹”或許是楚縣的行政長(zhǎng)官,這與楚國(guó)中央官制中多以“尹”作為行政機(jī)構(gòu)長(zhǎng)官的稱呼有關(guān)。鄭威曾指出縣公、縣尹在一地的同時(shí)存在就是一種地方模仿中央的楚王與令尹的關(guān)系模式。(62)鄭威: 《楚國(guó)封君研究》,第8—9頁(yè)。至于楚國(guó)的縣公,就目前的史料來(lái)看,春秋時(shí)期的縣公在中央的地位遠(yuǎn)超出所謂“地方長(zhǎng)官”的程度。不少縣公出身于楚王族和屈、斗等幾個(gè)大的世族。縣公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和支配能力非秦漢以后的“牧守”所能比,這種影響力可以跨越世代傳遞,具有明顯的分封和爵制的特征。
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縣公”情況更為復(fù)雜。筆者曾分析包山簡(jiǎn)中的司法文書,發(fā)現(xiàn)其中“地名+公”的職官常常越境參與處理其他地區(qū)的司法和行政事務(wù),而不限于本地的管理。(63)鄭伊凡: 《戰(zhàn)國(guó)楚縣初探》,武漢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7年,第44—47頁(yè)。游逸飛則從另一側(cè)面指出,戰(zhàn)國(guó)楚縣公在地方上不具有最高、絕對(duì)的權(quán)力,不能干預(yù)所有行政事務(wù),地方的司法和財(cái)政事務(wù)多由司敗、司馬等專業(yè)官僚負(fù)責(zé),中央各部門的長(zhǎng)官可以越過(guò)縣公直接責(zé)成地方專業(yè)官僚處理。(64)游逸飛: 《“郡縣同構(gòu)”與“政出多門”——包山簡(jiǎn)所見戰(zhàn)國(guó)楚國(guó)郡縣制》,《興大歷史學(xué)報(bào)》2016年第31期。這與嚴(yán)耕望等構(gòu)筑的秦漢時(shí)期郡縣行政長(zhǎng)官在本地的權(quán)力圖景大相徑庭。(65)嚴(yán)耕望稱秦漢時(shí)期的郡縣首長(zhǎng)在地方猶如“君父”,故以“長(zhǎng)官元首制”名之。參見嚴(yán)耕望: 《中國(guó)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之“序言”,《“中研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五A》,臺(tái)北“中研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3—5頁(yè)。鄭威分析了楚縣由縣邑之縣到郡縣之縣的轉(zhuǎn)變過(guò)程,楚王為加強(qiáng)中央集權(quán)而與世族世官把持的地方縣邑進(jìn)行權(quán)力博弈,常分割縣域以為封邑,并收回行政和司法權(quán),僅保留世族的經(jīng)濟(jì)特權(quán)。(66)鄭威: 《從縣邑之縣到郡縣之縣: 春秋戰(zhàn)國(guó)之際楚國(guó)縣制的演變》,《出土文獻(xiàn)與楚秦漢歷史地理研究》,科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58—69頁(yè)。這或許可以作為楚縣公從春秋到戰(zhàn)國(guó)轉(zhuǎn)變的背景。楚王以加強(qiáng)封君力量來(lái)壓制縣邑(后者本應(yīng)視為直屬于楚王管轄的勢(shì)力范圍)權(quán)力擴(kuò)張的行動(dòng),說(shuō)明無(wú)論封邑還是縣邑,對(duì)其性質(zhì)的判斷最終還是要落到中央對(duì)權(quán)力與資源的分配方式。而“地名+公”作為爵稱的現(xiàn)象直到楚漢之際還很常見,如劉邦稱“沛公”,項(xiàng)羽稱“魯公”,夏侯嬰稱“滕公”等實(shí)例不勝枚舉。(67)鄭伊凡: 《戰(zhàn)國(guó)楚縣初探》,第47—51頁(yè)。“某公”的稱呼不應(yīng)被直接理解為某縣的長(zhǎng)官,而被指稱的對(duì)象即使在脫離原職很久之后都還保留這一爵稱,這一現(xiàn)象應(yīng)當(dāng)被視為楚制和楚爵在秦漢之際的延續(xù)。
三、 楚縣公群體的多重身份屬性
第一節(jié)論及楚縣公經(jīng)常發(fā)揮重要的軍事職能,縣公有時(shí)也被交付以重大國(guó)政。如《左傳》哀公六年(前489)楚國(guó)再次滅蔡后,葉公諸梁就承擔(dān)了遷徙并重新安置蔡地民眾的任務(wù)。從相關(guān)文獻(xiàn)記載來(lái)看,至少?gòu)聂敯Ч哪?前491)到哀公六年的三年之間,葉公諸梁都在具體負(fù)責(zé)相關(guān)事務(wù),并屯戍駐扎于“負(fù)函”。“負(fù)函”位于今信陽(yáng)市區(qū)以南、冥阨關(guān)以北的山陵夾峙地帶,距今河南葉縣城南的古“葉”地有相當(dāng)距離。魯哀公十六年(前479)白公勝作亂,殺令尹、司馬,劫持惠王,葉公又率兵由蔡入郢,平定叛亂,在穩(wěn)定政局之初身兼令尹與司馬二職。值得注意的是,《左傳》記載葉公入郢之前“在蔡”(68)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03頁(yè)。,《國(guó)語(yǔ)·楚語(yǔ)下》也稱此時(shí)“子高以疾閑居于蔡”(69)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zhǎng)云點(diǎn)校: 《國(guó)語(yǔ)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531頁(yè)。。以上文獻(xiàn)都說(shuō)明葉公長(zhǎng)期不在葉地,而居于今河南上蔡縣境的蔡地。如果“葉公”真的是秦漢以后所理解的葉縣地方長(zhǎng)官,怎能長(zhǎng)期不在葉地,又如何管理“葉縣”的日常行政事務(wù)?還是說(shuō)身為“葉公”的沈諸梁實(shí)際上并不負(fù)責(zé)葉地的行政管理事務(wù)而葉只是其封爵食邑所在,具體事務(wù)另有當(dāng)?shù)毓賳T如“尹”或“大夫”執(zhí)掌?包山簡(jiǎn)中確有記載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葉地有“大夫”一職(70)包山楚簡(jiǎn)第130號(hào)簡(jiǎn): 期思少司馬勝或(又)以足金六勻(鈞)舍葉,葉大夫、集昜(陽(yáng))公蔡逯受。釋文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duì): 《包山楚簡(jiǎn)》,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頁(yè)。,或許是葉地的實(shí)際理政者。平定白公之亂后,葉公又曾率楚師伐越并取得戰(zhàn)略勝利。文獻(xiàn)顯示葉公在葉地有“食田六百畛”(71)繆文遠(yuǎn): 《戰(zhàn)國(guó)策新校注》(修訂本),巴蜀書社1998年版,第443頁(yè)。,功成身退后“老于葉”(72)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04頁(yè)。。值得注意的是《左傳·成公十五年》也記載“申叔時(shí)老矣,在申”(73)〔晉〕 杜預(yù)注,〔唐〕 孔穎達(dá)正義: 《春秋左傳正義》,〔清〕 阮元校刻: 《十三經(jīng)注疏》,第1914頁(yè)。,說(shuō)明縣公終老于任職所在縣的情況并不稀見,或許是因?yàn)橛蟹庖卦诋?dāng)?shù)亍I喜┖?jiǎn)《柬大王泊旱》中出現(xiàn)的“晉侯”,又被認(rèn)為是葉侯,可能就是葉公諸梁的后代。(74)劉信芳: 《上博藏竹書〈柬大王泊旱〉圣人諸梁考》,《中國(guó)史研究》2007年第4期。這表明葉公可能將其封號(hào)和采邑傳給后代子孫,如此“葉公”的身份就更像是封爵而非職官了,明顯具有采邑主的性質(zhì)。(75)參閱鄭威在《從縣邑之縣到郡縣之縣: 春秋戰(zhàn)國(guó)之際楚國(guó)縣制的演變》一文中的分析。此外,鄖公的情況也很有代表性,從楚成王到楚昭王的近200年間,史籍所見的“鄖公”無(wú)不出自斗氏一族。楚平王殺斗成然后立其子斗辛,《左傳》昭公十四年載“使斗辛居鄖,以無(wú)忘舊勛”,此后23年,吳師入郢之際楚昭王出逃而“奔鄖”,得鄖公斗辛護(hù)送昭王逃到隨國(guó)才免除一死。安倍道子曾討論鄖公斗辛的情況,認(rèn)為擔(dān)任“鄖公”的斗辛具有軍事性色彩,實(shí)際上是以鄖(今湖北安陸古城)作為其封邑。參讀安倍道子: 《春秋後期の楚の「公」について——戰(zhàn)國(guó)封君出現(xiàn)へ向けての一試論》,第195頁(yè)。近來(lái)有學(xué)者注意到縣公群體的這種身份特征,將之歸納為“本土化”,而本土化的加深不僅沒(méi)有削弱,反而提升了縣公在中央內(nèi)政管理上的話語(yǔ)權(quán)。(76)黃佳川: 《春秋時(shí)期楚國(guó)方城之外縣公群體角色的變遷——以沈尹戌、沈諸梁父子為研究對(duì)象》,《淮南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第6期。
綜合來(lái)看,葉公子高出身世族,其父沈尹戌曾任楚左司馬,沈縣在今安徽臨泉縣古城子,沈尹戌曾以沈尹身份聯(lián)合淮水流域的縣公群體負(fù)責(zé)應(yīng)對(duì)吳國(guó)的軍事入侵,其職能亦超出沈縣長(zhǎng)官之執(zhí)掌而具有中央權(quán)力的特征。(77)顧久幸: 《沈縣和沈尹——兼論楚縣的性質(zhì)》,張正明主編: 《楚史論叢·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頁(yè)。另外,田成方認(rèn)為“沈尹”不是沈縣縣尹,而是“太室內(nèi)掌管祭祀、占卜的神職官員”,可備一說(shuō)。參見田成方: 《東周時(shí)期楚國(guó)宗族研究》,科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90—93頁(yè)。葉公地位尊崇,威望極高,在入郢都平定白公之亂時(shí)“國(guó)人望君如望歲焉”(《左傳·哀公十六年》)。葉公本人在楚國(guó)擔(dān)任令尹等要職,率師平蔡伐越,其本人亦曾出使齊國(guó)。葉公在葉地當(dāng)有封邑,且其子承襲了“葉”的封號(hào),稱為“葉侯”,這都與把楚的“葉公”理解為秦漢以后葉縣的長(zhǎng)官與文獻(xiàn)記載及歷史背景存在較大距離,而把“公”作為地方之“邑”的行政長(zhǎng)官來(lái)看待也難免有隔膜之感。
類似魯陽(yáng)公、葉公這樣長(zhǎng)期在中央任職,活動(dòng)范圍在郢都圈,權(quán)力和地位超越地方的楚縣公不在少數(shù)。較為顯著的例子還有曾任蔡公的公子棄疾(楚平王),他曾趁楚國(guó)動(dòng)亂之際迫使靈王自殺并奪取王位。還有上文已提及的楚平王之孫白公勝(白地在今河南息縣境內(nèi)),曾囚禁楚惠王,殺死令尹、司馬而自立為楚王。就目前的文獻(xiàn)與考古材料來(lái)看,資料最豐富而能復(fù)原出歷代縣公的當(dāng)屬楚申縣,平勢(shì)隆郎和徐少華曾先后對(duì)申公進(jìn)行排比考析。(78)申縣在今河南南陽(yáng)市區(qū)的古宛城,參見徐少華: 《春秋楚申公序列疏補(bǔ)》,《簡(jiǎn)帛文獻(xiàn)與早期儒家學(xué)說(shuō)探論》,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版,第211—224頁(yè)。另參[日] 平勢(shì)隆郎著,徐世虹譯: 《楚王和縣君》,劉俊文主編: 《日本中青年學(xué)者論中國(guó)史(上古秦漢卷)》,第212—245頁(yè)。其中有幾個(gè)問(wèn)題對(duì)于認(rèn)識(shí)楚縣公的身份屬性尤其重要。從申公的出身來(lái)看,十位申公中有兩位王子、三位公族(斗氏與屈氏)成員,一位為令尹彭仲爽之子。申公大多出身顯赫,其中較早的兩位申公斗班和斗克還是父子相繼。申公在楚國(guó)當(dāng)屬要職,擔(dān)任過(guò)楚申公的人也多先后出任楚國(guó)中央的其他重要職務(wù)。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申公即使在任申公一職時(shí)也常活動(dòng)于郢都,或是參與主導(dǎo)楚國(guó)中央的事務(wù)。比如《左傳》和《系年》所見的申公巫臣曾先后出使秦、鄭、齊,參與伐陳,并在多項(xiàng)楚王決策中提供建議。(79)申公巫臣楚、晉、吳三國(guó)之間的事跡先后見于《左傳》宣公十一年、成公七年、昭公二十八年。又見于清華簡(jiǎn)《系年》第十五、二十章,參考清華大學(xué)出土文獻(xiàn)研究與保護(hù)中心編,李學(xué)勤主編: 《清華大學(xué)藏戰(zhàn)國(guó)竹簡(jiǎn)(貳)》,第170—173、186—188頁(yè)。申公叔侯又稱“申侯”,《通志·氏族略五》“申叔氏”條記載“楚大夫申叔侯,食邑于申”(80)〔宋〕 鄭樵: 《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頁(yè)。。以申公而有食邑于申,正可見其多重身份屬性。《國(guó)語(yǔ)·楚語(yǔ)上》載:“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81)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zhǎng)云點(diǎn)校: 《國(guó)語(yǔ)集解》,第500頁(yè)。從語(yǔ)境看,此時(shí)申公子亹不在申地而居于楚郢都王廷,這樣的情況并不罕見,《左傳》莊公三十年亦載:“楚公子元?dú)w自伐鄭,而處王宮,斗射師諫,則執(zhí)而梏之。秋,申公斗班殺子元。”(82)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247頁(yè)。子元以楚文王之弟的身份時(shí)任楚令尹,因與斗氏家族有矛盾而被申公斗班所殺,整個(gè)事情的發(fā)生也是在“王宮”。以上種種事例,均可見申公不似后世的“地方官員”而具有明顯的中央屬性。一般認(rèn)為,楚文王任命曾為申人的彭仲爽之子彭宇為初代申縣縣公,河南南陽(yáng)城區(qū)曾先后出土過(guò)多批彭氏家族的墓地和青銅器,其中就包括彭宇和彭無(wú)所墓,據(jù)其墓葬年代與銘文內(nèi)容揭示,彭氏家族墓地在申縣附近的年代跨度至少在150年以上。(83)徐少華: 《彭器、彭國(guó)與楚彭氏考論》,收入“中研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編: 《古文字與古代史》第2輯,臺(tái)北“中研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2009年印行,第279—302頁(yè)。相關(guān)考古資料可參見董全生、李長(zhǎng)周: 《南陽(yáng)市物資城一號(hào)墓及其相關(guān)問(wèn)題》,《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南陽(yáng)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南陽(yáng)春秋楚彭射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文物》2011年第3期。這表明在申公多次更換改任之后,曾任申公的彭氏家族成員及其后人仍長(zhǎng)期居于申地,并且其墓葬的等級(jí)規(guī)格都未見衰減,其政治地位與經(jīng)濟(jì)實(shí)力應(yīng)受到當(dāng)?shù)胤庖氐谋U稀I昕h縣公的這種“在地化”特征與縣公的“中央化”屬性展現(xiàn)了先秦時(shí)期縣公身份的一體之兩面。
結(jié) 語(yǔ)
強(qiáng)調(diào)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楚縣公的多重身份屬性,不是為了要混同封君與縣公,打破封建與郡縣二元認(rèn)知框架,而是要突出楚縣公所具有的不同于秦漢以后“地方行政長(zhǎng)官”而具有的爵稱性身份、封邑主性質(zhì)、中央性地位和在地化傾向。此前的研究可能過(guò)多強(qiáng)調(diào)和依賴現(xiàn)有理論框架,而局限于君、公、尹、大夫等在名義上的區(qū)分而輕忽對(duì)其實(shí)相的考察。本文的探討只是對(duì)這一設(shè)想的初步嘗試,還存在諸多粗疏之處。未來(lái)的研究應(yīng)更多集中在對(duì)縣公個(gè)案的聚焦分析,并考察長(zhǎng)時(shí)段內(nèi)縣公性質(zhì)的變化,同時(shí)充分注意游離在理論框架之外的歷史細(xì)節(jié)的復(fù)雜性和豐富性,從而對(duì)縣制在秦漢之前的發(fā)展歷程有更清晰和具象化的認(rèn)識(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