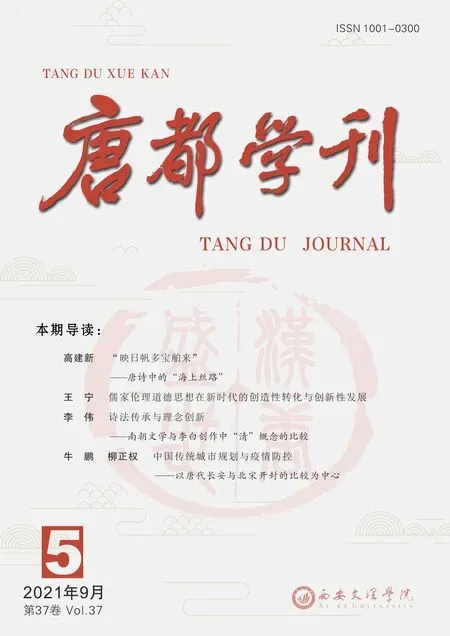朝鮮朝仁祖至景宗時期宗唐詩風論析
——以士大夫詩人群、委巷詩人群為中心
楊會敏
(宿遷學院 中文系,江蘇 宿遷 223800)
古代朝鮮近兩千年的漢詩風流變歷程如下:統一新羅(公元7世紀中葉至935年高句麗王朝建立)后期賓貢詩人群體詩學晚唐;高麗前半期(光宗至毅宗時期)宗尚初盛唐;高麗后期的“海左七賢”學宋詩;高麗末期的漢詩深受朱子性理學的影響;朝鮮朝前半期(朝鮮王朝建立至仁祖朝)的漢詩經歷了由朝鮮朝初期兼容并蓄、多元整合的詩風至以性理學為根底的宗宋詩風再到以白光勛、崔慶昌、李達為代表的宗唐詩風的振起。而仁祖朝(1623—1649)以后,金昌協、洪萬宗等朝鮮詩家在宗唐基礎上提倡漢詩應表現自我情感,凸顯自我,詩風為之一變。本文擬在探討仁祖至景宗時期漢詩風新變的背景因由,分析這一時期士大夫詩人群體、委巷詩人群體宗唐詩風的具體呈現、各自特質及其在朝鮮漢詩學發展史上的獨特價值與意義。
一、仁祖至景宗時期漢詩風新變背景原因分析
仁祖至景宗時期(1623—1724)漢詩風新變發端于對此前以崔慶昌、白光勛、李達為代表的宗唐詩人群存在情感缺乏、模擬過甚等弊端的反思與糾偏;此外,作為兩大漢詩創作主體之一的辭章派漸趨萎縮,道學派不斷壯大,從而導致了漢詩創作的衰退,而這一文學現象引發了金昌協、金得臣等詩評家的關注和思考,他們在前輩詩評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性情論、主意論、民族文學論等詩歌理論,詩歌風尚為之一變。除了朝鮮詩學發展的內部因由,中國明末至清代前期詩壇的宗唐風尚也是促成這一時期詩風轉向的重要外部因素。
(一)對仁祖朝前后宗唐詩派弊端之反思
宣祖(1568—1608年在位)年間自“三唐詩人”崔慶昌、白光勛及李達力倡宗唐后,大量的士大夫詩人、庶民詩人成為其響應者,再加之柳夢寅、李晬光、許筠等詩評家的推尊唐風的理論建構以及明代復古派詩集、詩論的東傳,最終使宗唐詩風代替宋詩風成為詩壇主流。這一詩壇風潮發展至仁祖(1623—1649年在位)至肅宗(1674—1720年在位)年間蔚為大觀。但隨著宗唐的各類詩人群體在創作實踐中出現的不同程度的模擬主義、形式主義等弊端,已偏離了糾正當時受性理學、江西詩派余弊及科試制度所導致的不良詩風之導向。對此,具有敏銳眼光的詩評家金昌協(1651—1708)指出宣祖朝為李朝漢詩由宗宋轉為宗唐的轉折點,但對宗唐詩歌的評價即“軌轍如一,音調相似,而天質不復存矣”“讀穆廟以后詩,其人殆不可見”[1]378,未免太絕對。雖然宣祖、光海君(1608—1623)、仁祖三朝受明代復古思潮影響最深,其時宗唐詩人的漢詩創作中程度不等地存在情感欠缺、過于重視格調形式、模擬過甚等弊端,但也不乏善于抒寫真性情、彰顯個性的作家,如生活在宣祖、光海君時期的許筠、車天輅、林悌等。許筠不僅主張詩歌要直率自然地表達詩人的性情之真,要“不相蹈襲,各成一家”[2],且其創作也不拾人牙慧、不做效顰之姿,均能抒寫性情,獨具特色。正因為此,其詩歌不僅在朝鮮詩壇獨步一時,也獲得中國明朝詩人的贊譽。車天輅詩歌以雄健奇壯之詩風見長,令明朝使臣朱之蕃(1548—1624)為之贊服:“朝鮮有車天輅者,文章奇壯”[3]2108,而林悌抒寫的誠摯的愛國情懷和內心的苦悶最引人注目。因此,金昌協所評不免偏執,但所論“詩道之衰”自宣祖始是準確的,盡管仍有許筠、車天輅、林悌等人以詩歌鳴于當世,但卓著者畢竟不可與此前同日而語。
(二)宣祖朝辭章派的萎縮與道學派的壯大
朝鮮朝漢詩自宣祖朝衰退,除了宗唐風尚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外,還應歸因于兩大漢詩創作主體之一的辭章派的萎縮,而與辭章派對立的道學派則不斷壯大。
雖然燕山君(1494—1506年在位)至明宗(1545—1567年在位)時期的四大士禍使道學派元氣大傷,但明宗末年辭章派實力衰頹,其一部分殘余勢力轉向道學派。繼明宗之后的宣祖時期道學派大獲全勝,由此掌握政權的道學派開始鎮壓不妥協的辭章派。而兩派的爭執焦點在其文學觀念的不同,辭章派專心辭章,而道學派雖也認為寫詩作文有必要,但更看重道學即性理學,斥詩文乃雕蟲小技。這種爭論由來已久,“己卯士禍”發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兩派文學觀的不可調和:“又光祖等,偏重道學,排斥辭章,每于經筵,論辭章之弊,至謂人主不可作詩,亦不可令臣下制進。故先進文學之士,多不好之。于是有道學派與辭章派之反目焉”[4]。上文中的趙光祖(1482—1519)即當時道學派的核心人物。在野黨的道學派除了抨擊辭章派獨掌權力、濫用職權外,還批判其不重經史之學問而只專注辭章,但道學派的排斥還未能從根本上削弱還處于政權中心的勛舊派的實力。而自宣祖登基之后,當政的道學派便開始鎮壓辭章派。三唐詩人、林悌等非辭章派的詩人大都仕途坎坷、命運多舛,但偏偏是處于逆境中的被辭章派打壓的這些詩人詩才卓越。在光海君時代,甚至出現了因詩禍而喪命的辭章派文人,著名者如權韠(1569—1612)、許筠(1569—1618)。被許多評論家譽為朝鮮中期最著名的詩人權韠天性憤世嫉俗,一生未曾應舉,志在放浪湖海,敢于諷刺時政得失、痛陳權門弊害,最終因寫詩譏諷光海君之外戚專橫的宮柳詩而罹難。他在遇害前將自己的詩稿打包托付給甥侄沈某保存,并在包袱背上題詩一首,名為《絕筆》:“平生喜作俳諧句,惹起人間萬口喧。從此括囊聊卒歲,向來宣圣欲無言”[5]。詩人首先對其離經叛道的一生作了總結,后兩句稍露出反悔之意,但為時已晚,三日后即被殺害。目睹朋友權韠以詩肇事,許筠發誓不再作詩,且試圖以武裝政變反對道學派的壓迫,卻最終以叛徒的罪名被處死。此外,還有因派別之爭而死于詩禍的道學派文人,如兼政治家與文學家于一身的柳夢寅(1559—1623)在光海君時代屬于北人,仁祖反正之后掌權的西人強迫他改事新君,深受儒家綱常濡染的柳夢寅堅持一臣不事二君,寫《題寶蓋山寺壁》一詩以表心志:“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房。傍人勸之嫁,善男顏如槿。貫誦女史詩,稍知任姒訓。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6],他最終也因這首詩而為舊主殉節。
宣祖年間,道學派內部黨派之爭愈演愈烈,此后近二百年,仍然錯綜復雜。道學派對外的文化高壓政策和內部的黨爭使不少無辜的辭章派文人和士林中人慘遭殺害,這不可能不對幸存的文人產生震懾。因此,仁祖至景宗時期,辭章派只好選擇屏聲靜息,辭章派的萎縮對漢詩產生了不小的負面影響,甚至使得朝鮮漢文學一度出現文盛于詩的傾向,如被譽為朝鮮朝文章巨擘的“月象溪澤四大家”即李廷龜(1564—1635)、申欽(1566—1628)、張維(1587—1638)、李植(1584—1647)就出現在這一時期,且這四人屬于執政黨道學派文人群體,代表當時文壇的主流。而這一時期的詩人有許穆、鄭斗卿、尹鑴、南龍翼、金昌協、金昌翕、申維翰、金得臣、崔成大、洪世泰等,辭章派詩人寥寥無幾。直到英祖、正祖以后,隨著黨爭的緩和、性理學統治的松動以及以實學派為主的新的思想理念的興起為道學派以外的文人創造了相對寬松的環境,由此才出現多元化的詩風。
仁祖至景宗時期漢詩創作的衰退引起了當時不少詩評家的關注和思考,除了上文提及的金昌協外,金得臣、洪世泰等在前輩詩評家許筠、李晬光、柳夢寅等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性情論、主意論、民族文學論等詩歌理論,這種迥異于主流文學觀的詩學轉向成為一時之風尚,而詩風也隨之產生新變。
(三)中國明清詩壇宗唐風尚的影響
明代文壇先后出現的“前七子”“后七子”皆倡導唐詩風。而明末清初詩壇,以陳子龍為首的云間派的復古宗唐的詩歌主張與詩歌創作占據主導地位,且對清初詩壇影響甚大。清初詩人吳偉業、朱彝尊、施潤章等人,皆受到云間派宗唐風的影響。順治初年,錢謙益、馮舒、馮班等人倡導取法中晚唐詩,使得對唐詩的學習更為全面,且明末開始流行的宗唐復古詩論仍在全國各地盛行不衰。可見,有清一代,直至康熙前期,宗唐仍為詩學主流。“面對中國明清易代、詩風更替的政治和文學格局,朝鮮詩家受國內北學派思想的影響,也開始有意識地學習清詩”[7],施潤章、錢謙益等清前期的詩人的宗唐風格受到了朝鮮詩家的關注與學習。如徐宗泰(1652—1719)對錢謙益詩風學杜的肯定與贊揚:“然觸事詠物、感奮時事是杜老之遺韻,其忠忱則至矣。”[8]到了康熙中后期,康熙帝力倡唐詩,在其周圍的以毛奇齡、朱彝尊為代表的執政大臣詩人群也倡導宗唐。李德懋在其《清脾錄·毛西河》中稱贊“毛西河奇齡全集,詩文高華逸宕”[9],并摘了若干詩句作為例證。而歷經了順康兩朝的另一詩壇大家王士禛以宗唐為主,兼宗宋元的詩學主張,尤其是其神韻思想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乾隆朝,在異域朝鮮朝詩壇備受推崇,被譽為“海內詩宗”。
二、仁祖至景宗時期宗唐詩風的具體呈現
仁祖至景宗時宗唐詩風的具體呈現主要在于以金昌協、金得臣、洪世泰等為代表的士大夫詩人群、委巷詩人群以唐詩為宗、注重“性情之真”與“天機之發”的詩學觀。與之相應,這一時期士大夫詩人群的“性情之真”說剝離了朱熹“心統性情”說的道德與理性因素,尤為強調自我與真情實感的抒發;而一生貧賤的委巷詩人群則有意在漢詩中凸顯自己不為名利所累的豁達,形成不事雕琢、自然天成的詩風。
(一)仁祖至景宗時期宗唐詩論的興起
金昌協所極力倡導的“詩緣情”“天機論”不僅在當時的士大夫詩人群、樂府詩人群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在繼之而起的實學派詩人群及發展壯大的委巷詩人群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響。特別是以唐詩為宗、注重“性情之真”與“天機之發”的詩學宗尚使這一時期的漢詩風也隨之產生新變。
針對朱子學載道的文學觀及宗唐復古中的模擬、偏重于形式等弊端,金昌協、金得臣、金昌翕、洪世泰等提出詩歌本于性情,且主張通過“天機”“靈氣”“應感”等靈感抒發性情。這些詩論源于中國,“詩緣情”自屈原提出“發憤以抒情”[10]到陸機的“詩緣情而綺靡”[11]已基本定型,且逐漸取代了“言志說”成為中國詩學主導性的命題;而“天機論”中“天機”一詞雖最早出現在《莊子·大宗師》,但不具備藝術理論意義。將“天機”含義提升至文藝創作理論層面的是陸機,他在《文賦》中不僅生動直觀地描述了靈感現象,且用詩化的語言闡明了藝術創作中靈感思維的突發性、偶然性、創造性等重要特征。“詩緣情”“天機論”傳入朝鮮后,為高麗至朝鮮朝諸多詩話家所接受,如崔滋、徐居正、許筠、柳夢寅、李晬光、李宜顯、南公轍等皆認為詩本于性情、發于性情,孝宗(1649—1659年在位)至景宗時期,“詩緣情”說被進一步深化和突顯;而“天機論”至16世紀初葉才為成俔(1439—1504)最先應用于文學領域,經由許筠、張維等人的積極推進,至朝鮮朝后半期金昌協、洪世泰等人的闡發而被賦予豐富的內涵。
總體來看,“詩緣情”和“天機論”通常被這一時期的詩論家相提并論,且呈現水乳交融之勢,金昌協即為這方面的代表,其在《外篇》中言道:“詩者,性情之發而天機之動也。唐人詩,有得于此。故無論初、盛、中、晚,大抵皆近自然”[1]375。他將性情、天機歸于“自然”,認為“性情之發”“天機之動”的詩歌才具有“神情興會”,才為自然之作。比之于宋詩,金昌協認為唐詩更勝一籌,因為“唐人之詩,主于性情興寄,而不事故實議論”[1]375,主張學習唐詩,但不應模仿而貴在創新,不能只求“聲音氣調”之形似,而重在學習唐詩吟詠性情的精髓。當然,他認為宋詩雖以“議論”為“詩家大病”,但仍有表現性情之真的感人之作。金昌協對詩歌如何表現“性情之真”或“天機之發”也有獨到的理解:“詩歌之道,與文章異者。正以其多道虛景,多道閑事。而古人之妙,卻多在此。蓋雖曰虛景閑事,而天機活潑之妙。吾人性情之真,實寓于其間。”[12]539金昌協認為詩歌本于與道德無關的性情之真,將性情從傳統的道德束縛中解放出來,肯定表現“虛景閑事”的詩歌才具有活潑的天機和真實的性情。這一詩論不僅有力地批駁了詩歌載道論,也為詩人進行個性化的創作鳴鑼開道。
金得臣(1604—1684)將“天機論”上升到詩歌本質的高度,認為詩歌乃“得于天機”[3]2115的產物,由“自運造化”[3]2115促成。“得于天機”意即詩歌創作源于靈感,通過靈感表現天機,進而創造感人、入神的境界。如他評價前輩詩人鄭士龍(字湖陰)的“江聲忽厲月孤懸”一句“寫景逼真”“對景益高”[3]2106,并將之歸因于詩人同江聲、孤月感性交融,產生共鳴,才創作出逼真入神的藝術境界。與天機論相呼應,金得臣欣賞渾然天成的詩風,他評洪萬宗詩為“天然超絕,得唐人景趣”[3]2118。可見,金得臣認為唐詩得于天機,富有意趣。
金昌協的詩歌觀還為同一時期以洪世泰為首的委巷詩人群的“天機論”提供了理論支撐,由此,也使委巷詩人與士大夫文人一起活躍于文壇。委巷詩人的天機論,除了重視詩歌情感的自然流露外,重在表明詩歌創作與詩人身份的貴賤無關,身份卑賤的人可能創作出更具天機的詩歌。
洪世泰(1653—1725)的“天機論”極力彰顯委巷詩人的存在價值:“夫人得天地之中以生,而其情之感而發于言者為詩,則無貴賤一也。”[13]473他主張詩歌乃情之發,即人的情感通過言語表達成詩,由于人的情感無貴賤之分,因此,詩歌本身也不會因為詩人身份的高低貴賤而產生差別。否則,這些里巷歌謠之作也不會被圣人以追求平等的意識而收錄到《詩經》中。洪世泰以平等為思想武器為委巷詩人爭取詩歌創作權,而且他進一步指出委巷詩人雖與士大夫詩人有身份差別,但同樣能創作出具有天機的詩歌:“蓋自薦紳大夫,一倡于上。而草茅衣褐之士,鼓舞于下,作為歌詩以自鳴”[13]473。文中的“草茅衣褐之士”即委巷詩人,他們雖然“為學不博,取資不遠”,但所抒寫的情景“風調近唐”[13]473,且皆為天機的自然流露。無獨有偶,李天輔極力贊同洪世泰的“天機論”,他在《浣巖集序》中言:“夫詩者,天機也。天機之寓于人,未嘗擇其地,而澹于物累者能得之。委巷之士惟其窮而賤焉,故世所謂功名榮利,無所撓其外而汩其中,易乎全其天,而于所業嗜而且專,其勢然也”[14]240。洪世泰強調詩歌創作應出于率真的性情,音韻自然流暢,有“神動天隨之妙”[13]305,如果故作奇巧反而有滯澀之感。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工詩之士,多出于山林”[13]472的觀點,他贊同莊子“嗜欲深者,其天機淺”[13]472的觀點,認為如果不能擺脫名利的羈絆,則不能作出好詩。以此推論,身份微賤者因為“嗜欲”少、天機深,比之于士大夫階層的詩人,更能寫出自然天成的詩歌。
(二)仁祖至景宗時期士大夫詩人群的宗唐詩風
仁祖至景宗時期(1623—1724),金昌協、金得臣、南龍翼、金昌翕等士大夫詩人群的漢詩創作踐行了其以唐詩為宗、注重“性情之真”與“天機之發”的詩學觀,其詩重視真情抒發,清新自然、含蓄蘊藉。
以金昌協為代表的仁祖至景宗時期宗唐士大夫詩人群,他們所倡導的“性情之真”說剝離了朱熹“心統性情”[15]說中的道德與理性因素,這也從本質上決定了其不同于這一時期其他深受朱子性情說影響的宗宋或唐宋兼宗的士大夫詩人群。如對唐詩稱頌有加卻又不廢宋詩的李宜顯(1669—1745)主張“詩以道性情”[16]453,“宋人雖自出機軸,亦各不失其性情,猶有真意之洋溢者”[16]429。但他推崇所抒發性情應恪守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觀,“皆有所補于世教”[16]453。只不過他所理解的性情之正不再局限于宋代朱熹、江西詩派領袖黃庭堅所謂的合乎三綱五常的天理的雅正,而將“雖多荒怪不經之語,而忠憤慷慨”的屈宋詞賦也界定為“性情之正”[16]447,這與清初提倡宋詩的黃宗羲所謂的慷慨激昂也屬于儒家的中和之美的詩教觀如出一轍,本質上別無二致。另有“性理之正學,經濟之大猷,煥乎斯文之宗門”[17]的李瀷(1681—1763)及“身傳正學,道接真源,嶷然為儒門之宗”[18]的尹東洙(1681—1763),二者陶寫性情皆以深厚的朱子性理學為根底。而金得臣、南龍翼、金昌協、金萬重等宗唐詩人群的性情之真與朱熹抑制性情與人欲的雅正大異其趣,不囿于道德、世教的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即為其詩歌創作的主題。
與其主張的“性情之真”相呼應,這一時期宗唐詩人群“天機之發”的詩學觀既是詩歌創作源于靈感的本質論,又是不加藻飾、獨創出奇、自然天成的風格論,這對此前宗唐詩派、江西詩派等出現的形式主義弊端具有一定的糾偏作用。唐宋兼宗的李宜顯在《陶谷集》中曾稱贊“唐以辭采為尚,而終和且平,絕無浮慢之態。所以去古最近,末流稍趨于下”[16]403,批駁“李、何諸子起而力振之,其意非不美矣,摹擬之甚,殆同優人假面,無復天真之可見”[16]403,李宜顯指出的前后七子復古導致的模擬、“無復天真”的弊病,其實,前后七子進行了反思與修正,如前七子領袖李夢陽晚年提出了真詩說、后七子核心人物王世貞提出真我說,與仁祖至景宗時期宗唐士大夫詩人群的天機論不謀而合,也表明他們對明代前后七子的接受日趨理性與深刻。
金得臣以唐韻、唐格、唐風、唐意趣品評詩歌,其漢詩創作也尚唐音,這一點得到詩論家的一致認同。如洪萬宗評價金得臣《木川道中》等詩“極逼唐家”[19],又如任埅曾贊曰:“金柏谷得臣平生工詩,雕琢肝腎,一字千錬,必欲工絕,其賈島之流乎!如‘落日下平沙,宿禽投遠樹。歸人欲騎驢,更怯前山雨。夕照轉江沙,秋聲生野樹。牧童叱犢歸,衣濕前山雨’等作,何讓唐人?”[20]與明代前后七子詩宗初盛唐不同,金得臣作詩取法晚唐苦吟派。樸世堂在《柏谷集序》中也曾指出金得臣繼承晚唐賈島等苦吟派作風,為了取境真實和窮形盡相,忘乎所以地“于境會象態”[21],以景抒情,感人至深。金得臣代表作有:《田家》:“籬弊翁嗔狗,呼童早閉門。昨夜雪中跡,分明虎過村。”[22]27還有《龍湖》:“古木寒煙里,秋山白雨邊。暮江風浪起,漁子急回船。”[22]19前一首語言質樸,情境淡泊、逼真。后一首也無雕飾,自然天成,韻味無窮,被朝鮮朝孝宗(1649—1659年在位)稱為“雖入唐音無愧”[22]235。
南龍翼(1628—1692)崇尚唐詩,且對初盛晚唐詩不分軒輊,其曾在《詩評·唐詩》中言其詩學之淵源:“余思學詩之法,李、杜絕高不可學。惟當多讀吟誦,慕其調響,思其氣力。五律則學王摩詰,七律則學劉長卿,五絕則學崔國輔,七絕則學李商隱,五言則學韋蘇州,七古則學岑嘉州”[23]。南龍翼《壺谷集》其主題內容大致可分為寫景詠物、抒寫閑適之情、表達忠君愛國思想等。不少詩作具有真率流暢、自然天成的藝術風格。如其五律《過江西寺》:“為訪江西寺,仍經水上村。草深分鷺色,沙軟落潮痕。遠樹重重合,輕霞點點昏。清晨鼓棹去,微月在山門。”[24]詩人以景抒情、不露斧痕,所寫之景明麗且寧靜寥廓,小草、白鷺、沙灘、遠樹、軟霞、微月一起營造了如夢幻般境界,令人感覺美妙無窮。
金昌協除了主張“詩緣情”“天機論”等詩歌理論,還極力提倡進行一場“真詩”運動,在仁旺山和北岳山之間的壯洞成立了“白岳詩壇”組織,其成員有金昌翕、李秉淵、金時敏、俞拓基、洪世泰等人。如其《又賦》詩云:“蒹葭岸岸露華盈,篷屋秋風一夜生。臥溯清江三十里,月明柔櫓夢中聲。”[12]358這首詩寫景如畫,物我交融,筆調閑逸雅致、天然渾成。
金昌協的胞弟金昌翕(1653—1722)尤為崇尚盛唐詩人,金亮行為其所作《行狀》云:“其詩格法雅健,一洗程式之陋。……自三百篇楚騷古樂府,以及乎盛唐諸家,精治熟習,折衷模范,用成一家之則”[25]295。金昌翕擅長山水詩的創作,丁若鏞曾贊譽道:“縱筆千萬言,煙霞落紙面”[26]。如《訪俗離山》一詩:“江南游子不知還,古寺秋風仗履間。笑別雞龍余興在,馬前猶有俗離山。”[25]196詩人將宜人的秋色與舒暢歡快的心情融為一體,心曠神怡之感盡現。金昌翕在41歲時移居到檗溪,從此開始了從山水詩到描寫山村景物、風土人情的題材的轉變,又如《葛驛雜詠(其一)》:“尋常飯后出荊扉,輒有相隨粉蝶飛。穿過麻田迤麥壟,草花芒刺易罥衣”[25]295。該詩則以暢達的語言敘述了飯后獨步信游的田園春光,意境優美,有超然自得之妙。
(三)仁祖至景宗時期委巷詩人群的宗唐詩風
這一時期,委巷詩人的卓越代表洪世泰(1653—1725)以唐詩為宗,在《柳下集序·自序》中稱其詩“斟酌古今,激揚清濁,渾融變化,合為一格,不出于唐杜之間”[13]305,而其得意門生鄭來僑為洪世泰所作《滄浪洪公墓志銘》,贊其“而于詩家用工尤專,神精所到,潛透妙悟,其遇境摛藻,天機流出,音調氣格,骎骎乎唐正宗諸家”[13]560。其《水村秋興》一詩云:
寒郊莽蒼日徘徊,九月西風吹水來。客里偏驚授衣節,愁時獨立望鄉臺。
江天鴻雁不知數,野徑菊花空自開。三角登高十年事,白云峰色滿深杯。[13]314
作者有意擬杜甫遷居夔州后所作《秋興八首》,以秋的蒼涼與凄清抒寫漂泊異鄉、懷才不遇的抑悒和憂傷,意境渾然一體、深遠蘊藉。洪世泰一生貧寒,愁懷滿腹,特別是“老而益貧,無以自存”[13]560,極易與晚年貧病交加、憂世傷時的杜甫產生情感共鳴,正如鄭來僑在《滄浪洪公墓志銘》中所言:“乃以公余,得放浪山海間,其詩益雄放橫逸,人以為得遠游跌宕之助,類老杜之夔后,公亦以為知言”[13]560。
而詩學洪世泰的鄭來僑(1681—1757)雖“而甚貧窶,家徒四壁”[14]240“亦不免窮厄其身”[27]573,仍努力踐行乃師的“天機論”,正如李天輔《浣巖集序》)所言:“余以為潤卿之詩與文,一出于天機而已”[14]240,洪鳳漢在《浣巖集跋》中甚至贊其曰:“自奮于孤寒之中,大肆于詩文之工,饑而其氣也不詘,老而其操也冞堅,所成就殆與洪滄浪相伯仲,其賢則過之”[27]573。且看其《打稻歌,上竹西相公》一詩:
西風瑟瑟入深谷,村西村南稻粱熟。韋巖相公命駕來,葛巾野服東山麓。
黃菊籬邊正爛熳,美酒甕閑亦堪漉。漉出美酒采黃花,陶陶不知秋日斜。
相公高坐顏半酡,老農當席遂高歌。大兒能耕女能織,十匹粗布百畝禾。
終歲衣食自有余,不愿駟馬與高車。高車從古多傾覆,愿公歸來與我同此樂。[27]491
詩人描繪出一派詩情畫意的豐收場景,農民與自然息息相通的融洽、詩人遠離仕宦的自得其樂之情躍然紙上,絕少藻飾的天機之美流露筆端。
另有崔奇男、金孝一、南應琛、崔大立、鄭楠壽、鄭禮南賦詩唱吟,且合編了第一部委巷詩人集《六家雜詠》,高時彥、蔡彭胤合編了《昭代風謠》,編纂詩集的主要目的在于凸顯這些貧寒之士能不為名利物質所累,創作自然天成之詩,如高時彥在《書〈昭代風謠〉卷首》中,說明了編撰此書的主要動機。他說:“與《東文選》相表里,一代風謠彬可賞。貴賤分歧是人為,天假善鳴同一響。”[28]
綜上所述,朝鮮朝宣祖時期,由于宗唐風尚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以及兩大漢詩創作主體之一的辭章派的萎縮,使得朝鮮漢文學一度出現文盛于詩的傾向。直到朝鮮朝英祖、正祖以后,隨著黨爭的緩和、性理學統治的松動,以及以實學派為主的新的思想理念的興起發展為道學派以外的文人創造了相對寬松的環境,由此才出現多元化的詩風、文風。這一時期不少詩評家關注和思考詩歌創作的衰退,在前輩詩評家許筠、李晬光、柳夢寅等人基礎上,加之中國明清詩壇宗唐風尚的影響,金昌協、洪萬宗、金得臣、南龍翼、金昌翕等士大夫詩人群進一步深化了性情論、主意論、民族文學論等詩歌理論,這一以唐詩為宗、注重“性情之真”與“天機之發”的詩學宗尚使這一時期的漢詩風也隨之產生新變。仁祖至景宗時期宗唐詩風的具體呈現主要在于以金昌協、洪世泰等為代表的士大夫詩人群、委巷詩人群以唐詩為宗、注重“性情之真”與“天機之發”的詩學觀。與之相應,這一時期士大夫詩人群的“性情之真”說剝離了朱熹“心統性情”說的道德與理性因素,尤為強調自我與真情實感的抒發;而一生貧賤的委巷詩人群則有意在漢詩中凸顯自己不為名利所累的豁達,且形成不事雕琢、自然天成的詩風。這一時期士大夫詩人群、委巷詩人群的詩學風尚一定程度上對繼之而起的實學派詩人群的詩學觀及漢詩宗尚產生了積極影響,并由此引領和決定了朝鮮朝后半期漢詩發展的基本走向和主要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