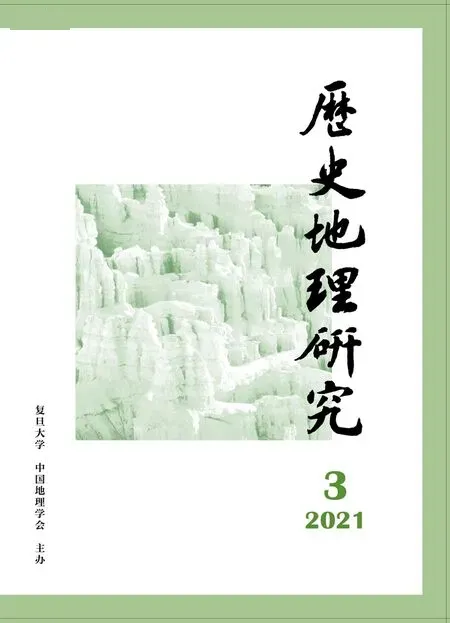感想三則
唐曉峰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北京 100871)
一、我們很幸運,趕上了三位老先生引領的學術盛世
這兩年歷史地理學屆要有好幾項紀念活動,包括紀念《歷史地理》創刊40年。《歷史地理》創刊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時我還在讀研究生。侯仁之先生問我要不要為新刊寫點東西,并提及我曾讀過《禹貢》半月刊的事情。于是我從一個初學者的角度寫了一篇紀念短文。我最早是20世紀70年代中讀到《禹貢》半月刊的,那時在內蒙古大學,不論是時代面貌還是刊文風格,都讓我感到與那個長袍馬褂的時代相距很遠。但后來的發展證明,禹貢學會所樹立的是一種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東西,在新的時代,其豈止是復興。由于注入新的思想,開啟新的實踐,歷史地理學實在是發揚光大了。
我的經歷讓我感覺20世紀70—80年代是中國歷史地理學迅速走向興盛的時期。那時,作為學科的三位領軍人物,譚其驤、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老先生,在學術上依然保持活躍,這在其他學科領域是罕見的。三位老先生都在研究的第一線,每個人從不同的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學科走向興盛的基礎特征。關于三位老先生,學界談得相當充分了,這里不必贅述,只談一點個人感想。
概括說來,侯仁之先生推動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自覺,他帶動了整個歷史地理學界的理論意識。理論意識的增強,有利于提升學科發現問題的能力與解釋問題的能力。現在,討論歷史地理學理論已經成為學界常態。這是一門學科成熟發達的重要標志。
譚先生協助顧頡剛先生創辦禹貢學會等的開拓作用和研究中的多方成就毋須重復。只想補充一點,這一點似乎被忽略了,卻是很重要的。在中國,研究任何歷史類問題,都有一個史學標準。中國史學界有強大的學術規范傳統,要求極高。歷史地理學從禹貢學會開始,是由一批最優秀的史學家舉旗,三位老先生均出身于此,尤其以譚其驤先生為中堅。在這樣的歷史地理學家面前,人們沒有任何懷疑。這是歷史地理學在中國立身的一個關鍵之處,也是他們帶領歷史地理研究與地理學成功融合的重要基礎。
史先生的獨特貢獻之一,如辛德勇所說,是全面的中國歷史地理體系構建,從早年協助顧頡剛先生編寫《中國疆域沿革史》開始,后來拓展為全面的歷史地理通論體系構建。史先生涉及的歷史地理問題,面最寬。史先生在浩瀚的歷史文獻中,以地理意識為主旨,左右逢源,揭示出許多意味深長的問題。他的《河山集》有深遠的社會影響。作家張承志說過:“我要是早讀到這本書,就考史先生的研究生了。”
三位先生引領學科走向興盛的另一個體現,是招收研究生。在歷史地理學界,除了三位老先生,原本還有一些中年學者,但人數不多。1978年起,三位先生開始招研究生,歷史地理學研究生的數量逐年增加,這是前所未有的。此后,他們本人的學術活力與年輕一代的朝氣交錯銜接,顯得生氣勃勃。另外,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生還有一項特殊的地位,即新中國最早的文科博士,這反映了歷史地理學當時進展的速度。有前輩先生的坐鎮,研究生們也充滿信心。
20世紀70—80年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是引人注目的。1979年,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的活動恢復,在西安召開大會,后來又創辦了《歷史地理》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兩份刊物,其鮮明的學科名稱令人耳目一新。一些重大的研究計劃在新形勢下起步,中國古都學會成立,各類工作性會議頻頻召開,優秀的研究生論文接連問世,等等。
20世紀80年代,我有幸參加了一些重要活動,都令我很難忘。例如,1983年的夏天列席了周振鶴和葛劍雄兩位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答辯會上,除了譚其驤先生,還有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陳橋驛先生、楊向奎先生等。答辯會場很簡單,只有一塊小黑板。但這是新中國首次文科博士論文答辯會,毫無疑問要在學術史上記下一筆。我還拍了一些現場照片。答辯結束后,一部分人前往莫干山開會,這又是一次重大學術活動。此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的第二次編委會,三位老先生全部出席。這是一次實實在在、深入討論圖集具體內容的會議,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會議參加者包括多個單位的學者專家,如高德、鄒逸麟、鄧銳齡、陳可畏、張海鵬、劉宗弼等,他們在當時還都算年輕一輩,我當然是更年輕的一輩了。當時三位老先生以及大家的討論,涉及每個圖組中各類問題的處理辦法。如果有會議記錄材料保存下來,那將是一份很珍貴的學術史資料。
順便說一下那次會議后一次難忘的旅行。莫干山會議之后,一些人跟隨譚先生乘車去浙江黎里古鎮,參觀了柳亞子故居。大家一路談笑,譚先生十分輕松。譚先生與柳亞子有親戚關系,譚先生為故居題了字。我還保存著譚先生當時題字的照片,以及在故居大門前的留影。回北京后,我精選了一張照片寄給譚先生,時值正式版《中國歷史地圖集》發行,譚先生贈給我一冊簽名本,彌足珍貴。
二、進一步認識到歷史地理學與社會發展的關聯性
地理學的發展史,包括內史和外史兩個方面,其中外史就是社會環境對于這門學科的推動。地理學是受外力推動最為明顯的學科之一,這是它的一個本質屬性。我們常說“經世致用”,這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地理學對外部社會事務的主動參與,另一方面是社會對地理學的推動。所謂推動,即外部社會向地理學的“提問”,需要地理學回答一些問題。地理學的“經世致用”之道,在本質上,就是和社會的深刻互動。從地理學史來看,一個社會在經歷一個時代后,會積累一些問題,每個學科都會選擇自己能夠回答的部分卷入思考。地理學也一樣,很多問題是其他學科回答不了的,地理學科也就因此不斷增值。一個敏感的地理學家,應該能察覺或不回避社會現實向地理學的提問。我覺得,三位老先生都具備這種敏感性,他們選擇的研究議題,越來越多地具有社會關聯性。
譚先生以治學嚴謹著稱,早時影響力似乎多在學界內部,20世紀70—80年代,他的社會影響迅速擴大。那時,譚先生在一些學術會議上的講話,經常通過油印本或其他方式傳出,為學界和社會所知,因為他講的內容不僅僅是學術,也常常涉及當時社會關注的熱點。比如邊疆問題、臺灣問題等,譚先生均堅持按照學術標準予以解釋。譚先生的講話,往往能廓清社會上流行的認識上的錯亂,因此十分引人關注。特別是他的《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一文,原是受翁獨健先生之邀做的一篇演講。這篇文章提出的兩個原則得到了學界的公認。第一,用清朝完成統一以后、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作為歷史時期的中國范圍;第二,在這一范圍之內所建立的古代政權都可以被認為是中國史中的政權,都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譚先生提出的這些標準,既合理又易于操作,推進了當時社會上一項重要的思想定位。隨著譚先生本人影響力的擴大,歷史地理學在社會上更加廣為人知。
侯仁之先生的社會關懷更主動一些。最突出的方面是關于大地之上文化遺產的研究保護、繼承發展問題,這是社會日益現代化過程中必然要解決好的大事,歷史地理學不可能繞開這個時代提問。侯先生的這一實踐是從城市歷史地理研究開始的。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他對一系列歷史名城遺址進行實地考察和研究,做歷史地理過程復原與價值判定,逐步建立了城市歷史地理研究與遺產保護一體化的研究范式。正是因為有著對文化遺產問題深切的關注與習慣性的敏感,1984年,侯仁之訪問美國期間了解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一事,回國后遂聯合其他幾位全國政協委員就此事提交了委員議案,我國于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遺產公約》。這項提案被評為新中國成立70年來最重要的政協委員提案之一。現在,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觀念已經深入人心。
70年代初,出任中國大西北戰區的司令員皮定均將軍向史念海先生提問:“假定現在就要進行一場戰爭,我作為司令員,進入陣地,部隊部署,糧草運輸,作戰計劃,大致都已就緒,我要再聽取一下,以前在這個地區曾經發生過什么戰爭?戰爭的兩方各是由什么地方進軍的?又是分別由哪些道路退卻的?糧秣是怎樣運輸的?戰地的用水又是怎樣取得的?其中獲勝者是怎樣取得勝利的?而敗北者又是怎樣招致失敗的?”史先生帶著將軍的提問去往一處處古戰場。在這些地方,雖然考察的是古代戰事,但所有的問題都具有現實性。
三、感到跨學科研究、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歷史地理學有很寬泛的視野,這不僅僅是就其對象的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來說,也是就它的問題類型來說。在這個學術領域中,可以有十分豐富的選項。說到選項,“問題意識”越來越重要,談的人也越來越多。前面提到,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很吸引人,因為史先生很善于從歷史事件中提取地理問題,他是這方面的大家。
現在人們更加強調問題意識,問題意識與概念意識不同,它更加從實際事務出發,因為從實際出發,研究的綜合性就要加強,涉及的學科就會增多。現在開歷史地理學術會議,內容的多樣性越來越強,正是這個趨勢的反映。對于地理學研究來說,引入相關學科是好事。科學史家已經指出,當今,從科學(學術)發展全局來看,已經進入了一個“橫向”大串聯的時代。當代所產生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孤單的老式學科可以回答的,所以,從問題的研究實踐出發,而不是從學科的傳統領地觀念出發,是當下的特點。地理學要處理異質事物的關系,更需要跨學科,對于古代的地理問題也是一樣。
在歷史地理學領域,侯仁之先生很早便主張多學科共同開展研究。跨學科是指發展,不是指本原。侯先生晚年曾大力推進環境考古研究的開展,他早在1973年就已依據英文文獻采用了“環境考古”一詞,并在1987年推動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古跡保護委員會環境考古分委員會”,這是典型的跨學科發展。我們一般說,侯先生在城市歷史地理、沙漠歷史地理兩個方面做出開創性貢獻,其實,環境考古學的創立,應該算是第三項。雖然沙漠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已經含有環境考古的特色,但正式確立的環境考古學,內涵要更寬闊,指導思想也更明確,更成熟。侯先生說:“史前環境考古是歷史地理學必不可少的延伸。”中國考古學會環境考古專業委員會會長莫多聞教授也這樣認為。歷史地理學展開跨學科研究的機會很多,當然,要這樣做,需要更寬的學術視野和綜合性的問題意識。
再有一點,地理學不是一個意識形態中立,或者說思想單純的學問,它的存在是一種社會存在、時代存在。我們在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的時候,也要關注一下這門知識(學問)在古代社會中存在的狀況和特點。這就涉及地理思想史的問題,也有人稱作“地理知識論”。古人不僅僅要“察”地理,還講“銳思”地理、“制作”地理,顯然含有思想、制度的東西。關于制度性的問題,譚其驤先生引領的行政區劃史研究是我們的經典,當然,對其他方面的制度他也有很好的研究(比如城市制度、人口制度、驛傳制度、邊疆管理制度等)。在王朝時代,地理性制度在多個方面都有建樹,關聯到大地域王朝的一種本質,值得繼續深入研究。歷史中的地理性制度,是文明特征,也是文化特征,必然具有意識形態屬性,所以也要開展地理學思想史的研究。我國古代地理學思想是中華文明傳統意識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特別希望對此有興趣的同行深入開展這個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談只是個人感想,算是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