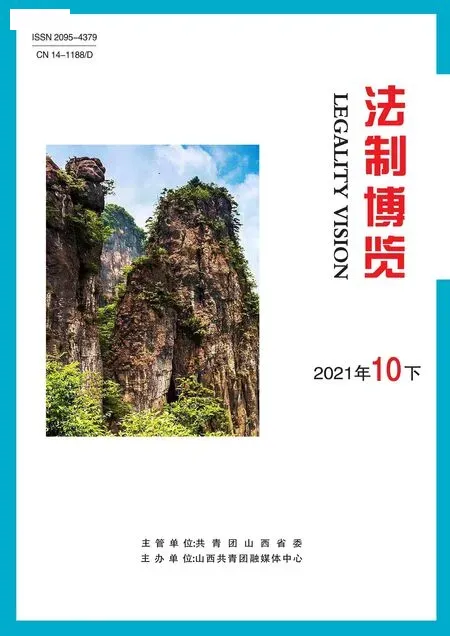需求理論視野下的犯罪心理矯治
——兼及正能量對“訴源”社會綜合治理的影響
林新英 羅小麗
(上杭縣人民法院,福建 龍巖 364200)
黨和政府向來重視社會綜合治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二〇三五年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即是“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個人不會無緣無故的犯罪,其墮入犯罪的深淵往往經歷了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哪怕是激情犯罪,也可能與被告人犯罪前長期的心理社會環境的潛移默化有關。被告人根植于心理社會環境并持續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因而在犯罪當中犯罪動機才會成為司法機關重點關注的方面之一。因此筆者認為,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被告人犯罪的深層次原因,進而從社會綜合治理角度采取相應措施,以達到弘揚社會正能量、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目的,未嘗不可。
一、需求理論與犯罪動機——不得不重視的社會治理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犯罪動機折射的是被告人犯罪時的心理需要,有可能是犯罪時的現實需求,也有可能是犯罪前長期累積在潛意識層面的心理需求。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的需求主要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五類。需要是一種推動個體行為的內在動力,它是因為個體內在缺乏而力求獲得滿足的一種內驅力。當個體的五種需求當中的任何一種或多種沒有得到滿足時,個體內在的心理平衡系統被打破,處于不平衡狀態,因而產生一種內驅力,形成動機,驅動個體產生這樣的或那樣的行為來滿足內在的需求。因此,個體行為(如犯罪行為)背后真正的根源在于需要(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解釋為犯罪動機)——當個體意識到自己某種需求未滿足的時候,就會形成內在驅動力,衍生動機,從而促使相應行為的產生。“人的任何活動,不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在意識或無意識層面寄托著人的愿望,有時表現在需要和動機當中,有時反映在我們可能無法說明的本能當中。”[1]而與被告人的心理需求相對應,全體社會人同樣也存在一定的心理需求,且這些需求存在一定的共性,并以社會共識的方式體現為了社會規則——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法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數據,全國法院2020年審結的一審刑事案件111.6萬件,判處罪犯152.7萬人;而2010年審結的一審刑事案件僅為779641件,判處罪犯100.6萬人。也即,從2010至2020年這10年來,判處罪犯人數增長了50%(不考慮累犯、再犯的情況)。這些數據一方面說明某種需求(包括意識及潛意識)未被滿足的被告人有一定的增長;同時也讓我們不得不反思,隨著社會發展、刑事法律修改,法網越織越密,全體社會人對于社會治理的心理需求是否被放在了合適的位置——也即有些行為是否必須上升到刑事法律評價的高度?同時我們也不得不反思,過去十年的社會綜合治理工作是否達到了相應的預期?近幾年在民事訴訟領域司法機關開始重視“訴源”治理,即通過各種手段盡量將矛盾化解在初期或是萌芽狀態,以此減少或減緩訴訟案件的形成。同樣在刑事領域,社會治理本身也是“訴源”治理的重要手段,通過社會綜合治理以減少或是減緩犯罪的發生,或是降低犯罪的烈度。
二、法律意識淡薄?——潛意識中的道德墮落
司法實踐中,“法律意識淡薄”往往是被告人自我辯解的常用理由。但仔細分析,“法律意識淡薄”真的就是被告人墮入犯罪深淵的原因嗎?不盡然。法律是最低層次的道德。也就是說,只要具備一般水平的道德認知,就應當知道只要遵守一般的道德標準,就不會違法犯罪。而所謂的“法律意識淡薄”所導致的犯罪,本質上并非對法律的不了解,而是潛意識中的道德墮落,導致突破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線。而被告人之所以常以“法律意識淡薄”辯解,一方面反映的深層次問題是被告人對其心理需求的不重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被告人心理的逃避。“法律意識淡薄”很多時候僅僅是一個表象,而其深層次反映的仍然是被告人某種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解決“法律意識淡薄”的方案不僅僅是普法本身,更重要的還在于我們常常爭論的法哲學問題:“法律的存在是讓人敬畏還是讓人信服?”筆者認為,如果法律是讓人敬畏的,就采取措施讓人敬畏它;如果法律是讓人信服的,就應當采取措施讓人信服它。歸根結底,“讓人敬畏、讓人信服”體現了法律的需求;而“我要敬畏、我要信服”體現了被告人的心理需求。從法律的需求到被告人的心理需求中,常常存在一個轉變的過程,從“讓你做”變成“我要做”也是我們社會普法的目標。要讓法律和道德最終深入人心并成為對被告人有效的行為規則,這個態度的轉變大致經過三個階段——即服從階段、同化階段和內化階段。“罪犯從違法犯罪到守法公民的轉變,實際上就是社會態度的轉變,期間大體上要經歷服從、同化、內化三個階段”。[2]
三、與原生家庭和解——未成年時期的家庭影響
我們現在重視未成年人犯罪,認為家庭因素對未成年人犯罪有著深刻的影響。從司法實踐來看,每一起未成年人犯罪,大概率都會使一個家庭陷入不幸;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每一起未成年人犯罪,其背后大概率都有一個不幸的家庭。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很多成年人犯罪其實也根源于其未成年時家庭的影響——家庭因素對于被告人犯罪的影響與其是否成年并不一定有著必然的聯系,只是因為家庭的影響大都在被告人未成年時期就已打下了烙印,只是有些是在成年以后才顯現出來。“未成年人犯罪的發生可視為未成年期這一社會化過程的特殊年齡階段中各內、外因素錯綜復雜的矛盾未能正確解決所致;”[3]而筆者認為,在未成年期社會化不成功的話,即使未成年時未發生犯罪行為,在成年后發生犯罪的概率也會更高。
《未成年人保護法》要求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但要怎么教育?怎么挽救?要教育和挽救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需要從根源上去了解未成年人之所以做違法犯罪行為背后的根源,這個根源就是原生家庭所帶來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的部分。所以從需求的角度入手發現,從現有的行為為切入點了解行為背后是有很多需要沒有得到滿足。我們看見的部分也就是我們能做的工作當中,很大一部分在于如何讓未成年人意識到原生家庭對其所造成的影響和傷痛之余,帶著理解和愛去看待原生家庭,和原生家庭和解。和解的關鍵是療愈未成年人與父母的關系。通過改變未成年人看問題的角度,借助關系的改善,達成對父母的理解,達到心靈的寬恕,從而最終了解到自己的需求并不是自己所認為的那樣沒有得到滿足,并不是父母不給孩子滿足,而是父母做了他們自己在那個當下最優的選擇。所以我們不要求他們是完美的,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去接受父母,而不是去改變父母。去接受原原本本的真實的父母,然后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如何做我自己,如何去面對我自己,如何對我自己今后的人生負責這部分上。而這些,都是在我們在了解被告人犯罪心理、考慮社會治理各項措施當中應當掌握的或是力求讓被告人掌握的。
四、心理暗示——重視正能量對“訴源”社會綜合治理的影響
人的行為及心理深刻受到周邊環境的影響。在預防和減少犯罪方面,對社會和心理環境進行治理、鏟除犯罪滋生的土壤將是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刑事領域犯罪案件源頭治理的重要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多次提到“正能量”,而我們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身即是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正能量。這些“正能量”某種程度上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心理狀態,起到了對社會和心理環境進行正向引導、正向治理的作用,進而影響到犯罪源頭綜合治理。因此,在需求理論視野下的犯罪心理與社會綜合治理,筆者認為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加強普法宣傳的針對性、有效性,培厚遵法守法社會正能量。在普法宣傳過程當中想要打造更好的宣傳效果,需要了解什么樣的宣傳形式和內容更有助于個體接受和記住,至少是在潛意識層面讓人受到影響。心理學研究表明,我們的記憶當中更容易記住那些視覺效果呈現出來的部分,視覺優于聽覺而被記住,負面信息優于正面信息而被記住,這是人類經過生物進化過程當中演化形成的一種本能。因此在普法宣傳的內容當中,一方面我們應當有針對性地通過色彩、圖像等視覺沖擊引起被宣傳對象的注意,同時通過營造聲勢增厚社會正能量,增加對全社會潛意識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有針對性的突出不遵循法律違法犯罪的懲罰和后果,如通過警示案例等方式有針對性地對重點人群進行宣傳,通過負面警示取得重點人群的犯罪免疫,進而培厚遵法守法社會正能量,提高法制宣傳的有效性。
二是構建“家-校-社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務體系。減少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需要提升整個社會的綜合治理能力,通過構建“家-校-社區”一體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務體系,從根源上進行心理防制和疏導,提升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素養。從已有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事實當中,我們發現圍繞三個核心點即“家庭、學校和社區”是未成年人成長過程當中接觸最多的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對于社區而言,可以通過成立家庭教育指導委員會等形式,定期向家長開展青少年心理健康輔導講座,提升家長的心理素養。在學校層面,把心理健康作為學校教育教學重要的模塊內容之一,把心理健康課作為必修課等等,切實把構建“家-校-社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務體系落地生根。
三是重視法庭教育的心理暗示作用尤其是正能量引導。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審理當中,在法庭辯論結束后要對未成年人進行法庭教育。在法庭教育過程當中,我們除了指出被告人的錯誤以外,還可以通過積極的心理暗示,通過借助積極的正面的語言——也就是正能量引導,讓被告人相信自己的明天是燦爛的,相信自己當下的力量是強大的,相信自己的命運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并且也相信過去所犯的種種錯誤是基于過去的錯誤的認識或不成熟的心智引發的,把關注點和注意力放在當前可以怎么做?今后可以做什么?如何正確做自己等內容上。當然,這不僅僅針對未成年被告人,對于成年被告人前述方法也同樣可以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