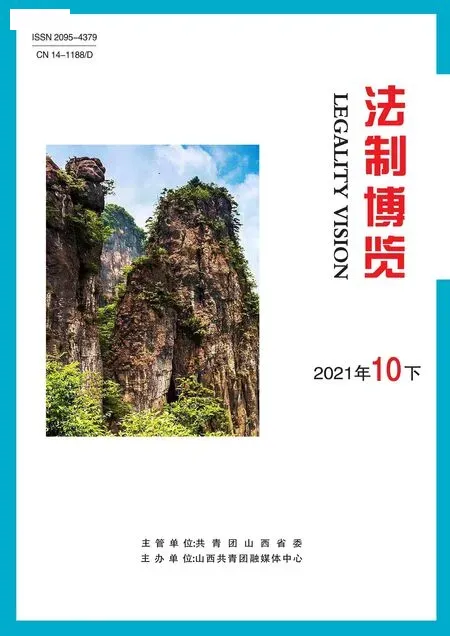中國古代刑法適用的法制思想
——從“刑罰世輕世重”與“三國三典”視角切入
何惠芳
(蘭州文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一、“刑罰世輕世重”與“三國三典”
縱觀我國法制史的發展,早在戰國時期,《荀子·?正論篇》就對“刑罰世輕世重”作出了解釋,強調要根據國家的具體政治情況、社會環境等因素來決定適用刑罰的寬與嚴、輕與重,從而制定出有利于維護政權、維護統治的刑法。在我國古代,一向以刑為主,“刑罰世輕世重”主要強調當社會秩序不利于統治者的統治時,就要用重典進行重治,從而以達到維護社會的穩定,實現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的法制之作用;反之,當社會秩序較為穩定時,再運用重刑就會過猶不及,這個時候就應當運用輕典,用以籠絡人心并顯示統治者的仁慈。[1]
西周時期,以周公為代表的統治者認識到:針對不同的社會情況,就應當靈活運用刑法典,采取不同的刑罰手段。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便產生了著名的“三國三典”法治思想,這種理論被后世歷代統治者所采用并且發展成為我國法制史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法治思想原則:“三國三典”理論即“三典刑三國”——“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2]
“三國三典”這一法治思想,其實質就是根據國家、社會具體情況的發展與現狀,而在刑罰處罰時采用靈活運用的方式進行調整,這樣才能更好地將刑法的功能體現出來。這里的“刑”就是治理的意思,“新國”是指新建立的疆域,因為新建所以政權并不穩定,加之新國剛經歷過王權的更替,因而用“輕典”來進行治理是最為恰當的,通過柔和的治國舉措來使國家休養生息,取得萬民的擁戴,爭取戰亂后的平穩過渡時期;“平國”是指承上啟下的平穩發展中的國家,此時國家已經發展了一定階段,一應國事均已走上正軌,其階級矛盾也趨于平和狀態,社會已經順利步入正軌,百姓安居樂業,此時再用“輕典”顯然不適應于國家發展需要,因而用“中典”來進行國家治理是最好的;“亂國”是指國家階級矛盾尖銳,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秩序出現混亂,犯罪現象越來越猖獗并且日趨嚴重,國家、社會處于動蕩不安穩之中,因而要用“重典”進行治理,嚴厲打擊違法犯罪行為,以達到穩定國家統治的目的。
二、“刑罰世輕世重”與“三國三典”對歷代刑法適用的影響
歷代統治者對“刑罰世輕世重”的具體適用,并不是簡單的輕罰或是重罰,而是輕法中有重刑,重法中有輕刑,輕刑重刑往往是交叉存在的,不能僅僅從表面去理解“刑罰世輕世重”與“三國三典”這樣的法治思想,只把其簡單地界定為刑罰適用過程中的輕重變化,實際上這兩種法治思想的核心是結合實際情況對刑法的靈活運用。
對于刑罰適用的輕重絕不是由統治階級肆意妄為的,它是要受到當時所處的社會階級關系、經濟條件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所制約。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都面臨著不同于以往朝代的社會形勢和政治格局,因此這就要求統治階級能夠因時制宜,與時俱進。基于“刑罰世輕世重”與“三國三典”法治思想的影響,一般在歷代王朝的興衰更迭中,一代王朝建立初期及發展時期,出于國家休養生息的需要,統治階級本著寬政養民的理念,對于刑法處刑都相對比較謹慎,往往寬宥省刑;而到了其統治末代時期,國家逐步呈現出衰亡現象,此時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不穩定因素日益增長,為了鎮壓各種反叛行為,強化統治秩序,往往就會實行嚴刑厲法。特別是在國家分裂、社會動蕩、戰爭頻繁時期。由此可見,“刑罰世輕世重”與“三國三典”的法治思想被歷朝歷代統治者認可并實行。[3]
在我國法制史上,對于“三國三典”這一法治思想的具體運用更為靈活的則是朱元璋。明朝在建朝之初,朱元璋便依照“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的原則,亦即奉行了“三國三典”法治原則中的“刑亂國用重典”的思想,以嚴刑治理天下。按照一般理解以及前文所論述,新朝建立之初,應當以休養生息為治國之策,以寬緩的刑法來進行治世,從而應當采用“三國三典”中所提倡的“刑新國用輕典”的法治理論,那么為什么明朝建朝之初,反其道而行之呢?朱元璋之所以如此,正是結合了明朝新成立國家之初的環境與條件才作出這樣的決策。朱元璋認為,雖然明朝建立了一個新的朝代,但是當時的明朝并不應該以“新國”來定論,而是更符合處于動蕩之中的“亂國”狀態,加之元朝統治的覆滅教訓,令他深刻認識到官僚治理不力所引發的后果,因此明朝吸取了這個教訓,在開國之初就確立了重典治吏的法治指導思想,采用了“刑亂國用重典”的法治思想,這在明朝當時國家治理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4]
綜上所述,我國古代的統治者們對如何靈活運用刑法有著清晰地認知,不論是“刑法世輕世重”還是“三國三典”,無一不昭示著國家適用刑法時不能一以貫之,要充分考慮國家與社會的變化,依據具體情況確定刑罰的輕重,如此才能靈活運用刑罰這一國家法制體系中最為嚴厲的處罰方式,在確保社會秩序的安定有序中發揮出刑法的作用。
三、正確理解“三國三典”與“刑罰世輕世重”
首先,“刑法世輕世重”與“三國三典”,都著重在強調刑法適用的靈活性,只是二者表達的適用標準分別是“世”與“國”。從《說文解字》里,可以找尋到“世”和“國”的二字的深意,之所以會將“世”定為三十年,而“國”要從囗從或,就是在表明一個短暫的時期與可變性,從而解釋出“世”與“國”的動態變化因素。[5]不論“世”也好,還是“國”也好,在刑法適用時要重點關注的就是它們的可變性的特點,也就是說在刑法適用上,“刑法世輕世重”與“三國三典”實際上都在強調刑法在當下社會中的靈活運用要核,而靈活運用的標準則是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據此可以推斷“三國三典”里講到的“國”,其實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政權組織,更準確地界定應該是當下的社會環境。正是基于此種解釋,明朝朱元璋才會結合當時的社會具體狀況,把建立之初的明朝定為“亂國”,從而采用了“刑亂國用重典”的法治思想。[6]
其次,還需要辯證地看待“世”與“國”這個標準,在我國古代蘊含的法制思想中,不能把“世”與“國”僅僅局限于一個政權或者一個國家從新建到衰敗的過程認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世”與“國”還可以特指在一個國家政權存在、發展期間的不同社會狀況。也就是說這種社會狀況的變化,即使是在同一個國家政權存在時期,既有可能產生“新國”“平國”的“世輕”“世中”情況,也有可能產生“亂國”的“世重”情況。所以把“世”與“國”簡單地認定為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政權,都是片面而教條的。[7]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司法改革與實踐中,應當充分利用我國法制發展歷程中的經驗與教訓,結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在相關刑法適用上把握好度,以便更進一步塑建刑法的公信力,完善刑法的執行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