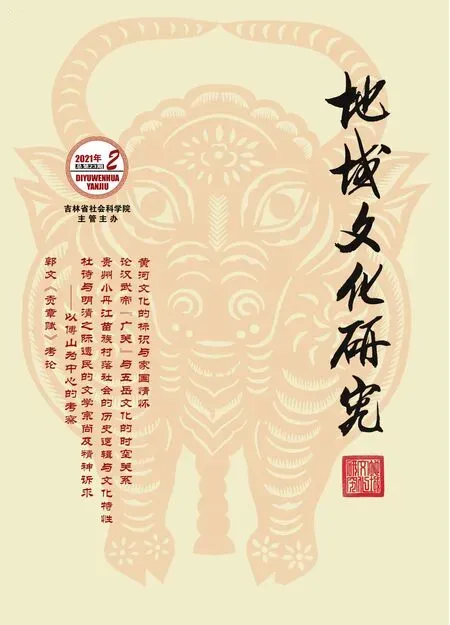“南北分治”視野下的遼代法制探析
張晉偉
一、遼朝南北面官制度概述
契丹政權肇始于907年,其伴隨著大唐王朝的分崩離析,傲然崛起于松漠故地,先后與五代、北宋對峙,是我國歷史上的又一個“北朝”。遼朝在崛起過程中,針對不同民族和地區的發展差異,創造性地開辟了胡漢分治的政權管理制度,即南北面官制度。在“兼制中國,官分南北”的原則下,南北各司其職,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①《遼史》卷45《百官志一》。。南北面官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隨著遼朝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封建化進程的推進,南北面官制度大致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分治到合流的發展進程。
契丹建國之初,是南北官制度的草創之際,由于其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較低,與之相對接的國家機構也多顯“事簡職專”,其大致可分為“朝官、宮衛、部落和州縣”四大組成部分。遼太宗在取得幽云十六州后,漢人在遼朝的地位日顯突出,“蕃漢分治”的政治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南北面官制度也在這一時期趨于定型。遼世宗時期,隨著封建農耕經濟在國家經濟的地位日益突出,統治者面對這樣的經濟社會形勢,進一步確立了南北兩大樞密院的職責劃分,南北面官制度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到了遼朝中后期,隨著國家封建化進程的加快和民族融合的發展,南北社會經濟的差異越來越小,南北面官逐漸走向合流和瓦解,在道宗時期,北院樞密使蕭孝忠就曾提出“一國二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并為一,天下幸甚①《遼史》卷81《蕭孝忠傳》。”的建議。遼朝的南北面官制度,是我國歷史上政權管理模式的一大創新,從其特色的行政管理制度中,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只有充分圍繞“生產力”這一基礎性的因素,適時優化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以古鑒今,其意義不言自明。司法制度作為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維系和鞏固政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南北面官制度”的大框架下,遼朝統治者經過多年的探索,逐漸開創出了一套與其主體政治制度相匹配的法律制度,這一司法制度,在遼朝兩百余年的統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也是本文將要論述的核心。
二、南北面官制度下的司法管理機構
1.北面官下的司法機構
遼朝以北面官管理契丹及諸部族的行政、司法等事務。據遼史記載,夷離畢院是遼朝北面官系統內的最高司法機構,下設夷離畢、左右夷離畢以及知左右夷離畢事等具體官職。夷離畢一職在遼建國之初亦有史可載,遼太祖七年(922),耶律阿保機下令群臣分決滯訟,以夷離畢直里姑掌亡捕;神冊五年(920),遼太祖任命漢人康默記為夷離畢,執掌刑獄之事: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析律意,論決重輕,不差毫厘。罹禁網者,人人自以為不冤②《遼史》卷74《康默記傳》。。遼道宗時,也曾詔夷離畢院曰:諸路鞫死罪,獄雖具,仍令別州縣覆按,無冤,然后決之;稱冤者,即具奏③《遼史》卷21《道宗本紀一》。。夷離畢院具有分管司法的具體職能,這一點無可辯駁,但通過史料記載:一方面,“執掌刑獄”并非夷離畢院的唯一職權,遼太祖在平定第二次諸弟之亂時,就曾命令夷離畢直里姑總管國內的一切政務,處理日常的政府管理工作。在對渤海的戰爭中,派遣康默記以夷離畢的身份統帥漢軍,協助作戰。遼道宗時,又以夷離畢替代皇帝,掌管部分祭祀職能,據遼史禮制記載,在祭祀活動中,皇帝皆親拜,至道宗始命夷離畢拜之④《遼史》卷49《禮志一》。;此外,夷離畢還有部分“諫議”的職能,遼道宗即位之初曾經對夷離畢院下詔曰:“令內外百官,比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⑤《遼史》卷21《道宗本紀一》。。另一方面,北面官的其他機構,亦有部分刑獄之權,特別南北樞密院正式成為遼朝最高的行政機構之后,褫奪了夷離畢院的部分刑獄職能,甚至直接插手訴訟之事,據遼史刑法志記載:故事,樞密使非國家重務,未嘗親決,凡獄訟惟夷離畢主之。及蕭合卓、蕭樸相繼為樞密使,專尚吏才,始自聽訟⑥《遼史》卷61《刑法志上》。。又如遼圣宗在太平六年(1026)以法令的形式規定:自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按輒申,及受請托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⑦《遼史》卷61《刑法志上》。。遼圣宗以皇命的形式,確立了樞密院對刑獄之事的總體掌控之權。
為鞏固統治基礎,緩解階級矛盾,遼朝在北面官系統中,設立了對應于南面官系統中“登聞鼓院”的機構,史稱“鐘院”,該行政機構自遼太祖神冊六年(921)始置,有冤屈的老百姓,允許其擊鐘鳴冤。鐘院的興廢幾經坎坷,遼穆宗荒淫無度,朝政廢弛,鐘院被廢,直到景宗耶律賢保寧三年(971)才被重新設置。
遼朝北面官制度下的司法管理機構,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呈現出不斷向中原傳統法文化靠攏的趨勢,如在司法權的分配上,由建國之初“夷離畢院”的一家獨大逐步過渡到后期的“司行不分”。總體而言,北面官制度下的司法管理機構,一方面體現了契丹族的傳統司法習慣,具有很強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則雜糅和借鑒了傳統中華法文化的思想和制度,對于遼王朝維系對草原諸部的統治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北面官制度下的司法管理機構亦有著許多致命缺陷,這些潛在的制度缺陷對于遼王朝日后的衰亡不無關系,如遼朝在各機構司法權力的分配上存在嚴重的疏漏,在君主昏聵或朝政不穩的情況下,司法權極有可能淪為政客角逐的工具。
2.南面官下的司法機構
在南面官的司法管理制度中,遼朝在總體上承襲唐朝制度,但在機構的管理和設置上又有所精簡,同時吸收和借鑒了宋朝的部分制度,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司法管理體制。南樞密院作為契丹南面官的最高機構,同北樞密院一樣,具有分理司法的職能,在遼朝之初,南樞密院暫時行使尚書省的職權,吏、兵、刑僅設立有承旨的官員,而無具體的分管部門。到了遼朝的中后期,隨著官僚體系的日漸完善,刑部最終被設立。遼朝南面官中的大理寺,職能與唐朝相同,主管刑獄案件的審理,所不同的是,遼朝的大理寺人員較唐朝有所精簡,僅設有大理寺卿、大理寺少卿、大理寺正、大理寺直等官員。遼朝南面官制度中的御史臺,職權在唐朝的基礎上有所擴大,兼具審判的功能①武玉環:《遼代刑法制度考述》,《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下設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官職。此外,遼朝的御史臺掌管兼理司法監察:嘗敕諸處刑獄有冤,不能申雪者,聽詣御史臺陳訴,委官覆問②《遼史》卷61《刑法志上》。。此外,遼朝還效法前朝,設立登聞鼓制度,并且成立專門機構登聞鼓院,設立知登聞鼓使專掌其職。
在南面官地方司法機構的管理上,遼朝一方面借鑒了宋朝的提刑按察制度,另一方面則承襲了傳統中原法系的“司行不分”。遼朝在全國設立五京,于每京設立警巡院,專掌亡捕治安;又以五京為中心,設立五道,以道為基礎管理各地刑獄案件。遼朝重視刑獄制度建設,效仿宋朝的“憲司”制度,由中央派遣分決諸道滯獄使、按察諸道刑獄使和采訪使等官員分察各道府州縣,處理積案陳案,肅察冤假錯案,如遼圣宗統和年間,曾派遣翰林承旨邢抱樸、三司使李嗣、給事中劉京、政事舍人張干、南京副留守吳浩等人分決諸道滯獄;后來,又復遣庫部員外郎馬守琪、倉部員外郎祁正、虞部員外郎崔祐、薊北縣令崔簡等分決諸道滯獄③《遼史》卷48《百官志四》。。各京府州縣的司法,由當地長官負責,如宰相室昉在擔任南京副留守期間恪盡職守,一時間“決獄平允,人皆便之④《遼史》卷79《室昉傳》。”。此外,遼朝在州以上另設有判官,協助當地長官處理刑獄案件。南面官制度下的司法管理機構,總體上體現出不斷完善和發展的趨勢,其脫胎于中原傳統的司法管理機構,卻有著自己鮮明的時代特色性。一方面,它經歷了由簡易、殘缺向復雜、健全的發展過程,如從最初的“樞密院代行司法權”逐步過渡到擁有獨立且完善的刑部;另一方面,則在舊有制度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如創造性地開辟了警巡院制度和冤案巡查制度。這些制度對于遼朝統治文明程度較高的遼東和幽云地區,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南北面官制度下的刑罰演變
1.北面官制度下的刑罰體系
契丹在草創之初,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刑罰體系,“凡犯罪者,量輕重決之①《遼史》卷61《刑法志上》。”,對于罪犯的處置方式,全憑部落首領的個人意志。刑罰制度的不健全性和不穩定性,是契丹內部動亂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契丹社會發展的落后性,遼朝在建國前夕的刑罰體系中,依然保留著濃厚的原始部落習慣氣息,如生瘞、凌遲、射鬼箭、投崖、炮擲等,如在第二次諸弟之亂中,養子涅里思跟隨諸弟反叛,遼太祖以鬼箭將其射殺;夷離堇涅里袞跟隨諸弟反叛,耶律阿保機不忍將其處死,命其投崖而死;阿保機還親自前往龍眉宮,車裂了逆黨二十九人②《遼史》卷1《太祖本紀上》。。但隨著契丹實力的加強,不少新附的漢人士大夫走進了耶律阿保機的帷幕,遼太祖重用漢人康默記掌管刑獄之事,當時,契丹各部剛剛實現了統一,并沒有制定嚴格的成文法令,康默記通過簡單的法理推理和民族習慣來裁決犯罪,認定刑罰,很好地履行了職責,此時,契丹野蠻的民族習慣法,也開始向文明化邁進。因此到第三次諸弟之亂時,對叛黨的刑罰處置,較前兩次,雖然還存在著射鬼箭等傳統處罰方法,但已有較大的改觀,如對于被脅迫參與叛亂的契丹宗室貴族,耶律阿保機僅僅把他們中的首惡予以杖殺;前任于越赫底里的兒子解里、剌葛,妻子轄剌已經實際參與到了叛亂的預謀中,耶律阿保機皆命人將其絞死;秋七月丙申朔,有司上諸帳族與謀逆者三百余人罪狀,皆棄市③《遼史》卷1《太祖本紀上》。。到神冊六年(921),遼太祖召集大臣修訂了“治契丹以及諸夷之法”④《遼史》卷61《刑法志上》。,北面官體系下的法律制度初步得以奠定,至于里面對刑罰有什么規定,已不得而知,不過從之后契丹人犯罪的處罰規則中,我們可稍窺一二。如遼太宗時,以南王府二刺史貪蠹,各杖一百⑤《遼史》卷4《太宗本紀下》。;遼世宗時,天德、劉哥、蕭翰、盆都等人謀反,耶律阮誅殺了天德,杖責了蕭翰,將劉哥流放到邊疆地區,罰盆都出使轄戛斯國⑥《遼史》卷5《世宗本紀》。。從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契丹舊有的刑罰處罰方法大多被淘汰,契丹人犯罪的處罰方法大多被封建制五刑所取代。但由于北面官刑法制度草創不久,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仍然有大量原始習慣法的存在,如應歷十二年(962),國舅帳郎君蕭延之奴海里,強陵拽剌禿里年未及笄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宮刑,仍付禿里以為奴⑦《遼史》卷61《刑法志上》。。遼穆宗時期,由于其“荒耽于酒,畋獵無厭”,遼朝的北面官法制再次遭到了破壞,大量的舊刑酷刑被再次啟用,如沙剌迭因偵鵝失期,被處以炮烙、鐵梳之刑,雉人壽哥、念古因觸怒龍顏而被肢解,盡管如此,由于遼朝的法制已初有成果,深入人心,以至于穆宗不得不下詔曰:有罪者,法當刑。朕或肆怒,濫及無辜,卿等切諫,無或面從①《遼史》卷6《穆宗本紀上》。。至景宗以后,原北面官制度下的舊有的刑罰體系基本被傳統漢法刑罰所替代。
2.南面官制度下的刑罰體系
契丹在建國前夕,因其統治的漢人數量有限,并沒有專門針對漢人的法律。遼朝建立前后,隨著五代戰亂頻繁,大量的漢人北上流亡或被掠入契丹,漢人在契丹的地位越來越顯重要,遼太祖根據其風俗習慣,建立了“頭下軍州”制度,采用漢制漢法管理漢人,到神冊六年(921),在修訂治契丹及諸夷之法的同時,同時確立了漢法的地位,漢人治罪,斷以《律令》。遼太宗在取得幽云十六州后,又進一步改進和修訂了漢律,以適用其在廣大漢地的統治。遼朝初期的“漢律”基本延續了唐律的規定,漢人的刑罰制度與唐律相同,即以“笞杖徒流死”為主要刑罰手段。
3.遼朝中后期南北刑罰的融合與發展
遼朝在法律上的胡漢分治,是基于二者生產力水平和文化風俗不同而制定并實施的,隨著遼朝國力的增強和各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面官制度下的傳統契丹刑罰逐漸被“漢式”刑罰所取代,另一方面,傳統的漢式刑罰也深受“契丹刑罰”的影響,到遼朝中后期,南北刑罰已幾近融合,基本上不再有對立和差別了。傳統契丹刑罰的萎縮甚至消亡,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契丹傳統酷刑的減少,如梟磔、炮擲、投崖、生瘞等刑罰,在景宗以后就很少被啟用。第二,部分傳統刑罰的適用范圍發生了變化,如“射鬼箭”由一種普遍性的刑罰轉變為針對敵國“軍事刑罰”,耶律阿保機草創國家時期,射鬼箭是契丹民族內部的重要刑罰,多用于“謀反”、“謀叛”等動搖國家統治根基的大罪,然自圣宗朝以后,遼朝境內的漢蕃諸族,因犯罪而被處以射鬼箭之刑的在史書中已鮮有記載;反之,射鬼箭多用作處置戰俘或者間諜的特別手段,如在遼景宗、遼圣宗時期,就曾多次將被俘宋軍處以射鬼箭之刑,如丁亥,獲敵人,射鬼箭②《遼史》卷9《景宗本紀下》。;庚辰,以所俘宋人射鬼箭;謀魯姑、蕭繼遠沿邊巡徼,以所獲宋卒射鬼箭③《遼史》卷11《圣宗本紀二》。等。又如在遼圣宗時期,對北宋潛入遼國內部的間諜處以射鬼箭之刑④《遼史》卷14《圣宗本紀五》。,興宗時期,對抓獲的西夏間諜處以射鬼箭之刑⑤《遼史》卷19《興宗本紀二》。。
傳統漢式刑罰受契丹舊俗的影響,亦在以下幾個方面得以體現:第一,凌遲制度的確立。凌遲是古代的酷刑,其始自遼代,不光被同時代的宋朝引為法定刑,更影響了我國的刑罰制度近一千年。史載曰: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⑥《宋史》卷199《刑法志一》。。遼代,凌遲作為法定刑罰之一,一般被用作懲罰危害國家安全的大罪上,如在遼圣宗時,曾經將抓獲的宋朝間諜及其窩藏者一并凌遲于鬧市,又如在遼道宗時期,對反叛的韃靼首領磨古斯處以凌遲之刑,不過從總體上看,凌遲在遼朝并未得到大規模運用。第二,墨刑的死灰復燃。墨刑是古代奴隸制五刑之一,早在南北朝時期,就被中原王朝束之高閣,在遼朝,受契丹舊法和游牧民族傳統習慣法的影響,墨刑再次大行其道。在遼朝,墨刑在一般情況下是被用作徒刑的附加刑:如遼朝曾規定:三犯竊盜者,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①《遼史》卷61《刑法志上》。。終遼一世,對墨刑的運用都很謹慎,在重熙年間,朝廷開始著手縮小和規范墨刑的使用,遼興宗原打算廢除“重罪徒終身者”的墨刑,后改為刺頸;遼朝還出臺措施,禁止主人私用墨刑: 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頸者聽②《遼史》卷61《刑法志上》。。針對盜竊犯罪,朝廷還規定:初犯刺右臂,再刺左臂,三犯刺頸,四刺左腿,第五次犯罪則要被處死③《遼史》卷61《刑法志上》。。經過百余年的發展,遼朝的墨刑最終實現了由“刺面”到“刺身”的轉變,不得不說是一個進步。第三,杖刑的民族特色化。杖刑在遼朝被廣泛運用,遼制: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決之;又有木劍、大棒、鐵骨朵之法。木劍、大棒之數三,自十五至三十,鐵骨朵之數,或五或七④《遼史》卷61《刑法志上》。。遼朝有折杖法,但與宋朝的稍有出入,是官員貴族的特權,據遼史刑法志記載:木劍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寬宥則擊之,例如在平定諸弟之亂時,遼太祖不忍處死其弟剌葛和迭剌哥,杖而釋之;又如在遼穆宗時期,蕭眉古得、婁國、李澣等人密謀叛逃后周,眉古得、婁國等人事泄被殺,李澣則被執行杖刑后釋放⑤《遼史》卷6《穆宗本紀上》。。第四,封建制五刑的變化。自開皇律正式確立封建制五刑以來,笞杖徒流死,成為各封建王朝刑罰的基本種類,遼初,以漢律制漢人,笞刑普遍存在于南面官系統之中,而契丹民族內部,則杖刑盛行。后來,隨著遼朝境內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杖刑的地位愈發重要,而笞刑則漸漸淡出了遼朝的刑罰體系,終遼一世,笞刑不再作為遼朝的制刑被保留。但笞刑不被作為法定刑罰,并不代表其在遼朝的刑罰體系中被完全廢除,在遼朝的日常的司法活動中,笞刑仍然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如遼圣宗統和年間,有三個士卒擅自出營劫掠,被笞以徇眾,其所獲物也被分賜左右⑥《遼史》卷12《圣宗本紀三》。;再如北大王帳郎君曷葛只里言本府王蒲奴寧十七罪,“詔橫帳太保核國底鞫之,蒲奴寧伏其罪十一,笞二十釋之”⑦《遼史》卷11《圣宗本紀二》。。
四、其他中原司法制度在契丹的融合與引入
遼法走向成熟的過程,也是其法制建設向中原法系逐漸靠攏的過程,隨著遼朝文明程度的不斷加強,贖刑、八議等制度也逐漸被統治者青睞,成為遼朝南北面官制度下兼用兼通的司法制度。
1.贖刑制度:在契丹的胡漢司法制度中,最初皆有贖刑,早期遼朝建國之前,贖刑便被廣泛運用在契丹部族的刑事犯罪之中,如在第二次諸弟之亂中,對于擅自劫掠人口財物的30 多名罪犯,遼太祖將他們“俾贖其罪,放歸本部⑧《遼史》卷1《太祖本紀上》。”。而對于漢人,則參照唐律的有關規定。遼圣宗至遼道宗年間,隨著遼律的不斷完善,贖刑被進一步規范化。遼法規定:凡是官員因執行公務造成的過失犯罪,或者年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的人犯罪,都可以以贖刑代罪①《遼史》卷61《刑法志上》。。遼的贖刑制度,脫胎于唐律,卻與唐律不盡相同,它結合了胡漢兩種司法制度的特征,簡化了贖刑的適用程序,縮小了贖刑的適用范圍,如刪去了唐律中殘疾人的“贖刑”特權,限制了官員適用贖刑的種類等。
2.八議制度:八議制度源于周禮中的“八議之辟”,是“刑不上大夫”的基本原則在刑罰適用上的體現,曹魏時期正式入律,在唐朝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遼朝沿襲并推廣了唐朝的八議之法,并在貴族之間廣為應用:如在遼圣宗時期,都統劉六符在征伐高麗的戰爭中,因延誤軍期而被下獄,因為八議制度而免其罪責②李玉君:《文化認同視閾下的遼代立法與司法實踐》,《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11期。。又如在遼圣宗時期,奚王籌寧殺無罪人李浩,所司議貴,請貸其罪,令出錢贍浩家,從之③《遼史》卷12《圣宗本紀三》。。遼道宗大康七年(1081),奸臣耶律乙辛因為走私犯罪被抓捕下獄,按律應當處以死刑,耶律乙辛的同黨燕哥上奏皇帝當入“八議”,耶律乙辛被免去一死,擊之以鐵骨朵之刑,并且軟禁在幽州④《遼史》卷110《列傳四十·奸臣上·耶律燕哥傳》。。
3.訴訟制度:遼朝在訴訟中同樣可以看到中原傳統的司法制度的影子,如“同居相隱”制度,遼朝在建國之初,奴隸屬于主人的私有財產,一切懲處均由主人所決定,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家封建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到遼圣宗統和年間,奴隸制度已成為阻礙遼朝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朝廷先是頒布法令,禁止主人擅殺奴婢;為了緩和二者之間的矛盾,又進一步下詔:主人如果犯的不是謀反等大罪或是要被處以流刑以上的,奴婢不得主動告發;若奴婢犯了死罪,應該交給有關部門處理,主人不得擅用私刑。奴婢和主人屬于同居關系,他們之間的相互隱告正式為律法所容許⑤冀明武:《遼朝法律中儒家文化略論》,《北方文物》2015年第4期。。遼朝中后期,為了懲治官員的貪腐問題,又進一步放開了“同居相隱”的范圍,遼道宗下旨規定,對于貪污及侵占兩貫以上錢財的官員,允許奴婢告發主人⑥《遼史》卷21《道宗本紀一》。。
五、遼朝南北分治下的司法制度簡評
遼朝的“胡漢分治”的特殊司法制度,適應了帝國內部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差異,緩和了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是遼朝得以延續二百余年的重要原因。司法上的胡漢分治,一方面尊重了各民族之間的文化和習慣,另一方面則有利于做到區別對待下的相對公正。后世的少數民族王朝,如金元清三代,無不借鑒遼朝的經驗教訓,試圖鞏固其統治根基,延續王祚永傳。然卻都只是管中窺豹,未得其精華。遼朝南北分治的司法制度,是我國古代司法制度的一次重要創新,是中華法系在特殊環境的升華,對于當下法治之建設有著“推陳出新,革故鼎新”之效。概括而言,有如下幾點:
1.司法制度的建設必須建立在其社會物質的客觀基礎上。遼朝在生產力水平和文化較發達的幽云渤海等地區頒行漢制法律,而在發展水平較落后的北部部族地區建立了簡單通俗的民族法律,既沒有強迫漢人遵從原始的契丹習慣法,也沒有不顧時代的發展,強迫北部各族接受先進的漢法。隨著各地區發展的逐步平衡,契丹的一些落后刑罰逐漸被漢制刑罰所替代,中原法系逐漸滲透到遼朝司法的各個方面。遼朝在司法制度上的區別對待,順應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要求,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在我們當今的司法建設中,也應注意到這一點,如在死刑等刑罰體系的存廢,必須建立在我國社會現有的經濟基礎上,既不能滯后,也要避免太過超前。
2.司法制度建設應當尊重文化和地區差異。尊重差異,因俗而治,是遼朝司法制度的又一大成功之處。遼朝針對不同民族和地區,采用適合其文化風俗的司法管理方法和刑罰體系,對于鞏固其統治有著重要的歷史作用。這對我國司法制度的啟示有:要廣泛關注少數民族地區的司法制度建設,合理運用少數民族文化中對法制建設有利的一面,重視民族區域自治法的修訂和完善,在堅持法治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尊重文化差異,妥善處理各類司法案件。
3.必須保證司法權的獨立行使,嚴格限制行政權力插手司法事務。遼朝中前期,以夷離畢院行北邊刑獄之事,然自圣宗以來,南北樞密使開始插手刑獄,皇帝甚至以詔命的形式,授予了二者直接干預司法的權力,從而導致遼朝中晚期冤獄的頻發。南北院樞密使和南北府宰相利用司法權參與政治斗爭,黨同伐異,導致朝政烏煙瘴氣,遼道宗時期的十香詞案和天祚帝時期的文妃案無不如此,頻繁的內訌極大的耗損了遼朝的國力,既而被新興的金朝所滅。這啟示我們:必須嚴格司法權的界限,保證檢察權和審判權的獨立運用,堅決避免行政干預司法。
4.法律移植與借鑒必須充分考慮現實國情,不能照搬照抄。如在遼朝境內,漢法的實行基礎是以宗法制度為根本的農耕經濟,而契丹北面法制的根基則是自由粗放的游牧經濟,遼初曾將漢法的連坐制度引入北面官法制系統,但由于沒有廣泛的民眾基礎和文化基礎而被最終廢止。這啟發我們,在借鑒和移植法律制度的同時,應當充分考慮本國的經濟文化基礎和社會基礎,避免不切實際的“濫搬濫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