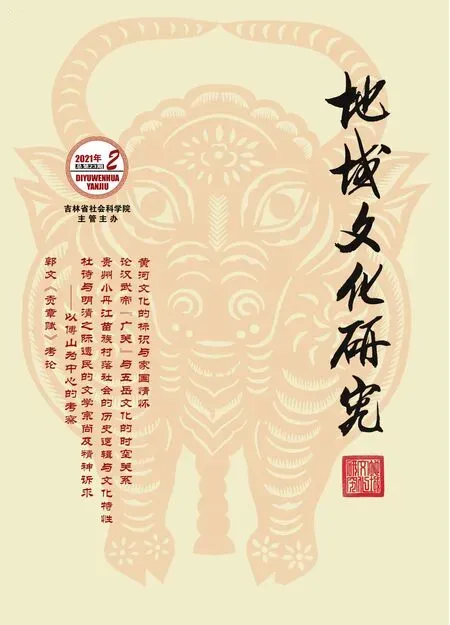貴州小丹江苗族村落社會的歷史邏輯與文化特性
葉成勇
2017年8月,筆者帶領貴州民族大學歷史系5名文物與博物館專業學生在榕江縣小丹江進行了25天的調查,比較系統地搜集了當地的各種資料,初步完成了《小丹江村志》的修撰。本文是對其中一些問題的初步思考,是作為《小丹江村志》的導論部分來寫,初衷是用比較通俗的方式引導大眾閱讀村寨志,這也是我們對傳統村落社會歷史文化書寫的一種探索。對此,懇請各位同好的批評指正,也借此機會與大家共同探索村寨志的書寫。
小丹江,清水江上游一支流也。小丹江村則位于小丹江河上游兩條小支流的交匯處,隸屬于榕江縣平陽鄉,轄小丹江大寨、小寨、新寨、南丹共四個自然寨,地處榕江縣西北邊壤,距離縣城百余公里,與雷山、劍河、臺江三縣接界。該地辟處雷公山腹地幽境之中,四周層巒疊嶂,山聳林深,綠水如碧,環繞其間。村支兩委駐大寨,苗語稱“昂切”(苗語音譯),漢文獻稱為“養提”或“養堤”,沙子寨之意,小寨稱為“養擺”,坡上寨之意。村內居民345 戶,1,420余人,苗、漢民族雜居,以苗族為主,姓氏多達30余種,而以楊姓為多。小丹江水源十分發達,是雷公山區域苗族社會的黃金水道,連接著內地與苗疆,幾百年的木材貿易,不斷地加強了各地的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聯系。歷史上雷公山腹地的木材順流而下,進入清水江,再運往長江水系。歷史悠久的小丹江村,民族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各民族文化多元融合,是觀察研究苗族社會文化的重要窗口。
一、大小丹江之含義
大小丹江,即大丹江和小丹江,當地人講大丹江在今雷山縣城一帶,小丹江,即是榕江小丹江村一帶。但乾隆《貴州通志》卷24《武備·師旅考》把大小丹江看作是不同的區域,而不是兩個地名。“清江、古州諸地界亦牙交繡錯,生苗聲氣相通,盤踞其中者為桃繞等四十八寨,名大丹江。右有烏疊等二十余寨為藩籬,名小丹江,左有雞講等十余寨,切近九股,兇惡尤甚,又大小丹江所恃以濟惡之區也。”這是雍正六年(1728)張廣泗從八寨(今丹寨縣)出發,由西往東開辟苗疆時的記錄。其對苗族多有污蔑之詞,可置而弗論,但關于地理上的記述則是我們理解大小丹江的重要依據。要搞清楚大丹江的具體位置,必須找準桃繞、烏疊、雞講三個地名所在地。桃繞,就是現在雷山縣附近及陶堯一帶;烏疊,即榕江兩汪鄉之烏計;雞講,現雷山西江。從地圖上看,陶堯處于雷公山腹地正中位置,從西邊的丹寨往東看,西江在陶堯左邊,烏計在其右邊,與文獻記載很是相符。
還有一條資料可以證明,就是乾隆元年(1736)正月平定苗疆包利、紅銀起義時,張廣泗坐鎮凱里,派三路大軍并進。①(清)鄂爾泰等修,靖道謨、杜詮纂:《貴州通志》卷25《武備·師旅考》之苗疆師旅始末條。乾隆六年刻,嘉慶修補本。中路軍指向是大丹江之桃繞、雞勇等寨,雞勇,今雷山記勇,在桃繞之西面。左路指向烏堯、防里等寨,烏堯,現雷山烏堯村,防里,雷山黃里村,與西江縱向形成一條線。右路軍指向小丹江之烏疊、留神等寨。留神,今榕江樂里鎮之列辰村。這些地方距離小丹江村多在30—40公里左右,顯然是用兵的重點區域。戰事結束后,清政府在今雷山縣城設丹江廳,在今小丹江村附近設有小丹江汛。屬于古州廳。
這樣,發源于雷公山東面原始森林的小丹江河穿大寨與小寨而過,與來自劍河昂英的小河交匯于大寨寨口處,下流經過兩汪及劍河之太擁、南哨而匯入清水江,成為清水江的一條支流,這條河所在區域就是清代所稱之小丹江地區。而源自雷公山西面,流經雷山、臺江而匯入清水江的巴拉河區域,即稱為大丹江地區。大小丹江一西一東,彎彎曲曲,并行而流,河流兩岸分布著很多苗寨,清代已是苗疆腹地,至今仍是苗族最重要的分布區。與大小丹江并稱的還有九股河,同為清水江上游,“沿岸數百里,皆生苗巢穴”②(清)余澤春等修,余嵩慶等纂:《古州廳志》卷7《武備·紀兵》,光緒十四年刻本。。今當地人稱大丹江在今雷山縣城一帶,小丹江為榕江小丹江村一帶,明顯帶有行政區劃的概念,應是清政府平定設治后的歷史記憶。
小丹江村雖然處于小丹江河的最上游,本應屬于苗疆的腹地,但是在清代開辟苗疆的軍事活動中,這里往往都成為重要的軍事據點,而不是我們現在眼中的邊緣地區的小丹江。大小丹江是地理上的區分,也是清軍用兵的戰略防區。張廣泗正是抓住了大小丹江苗族“地界牙交繡錯,聲氣相通,互為依恃”的根本特點,綜合考慮了當地的自然地理與河流走勢、民族分布格局和國家一統治理需要,其劃分和定位有其科學合理性。
二、小丹江三百年的歷史進程
(一)“三百昂擺,八百丹江”:關于三百年前千家寨的模糊記憶
關于小丹江歷史,直接文獻資料和調查資料反映的大概只有300年的歷程,也就是從清雍正時期開辟苗疆時算起。但雍正以前此地已有土著居住,主體居民是苗族。由于苗族無文字,這段歷史都要靠口傳,尤其是早期的歷史記憶,只能靠口傳。當地苗族古歌提到很久以前苗族先民從都柳江先入榕江車江大壩,后沿著平永河來到了小丹江一帶居住。隱匿在深山伐木為屋,開山造田,躬耕山野,過著一段長期的安定生活,逐漸發展到“九千地七萬寨”的繁榮景象。由于人多住不下,一部分遷往雷山,一部分遷往臺江、劍河。這當然是一種模糊的歷史記憶,似乎表明這里曾經十分繁榮,人多地窄。據傳世的清代地方漢文獻間接推斷,這里確實比較繁榮,屬于當時的“生苗區”,被稱為“千家寨”。據乾隆《貴州通志》記載,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在獨山州知州魯朝聘的招撫下,八寨附近生苗及“其極遠之千家寨俱后先歸化,隨筑城設官,隸都勻府。”①(清)鄂爾泰等修,靖道謨、杜詮纂《貴州通志》卷24《武備·師旅考》,乾隆六年刻,嘉慶修補本。看來,當時從都勻經八寨,有陸路可通小丹江,沿線開始筑城設官。當地現在比較可信的說法是“三百昂擺,八百丹江”。昂擺,也寫作“羊排”,今小丹江村小寨所在地,傳說這里曾居住300戶人家,人們很富裕,過鼓藏節時有30 對(60 頭)水牛打架。丹江,應該就是與小寨隔河相對的大寨,人戶甚多,但反而貧窮,遠不如小寨,還要依附于小寨,這隱約地反映出苗族社會內部的分化。昂擺和丹江合起來就是“千家寨”,但當地并無“千家寨”之稱,而是叫“三百昂擺,八百丹江”。由此可見,這里很早以前就是人煙輻輳的苗族聚居區,而且其社會內部已經有很大的貧富分化了。結合雍正年間開辟苗疆之時,“千家寨”歸化朝廷的歷史,我們推測小寨所在地很可能是朝廷筑城設官之地,里面住著當地歸化了的苗族上層,也住著朝廷派來的管理者。又據乾隆《貴州通志》卷25《武備·師旅考》苗疆師旅始末條記載,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包利、紅銀起義,該年五月初三日,起義軍“誘陷小丹江汛,千總劉文魁及兵丁二百人并其家屬盡被屠戮。”據此,所謂“筑城設官”,就應該是小丹江汛城,官就是千總劉文魁,駐扎有兵丁二百人,另外當還有隨軍開墾的眷屬。所謂“三百昂擺”大概就是指這個規模。但正是因為此次戰爭,小丹江汛被徹底破壞,官兵全無,“筑城設官”只有短暫的7年時間就失敗了。當地傳說,因為一場火災,“昂擺”很多人就跑掉了,其中的金氏家族去了今雷山羊排。羊排之名就是由金氏把“昂擺”帶過去的,只是音譯出現了變異。
總之,今小丹江一帶,當地人說“三百昂擺,八百丹江”,漢文獻有“千家寨”之稱,這就是小丹江千家寨的大致來歷。
(二)雍乾之際的風云劇變與納入一統
在雍正年間鄂爾泰、張廣泗開辟苗疆的大背景下,當時東部苗疆的開辟已始于雍正五年(1727)八月,鄂爾泰檄黎平知府張廣泗招撫古州“生苗”。②(清)余澤春等修,余嵩慶等纂:《古州廳志》卷7《武備·紀兵》,光緒十四年刻本。六年夏,張廣泗開八寨,以通運道,分兵進攻大小丹江,出奇設伏,盡焚負固之雞講五寨。前文提及的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千家寨”歸化朝廷之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小丹江的歷史開始發生根本性轉變,是被納入國家一統的重要標志和開端。但不久因“征糧不善”,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包利、紅銀起義,苗疆戰火再起,“圍攻新疆各營汛,阻截運道。”由于起義隊伍聲勢浩大,朝廷戰事不利。乾隆皇帝即位后于本年(1736)十月改派湖廣總督張廣泗經略苗疆戰事。至乾隆元年(1736)正月,張廣泗移節凱里,調度諸軍,于是分兵兩路,會剿高坡,復分兵三路會剿大小丹江。①(清)鄂爾泰等修,靖道謨、杜詮纂:《貴州通志》卷25《武備·師旅考》之苗疆師旅始末條。乾隆六年刻,嘉慶修補本。高坡即高坡苗居住地,非指一處,而是一個片區,苗“自清江來者仍其舊,居山者曰山苗曰高坡苗”,可能就是前文所謂的以烏計為核心的十余寨。也就是《古州廳志》記載的滾縱汛管轄的125寨高坡苗寨,主要分布在今榕江西北部兩汪一帶,可能是指今短裙苗支系苗族,這一帶正是小丹江流域的核心區域。乾隆以后古州鎮四汛中已無小丹江汛,該汛應是在雍正年間被起義軍所摧毀,從此未設。據光緒《古州廳志》卷7《武備·塘汛》記載“古州地方系新辟苗疆,水陸崎嶇疏闊,原分汛塘以資防范,且通郵遞而捍衛行旅計,安設四汛十九塘。”苗民起義被平定后,小丹江汛不存在,小丹江的駐防巡邏由四汛中的滾縱汛完成,該汛“羅列屯堡,環居山徑,崎嶇水陸狹險,鎮壓牛皮大箐,控制千家寨暨瑤苗各處地方,管轄高坡苗寨125寨,實為古州之犄角,保障之屏藩也。”牛皮大箐,就是雷公山腹地。看來,鎮壓牛皮大箐,控制千家寨及周邊各族勢力是滾縱汛的核心任務。據此推測,屬于古州鎮西北部滾縱汛的千家寨,應有塘兵駐扎。又據《古州廳志》卷7《武備·紀兵》,乾隆元年(1736),張廣泗平定起義,先后共掃蕩毀除1,224 處苗寨,赦免388寨,陣斬17,600 余人,俘虜25,000 余人。乾隆皇帝“詔盡豁新疆錢糧,永不征收”,又“從苗俗處分,不拘律例。”《古州廳志》的相關記載錄自魏源的《圣武記》,當可信。在這次戰事中,小丹江汛被毀,苗寨也可能遭到掃蕩,苗民受到牽連,千家寨中的小寨,尤其是上層人物受到重創,很多人被迫遷徙。“千家寨”之名淡出歷史的記憶。
張廣泗自八寨向東開辟苗疆時,已分兵進入小丹江,后設小丹江汛駐兵二百人。小丹江此時的苗寨,據田野調查,當在今小丹江的“歷昂”和“由昂”田壩中或旁邊的坡地上。苗疆起義被平定后,重設滾縱汛,其中駐扎在小丹江的塘兵應在后面不遠處的一座尖山上,現在小丹江大寨背后尖山上有營壘一座,半山還有戰壕,戰壕中立有一根鐵柱。這正符合“羅列屯堡,環居山徑”的記載。屯兵戰壕中的鐵柱應是張廣泗等于乾隆元年(1736)平定大小丹江后派人所立,屬于記功性質的紀念柱。當地人認為屯兵戰壕和其中的鐵柱是官家斷他們的龍脈,名曰“斬龍”,以防止再出“王子”或“反王”。千家寨此時有的人被迫遷移到山上或逃離此地。當地人說在現在寨子背后坡頂上叫“屋背坡”,就是從由昂遷徙上去的。遷徙的背景應是乾隆年間張廣泗平定包利、紅銀起義,當地人為避兵亂而上去的,而現在的小丹江大寨應是張廣泗等招撫或“赦免”后陸續搬下來的。當地還傳說,最早的祖先是住在“由昂”田壩里,后來這個地方出的女孩子很有本事,都進京趕考去了,而男孩子則很無能,于是老人們就商議集中搬到現在村寨的背后面叫“屋背坡”的地方居住,建有蘆笙坪,擊鼓吹蘆笙。住了一段時間,某家的狗跑下山去滾水塘,身上帶著水綠瓢回家。主人們才知道山下面有水塘,有飲水之處,人們又才逐漸搬下來,以水塘為中心居住,形成現在的村寨。這個故事很可能是對乾隆初年發生在當地平定苗民起義及其招撫的一種隱喻。
(三)走向繁榮與急劇衰落
乾嘉道時期,由于木材貿易,漢人不斷進入,苗漢通婚,文化融合,小丹江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并逐漸走向繁榮。
此時期整個苗疆比較穩定,社會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特別是外地漢人的進入,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要素促進了苗疆的開發。小丹江一帶林木順流出山,貿易往來增多,逐漸形成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發展的態勢。小寨雖然可能在包利、紅銀起義中遭受重創,但并未消失,當地居民曾挖出當時的漢文界碑、磚瓦窯址、碾坊等,可能是塘兵的遺存,大寨的人們在附近修房屋和耕地時也不斷有屋基和瓦片發現。但現在小丹江的諸多姓氏中,以苗族楊姓最早進入小丹江,傳十代人,距今約200余年,張姓和楊姓稍晚,張姓自臺江遷入。楊姓居住史據大寨楊光能先生家藏其祖上契約文書推斷,至少已在160多年前的道光末年自歸備(方言讀bì)寨遷入。在村寨附近坡地上,還有清道光年間典型的漢式墓碑,制作精致,雕刻十分精細。這些都清楚地表明到了道光年間,這里出現了繁榮景象,漢人及其文化在當地的影響很深入。漢人落戶當地被稱為客籍。雖然文獻無法直接證明這時小丹江的客籍情況,在文獻缺乏的情況下,我們只有拿《古州廳志》卷3《田賦志》所載經過咸同時期戰亂后小丹江周邊的數字作間接的理解。南丹有苗民41 戶,307 丁,南丹和丹章客籍共36 戶,158丁,而今平陽鄉羊社有苗民203戶,600丁,客籍99戶,307丁。丹章,即今小丹江。據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小丹江當時有不少的客籍漢人。
但咸同時期,由于張秀眉領導的苗民起義波及此地,這里又遭受重大損失。《古州廳志》卷3所載戰亂平定后“養堤”(今大寨苗語音譯)只有苗民10戶,23丁,是人口最少的苗寨之一,與之差不多的是養汪街上(今兩汪鄉所在地),也只有12戶,35丁,皆無客籍漢人,真所謂“漢苗俱弊”。《古州廳志》真實記載了余澤春親歷四境所見戰后的情況:“有前藩衍雞狗相聞,今僅存數十破落戶,或合寨榛莽無一人者,或新遷數家聚處以防他盜者,周歷按稽,不及十之一二。”①(清)余澤春等修,余嵩慶等纂:《古州廳志》卷3《田賦志》,光緒十四年刻本。戰事結束后,地方政府迅速整治,恢復社會經濟秩序,對村寨采取或小寨并入大寨,或數寨聯為一寨,又力行保甲,清查戶口,確定田產,招撫流民等等。這樣小丹江人口當有所增加。清后期至民國時期,社會經濟稍有復蘇,但世道艱難,亂象叢生,小丹江在艱難中堅韌地生存下來。這時期除了楊姓、張姓外,不斷有一些姓氏遷入,如陸氏從雷山治安堡遷入,李氏從劍河南加遷入,但規模不大。村寨中還保留有120多年前的古民居,修建者是當地楊氏八大房中的楊再能,因做木材生意發財而建造。這幢民居據說是請湖南的工匠修造了一年多,完全按照漢人的風格建造,原來有天井,后來因主人家打官司敗訴,廂房和前廳被拆除賣掉,以作為賠償。總體而言,這時的小丹江一帶,姓氏雜多,但人數都很少,或經商,或投靠親友,或避亂,皆為求生存而從周邊自發遷來此地。至解放初期,也只有68戶人家,180余人。
三、契約文書所見社會、家族與個人的歷時性互動
從楊光能先生家藏的26份契約文書可見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一些狀況。
第一,清代當地地名稱謂很復雜。光緒五年(1879)《古州廳志》稱現在叫“昂切”的大寨為“養提”或“養堤”,這真正反映了其本名。但除此之外,當地契約中卻稱謂不一。在道光三十年(1850)的兩份契約中分別有“油羊寨”“由羊寨”。“油羊寨”“由羊寨”現早已無人居住,變成了由昂田壩,但當地人說以前確實有人居住,現在種田時還不時挖出一些屋基和瓦片。光緒二十一年(1895)一份契約中寫作“小丹章”,民國時期又稱小丹江,或小丹江上寨和下寨。可見,小丹江這個漢語稱謂雖在雍正年間朝廷開辟時確定下來,但作為地名要晚至民國時期才被當地人穩定地接受。而小寨叫“昂擺”,道光十一年(1831)的一份契約中稱今小寨即為“羊排”,只是音譯不同而已,這是比較早的地名,一直比較穩定地使用,說明當時繁榮之時確實叫“羊排”。
第二,楊氏作為主要的姓氏,經濟活動最頻繁。楊氏在大寨是當地“八大房”中一房、二房和七房,南丹則是二房。道光年間楊秀乾、楊朝文實力雄厚,都是從附近苗族人手中大量購買田地、杉樹林地,甚至購買屋基,共有6 份契約。一次性交易數額不等,最大一筆是道光二年(1876)楊朝文買苗人呧淚九絞包母子四坵水田,共禾76把,花費252兩銀子,這是非常大的一筆,說明其財力之豐厚,苗族土地被迫向少數人集中。這種現象的普遍存在,成為后來咸同苗民起義的原因之一。
第三,咸豐同治年間只有一份契約文書,而且在咸豐早年,即咸豐三年(1853)楊秀乾又買苗民杉樹林一塊。這時期契約稀缺的原因主要是咸同苗民起義的影響,社會經濟遭受打擊,人民生產生活不穩定。
第四,清晚期光緒宣統年間,出現了恢復性發展。光緒初年,清政府妥善處理了戰亂后的田土及其田賦確認登記事宜,減輕各種負擔,招撫流民,維護社會秩序,社會經濟漸趨發展。土地交易又趨于頻繁。我們發現了光緒元年(1875)由貴州通省善后總局、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貴州下游善后總局聯合下發的土地確認執照。這是當地社會從亂轉治的很重要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此后土地買賣又頻繁起來,光宣時期共有10份契約,主要還是楊氏買進,但也有賣出,還出現了家族內部的土地糾紛與交易。苗民幾乎沒有參與交易,執筆人與憑中人很少見到苗人的名字。說明苗族在咸同時期受到損失更大,以后長時期未能恢復發展,而楊氏仍保持了很強大的實力,沒有多大損失。交易對象有田土、山坡、杉木林地、房屋地基、陰宅地等,類型增多,對象復雜化,但額度都較小。很有意思的是,這些文書中有楊再清的陰地擇吉書和其死后的一篇祭文,文采非凡,推算精細,從字跡看,應是同一人書寫,具有深厚的堪輿術修養。
第五,民國時期,地方社會經濟繼續緩慢發展,但匪亂嚴重。1932年農歷十月初六日的一封書信中提到國民黨征兵的事情,其中還有提及別人向他借貸之事。有契約5 份。這時期錢幣使用混亂,有光洋銀圓、法洋銀圓及銅錢、禾銀、紋銀等舊錢幣。有一份契約中提到早年的契約毀于匪亂,也說明了匪亂之害。
另外,李仁林先生家藏契約34份,主要集中在清末至當代,剛好可以補前批契約的不足,這里再著重分析。
第一,清末期,李氏從福建進入小丹江,購置田地頻繁,自光緒二十年至宣統三年(1894—1911),達6次,主要從苗族和楊氏手中購置田地、屋基和杉木山場。主要銀兩集中購買地基(兩宗,花28兩多)和田地(兩宗合計20石的產量,花20兩多),而杉木林場非常少(3兩多)。這反映了剛遷入的家族關注不動產的傾向,重在解決吃住的問題。
第二,民國時期,李氏購置田地更加頻繁,達12次,絕大多數是買田地,杉木山林一處,另外還有購買屋基(2 處)、別人贈送陰地、典別人的田耕種。交易額度都不大,土地購買來源較廣,有來自苗族、楊姓、皮姓、曹姓,但主要還是來自李氏內部,這一點說明交易的族內優先原則。現今看到1926年契約有民國十八年(1929)納稅時的契尾,并蓋榕江縣印、榕江縣征收局關防,契約上也加蓋此兩種印,還貼有一張1 角的印花稅票。契尾實名“新買契”,是白契向官契轉化的形式,既是新買契,也充當契尾的作用。這應該是貴州軍閥時期的征收方式。1932年契約和契尾上都僅有榕江縣政府印,契主民國二十六年(1937)到官府納稅時,重新按照貴州省政府財政廳發行的官契紙謄寫一遍,并作財產登記和應納稅額,納稅后附有“買契納稅憑證”,即契尾。從內容和形式看,官契重在財產確認和登記,納稅憑證重在納稅行為的確認,一前一后,但都包括了買賣事實的認可、財產登記和納稅記錄。比較上述兩張契約,發現后一張少了榕江縣征收局關防印和印花稅,而采用貴州省財政廳統一制定的官契,但官契需要購置,其實里面已包含了印花稅,而且漲為5角。就稅率而言,前一張為6.35%,后一張為13.75%,漲了2倍多。這說明從1929年至1937年中,有過一次稅務改革,農民負擔明顯加重。
第三,新中國成立后,小丹江屬于榕江縣第四區平陽鄉一村。從李樹清的土地房產所有權臨時執照可見,小丹江1952年8月完成土地改革,李樹清記錄了土改前后田產變化,結論是土改后較土改前增產31.5斤。合作社開始后積極參加入二股股金,后又因為家庭人口多,糧食不夠吃,又退出股金,這說明當時的合作化過程還是比較溫和的,農民進退都比較自由。據1953年農歷九月十三日的一份文書看,李樹清是一村第六組會員,貧農成分。該文書由村出具,目的是向平陽人民鄉政府申請李樹清自產自砍條木二十根趁漲水放江出售。另一份文書在農歷九月二十四日,內容是盤壽炙和李仁明申請共同趁漲水放江出售條木之事。其中“平陽人民鄉政府”稱謂與現在的稱謂“平陽鄉人民政府”有明顯差異,不知是書寫錯誤還是實質性的不同,對這種變化頗值得注意。還有一份也與杉木有關,是楊正楷因錯砍李樹清5根杉木,經地方調節而退還的錯字據。可見出售木材一直是當地民眾獲得經濟收入的重要方式。
四、關于“招龍”習俗:文化融合的個案分析
我們2017年8月在榕江小丹江調查了25 天,開始大家一起了解小丹江,3 天后都有了一些基本印象和特殊的信息。一周后,我們發現這里的信仰中“龍”的這個文化意象很普遍,但這個龍文化又有不同,二月二招五方龍(金木水火土)以保寨,儀式非常隆重,是招水龍,稱為“大龍”。二月中的龍場天各家各戶又可以招小龍進家,一般置于屋背后屋檐下,只是土龍,叫招地脈龍神。兩種龍只是形態大小不同而已,都是用木頭雕刻拼接成牛頭魚身蛇尾,雌雄成對。另外,人死后,生者若以為祖先保佑不力,則在二三月間請鬼師擇吉日招墳龍,護佑祖先靈魂,進而保佑生者,也屬于土龍。所有招的龍都是求吉祥,保平安的,可見龍在當地傳統社會中的地位。但這種招龍現象其實在雷公山周邊民族地區很常見,如果我們僅此而已,則很難發現其在小丹江的真味。此前我們聽當地人講一個“銅鼓巖”故事,講到以前這里曾經吃“牯藏”,后來因為牯藏頭很貧窮,吃不起,而且銅鼓成器了(大概指有了靈氣),變老虎叫,要吃很多肉,威脅到了人,于是大家商議把銅鼓埋起來,等以后生活好了再吃“牯藏”。這個故事又跟當地傳說的苗族李氏家族祖上的“老虎公”有關,因為“老虎公”就是當時的鼓藏頭。這件事情的發生距今已有6代人,約在120 多年前,但直到現在吃“牯藏”傳統仍未恢復。這個傳說與招龍其實有內在關聯性。特別是招大龍,在滿足村民歡娛的同時,可以節約財富,吃牯藏被取消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吃“牯藏”的祭祀儀式性功能。隨后,家里招土龍和墳山上招墳龍,進入家的層面。可以說龍變成了當地人的主神。祭祀五方龍的習俗是漢族的文化,這一點與小丹江濃厚的外來漢文化傳統很吻合。其背后的深層原因是這里地處清水江上游,木材資源豐富,漢族不斷涌入,以求得生存之所。用招龍替代吃“牯藏”,實質上是漢族中的龍文化在主導地方信仰文化變遷。在變遷中,漢族的五方五色龍,則變成了五方五行龍,而且主要是祭祀與地方密切相關的犀牛龍(水牛龍),這就是文化融合。既有外來的影子,也有本土的觀念和實際的社會功能需求。
五、從牛棚到村落的變遷及其對理解先秦時期“廬井”的意義
在黔東南苗侗地區,牛棚是個常見之物,一般都在遠離村寨的田地之中或坡頭上,主要圈養牛,但也放置一些農具和養殖工具。在很遠的一些坡地的牛棚也長期可住人,存放糧食,但建筑本身比較簡易。這個現象,經過反復調查追問,發現牛棚的形成有經濟、社會結構兩方面的原因。經濟方面是田地比較遠,施肥不便,就地圈養牛,便于積肥與耕地,這一點當地人都講得很清楚。但就此止步,則難以理解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我們要問為什么,為什么還可以住人,而且都是上點年紀的中老年人,又可以存放糧食。這是一個結構問題,原來當地人分田地時,近處每家都有一點,但近處的田地很有限,人們往往要到較遠的山坡上開墾耕種,而且每家多是開成集中成片的梯田土。這樣,遠處的牛棚就成為管理耕作的臨時營地,可以休息炊飲,儲藏器具和糧食。為什么都是中老年人呢?因為子女成家了,寨里的房子有限,老人不愿意跟子女一起吃住,他們就得往牛棚去。再者,原來多養水牛,現在則多養黃牛。水牛吃得多,糞便少,黃牛吃得少,糞便多;水牛力氣大,要滾塘水,黃牛則相對力氣小,不需要滾水。水牛漸次退出,重要的原因是現在機耕犁出來了,越來越流行,水牛的作用可以被替代,養黃牛更簡便些。
如果再往深度想想,是不是當地人在很早時期就是住在田邊地頭,分散居住,哪里有田,哪里就住著人家,與牛和犬為伴。這不就是村寨形成以前的人們耕田而食,兼養殖狩獵的生活場景嗎?據我們在小丹江的調查,確實能夠證實我們的推測。現在小丹江村寨旁邊有兩個田壩,分別叫“由昂”和“歷昂”。“由昂”田壩中還有七座牛棚,仍在使用。“歷昂”田壩中及周邊原來也有的,住的是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東一家西一戶。由于很分散,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國家統一把他們集中起來,分田地森林給他們,遂發展形成了現在的小丹江村新寨。“昂”是苗語,指居住的寨子,“歷”是田的意思,合起來,“歷昂”就是田中的寨子或有寨子的田。苗語“歷昂”之含義說明了人們當時以田為居住地,田和居住地重疊,二者互相依存。現在小丹江大寨苗語名稱叫“昂切”,“切”,沙子,直譯是沙子寨的意思,大概是指由眾姓共建于小丹江河流沖積而成的沙土臺地上的苗族寨子。雖然都是“昂”,但內涵已經不同,由“由昂”“歷昂”變成“昂切”,實質上是由依賴田地的生計而形成的分散居住,變成了眾姓聚居的合寨居住。以上故事和地名所反映的當地苗族村落形成的過程及其早期的歷史,是很真實的,而在現實中保留的大量的牛棚其實就是最早的苗族居住形式的縮影和變體。由于生產力發展和人口的增多,人們才聚居成村落。苗族的牛棚,客觀上適應了苗族遷徙中山地半耕半牧經濟,因而得以長期保留,以作為村落聚居生活的重要補充。
上述推測和認識還啟示了我們對中原地區早期歷史中人們的居住形態變遷的理解。先秦時期文獻有“廬井”一詞,廬,房舍,井,井田。《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詩經·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廬,疆埸有瓜。”鄭玄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孔穎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于田中種谷,于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漢書·王莽傳中》:“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漢書·食貨志》總結的先王制土處民之法中有井田廬舍,“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春令民必出于野,冬則比入于邑。”顏師古注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也。”①(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19-1121頁。《通典·食貨四》:“因井廬以定賦稅。”由此可見,作為田中屋的“廬”,一般是春夏居住,這正是滿足農忙季節耕作的需要,而且各在田中,說明比較分散,故有“在野曰廬”之謂,而里則是聚居之所,而且往往是秋冬季節從在野之廬中才能返回聚居,按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進行管理。《史記·刺客列傳》記載聶政是戰國時期魏國軹縣“深井里”人,深井,就是軹縣的一個里的名稱。反映了由生產生活的廬井向聚居的里的一種過渡,數里合起來又稱為邑,比較集中,有一套比較系統的經濟文教制度來維系。班固所言先王以“井田廬舍”制土處民之法,大概是子產對此前的八家共耕一井之地的土地制度進行“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改革后的情形。“廬井有伍”則表明在野的廬舍大概以五家為單位,這里“井”就已經打破了八家共耕的定制,而是五家為耕種單位,似乎表明生產力的進步。戰國“深井里”這類名稱則表明在原來某個“井”的地方按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的規制建立了一個新的“里”,有的“里”正是“廬井”的發展擴大,說明井田制的徹底退出,里坊制的開始。結合前述認識,以往認為從“五家為鄰”到“五鄰為里”是兩級基層建置的看法并不合理,而應該是“鄰”“里”一體化,具有經濟和社會管理的分工性質,合“鄰”“里”于一體的里才是真正的基層建置。按照班固的說法,里已經有明教化的“里序”和管理生產活動的“里胥”。但不管是八家共一井,還是“田有封洫,廬井有伍”,都形成了田地和房舍合二為一,因此在野的廬舍既可稱為“廬井”,也可稱為“井廬”。
“廬井”“井廬”與苗語“歷昂”就是一個意思了,指的就是田和房舍,是并列的共生的關系,有田就有房舍,有房舍就有田。田中有房舍,房舍與田地合一,這種關系是基于特定的耕作體系和社會經濟關系。由井向里轉變恰好類似于苗族的由“由昂”向“昂切”的轉變,即由分散的勞作散居向眾姓聚居轉變。不過在中原地區。不過在中原地區很早就在廬井的自然形態上編戶里伍,征收賦稅,而形成一定的基層行政區劃和建置單位。而在苗族地區,從原生的“歷昂”向村寨聚居,經歷了一個自發而漫長過程。苗族吃“牯藏”很可能是其聚居后發展出來的一種具有自我協調功能的社會組織生活形式。從苗族牛棚干欄式建筑的傳統遺風來看,應該是與新石器時代河姆渡文化干欄式建筑形態和居住相類似的,到了明清時期不斷地受到了漢族居住形態的影響,而變成了現在的吊腳樓建筑風格和樓居的居住形式,進而形成聚居的村落形態,但傳統的居住形式則以牛棚形式隱含地得以繼續存留至今。苗族歷史上由“歷昂”到“昂切”的村落變遷史和中原地區早期由“廬井”到“鄰”“里”的基層建置變遷有驚人的相似,也有本質差別。相似之處為都是從生產生計方式向社會組織化轉變,從原生經濟組織向次生社會組織轉變。不同的是中原在這個轉變過程被納入國家結構過程,而苗族則長期處于村落狀態,沒有導致國家的出現。
小 結
對村落社會歷史文化變遷的探索作為一種有意義的“碎片化”研究,應該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一個層次。榕江縣小丹江村是貴州省雷公山腹地的一個典型苗族村落社會,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演進過程。本文比較詳細地梳理的大小丹江的含義和小丹江三百年的歷史演變邏輯,分析了所發現的清代以來村里的民間書寫文書中的社會、家族與個體互動過程。特別是對當地社會中的“招龍”習俗和從牛棚到村落所隱含的苗族聚居形態的變遷及其對理解先秦時期“廬井”的意義,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把小丹江社會中民族群體與國家力量、經濟政治與文化信仰做了一番貫穿,對其區域社會史的結構性和歷時性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成果的呈現也顯得比較靈活,以問題為導向,突出了地域性的歷史邏輯和文化特性。
其中,關于苗族歷史上從牛棚到村落聚落形態的轉變是本文發掘到的一個新問題,不僅關系到對貴州黔東南地區苗族社會經濟形態歷史發展的認知,還對中原地區先秦時期的基層社會結構的變遷有重要啟示意義,很值得進一步探討。這樣的研究方式既是在中國大歷史框架下的微型區域社會史的解剖,又是以小歷史與大歷史相互參照,古史與今事相互衡鑒的一種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