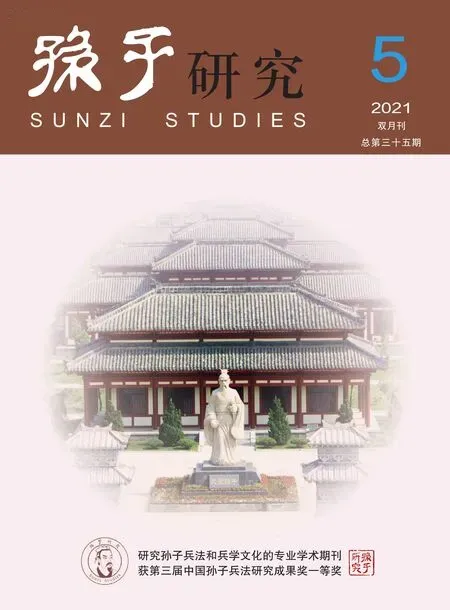孫子淺見
劉殿爵著 潘嘉玢譯
譯者按:在撰寫《域外孫子學文獻總覽·英語卷》收集資料時,發現劉殿爵(D.C.Lau)教授1965年刊載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報》第28 卷第2 期的譯作,標題是“Some Notes on the‘Sun tzu’”。此文聞見者甚少,現譯成中文以饗讀者。
一
兩千多年來,《孫子》一直被認為是軍事學中最權威的著作,這一認知不僅在中國傳承,而且在中國文化影響所及的鄰國,尤其在日本推崇備至。在歐洲早在1772年,耶穌會士讓·約瑟夫·瑪麗·阿米奧(Jean Joseph Marie Amiot,錢德明)的譯本首次問世,但未引起專業漢學家的重視,譯文僅限于法語一種。在近期的歲月中,英國雖曾有過多個譯本,但1910年出版的萊昂內爾·賈爾斯(Lionel Giles,翟林奈)的英譯本已廣為人知而久負盛名,盡管其譯文難以令人滿意。半個世紀后,這一名著又有新的譯本問世,自然備受歡迎。結果,很遺憾,塞繆爾·格里菲思(Samuel B.Griffith)將軍的新譯本〔1〕證明令人大失所望。毫無問題,譯者具有軍事學專家的資格,在這點上,我作為專門從事漢學研究工作者無法提出任何批評。但是,格里菲思既要克服古典著作時期文字上固有的缺陷,又要解決文本中真正的難點,這任務對他來說是太艱巨了。公平地說,人們應當銘記,《孫子》給讀者帶來的困難,要比同樣古老的其他任何著作帶來的困難大得多。因為大多數的古籍吸引了后來歷代學者的關注,大多數學者都對這些古籍文本的難點作學術性的注釋,留下了他們的印記。相比之下,《孫子》幾乎是被忽略了。〔2〕確實,對《孫子》的注釋并不算少,但是,從曹操起的注釋家都是實干家(如果不是真正的軍人的話),并沒有采取刻苦鉆研的治學方法。這樣的注釋家往往不重視句子的結構語法,遇到文本中有歧義之處強行作出自己的解釋,其結果只能是誤導粗心大意的讀者。
《孫子》的難點很多,可能非用哲學的方法求解不可。面對這么多困難時,本人時常企望自古以來對這文本有更多的學術關注。在少之又少的情況下,本人無意之間發現一位清朝的學者寫出對《孫子》文本的一個明確的詮釋,而使我感到遺憾的是只此一個,絕無僅有。該實例的文字如下: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3〕之(pp.41-4)。〔4〕
‘(3/12)〔5〕Consequently,the art of using troops is this:When ten to the enemy’s one,surround him:(3/13) When five times his strength,attack him;(3/14) If double his strength,divide him.(3/15) If equally matched you may engage him.(3/16) If weaker numerically,be capable of withdrawing[reading逃 ];(3/17) And if in all respects unequal,be capable of eluding him,.....(pp.79-80,my italics).
把“能”字一次譯成may,兩次譯成be capable of,這樣一種表達預示動作的意思都不合適。王引之聽從其父〔6〕指點,提出“戰”和“守”后面的“之”字均應刪去,而“能”在這三處應等同于“乃”。〔7〕據此理解,這段文字應譯為:
Hence the way of employing troops When ten times the enemy’s numbers,surround him;when five times,attack him;when double,divide him.When you and the enemy are equally matched,then fight him;when you are inferior in numbers,then take the defensive;and when you are not matched for the enemy,then avoid him.〔8〕
再舉一例: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p.121)。(7/21) During the early morning spirits are keen,during the day they flag,and in the evening thoughts turn toward home(p.108;my italics).
顯而易見,“歸”字取“回去”的意思不適用于“氣”(士氣)。譯者純粹為了避開這一難點硬將“想回家”(thoughts)的英文字塞進來,是不可接受的。格里菲思所依據的孫星衍版本〔9〕援引《廣雅》將“歸”定義為“息”,并引用《左傳》的話: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10〕孫接著說,因為“竭”的意思是“精疲力竭”(spent),而“息”的意思是“熄滅”(extinguished),兩字的意思互通,“歸”在這句話的語境中〔11〕應取“息”的意思。然而,孫對《廣雅疏證》自作主張的解釋,失之謬誤。因為《廣雅》界定“息”為“歸”,不是界定“歸”為“息”。《廣雅》的用意無可置疑,在第二章(2B)〔12〕中,我們看到一連串的十個“息”字全都定義為“歸”(to return),而在第五章(5A)〔13〕再次把“息”和“歸”一道都定義為“返”(to return)。
盡管孫對《廣雅》中“歸”字的詮釋論據不足,但是對我們的問題有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在昔日古文〔14〕中,“歸”與“饋”兩字互相通用,“饋”的異體字是“餽”,而“餽”有時作“匱”字用。〔15〕由于《毛詩古音考》(Mao)〔16〕將“匱”定義為“竭”,因此銳氣的“歸”就等于銳氣的“竭”。于是上述那段文字可譯為:
Hence morale is high in the morning,slack at noon,and spent in the evening.
因為在語言和文本方面的難點很多,格里菲思譯本的錯誤屢見不鮮,而且有些是相當嚴重的錯誤。盡管如此,我無意在本文中討論這些問題。更確切地說,我打算討論一些更大的問題,有些是文本方面的問題,另一些則是有關如何理解《孫子》中的某些基本概念。
二
我以為戰國時期的作品,一般說來是用較短段落的文字編纂而成的;而把很多短文編在一起構成一章的基礎,往往就是這些短文有著某些共同的關鍵性的短句。因此,注釋者或譯者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表明他怎樣把一章分成較短的段落。其重要性有兩點:一是他必須從整體上看清文字的統一性;二是他必須提防把原本不在一起的文字硬湊成統一的意思,不能對此做法渾然不覺。第二點尤其重要,因為只有毫不懈怠、時刻警惕,才能看出一段貌似連續性的短文中的一個關鍵詞或短語的意思,出現任何細微的湊合之處。格里菲思的譯本對每一篇的譯文都切割成非常短的小節。很難了解他分割正文的主要原則,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似乎是因為把注釋插入正文而造成的割裂。因此,凡譯者確定不插入注釋的正文,每節都會比較長。無論如何,把正文分割成這么短的小節,不僅對讀者沒有幫助,而且實際上搞亂了一個篇章有時是順理成章的真正的分段。
當然,把一個篇章成功地分為若干個真正的組成單元是一項很困難的任務。你必須主要依靠自己對正文的理解力,特別是依靠自己的敏感性,區別這一節和另一節之間在含義上的差異,即便這些差異有時并不太明顯。但是,可以在正文中找到必須充分利用的有幫助的途徑。例如,正文中往往有的標題語(caption)或重復概述(recapitulation),或二者兼而有之。〔17〕舉一個最明顯的標題語的例子如下:
凡用兵之法 (pp.21,33,41,105,124,132,181),出現在2/1,3/12,7/1,7/26,8/1,11/1。
其他例子:
凡處軍相敵 (p.144) (9/1)。
凡火攻有五 (p.215) (12/1)。
重復概述的例子:
此軍爭之法也(p.117) (7/16)。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p.171) (10/8)。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p.175) (10/16)。
標題語和重復概述兩者兼用的例子:
(a)故知勝有五(p.48) (3/24)。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p.51) (3/30)。
(b)故用兵之法也(P.124)(7/26)。
此用兵之法也(p.131) (7/33)。
(c)將軍之事(p.199) (11/24)。
此將軍之事也(p.201) (11/47)。
有一處比較復雜: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p.2)(1/2)和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p.8) (1/10)。
乍一看,好像一個是標題語,一個是重復概述,但證明并非如此。從第3節到第9 節,其內容是分別解釋第2 節所提出的“五事”。因此,第10 節只是重復標題語的后半部分,而“曰”是引出后面論述的那段話。這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標題語的重復是必要的:一是因為最初的標題語與其論述的內容相距太遠;二是因為如果不重復,就容易把標題語的這部分所講的內容與“五事”的解釋混淆。
由于格里菲思不了解這一行文的慣例,他對每一次出現的標題語都采取臨時變異的譯法(ad hoc translation)。如“用兵之法”,他有很多譯法:“generally in war”(3/1),“normally,when the army is employed”(7/1),“the art of employing troops is that”(7/26),“in general,the system of employing troops is that”(8/1),以及“in respect to the employment of troops”(11/1)。只有3/12 譯成短句“the art of using troops is this:”,這是他偶爾用了一個發揮原來真正功能的慣用短語。在以上所舉的多個例子中,盡管對標題語的譯法攪渾了它的作用特性,但并沒有引起嚴重的誤解。然而在某些情況下,結果就不那么幸運了。如第二篇開頭:
凡用兵之法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軍舉矣(pp.21-2)。
(2/1) Generally,operations of war require one thousand fast four-horse chariots,one thousand four-horse wagons covered in leather,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mailed troops.(2/2)When provisions are transported for a thousand li expenditures at home and in the field,stipends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advisers and visitors,the cost of materials such as glue and lacquer,and of chariots and armour,will amount to one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a day.After this money is in hand,one hundred thousand troops may be raised(p.72).
以上的英譯文錯把標題語當作主語,插進動詞“require”(需要),并把條件子句變成賓語。無疑,這使人感到奇怪,難道凡用兵“作戰”就該需要一個具體數目的戰車、車輛和軍隊嗎?可以想象這是取決于作戰的規模。這段文字應當翻譯如下:
The method of employing troops When one thousand fast four-horse chariots,one thousand four-horse wagons covered in leather,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armour-clad troops are used,if provisions have to be transported over a distance of a thousand li,then what with expenditure at home and in the field,on the guest advisers,on materials such as glue and lacquer,and on the supply of chariots and armour,it will cost one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every day before one hundred thousand troops can be raised.
再如,第九篇:
凡處軍相敵 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勿登;此處山之軍也(pp.144-5)。
(9/1) Generally when taking up a position and confronting the enemy,having crossed the mountains,stay close to valleys.Encamp on high ground facing the sunny side.(9/2) Fight downhill;do not ascend to attack.(9/3) So much for taking position in mountains(p.116).
這里譯者再次沒有認出標題語,而把它當作第一句的部分內容。顯然,“凡處軍相敵”是一個總的標題語,據此按4 種地形的順序論述部署軍隊——(1)山地(9/3),(2)河水(9/7),(3)斥澤(9/9),(4)平陸(9/11)。此外,這段文字作了如下的概括:
The advantages of armies positioned in these four ways were the means by which the Yellow Emperor triumphed over the Four Emperors.
最后一個例子在第十一篇:
將軍之事 靜以幽,正以治(p.199)。
聚三軍之眾,投之于險。此謂將軍之事也(p.201).
(11/42) It is the business of a general to be secure and inscrutable,impartial and selfcontrolled (p.136)。
(11/47) To assemble the army and throw it into a desperate position is the business of the General (p.137).
顯然,此處首先出現的“將軍之事”是標題語,再次出現的是重復概述。從標題語到重復概述為止,中間所講述的一切都屬于將軍之事。在第43 節所說的話(即“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盡管緊接在標題語之后,以及第47 節(即“聚三軍之眾,投之于險,此將軍之事也”),盡管出現在重復概述之中,但是都不能取代“將軍之事”的地位。把事情搞得復雜化的是,譯者毫無理由地把第46 節和第47節之間的話,換成譯文中按先后順序的第50 節、第48 節和第49 節。
三
發現古代文本中的一些文字與其前后不相關,這種現象并不少見。當然,在此情況下,理想的做法是把散失的文字恢復成原樣。不用說,這實際上根本做不到,因為在多數情況下,連這些文字是從哪本找到的著作中來的,還是從某一本別的著作中輯佚出來的,都說不清。道理很簡單,這些錯誤往往追溯到成書時的竹簡,確實是因為系結竹簡的繩子斷了,或者竹簡本身損壞,使得一片竹簡錯位。可以預料,我們很少能把這破損的竹簡片恢復到原來的位置。但是,我們要看到有很多竄入的文字較長。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理由設想這段文字出自一個陌生的來源。它可能是一種表述有所差異的前后文;或者這一段文字被采納,是因為它是鄰近段落中恰好論述同一主題的句子。
那么,譯者碰到這類句子該怎么辦?謹慎的做法是,譯出這類句子并加注說明其緣由。看來格里菲思在這方面的做法不規范,前后矛盾。例如,在9/15 和9/16 之間,刪去了下面的句子: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p.150)。
對此,譯者不僅加注說明已刪去,而且在頁下注中實際上又翻譯了被刪去的句子 (p.118,注1)。再者,在11/24 之后,我們被告知有7 句話已刪去,但是我們沒有看到被刪去的這段話的譯文。這是我們必須回歸到原樣之處。還有多處譯者刪節后不做解釋。
在11/41 和11/42 之間刪去以下的句子:
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pp.198-9)。
然而,譯者沒有做注解。
有一處確實令人困惑不解,7/9 之后的原文如下:
(a)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b)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p.112)。
這些句子在11/51 處重現〔18〕,但格里菲思沒有刪去所有句子,而是刪掉第一部分(即a 部分),翻譯了其余部分(即b 部分),成為7/10 和7/11 的譯句。為何刪去未說明任何理由,而兩處同樣的句子翻譯卻不相同。這似乎表明他并不知道是重復的句子。
除了刪節省略外,還有許多重新安排句子的問題。如在第十一篇中就廣泛采用了。再則,第九篇第27 節(即“來委謝者,欲休息者也”)應在第43 節和第44 節之間;第28 節和第29 節的句子的原來順序也搞顛倒了。
重新回到上述的11/24 之后所刪去的段落,原文如下: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凡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淺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p.202)。
而刪去這段文字的理由是,這些句子……再次界定前面的從第2 句到第10句所定義的名詞,并進而推論說“看來是注釋竄入正文”(p.133,注2)。我們不妨看看11/1 至11/14 的句子,搞清楚這樣刪節是否正確。這段原文如下:
用兵之法 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p.181-9)。
這段文字區分了九種地形,它們三次重復按同一順序表述:(1)散,(2)輕,(3)爭,(4)交,(5)衢,(6)重,(7)圮,(8)圍,(9)死。然而,在被刪節的段落中,只有六種地形,排列的順序是:(1)絕,(2)衢,(3)重,(4)輕,(5)圍,(6)死。不僅排序不同,而且在較長的地形名單中,“絕地”消失了。再則,眾所周知,有些定義略有不同,而另一些盡管不盡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樣的。因此,說“這些句子再次界定前面定義的名詞”是不正確的;由于地形名單不同,就說是“注釋竄入正文”也是不正確的。
格里菲思所以有理由要刪去上述的這些句子,估計是拘泥于“九地篇”篇名。由于這段話只列出六種地形,它似乎明顯不屬于本篇。對這種推理,不敢茍同,因為它把篇名看得太重了。一般說,篇名只能大致表述該篇的內容。如果我對很多篇內容構成的推測是對的話,我保證沒有哪一個篇名能涵蓋該篇各個段落小節的意思。審視《孫子》的整體就可證明這一點。第一篇篇名“計”,但17-27 節與“計”無關;第十篇篇名“地形”,但18-21 節與地形無關;第十二篇篇名“火攻”,但15-19 節與火攻無關。如此等等,不贅。如果一篇篇文章所包含的內容與篇名毫無關系的現象屢見不鮮,我們就單憑篇名這一點刪除任何段落文字,那是輕率魯莽之舉。再回過頭去說上述被刪去的文字,盡管它出現在“九地篇”中不恰當,但那是再一次探討地形的分類,而地形主題的討論并非專屬于第十一篇。因此,不能刪除這段文字。第十篇開頭如下:
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pp.167-71)。
這段話與那段被刪去的話一樣,都是六種地形。
再則,在第八篇里,可見:
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pp.132-3)。
盡管這里是五種地形,但有意思的是,五種地形(第一個除外)中的四種地形,在被刪除的那段文字中都有,而這五個地形數目與九地篇中被刪去那段的地形數目(第三個除外)一致。“絕地”是被刪段落中的一個地形,但不在九地之列。由于只有在被刪段落中對“絕地”作出定義,因此這個段落對我們了解該名詞是必不可缺的。格里菲思刪掉這段話在先,接著誤解了這個名詞,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將“絕地無留”這句話譯為:
(8/4) You should not linger in desolate ground(p.111).
如前所述,絕地的定義如下:
To send your troops away from your country over the intervening state is to send them into cut-off terrain.
因此,8/4 也應譯為:
Do not linger in cutoff terrain.
在被刪段落中的其他地形的定義中,有些與列名九地的定義大不相同,而有的略有不同,但足以補足我們對已定義的名詞的理解。在11/6 中,衢地的定義是:
territory of the feudal lords which can,in its nature,form part of a number of states and which will enable the one first to take possession of it to gain the multitudes of the Empire.
但在被刪段落中,定義更簡短:
Ground that is open to access from all directions is chu ti.
死地在11/10 中僅僅列出其特點:
terrain in which you will survive only if you fight with all your might but perish if you fail to do so.
而在刪去的段落中給出正確的定義:
Terrain from which there is no way out is ssu ti.
說到有關地形的分類,值得重讀第一篇中的一段話:
地者,遠近險易廣隘死生也(p.6)。〔19〕
或許,對此也可視為是一種地形分類。在第十篇,有一段文字: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p.175)。〔20〕
《通典》講“險厄”作為“險易”。而“遠近”是一個反義對言(a pair of opposites),因此它之前的對言也該是一個反義對言。如果我們認同《通典》之說,那么此處的四種地形與1/6 中最初的四種地形完全一致,此外,我們在10/1 中看到“遠”和“險”,二者分別在10/7 和10/6 中做了進一步說明。
如我們所見,死地分別出現在九種地形分類中、第八篇的五種分類中,以及被刪段落的六種分類中。
從以上長篇的討論中,我們得出如下的結論:單單因為一段文字與它所在的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不一致就把它刪去,這樣的做法毫無意義。相反,我們應當公平對待所討論的一個共同主題(如討論中的地形分類)中的所有文字,把全部的文字并列在一起,意義重大,因為同時讀這些文字,可起到觸類旁通的作用,哪怕是細微之處。
四
關于文本中的許多問題,我們得先討論思想理念的問題。格里菲思對《孫子》基本概念的理解有許多處尚待完善。先就“眾”和“寡”的概念說起。〔21〕從6/13 至6/15,我們討論這兩個概念,這幾段的大意是: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如果我軍兵力集中而敵軍兵力分散成十處,那么我軍實際上集中全部兵力對付敵軍的十分之一兵力。這樣實際上能使我兵力不足敵兵力十分之一的劣勢轉為優勢,只要我采取主動攻其無備就可實現這一轉化。防備敵眾多可能的攻擊點,不得不分散兵力,從而因分散而兵力變少了。這一段的討論總結成下面兩句話:
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p.95)。
這兩句話,格里菲思譯為:
(6/16) One who has few must prepare against the enemy;one who has many makes the enemy prepare against him.(p.99)
這樣的譯文是把孫子的原意搞顛倒了。按此譯文的說法,兵力少必須防備眾多可能的攻擊點而不得不分散兵力。另一方面,兵力多就要使敵人防備己方,即兵力多時能集中兵力對付原先少又不得不分散兵力的敵人。換言之,打起仗來,兵力少的會變得更少,因為兵力分散;兵力多的會變得更多,因為兵力集中。之所以搞成這種狀況,是由于沒有領悟《孫子》書中的教導。孫子努力說清楚的,恰恰是打仗時如何從劣勢轉變為優勢的問題。一旦結論和《孫子》總結的教導背道而馳,這樣的譯文必定是根本性的錯誤。這兩句話應譯為:
It is the one who has to prepare against his enemy who is few and the one who makes his enemy prepare against him who is many.
對于“奇”和“正”的一對名詞,格里菲思再次沒有全面理解。在第五篇中對“奇正”名詞論述的結語如下: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p.69)。
格里菲思的譯文是:
(5/11) In battle there are only the normal and extraordinary forces,but their combinations are limitless;none can comprehend them all.(5/12) For these two forces are mutually reproductive their interaction as endless as that of interlocked rings.Who can determine where one ends and the other begins?(p.92).
我用斜體字表示原文中沒有的意思。在譯者添加的許多字中,最嚴重的莫過于“interlocked”(連鎖)一詞,因為在漢語中就是像圓環一樣“沒尾或沒尾的”東西。格里菲思不僅捏造出另一個環,而且還把兩個環連鎖在一起。這不合適,因為“連環”一詞是在古代文學的作品中已是久經證實的名詞,如果作者指的是“連鎖的圓環”(“interlocked rings”)就沒任何理由不用該詞。況且,該詞堪與它之前的文字中“終而復始”的“日月”、“死而更生”的“四時”相媲美。所有這些都是循環(“圓環”)的,不可能用“連環鎖”來舉例說明。而拿“五聲”、“五色”和“五味”作比較,可能誤導了格里菲思。他將“變”譯為“組合”(“combinations”),是他放任自己走上誤解的歧途,無論這譯法用于奇正的概念或聲、色、味的感覺都是錯誤的。的確,“五味”和“五色”因組合而產生無窮的不同的味、色,但堅持這點就使類比的本意超出合理的限度。用“五聲”、“五色”和“五味”作類比,歸根結底,其重要的意義在于:從極小數目的基本單元能產生無窮的變化,不論基數是五個或只有兩個。
格里菲思將“奇”和“正”當作奇兵和正兵似乎是造成誤解的根源。的確,這名詞有時可指兵力,如“奇兵”短語,但總體說來,這概念適用的范圍比兵力大得多。“奇”和“正”最好分別譯為“crafty”,和 “straightforward”。后者指一般可預料到的(直譯為“率直”),而前者的意思字面很清楚(直譯為“狡猾”)。重要之處是,不論“straightforward”或“crafty”本身無法確定自己是“正”或“奇”。一樣東西是“此”還是“彼”,取決于你認為對方所期望的是什么。讓我們用猜猜看的游戲來說明這個問題。假定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a 和b,而你要選擇對方沒預料到的。如果一開始a 是大多數人所選擇的,那它就是“正”,b 是“奇”。但是,如果你認為對方看出這點而期望你選擇b(“奇”),那時實際上b 成了“正”,而你選擇的a成了“奇”。不過,你會認為對方也同樣又看出這一點,于是a 再次回復到“正”,而你將選擇b。這一過程會無期限地進行下去。這就是所討論的《孫子》那段文字的本意,應翻譯如下: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war,there are no more than “crafty” and the “straightforward”,yet these are capable of inexhaustible change.The “crafty” and the “straightforward” produce each other like a ring and who is there that can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處因誤解一個關鍵詞而扭曲了意思。盡管格里菲思對該關鍵詞談了一些看法,但他沒有做進一步的研究。在第一篇即“計篇”中,談及己方的情況要與敵方情況作比較,并應按照很多項目作出估計。根據估計的成果就可以預測戰爭的結局。總結這點的文字如下: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勝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p.19)。
了解這段話的意思取決于如何理解關鍵詞“算”字。格里菲思是知道這一點的。他在注釋中說:“在初步計算中采用某種計算工具。操作的功能表明是這樣一種工具,可能是原始的珠算(p.71,n.1)。
而他的譯文如下:
(1/28) Now if the estimates made in the temple before hostilities indicate victory it is because calculations show one’s strength to be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enemy;if they indicate defeat,it is because calculations show that one is inferior.With many calculations,one can win;with few one cannot.How much less chance of victory has one who makes none at all! By this means I examine the situation and the outcome will be clearly apparent” (p.71).
譯文的后半部分真令人吃驚。由于預測戰爭結局的依據是,按照明確說明數量的項目所做的估計,那么究竟是經過很多次計算,還是很少次計算,或者根本沒計算就得出這個估計呢?這譯文的荒謬之處正說明他是譯錯了。錯誤的根源是,他在通篇文章中把“算”當作“計算”了。譯者這樣譯,扭曲了后半部分的意思,因為即便他多少知道大概的意思,但他仍沒弄明白句子的正確結構。“得算多”是不能譯作“it is because calculations show one’strength to be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enemy”(“得算少”同理)的;“得”的意思只能是“gain”(獲得)、“get”(取得)或“win”(贏得),而“算”一定是其賓語。“算”的確代表一種計算器,更準確地說是用于計數的計數桿,而不是格里菲思所認為的珠算。在“計篇”中的戰局預演過程中,在任何一項取得優勢的一方會獲得一根或多根計數桿,從而贏得積分(具體的積分方法不得而知)。最后再計算桿的總數,哪一方獲得的桿數多就可預測是取勝的一方。因此,這段文字應翻譯如下:
It is by scoring many points that one wins a war before the event in a rehearsal in the temple;It is by scoring few points that one loses a war before the event in a rehearsal in the temple.
The side which scores many points will win;the side which scores few points will not win,let alone the side which scores no points at all.When I make observ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is,The outcome of a war becomes apparent.
五
還有兩個問題,我想討論一下,這并不是因為我可以提供有充分把握的答案,而是因為這兩個問題本身確有意義,應當引起《孫子》研究者的重視。
在中國古籍中,對不同的技術名詞采取相同的語言方式表達,并不鮮見。出于與眾不同的創新目的,對此最好利用現行的表達方式,而勿遵從直到近代還存在的傳統,杜撰一種新的表達方式。“聲”字的例子足以說明,這個字在傳統的語音學著作中有很多不同的用法,使現代的學者不勝其煩。《孫子》中的“形”字似乎與此類似。一方面,它表達“可觸知”的“形狀”;而另一方面,它作為動詞,是“顯示”或“使之顯示”的意思。例如: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p.76)。
Hence when one who is good at setting the enemy in motion shows himself,the enemy is sure to follow after him.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p.93)。
Hence by making the enemy show himself while remaining invisible,I shall be concentrated while the enemy will be divided.
按此用法,“形”也被用作近乎“勢”的同義詞(a near synonym of shih)。
以下的例子清楚地表明這點: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p.63)。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p.79)。
這兩句非常相似,使人感到一句中的“形”等于另一句中的“勢”。對此《淮南子》第十五篇的一句可以證實:
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于千仞之堤,若轉員石于萬丈之溪(《四部叢刊》ed.,15.11b)。
這顯然是將《孫子》中的兩句異文合成另一文本,而其中只用“勢”字。
能夠發現用兩種不同方式表達一個詞語,是一回事;但能說出每一次用哪種方式表達該詞語,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形”就是如此,用于下面這段最長的文字中的“形”令人十分困惑:
(6/22,23)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處。(24)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25,26)因形而錯勝于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而不復,而應形于無窮。(27-30)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pp.99-103)。
在這段文字中,看來“形”有時如6/24 中的意思是“形狀”,這段話可譯為:
Hence in giving shape to your army the highest you can attain is to make it invisible.If you are invisible,then even penetrating agents will not able to spy you out,nor can the clever lay designs against you.
另一方面,末尾部分將“兵”與“水”相比,尤其最后一句,幾乎可以確定“形”被用作近乎“勢”的同義詞。于是就有這種可能性:盡管整段文字通過用同一詞語討論同一主題,但實際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而是由很多分散的小節組成。果若如此,我們不得不放棄試圖從頭到尾用同一方式解釋該詞語,而必須確定在各種情況下如何使用詞語。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全”的名詞。第三篇開頭如下:
凡用兵之法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pp.33-4)。
(3/1) Generally in war the best policy is to take a state intact;to ruin it is inferior to this.(3/2) To capture the enemy’s army is better than to destroy it;to take intact a battalion,a company,or a five-man squad is better than to destroy them.(3/3) For to win one hundred victories in one hundred battles is not the acme of skill.To subdue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is the acme of skill”(p.77).
格里菲思是按中國注釋家的注釋,認為“全”是完整地俘虜敵人。實際上,注釋家們無一例外地都這么認為。〔22〕但是,“全”通常的意思是“保存完整”,而使它的意思成為“俘敵完整”,多少是引申了原意。令人遺憾的是,在整段文字中沒有明確表達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這個“全”字。例如,最后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這句話把“全”解釋成敵我都行。如果不放一槍,我方完整地俘獲敵人,當然我方也就保全了自己。
不過,讀到下面的句子時,應當如何詮釋“全”字的問題就變得突出了:
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pp.40-1)。
格里菲思譯為:
(3/11) Your aim must be to take Allunder-Heaven intact.Thus your troops are not worn out and your gains will be complete.This is the art of offensive strategy(p.79).
第一個譯句的結構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在語法上有三個疏忽之處:其一,在“天下”之前有“于”字;其二,“全”字之前有“以”字;其三,“全”與“天下”是分開的。無論“全”的含義是什么,句子的開頭部分的意思只能是“以‘全’為手段在‘天下’進行對抗”。
而如果“全”指的是所取得的成果,那會和“取得全勝的成果”重復。因此,有理由提出“全”指“保全自己”的看法。按此看法,保全自己和取得全勝是區分開的。這樣的區分可見于以下文字: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pp.54-5)。
(4/7) The expert in defence conceal themselves as under the ninefold earth;those skilled in attack move as from above the ninefold heavens.Thus they are capable both of preserving 23 themselves and of gaining a complete victory(p.84).
上文中的“全”與3/11 中的“全”分別形容“勝”和“利”,都是“完全”的意思。因為“全勝”和自我保存區別明顯,上文中的“全”不可能意味著“自我保存完整”。實際上,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全勝”是一個很常見的名詞,它的意思總是“全面的勝利”。因此,令人好奇的是看到《管子》中的句子:
故能全勝大勝(《四部叢刊》ed.,6.10b)。
尹知章評注:
全勝謂全我而勝彼。
By chuan sheng is meant ‘preserving oneself and overcoming the enemy’”.
對“全勝”這么耳熟能詳的名詞竟作出如此匪夷所思的詮釋,令人無法理解。除非那是延續到唐代尹知章時的傳統的詮釋,即在軍事的語境中將“全”詮釋為“保全自己”。尹的錯誤僅在于誤用該詮釋。如果推測是傳統的詮釋成立的話,那么我們會豁然開朗,對討論中的段落照此詮釋“全”字。在《孫子》書中有一句話似乎是支持這點的。那是第十二篇的最后一句:
此安國全軍之道也(p.222)。
This is the way the state is kept secure and the army intact.
而“全軍”一詞在所討論段落3/2 中也出現過,顯然用于表明“保全自己的軍隊”之意。
于是第三篇開頭可翻譯如下:
The method of employing troops It is best to preserve one’s own state intact;to crush the enemy’s state is only a second best.It is best to preserve one’s own army,battalion,company,or five-man squad intact;to crush the enemy’s army,battalion,company,or five-man squad is only a second best.For to win a hundred times in a hundred engagements is not the way best;the very best is to subdue the enemy’s army without fighting at all.
在同一句中前面的一個名詞指自己,后面的同一個名詞指敵人,用這種方法去理解原文,會遭到反對。對此我承認確實是個難題,但是在含義隱晦的文本中,這樣模棱兩可地用同一個名詞,并非絕無僅有。由于新的詮釋勝過舊的詮釋,相比之下,這點費勁難解就不必太在意了。
在同一篇的第11 節(即“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或許可以意譯如下:
Only by competing in the Empire with preserving oneself intact as an inviolable principle can one ensure total gain without even blunting one’s weapons.This is the method of planning attacks.
【注釋】
〔1〕《孫子兵法》,塞繆爾·格里菲思(Samuel B.Griffith) 譯并作導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叢書代表作),克拉倫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1963年版。
〔2〕只有清代知名學者俞樾評述《孫子》,但僅僅兩頁(見《諸子平議補錄》第三章,中華書局1956年版)。
〔3〕從“逃”字改為“守”。參見楊炳安《孫子集校》(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頁)。讀作“守”為好,因為這段文字討論不同的敵我數量對比情況下,采取的各種行動方式,而“逃”和“避”之間差別太小了。
〔4〕援引中國文本的頁數,指的是《十一家注孫子》,中華書局1962年版。該書依據1961年上海圖書館照片復制宋本,有限量版。我之所以采用該版是因為孫星衍版有爭議。見注釋〔9〕。
〔5〕為方便讀者查閱出處,斜杠前者指中文本篇序號,斜杠后者指格里菲思譯文的分段號。未援引英譯文處,用此標示,則指其相應的中文。
〔6〕見王念孫:《讀書雜志》,《萬有文庫》本
〔7〕《經傳釋詞》,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34頁。
〔8〕凡未注明頁次的是譯者所譯。
〔9〕格里菲思在其導言中稱:“孫星衍是清代研究《孫子》的主要權威,其版本(與吳人驥合作)是約二百年來的標準本,也是本譯本所依據的版本。”(第19頁) 遺憾的是,格里菲思用了孫校本中受到批評的部分。《十一家注》的編者指出,孫校本與明版本相比,可以看出“孫校本有許多明顯的武斷之處”(第268頁)。格里菲思翻譯時很可能沒看過《十一家注》,但他肯定看過楊炳安的《孫子集校》(中華書局1959年版),因為在其參考書目中有該書。楊炳安首先指出孫星衍主要根據《通典》和《太平御覽》進行校訂的,接著說:“此外,孫有多處疏忽。有些地方,沒能指出《通典》和《太平預覽》中的修改和增添純屬臆想,而另一些地方又盲目跟從這些著作中給出的錯誤解讀,更有甚者,孫對這些著作中實際上校訂正確之處卻未予采納。”(第七頁)
譯者不打算討論這個問題,但要舉一例說明孫沒有讀懂原文之處。在第六篇中有一句: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p.87)。
遵照孫校本(按《太平御覽》去掉第一個“不”字改為“必”),格里菲思譯句如下:
(6/5) Appear at place to which he must hasten;move swiftly where he does not expect you(p.96).
孫的校訂搞亂了原文的意思,因為后文接著說: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p.87).
“That one can march a thousnd li without wearing oneself is because one marches through territory that is unoccupied;that one attacks with the confidence of taking one’s objective is because one attacks what the enemy does not defend.
這是對前面的話的一種解釋。正如同行于無人之地那樣,攻其所不守。這證明兩處都應讀作“不”。在第一篇中也有同樣的意思: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p.17)。
Attack where the enemy is not prepared;go by way of places where it never occured to him you would go.
再則,在第十一篇中還有句子: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p.192)。
Troops are such that speed is is the supreme consideration.This is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what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enemy,to go by way of unexpected paths and to attack where the enemy has made no preparations.
貫穿在所有這些句子中的意思至少有兩層。其一,行于無敵人之地;其二,攻擊的目標是無防備之處。因為在該處敵人從未遭到過我方的攻擊。如果按照孫的修訂,那是攻其必守。這不僅搞亂了上述句子的意思,而且背離了其他多處有同一意思的句子。因此,這句話(即“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應譯為:
Go by way of territory that the enemy does not make for,and make for places where it never occured to him you would make for.
〔10〕《左傳·莊公十年》。
〔11〕《孫子十家注》(《四部備要》ed.,hsu lu,p.13b.)。
〔12〕王念孫:《廣雅疏證》,《萬有文庫》,第215頁.
〔13〕王念孫:《廣雅疏證》,《萬有文庫》,第497頁。
〔14〕例如,《論語》魯版本“舞而歸”(5/27)中將“歸”讀作“饋”;同樣,鄭版本“齊人歸女樂”(18/4)中將“歸”讀作“饋”。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叢書集成》,第1384、1398頁。
〔15〕例如這句子:“四谷不收謂之餽。見孫詒讓《定本墨子間詁》,1.17b。
〔16〕《毛詩古音考》第247頁。
〔17〕在古代文本中采用標題語和重復概述并不鮮見。《荀子》第九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8〕楊炳安注(《孫子集校》,第36頁)。
〔19〕(1/6) By terrain I mean distances,whether the ground is traversed with ease or difficulty,whether it is open or constricted,and the chances of life or death (p.64).
〔20〕(10/17) Conformation of the ground is of the greatest assistance in battle.Therefore to the enemy situation and to calculate distances and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of the terrain so as to control victory are virtues of the superior general(p.127-8).
〔21〕應該指出格里菲思的譯文有一個特點,盡管這是順便提到的事,即他對同一中文名詞慣常采用意思一樣的不同譯名,無疑這是為了文字上的優美。如果翻譯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這樣做無可厚非。而像《孫子》含義非常隱晦的專業著作,翻譯越忠實于原著,越有助于無法讀懂原著的讀者。這一點對于翻譯專業名詞尤為重要。遺憾的是,格里菲思只顧文字上的優美,而不考慮要小心翼翼地忠于原著,甚至無視必須絕對忠于原文之處。其語境中的一個例子足以說明我心中的想法:在6/15(p.98) 中,名詞“寡”有五次是同樣的意思,而譯成“few” 只有一次。一次譯成“fragile”,一次譯成 “vulnerable”,還有兩次譯成“weak”。
這種譯法是不顧在《孫子》書中“弱”也是一個專業名詞,而“weak”應當準確地保留其譯名。
〔22〕賈林是唯一表白他認為該名詞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他評論說:“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為上。”但是,賈林盡管說“保全我國”的話,他仍然堅持“全得敵國”的理念。因此,他似乎要將“全”解釋成保全敵我兩方。
〔23〕譯者用“preserving”代替格里菲思譯文中的 “protec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