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麟為什么會轉向馬克思主義
李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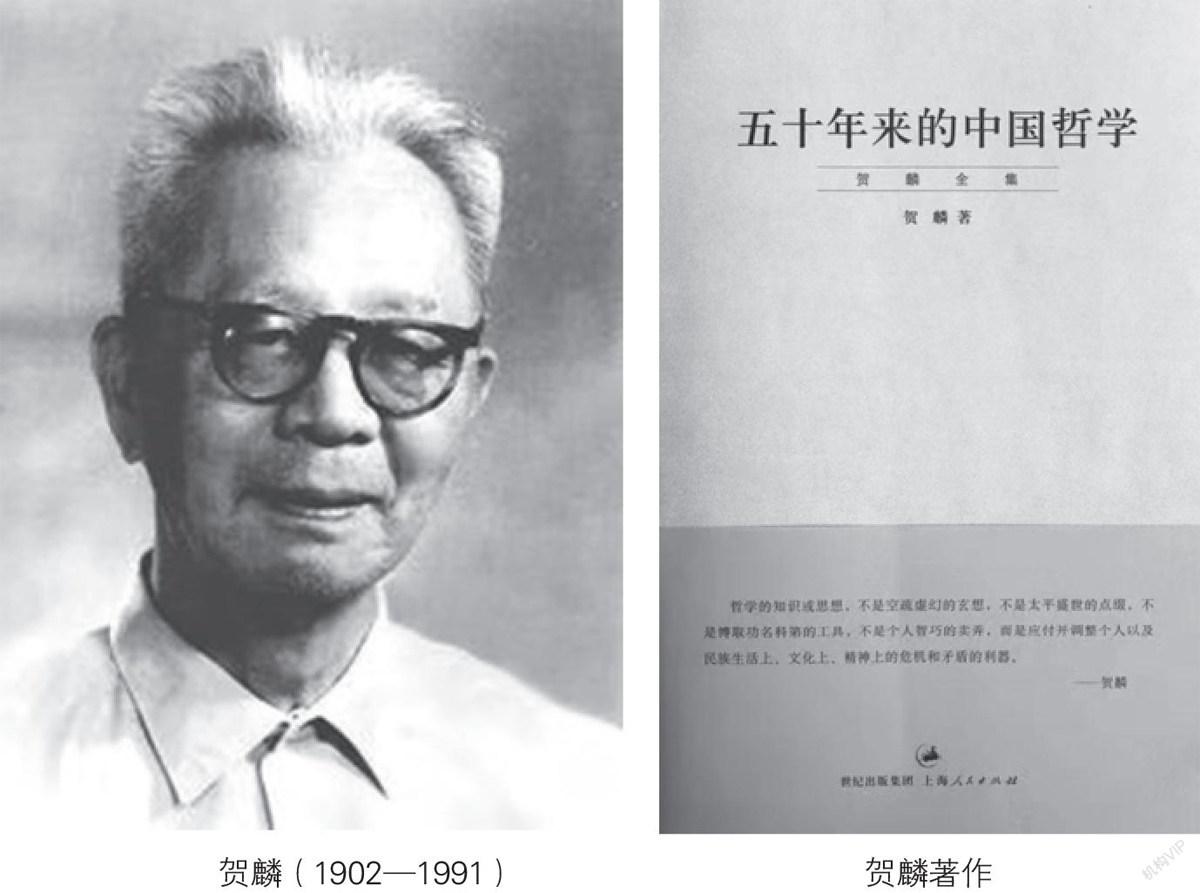
賀麟(1902—1991),四川金堂人,是現當代中國杰出的哲學家。1986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等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賀麟學術思想討論會”,對賀麟一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充分肯定了賀麟在哲學思想、黑格爾哲學研究、翻譯西方哲學、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等方面的地位及貢獻。他與馮友蘭、金岳霖、熊十力等各創自己的哲學體系。他精通黑格爾哲學,論述遍及黑格爾哲學的各個方面;他翻譯的《小邏輯》,學術界公認為繼嚴復的《天演論》之后影響最大的學術著作中文譯本;他在中國較早倡導中西文化研究。在哲學這塊土地上,賀麟辛勤地耕耘了一生。這期間,雖說步履艱難,但最后終于從唯心主義走向唯物主義,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一、“我也懂點馬克思主義”
194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賀麟面臨要留在內地,還是隨蔣介石政權南遷的抉擇。對此他在《我和胡適的交往》中有所說明:有人勸我以走為好;但我想,我又不干壞事不犯罪,干嗎要走呢?而且這么多書怎么帶走呢?我也懂點馬克思主義,知道共產黨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可怕,知道共產黨也需要我這樣的知識分子。
從常識講,去留問題是因每個人的處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當時知識分子對時局的基本估計。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說他曾邀請陳寅恪、楊樹達、梁漱溟等人去香港,但均未成功。對此他感嘆到:“國家遭此大變,但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亦證當時一輩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新政權都抱與人為善之心。”賀麟是錢穆舊友;這個分析,對賀麟來說,也是真切的。北平圍城期間,南京方面曾3次讓賀麟離開,但他終于沒有走。賀麟當時的想法是:“我不愿意提個小包,像罪犯一樣跑掉,也不愿再與蔣介石有聯系。就是到美國去也不會如學生時代那樣受優待,何況我的愛人女兒決不做‘白俄。”有一天,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的汪子嵩來找他,對他說:“地下黨城工部托我轉告賀先生,城工部負責人的意見希望賀先生不要到南京去。我們認為賀先生對青年人的態度是好的。”中共地下黨也開始做許多大學教授的工作。在賀麟的去留問題上,當時的地下黨員汪子嵩、袁翰青都起過作用。經過反復、鄭重地考慮,他三次拒絕了南京政府請他離開北平飛往南京的要求,決定留下來,迎接解放。據他的女兒回憶,“院里的伯伯叔叔們也都沒有走,整個北大的教授們絕大部分也沒有走”。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城,歷史開始新的一頁。
二、通過土改的社會實踐真切認識到辯證唯物論的實踐性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舊中國留下來的廣大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觀念與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吻合的。讓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土改就是期望通過這一實踐來改造其思想,以此爭取知識分子對新生政權的認同,并借知識分子的力量推動土改運動的開展。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個群體,第一代現代新儒家中的馮友蘭、梁漱溟、賀麟以不同方式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馮友蘭參與了北京郊區的土改,梁漱溟考察了四川的土改,賀麟參與了陜西土改。他們都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表達出土改對他們的教育意義。賀麟通過參加土地改革、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逐漸轉向唯物主義。
1951年4月2日,他在《光明日報》發表《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一文,贊同唯物論。土地改革作為思想改造的實踐平臺,是第一代現代新儒家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他在那篇文章里闡述了他的思想,認為土改的社會實踐,使其否定了“靜觀世界”的唯心論觀點,認識到辯證唯物論的實踐性。他說:“靜觀世界”,不惟站在外面不能改造世界,就連對世界的認識也會很膚淺、表面、外在;而深入參加實踐斗爭,不惟對變革現實盡了一分子的努力,而且于變革現實的實踐中,除增進了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外,又復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這次的新經驗使我一方面深切感到過去多年來脫離實踐的書本生活,不知錯過了多少偉大的實踐斗爭的場面,也就錯過了在實踐斗爭中改造世界、認識世界和改造自我的機會;另一方面同時也就幫助我否定了“靜觀世界”的唯心論觀點,而真切認識到辯證唯物論的實踐性。他的女兒后來回憶父親時寫道:“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調查體驗。唯心論只講概念,不接觸實際,而只有通過實踐得到的思想才真正有力量。過去以為唯心論注重思想,唯物論不重思想,現在看到共產黨的辯證唯物論也非常注重思想”。后來他又參加了教師的思想改造運動,當時亦叫“洗澡”。他說他是經過痛苦的思想斗爭來檢查自己的。雖然那時對自我批判和群眾的批判,有些人上綱過高,但是他還是以改造自己,適應新社會的態度來對待,還是實事求是,自己想通了的才承認。1957年4月11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接見周谷城、胡繩、金岳霖、馮友蘭、賀麟、鄭昕、費孝通、王方名、黃順基等10人,并共進午餐,飯后又談到3點多鐘。賀麟根據同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寫了《必須集中反對教條主義》在《人民日報》發表。他說:“過去我對于唯物論還有一個錯誤的看法,我以為它有些騖外,只重改造外在世界,改造物質環境,而不重向內用力去求自我改造和思想改造。及我發現馬列主義者最注重宣傳、教育和學習,把搞通思想、改造思想放在重要的地位時,于是我又以為唯物論者一面重改造思想一面又重改造世界,不是自相矛盾就是陷于二元論,或者表面是唯物論而骨子里卻是唯心論。因為我總以為只有唯心論才重思想,唯心論者認思想創造世界,認沒有思想就沒有存在,沒有知就沒有行,認要改造世界,先須改造思想,甚至有許多唯心論者只求改造思想,不愿改造世界。……在這次土改工作中,我才開始認識到唯物論與搞通思想不可分”。他最后總結說:我現在才明白了,何以只有辯證法唯物論才是真正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哲學,何以無產階級真正覺醒起來,必然會尋找到辯證法唯物論的哲學。
用今天的眼光看來,賀麟作為一個著名哲學家,敢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公開檢查自己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這種精神是應該肯定的。
三、《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闡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底蘊
改革開放以后,賀麟以前所未有的暢快心情活躍在國內外學術舞臺上。他于198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新的治學歷程,撰文、編書、講學、帶研究生、對外學術交流、出國訪問等,度過了充實、祥和的晚年。他所著的《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獲光明杯優秀哲學社會科學著作榮譽獎。
1986年,賀麟將舊作《當代中國哲學》改名為《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交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寫的序言中特別說明:“由于我當時對于辯證唯物論毫無所知,所以這次作了較大的修改。”新版將孫中山的知行說定位為“代表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對這個問題最高最新最進步的成就”;同時將思想譜系連接到毛澤東的《實踐論》,將后者作為知行哲學歷史發展的最后階段,“代表無產階級新民主主義的實踐論”。賀麟所做的思想譜系的變動,亦即砍斷孫中山與蔣介石的聯系,而將孫中山直接與毛澤東連接在一起。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陣營中,我們可以看到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認識論方面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現代認識論的內涵;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先秦諸子在現代的面貌。賀麟接通了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認識論思想的聯系,在現實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同時也為毛澤東思想研究提供了哲學基礎。
對于賀麟的一生,任繼愈先生在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一書序言中有一段很中肯的文字,他說:“如果深入地了解賀麟先生的為人與辦學,會發現他是舊中國成長的知識分子,從他身上可以看到影響深厚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這個傳統表現在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他是研究西方哲學的少數的專家,而他思想深處更多的是儒家入世、救世的傾向,往往被忽視。他的治學不光是說說而已,而是要見諸實行;他講學偏重在西方哲學,而用心卻在中華民族的安危存亡。他不滿足于講論的義理之學,他還要付諸實踐,參與社會活動和社會文化變革。可惜他所操之術和他的善良愿望未能吻合,以致走了彎路。直到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才算找到了最終歸宿,給自己找到了一個足以安身立命的地方。……雖說步履艱難,但是立足堅實,當初不輕信,既信了就不動搖。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在賀先生身上也體現得比較充分。”以上這段文字,算作對賀麟哲學思想的結語;更是告訴我們賀麟先生也與同時代的愛國知識分子一樣,也希望通過學術建國的思想和行動來為中國進步貢獻自己的學識。他的《文化與人生》就是一部這樣的書,書中每一篇文字都是由中國當前迫切的文化問題、倫理問題和人生問題所引起,而根據個人讀書思想體驗所得去加以適當的解答。
四、運用馬克思主義從事西方哲學研究
改革開放后,賀麟將治學的重點轉向西方哲學史,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撰寫和翻譯西方哲學,思考逐步轉向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賀麟的《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可以說是其介紹西方現代哲學的代表作。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是賀麟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學開設現代西方哲學課程的講課記錄,80年代經作者重新進行審閱和修改而成;下篇是新中國成立后寫的。上下兩篇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本演講集,賀麟不僅介紹了西方對我國有影響的哲學家,如柏格森、詹姆斯、杜威、羅素等,而且也介紹了在我國影響不大的哲學家,如愛默生、懷特海、桑提耶納、布蘭夏爾德等,足見賀麟對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工夫之深。正如周谷城在該書的序中說:“這本講演集大可以作為現代西方哲學史的入門書,也可以作為現代西方哲學史的補充讀本”。尤其是下篇,在分析批判方面,作者力求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為指導;特別是于對實用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的批判方面更是如此。新中國成立之初,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許多著作還未有中譯本,賀先生便直接從德文本引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來分析評論西方哲學。當然,這次講演集出版,這些引文均對照馬恩有關著作的中譯本作了統一,但指出這一點還是有必要的。因為它反映了賀先生在1949年以后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從事哲學研究的熱忱,也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
賀麟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有其三個原因:首先,熱切地關注國家的命運是他轉向馬克思主義認同的內在動力。當年學界中人,多抱學術救國之志,賀麟又何嘗不做如是想!從清華畢業的時候,他跟好友張蔭麟說:“一個沒有學問的民族,是要被別的民族輕視的。”其次,黑格爾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來源之一。作為黑格爾研究專家又有“幸運”一面:由于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之一,因此新中國關于黑格爾的研究與翻譯尚有一席學術之地。這也被認為是賀麟從“唯心論”轉向“唯物論”的內在關聯因素之一。黑格爾及之后的馬克思提出的哲學理論都完全可以解決客觀條件發展變化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對立及沖突。賀麟曾認為,“就作介紹工作的人來說,不介紹黑格爾使人懂得,不好;介紹黑格爾使人懂得了,不批判黑格爾,進而提高到馬克思唯物主義哲學也不好。就讀者來說,讀不懂黑格爾,不好;讀得懂黑格爾不能批判,作了黑格爾唯心論的俘虜也不好。這就是我深切感到的介紹黑格爾哲學的矛盾”。黑格爾的哲學對于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它是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甚至是整個馬克思主義體系的理論之源。最后,中國傳統哲學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相通性。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中所蘊含的唯物主義及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與發展,并為人們選擇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基因。這些契合點及互補處為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結合提供了可能性,隨之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賀麟的學生洪漢鼎指出:“在我看來,賀麟教授是能把西哲用中國語言表達出來的一位大哲學家。賀先生翻譯了很多黑格爾的東西,是研究黑格爾的專家,同時又是研究陽明學、陸王心學的代表性人物,所以他往往把黑格爾的理論一方面跟朱熹的理學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從王陽明心學的角度進行批判,等于把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結合起來了,因此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綜上所述,賀麟一生的最大兩個成就,一是用文化溝通中西主流思想的方法論,由此而為中國古代思想,特別是儒家,找到一條新路,即他提出的儒學宗教化、藝術化和哲學化。二是他對西方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思想的精湛的研究和翻譯,使“西人精神深處的寶藏”傳入中國,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理解和創造性地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在哲學史的思想淵源的發掘與進一步的研究方面,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