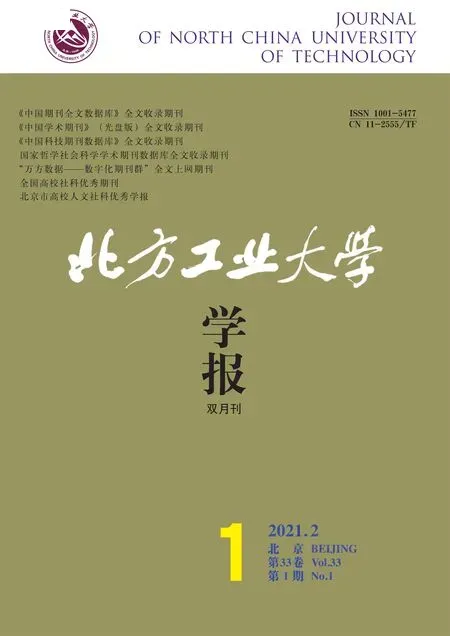高翔“畫為書余”說探析*
郭院林
(揚州大學文學院,225002,揚州)
清代汪鋆對“揚州八怪”有這樣的評價:“惜同時并舉,另出偏師,怪以八名(如李復堂、嘯村之類),畫非一體,似蘇、張之捭闔,偭徐、黃之遺規。率汰三筆五筆,覆醬嫌粗;胡謅五言七言,打油自喜。非無異趣,適赴歧途。示嶄新于一時,只盛行乎百里。”[1]汪氏認為“揚州八怪”雖然有異趣,但只是以偏師取勝,不算是正途,其影響也有限。這種評判反映的是評價者成見在心,不能容納新的藝術現象。倒是鄭午昌看到了“揚州八怪”的價值:“八怪……標新立異,機趣天然,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其或自放太過者,則亦不免粗獷之譏,然時人多師法之,大有轉移清代畫風之勢。”[2]八怪之一的高翔在繪畫方面別具一格,確有轉移清代畫風之勢。高翔畫作流傳不廣,詩歌也沒有刻印出版,今人研究多為介紹性質或文獻輯佚,而對其繪畫特色及其繪畫理論研究不夠。
高翔(1688—1753),字鳳崗,號西唐,又號犀堂、西堂、樨堂等,別號山林外臣,擅畫山水花卉,間作佛像人物;詩、書、篆刻也為世人重視,與高鳳翰、潘西鳳、沈鳳并稱“四鳳”。高翔好友汪士慎作有《西唐先生畫山水歌》,其中有關繪畫藝術特色與理論的詩句有:“瓦硯墨瀋常不竭,兔毫鼠尾皆成龍。……一筆兩筆峰插天,千林萬麓臨深淵。手辟心游意無盡,云根劃斷排空煙。……縱橫何暇法古法,狂掃已越荊、關前。先生作畫名書余,(薏田《書余說》云:“猶云詞為詩余。”)兩字流傳昔未有。從來畫法本書法,(樊榭銘云:“堁手作畫在倉頡后。”)曲折淋漓在心手。”[3]詩句注釋中提到的薏田即姚世鈺,他在《孱守齋遺稿》卷四《西堂山人書余說》:“余友西唐山人自題所畫曰書余。語人曰:‘吾之畫,吾書之余也,猶之詞之為詩余云爾。’”高翔的繪畫作品上也常鈐“西唐山人書余”一印。由此可以看出,他倡導“畫為書余”說,這對當時清代畫壇而言是一股清新的風氣,也樹立了寫意的大旗。那么“畫為書余”說的內涵為何?高翔作品如何體現這一觀點?其理論來源來自哪里?內在審美依據何在?高翔樹立這一觀點與當時社會背景有何關系,以及在當時的氛圍中,高翔這一理論有何個人追求?本文試圖對高翔“畫為書余”說涉及的上述問題作一探析,希冀能夠推動“揚州八怪”以及揚州畫派的理論研究。
1 “畫為書余”說的表現與內涵
現藏故宮博物院高翔傳世精品《溪山游艇圖》軸,畫高山峻嶺,自右向左逐漸降低,山坳白云飄渺,林木繁茂;左山頂及右山底有房舍、幽篁、籬墻。山腳平溪一泓,臨水有樓亭水榭,水中一舟載客泛游。山石皴染并施,林木勾點結合,構圖高遠,用筆圓潤,意境清幽。其中題識有“特將殘墨畫山丘”,時年作者35歲。[4]另有《梅花圖軸》繪梅花,一枝昂揚上展,一枝被風雨折斷下垂,枝上梅花寥寥數朵。構圖新穎,筆墨簡潔勁健,設色清淡,別具風致。現藏上海圖書館《山水冊》,共十二開,或畫煙嵐幽居,或作林泉水榭,或畫蕉林對溪,或作高山平湖,或畫松下聽琴,或策杖歸山,或畫環江樹舍,或作策蹇尋幽,用筆簡淡,景物幽深。總體看來,高翔畫作俱用筆洗練,墨色清淡,構圖疏遠,意境幽深。
高翔評論自己的山水畫說:“吾以山水勾勒為奇,以皴染為偶,蓋將離絕遠去筆墨畦畛之外。……而客猶剪剪拘拘, 執唐宋作家院體筆虛、筆實、六法、六病之常格以繩之,……”[5]所謂“筆墨畦畛”,也就是作畫的技巧與規范;要超越這些,關鍵還在畫者自身的內在修養。他對繪畫學史與繪畫界現象進行評論道:“畫宗分南北,論說紛如麻。大要無多旨,筆墨生清華。天成靈秀姿,揮灑任橫斜。不在巖壑奇,不患時眼遮。能品遜逸品,士氣勝作家。甜邪與俗癩,四病休相夸。金丹不可得,換骨事終賒。縱有盧扁在,束手徒咨嗟。是惟同心者,所見當無差。”[6]“山壑之奇”屬于取景的客體,“時眼”是當時的欣賞觀念,“能品”是技術之作,“逸品”則是胸中逸氣所產生的作品,所以一個人的氣質遠比技法重要,更為關鍵。“邪甜俗賴”是元代黃公望在《寫山水訣》篇中提到的四種弊病:“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字。”[7]元末明初的王紱在其所著的《書畫傳習錄》中解釋為:“邪,是不正規,不學古人,信手涂抹,妄生枝節;甜,是只在色彩悅目上下功夫,于傳神上則無能為;俗,則務華媚柔細;賴,指一味摹擬古人,泥古不化。”從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高翔認為山水畫的成敗不在于所取景致,也不應受通俗觀念影響,技巧不是決定因素,最高境界還取決于作畫者和欣賞者的內在氣質,而非后天習得。
高翔“畫為書余”說缺乏系統論述,我們只能從他的畫作和題畫詩的內容及其風格來理解。從上引《西唐先生畫山水歌》可以看出汪士慎對高翔不師古法、自成一格的山水畫十分推崇,也可以看出高翔作畫特點:“……一筆兩筆峰插天, 千林萬麓臨海淵。手辟心游意無盡, 云根劃斷排空煙。……縱橫何暇法古法,狂掃已越荊、關前。……”在中國畫史、畫論中,荊浩、關仝并稱“荊關”。荊浩、關仝以北派山水名世,畫風雄峻繁密。而高翔繪畫用筆簡潔,似乎為書家的筆法。
高翔自評《山水冊》云:“信筆入縹緲,咫尺迷云煙。”[8]金農評價其畫云:“高生作圖畫,送予還鄉土。淡墨善工愁,至情寫終古。”用墨清淡是可見的形式,而所謂“工愁”與“至情”則是不可見的思想感情,這也就是高翔自己所認為的“士氣”與“逸氣”。《冬心集拾遣·題高翔畫冊絕句十二首》的第五首云: “高山流水思渺然,精華落紙總云煙。看君惜墨如金意, 畫訣全參冷處禪。”第七首云: “帆影粘天淡欲無, 松嵐遠寺半模糊。可知著紙無多筆,便是江天萬里圖。”跋: “嘗見西唐山人畫梅,皆疏枝瘦朵, 全以韻勝。……隨意涂抹,而氣韻靈動,非食煙火人所能夢見。……觀之者恐嗤吾曹皆山中白云耳。”[9]《冬心齋研銘·西唐山人畫山研銘》:“作畫不燒枯樹枝,鼠須蘸墨何所師?妖花暴禽君弗為,隔江晴翠窗案間。故宮紈扇湘竹斑,輕描細染南朝山。”[10]無論是惜墨如金,還是疏枝瘦朵,都是形式上用淡墨,以簡馭繁,“韻”很抽象,更多是內在精神,而達到“韻勝”的關鍵也在于“冷處禪”。
“禪”為佛教名詞“禪那”簡稱,梵語的音譯,意為“思維修”或“靜慮”。作為佛教的一種修持方法,摒棄外緣(外在事物),不受其影響;把神收回來,使精神返觀自身(非肉身)即是“禪”。這其實就是強調畫者的內心認識。禪悟的各種途徑與方法,歸根到底是為了見性。方立天認為“見性”,就應實行無相、無念、無住的法門,也就是不執取對象的相,不生起相對性的念想,保持沒有任何執著的心靈狀態。”禪宗追求的自由“表現為以完整的心、空無的心、無分別的心,去觀照、對待一切,不為外在的一切事物所羈絆,所奴役,不為一切差別所拘系,所迷惑。”[11]金農評價說:“煙泉奇想本天開,林木無妨信手栽。”[12]高翔畫作正是以禪理通畫理,打破現實局限,而作心靈的寫意。高翔畫作多寫“云”,如“云凈天空有墮痕”(《題呂半隱山水二首(其二)》),“咫尺迷云煙”(《題山水冊頁八首(其一)》),“沖煙弄云亂”(《題山水冊頁八首(其二)》),“云澥幻奇跡”(《為鏡秋作〈笙山圖〉并題》)。[13]“云”具有悠閑的意味,觀照者將自身的情感附加其中,云由外在的自然物象轉化為悠然自在的禪意象征, 自此而與心靈融為一體。
高翔大幅山水畫缺乏氣韻,筆墨顯得松散,張庚批評他“于近人問途徑”(《國朝畫征錄》),認為這是沒有學習古人筆法的緣故。筆者認為,一方面是高翔沒有機會到名山大川進行體驗,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高翔的理論突破與創新。高翔繪畫用筆簡靜,書卷盎然,無論是疏枝瘦朵、帆影粘天、山疏瘦樹,都可以看出作畫者高翔對描繪客體的輕視,或者說是縮小客體的重要性,其目的是為了突出主體的性情。“信筆”或“隨意”不是任意而為,而是以意為主。正因為如此,他才能“以山水勾勒為奇”,一筆兩筆即成千林萬麓,無多紙筆即是萬里江天。從中可以看出高翔畫作不注重客觀寫實,而是借畫作抒寫性情,注重距離美與朦朧美,以寫意為主,是真正意義上的“寄情山水”“意內言外”。高翔“畫為書余”說不僅在形式與結構上認為畫為書余,更為根本的是他認為書更具有表意的功能。
“畫為書余”說反映了高氏對當時精描細摹畫風的鄙視,所以他才認為書法是主,畫為其次。“畫為書余”,原因在于書法更為抽象,更能反映個性。正如詞被稱之為詩余一樣,高翔把畫稱為書余,在認識觀念上有主次之分。從表述意義豐富性的角度看,繪畫的形象性反而局限了主體思想的表達,也局限了讀者的想象與二次創作性的閱讀;在這個意義上,畫為書之余,繪畫不及書法表情達意。高翔畫作的妙處不在于對客體精確描繪,而在于表現主體的內在精神,通過畫面與文字書寫,激發讀者想象,這樣才能“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陸機《文賦》)。總之,“畫為書余”說體現了高翔追求古樸淡雅,追求抽象寫意的藝術理念。
2 “畫為書余”說的師承與審美依據
高翔少年時期崇尚石濤,后結識為友,常相往來,情誼深長,受益頗深,是石濤的摯友和忠實追隨者。高翔“畫為書余”說師承石濤繪畫理論。石濤曾對李驎說過:“所作畫皆用作字法布置,或從草書,或從篆隸,疏密各有其體。”[14]而且他還提出書畫同源,在《石濤畫語錄》說:“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丘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后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岳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太古無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畫。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一畫是形象的基本單位與元素,所以是本、是根,它是眾畫的基礎與基調。[15]這里所說的一畫,是指書法上的筆畫,筆畫雖然簡單,但每一筆都應該具有變化,都有自己的形式,一畫就是繪畫的最小單位。所謂“一畫”實際就是一劃,也就是筆畫,這是繪畫的構成元素,也是繪畫的開始,所以,“此一畫收盡鴻蒙之外,即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終于此”(石濤《畫語錄·一畫》)。
石濤反對技巧的作意,而崇尚天真傳神,在《鳳岡高世兄以印章見贈,以書博笑,清湘遺人大滌子草》提到:“書畫印章本一體,精雄老丑貴傳神。秦漢相形新出古,今人作意古從新。靈幻只教逼造化,急就草創留天真。”他認為書法與繪畫都以氣勝,以少為精,如其題畫詩跋:“作書作畫,無論老手后學,先以氣勝得之者,精神燦爛……多則泛濫,少則精雄。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畫作個性基礎乃在一畫之中可見,一畫之法也就是自我個性。“我”乃創作主體的泛稱。“本之天而全之人”,天是自然,是外在客體,而人是主體個性。美的客體與能夠表現美的主體相結合,才有美的畫作,這是石濤的經驗之談。“山林有最勝之境,須最勝之人,境有相當。石,我石也,非我則不古;泉,我泉也,非我則不幽;山林知我山林也,非我則落寞而無色。雖然,非熏修參劫而神骨清,又何易消受此而駐吾年?”(《山林勝境圖題跋》)強調主體感受與表現能力,這些理論強調主體的內在精神與以簡馭繁,直接影響到高翔的繪畫觀念。石濤強調作畫要有個性,崇尚古淡,不要跟隨時代風氣:“筆墨當隨時代,猶詩文風氣所轉,上古之畫,跡簡而意淡,如同漢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畫,如初唐盛唐,雄渾壯麗;下古之畫,如晚唐之句,雖清麗而漸漸薄矣;到元則如阮籍、王粲。倪黃輩,如口誦陶潛之句:‘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恐無復佳矣。”越往古代追尋,藝術形式越古樸與混溶,這才是高翔與石濤他們的藝術追求。
當然,石濤關于書法與繪畫二者聯系的觀念也是淵源有自的。曹植曾在《畫贊序》中說:“蓋畫者,鳥書之流也。”[16]鳥書為書體之一,屬篆書的變體。此論則視畫為書之附庸。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提出線是畫的基礎:“無線者,非畫也。”元代大畫家兼書法家趙孟頫,是“書畫同源”之說的最早的提倡者。北京故宮本《秀石疏林圖卷》卷后可見他在自己畫的《秀石疏林圖》上題寫了“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宗白華斷言:“中國畫自始至終以線為主。”[17]而書法藝術與線最為接近,是用線的運行來表現主體思想的。無論古今中外,最初藝術形式都與線相關。而中國書法與線又有所不同,突出特點則在于筆。[18]毛筆柔軟,一筆一畫都具有自己的表現力,而不是單純的幾何線。同時書法對象是文字,漢字先天性就是表意的,所以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中說:“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19]實際上,書法來源于繪畫,先有具象,然后才有抽象的文字。因為漢字象形的特點,所以與繪畫具有密切聯系。
如果從事物發展過程看,萬物的發生都是從少到多,從簡單到復雜的一個過程,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道德經》)。據說倉頡造字就是模仿自然物象,而這也就是漢字的象形特征,因為象形才發展出表意。文字強化繪畫,繪畫強化文字,思想和含義得到了完美的表達。我國詩、書、畫向來兼容不分,相輔相成。漢字形聲俱備,以象形表意為主,不論聲音情意,已有造型圖畫之美。字能見其意,而畫在達意方面而言,實在是“書之余”。所以高翔的“畫為書余”說正可以從寫意的角度來理解,可以看作寫意大旗的宣示。
3 高翔的性情與藝術追求
揚州地處運河與長江交匯之區,水運便利,尤其是清代,鹽商聚集,帶來經濟繁榮,同時也促進了當地的文化事業的發展。《揚州畫舫錄》記載,雍乾時先后居揚畫家達80多人。繁華的經濟培育了藝術市場,也從不同方面陶鑄著藝術家的風格。前引金農評論高翔畫作時,多次提到高翔畫作是不食人間煙火人所作,其實恰是反映了高翔不與俗流的高超人格。高翔甘于貧賤,笑傲富貴,正如金農所評價:“西唐山人甘草莽,瘦肩削玉狀貌古。傲俗竟如寺僧床,笑視朱門若蓬戶。”[20]雖然高翔居住地離商人富戶不遠,但似乎各不相干,汪士慎有詩云:“五岳堂上生清風,檐花石竹香蒙蒙。兩深苔老戶常鍵,二分月墮蓬蒿中。”《和西唐行盦雅集未赴之作》:“野人久已心如水,蓬戶春寒懶拂箋。”[21]雖然生活艱難,但他與汪士慎卻能夠引為知音,慰籍彼此的心靈。汪士慎在《贈西唐五十初度二首》中寫道:“猿鶴狐蹤不易同,到今誰復問窮通。七條弦上知音少,三十年來眼界空。每欲放杯還藉酒,不言生計轉如篷。相交相愛垂垂老,朝夕過從風雨中。”[22]用好友的話來說,那就是“嗜好殊人推狂夫”[23],“耽幽性所偏……孤調與誰憐”。[24]高翔在《山水冊(三)》提到:“心癖無機事,家貧有破書。年年居硯北,自喜作閑居。”[25]高翔在常人看來是怪,是“狷潔不可浼”。[26]他耿直,不肯同流合污,毫無世俗之心。其六:“莫怪蓬萊少,連朝風雨多。空齋容懶慢,點筆自為摩。”對世俗懶慢,卻對繪畫執著。其七:“茂林坐終日,青山娛我情。更憐白云外,西走晚淖聲。”其八:“老樹入云拏,林皋處士家。窗閑何所事,終日弄煙霞。”在繁華的揚州市過著隱逸的生活,這是他的超塵脫俗,正是他的這種精神追求,才使得他提出“畫為書余”說。
高翔重視繪畫表達主體思想,從而也注重畫作的學識基礎:“擁書鼓神智,猛如食葉蠶。垂老且弗惰,趣味殊自甘。”高翔讀書不是為了入世,而是為了自己的內在修養。華喦贈詩也稱高翔:“養學固履道,抱德誠足耽。沖靜自然古,恬潔無可貪。”[27]高翔出生于書香門第,父親高玉桂是位貢生,祖父高治安是詩人。高翔嗜書而不好交友:“避客年來高鳳岡,扣門從不出書堂。”(董偉業:《揚州竹枝詞》)高翔在29歲時就將自己的住所題名為“煮字窩”,這也可以看出他的修養與追求。“煮字窩”是江都盛端明的住所,盛端明鉆研古文字雖處窮惡之境而矢志不渝。(參閱故宮博物館楊維楨書《煮字窩銘》軸)高翔也像盛端明一樣熱衷藝術。《月夜青燈圖》可以看出高翔在深夜挑燈夜讀的情景。高翔題畫詩往往將寫景與歷史反思結合起來,從而令讀者能夠跨越時空,產生聯系與思考,如:“最繁華地久知聞,無賴多因月二分,廿四橋頭簫隱隱,玉人難覓杜司勛。”[28]類似的題畫詩多寫平山堂上的歐蘇、紅橋的王士禎,從中可以看出高翔深厚的學術功底。據友人汪士慎記載,乾隆七年(1742),友朋雅集小玲瓏山館,高翔作《雨中集字懷人詩》120首,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學。[29]
此外,高翔的童真性格也是他藝術獨創風格形成的原因之一。在他50歲時,友人還評價他“松筠健質嬰兒性,日日斑衣戲老萊”。[30]老萊子是二十四孝人物之一,為了使年邁的父母開心,在自己70多歲的時候還時常穿著彩衣,做嬰兒動作。詩中不僅寫高翔怡悅父母,而且始終保持著童心。他的言談也是“笑談隨處見天真”。[31]李贄為明代哲學家,力倡“童心說”,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32]藝術創作確實如此,沒有童心,便少了真善美。
高翔的藝術特色與其禪修功夫也密切相關。他一生追隨石濤,甚至在石濤死后還時常祭奠。石濤出家,藝術多得禪理,其《畫語錄》也是禪宗表現出的思想火花。如上所述,高翔繪畫多得其傳。另外,好友汪士慎和他都好茶,茶禪一味。揚州佛教源遠流長,有“八大名剎”之說,平山堂(法凈寺)、觀音山、禪智寺、鐵佛寺都是他常去禮佛之地,也是他繪畫作詩的題材。鐵佛寺古水禪師是他的好友,他有多首詩歌寄給古水禪師。天寧寺和尚筑成“彈指閣”,他為之畫圖并作詩《彈指閣》。他的《鐵佛寺詩》中就有“佛容常自在,頑鐵不消磨”,很有禪味。乾隆七年,他和汪士慎等集會于寒木山房,瞻禮觀音畫像,遂作有《六月十九日瞻禮大士畫像》,其中提出:“未窺釋氏書,難以論終老”,“吟懷入禪味,藉以寫孤抱。”[33]
八怪崛起前的揚州畫壇,康熙年間顧符禎、蕭晨。顧作山水,工細入毫發,臨古跡可以亂真,如《論松圖》;蕭師法唐宋人,人物設色妍雅,衣紋清勁。而高翔一反以往畫壇的風格,以淡墨寫意,以簡馭繁,減弱客體的真實感,而突出主體的抒情性。他提出“畫為書余”說,一方面表明自己不與主流畫壇合作,另一方面也豎起大旗,走向寫意派。書畫互通,一則基于作者深厚的學識,二則也是禪理認識的提升,三則是主體創作者甘于淡泊,另辟蹊徑的理想追求。高翔“畫為書余”說為清代畫壇提供了新的方向與嘗試,從而也豐富了我國的繪畫實踐與繪畫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