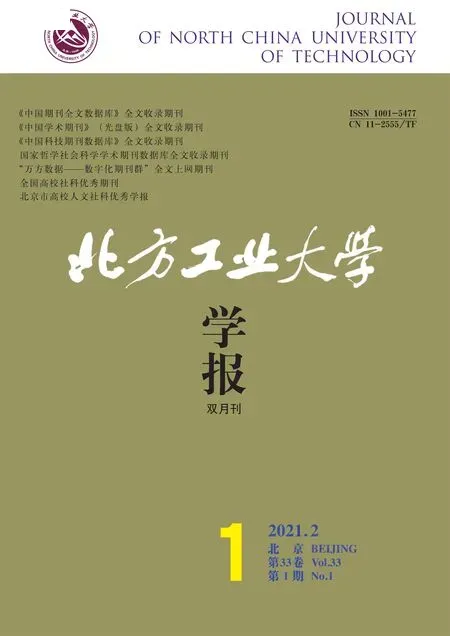一多不分:獨特的中國傳統文化“天人”觀*
谷文國
(1.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100872,北京;2.中國人民大學茶道哲學研究所,100872,北京)
中國古人獨特的“天人觀”——宇宙觀、思維方式和道德觀集中體現了傳統文化一多不分的特質。《中庸》里面講“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為物不二”即是道,是一;“生物不測”即是萬物,是多。“不測”寓意不定,即變化,表示沒有絕對之意。孟子說“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一本”喻意的亦即是道和萬事萬物之間的一多不分。
1 盤古開天辟地:一多不分的宇宙觀
把握傳統文化一多不分的內涵,首先應該從中國古人對宇宙(也即天地)的思考和認識,以及對自身的起源,也即整體上對天地人之間關系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古人對整個宇宙(天地)起源和發展的解釋相較于西方,凸顯了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重要而根本的一個特色,即一多不分。正是基于對宇宙(天地)的起源和發展從整體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中去認識和理解,中國古人形成了看待經驗世界和自然以及人類自身的獨特的思維方式和道德觀。關于這一點,西方學者葛瑞漢(Graham)曾敏銳地指出:
中國宇宙論將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互相依存的。它不用超越原理解釋萬物,也沒有規定一個超越的源頭,一切事物都由這個源頭產生出來……這種看法新奇之處,在于它揭露了西方詮釋家的先入為主,以為“天”和“道”這種概念必定含有西方那種終極原則的超越性。[1]
葛瑞漢的觀點之所以顯得特別,是因為他在某種程度上跳出了西方的單線單向思維模式,洞察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根本之處。它和西方基督教的宇宙觀,即一切事物都最終取決于一個并且只有通過一個超絕的創造萬事萬物的至上神才獲得其意義,是截然相反的。這可以從中國最著名的創世神話——“盤古開天辟地”來比照。盤古開天辟地最集中地展示了中國古人對宇宙(天地)的整體看法,也即如何從人與天地萬物之間不可分割的整體性的關系之中去理解和把握整個宇宙(天地)。在張光直先生看來,“這種宇宙觀在中國古代存在的特殊重要性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明在它的基礎之上與在它的界限之內建立起來這件事實。中國古代文明是一個連續性的文明”。[2]
1.1 天人合一:一多不分宇宙觀的起源與發展
盤古開天辟地的故事最早見于三國徐整所著《三五歷紀》: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在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故天去地九萬里。后乃有三皇。天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啟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為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云。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岳。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里。肌肉為田土。發為星辰。皮膚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甿。
這固然是后世的神話,但由此正可看出中國古人對宇宙(天地)起源的獨特看法,也即“充滿互系的宇宙”,用中國傳統的術語來說就是天人合一。張光直先生也認為天人合一是“傳統的重要宇宙觀”。[3]天人合一的思想獨特地揭示了古人關于天地人三者之間相互依存和轉化的關系,這種互系性的關系維系著彼此之間的連接和會通。張光直先生曾舉15世紀墨西哥的阿茲忒克人為例,說他們“視宇宙為各種生命力之間的關系的反映,而生命的每一個方面,都是在一個內部關系互相影響的宇宙體系中的一部分”。[4]
這種描述何嘗不能用來描述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呢?它同古希臘本體論和形而上學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不存在“希臘抽象意義上的秩序法則,沒有超然無上的一獨立于被秩序化的世界,并將被秩序化的世界作為它效力的結果。相反,中國只有發現于世界本身之內的、永遠變化中的過程常性。是它使得世界具有某種連貫性和定性,又由于其內在的不定性而顯得出新和不可預測”。[5]
盤古“生在其中”已然昭示著天人之間的聯系要比后人想象的更為密切和融合。《莊子·齊物論》中所謂“天地與我并生”充分表達了古人對天地人的根本看法。它絲毫不同于西方那種單線、單向的絕對邏輯推演,規定萬物必須從一個處于人類經驗之外的、至高無上的“絕對物”那里虛無地創造出來。“并生”二字很鮮明地點出了天地人之間那種互相依存的互系性,而且作為一個動態的延續過程,它是持續存在的。相信這種“存有的連續”是中國古代宇宙觀的一個主要基調。[6]這里面沒有絕對主宰,也沒有二元對立,是真切實在而不言自明的。熊十力先生曾指出:“吾人或一切物之變化自新,即是人與物各各自變自化,自創自新,未有離吾人或一切物而獨在之化源也。”[7]牟復禮也認為:“中國沒有創世神話,這在所有的民族,不管是古代原始,還是近現代的民族中都是獨一無二的。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不存在創世者,沒有上帝或終極起因,也沒有超然于宇宙之外的東西。”[8]
“神于天,圣于地”所表達的也不過是盤古能夠窮盡天地之精微,與天地同體,絕不像西方那個不能為人的智慧所把握的上帝一樣。所以隨著天日高地日厚,盤古亦隨之變化而實現與天地的合一。這種合一無疑就是徹底的融合,也即變通,即人與天地萬物之間所形成的那種動態的生生不息的共生關系,它并不屬于人類經驗之外的超絕的世界,而就在人們日常生活的天地萬物之中。按照張光直先生的看法,“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概念,建基于人類和自然之間一種和諧的關系,建基于傳統文化行為的一致性,這些行為表現在農業、建筑、醫藥、畜牧、烹飪、廢物處理以及物質生活的每一方面。而西方觀念卻不然”。[9]
盤古“垂死化身”的事實則進一步說明我國古人認為人和天地萬物在根本上是和諧、渾然一體。莊子說“萬物與我為一”就是對此最好的詮釋。自然界的一切,無論日月風云抑或江河草木都是作為人的盤古身體的某個部分化生的。這就意味著萬物不是由另外一個獨立于其外的上帝創造的,彼此之間沒有一個超絕、凌駕于一切之上的東西存在著。萬物在某種程度上是作為人的盤古的某種延續,而作為人類“黎甿”又復從天地化生而來。說明人與天地萬物之間存在著一種變——通的關系,這種變通也即道,其最重要之處在于在變化中沿循連續,沒有西方那種絕對抽象意義上由一創造多的問題。《大戴禮記·哀公問》說“大道者,所以變化凝成萬物者也”,即是變通之意。
莊子不是曾說“圣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嗎?對于不能為人的直接經驗所認知和把握的六合之外的一切東西,古人是不去作抽象的思辨和論證的。一切辯域都在六合之內。因此,莊子說“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莊子·天下篇》)
1.2 互系變通:一多不分宇宙觀的連續性
發端于古希臘的西方宇宙觀觀念與連續性的中國文化有著根本的不同。在這一點上,安樂哲先生也認為中國的宇宙觀是一個“不斷發展和成長的過程,每一環節都比上一個更有意義,沒有命中注定潛在能力的線性實現”。[10]
就連續性而言,牟復禮(Frederick W.Mote)也表達過相近的論斷:“真正中國的宇宙起源論是一種有機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論,就是說整個宇宙的所有的組成部分都屬于同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且它們全都以參與者的身份在一個自發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11]張光直則進一步指出,牟復禮所說的這個“有機物性的程序”,“呈示三個基本的主題:連續性,整體性和動力性。存在的所有形式從一個石子到天,都是一個連續體的組成部分……既然在這連續體之外一無所有,存在的鏈子便從不破斷。在宇宙之中任何一對物事之間永遠可以找到連鎖關系”。[12]這種“連鎖關系”就是互系性、連續性。這個動態的過程恰恰與西方相反,沒有無中生有地制造、創造一類的普遍遵循唯一神的旨意的說法。變化連續都在人類的經驗世界之內,這種連續包括“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連續,地與天之間的連續,文化與自然之間的連續”。[13]
即宇宙中的一切都處在連續之中,“不是來自‘無中生有’,不是從什么獨立、外在本源而來,不是從‘一神’、‘自然法’概想而來,不是從柏拉圖‘繆斯’理想而來,也不是從什么標新立異、遁世隱居的天才那里來”。[14]關于這一點,杜維明先生也曾經指出,“中國哲學的基調之一,是把無生物、植物、動物、人類和靈魂統統視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關乃至相互交融的實體。這種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長江大河來譬喻的‘存有連續’的本體觀和以‘上帝創造萬物’的信仰把‘存有界’割裂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學決然不同”。[15]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則根據考古發現的新材料指出“中國的形態叫做‘連續性’的形態,而將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態”。他同時比較分析了西方文化及其思維方式的弊端,不妨摘引如下:“產生那種適用于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一般理論的那種西方經驗,必然從它一開始便代表從其余的人類所共有的基層的一種質上的破裂。當我們檢討那已被追溯到近東的那種經驗的史前史時,我們果然見到另一類型文明的形成,而這種類型的特征不是連續性而是破裂性——即與宇宙形成的整體論的破裂——與人類和他的自然資源之間的分割性。”[16]
正是基于這種不同于西方的互系的、和諧變通的宇宙(天地)觀,古人形成了認識宇宙(天地)的方法,即在長期的日常生活經驗之中,在“延續、生成、生息萬變的現象世界”[17]中通過“觀”和“感”來審視和把握自身與天地萬物之間的關系。
2 觀與感:一多不分的思維方式
《周易·系辭下傳》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法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氏即是被視為人類始祖的三皇之一伏羲,后于盤古而生。“觀”,按照《說文解字》的解釋,表“諦視”之意。《榖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段玉裁注:“凡以我諦視物曰觀,使人得以諦視我亦曰觀。”可見“觀”是貫通人與萬物之間的,能為人的生活經驗所把握和認知。之所以遍觀上下遠近,就在于試圖從天地萬物之間的聯系中通曉一切物事,實現彼此的會通。這種會通作為人的活動本身就其本質而言不是單向的,而是在彼此的互動往復中作為天道的一個重要部分構成天地化生。
2.1 觀:一多不分的認知方法
《周易》中有“觀”卦,次于“臨”卦之后,謂“能臨物者,因其順乎天行而有容,可以為萬物觀仰,故觀之時與臨相同,亦具四德。能使物可觀者,即天道依其神明而妙萬物之德也,物既成器可觀,則可薦之于神明。故人能仰觀此物,實即仰觀此神明之德,是即觀也。”[18]是故,“觀”雖指向的是天地萬物,實則是觀萬物之所以上通于天而天示為神明之德者。簡言之,仰觀神明之德即觀天地之道。《周易》謂“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順”是順乎道之意,“巽”即入,觀天下即寓意要順天之道而為。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的真實含義亦即如此。“神者,妙萬物而不遺者也,大觀秉乾元之德,故可妙萬物而不遺,行乎四時而不違,是所謂天之神道。”[19]“觀”豈不是要與“道”打通之意?王弼謂:“統說觀之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20]可見“觀之道”在于“以觀感化物”。這就把觀和感與物通貫起來,納入到一個互系的狀態之中。
相較于西方而言,這里的觀更多地指的是用心去觀,而非單純地用眼。古人認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黃帝內經·靈蘭秘典論》)。《周易·系辭上傳》不是說“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嗎?故可說“觀”在于通過心眼相通進而與天地萬物相通。“圣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之意就在于從人類自身的經驗中把握到通貫于一切變化之中的延續性的恒常之道。東郭子曾問于莊子,所謂道,惡乎在。莊子說“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后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知北游》)可見沒有“道”外之物,亦可以說“道”遍布于天地萬物之中,并非在天地萬物之外獨立存在。任舉一物,皆可以征驗大道。道是一,而萬物是多,道無所不在即意味著一多不分。
始于伏羲的“觀”即是觀于萬事萬物,這里面固然有其作卦的意思在其中,但實際上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要“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即要與天地萬物打通。“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周易·系辭上傳》)就將“觀”的功用推延至更廣闊的人生實踐之中。這種實踐完全是人類自身活動的經驗體現,并不必然與抽象的超絕的東西聯系在一起。
2.2 感:天人之間的相應
觀而后有感,感而后能通,所以《周易》中講“《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即動于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即意味著人與天地萬物是息息相關、可以會通無礙的。六祖慧能大師在《壇經》中說“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指的也是通感之義。《禮記·學記》中謂“感于物而后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就凸顯了感的重要性。觀之于外,自然感之于內;內心有感,天地萬物亦自然有應,感應道交,就形成了我國古人獨特的“天人相應”的思維方式。我國古代中醫理論著作《黃帝內經》中即說“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也”。它完全不同于西方上帝式的啟示,呈現為自上而下的一種絕對命令和約束,人類只能聽從于上帝的安排。
從這個角度而言,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孟子·盡心上》),可以視為是對古人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闡釋和發展。反身而誠之所以被古人視為重要的修身路徑,也在于天地人之間的互系和感通。觀、感打通了人和天地萬物之間的聯系,證明天人之間截然不可分割,一切事物莫不處于互相依存的關系中,亦莫不可以會通。這種會通無疑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它所體現的正是一種存有的連續。作為人的盤古垂死化身為天地萬物,天地復又蘊生人類,這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國古人的思維方式必然是天人相應的,也即必然要從彼此之間的互系和通感中去理解和認識萬事萬物。王陽明先生曾說:“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傳習錄》下)。這豈不是宇宙天地萬物與我為一,彼此能相通、感應的意思?如果天人之間是西方式的既二元然對立,如何能實現兩者之間的感通呢?倪德衛(David S.Nivison)也曾指出,“宇宙與‘此心’一體,與我們一體,滲透著心性,內在于我們,而不是外在于我們”。[21]這種互系性的思維方式對我國古人道德觀,即以仁德為本的五倫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3 天生德于予:一多不分的道德觀
《禮記·禮運》謂人乃“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這正是從天人合一的角度理解和詮釋何為人。這里的“人”顯然不是西方意義上作為單獨個體由上帝按照其形象創造的人,而是處于互系關聯之中的作為社會性的人。換言之,這里的人是作為“存有連續中的一個環節,和天地萬物發生有機的關聯,而不是獨立于自然之外,由上帝根據自己的形象所創造的特殊靈魂”。[22]莊子假舜之言謂:“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莊子·知北游》)
這即是“作為存有連續中一個環節的人”與“天地萬物發生有機的關聯的”根本體現所在。德者,得也。所得即天地之道,也即得一。故而其道德亦莫不法天則地,遵循天地秩序。“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周易·系辭上》)就是對道德效法天地的一種最好描述。天行健、地勢坤也同樣可視為是人類道德導源于天地的一個側證。莊子說諸多“一曲之士”“寡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莊子·天下》),從反面凸顯了人與天地之間的密切聯系。神明之容即神明之德,莊子此句寓意人已很難達到古人所謂的與天地之德合一的境界了。
從《論語》來看,“天生德于予”的說法固然展現了孔子對自身德性的一種自信,但也從另一個側面透露了古人關于道德來源于天的看法。也即中華傳統的人倫觀念、對于人來說由己而出的道德,其實與天地之德是不二的、原為不分的、共生的。所以,孟子常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在于使人們能夠“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下》)。
《周易·系辭上》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坤以簡能;易則易,簡則易従;易則有親,易従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23]這不就是從天地萬物之間的關系的角度洞察人類道德的起源嗎?天地人之間的互系性決定了人類五倫觀的產生也必須從一多不分的角度去考慮。安樂哲先生曾指出,“‘互系性’的宇宙觀起到的作用是儒家思想發展進化的特殊場域,在這一宇宙觀內,任何事物都不是脫離它所在的環境關系,自己孤立發生的”。[24]
從甲骨文以及早期儒家文獻對“仁”的界定和描述中可以看出,仁德必須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才能被正確體察和認知。“五倫”作為人類普遍存在的經驗的整體性,從根本上決定了“把經驗意義的關系作為互相構成性的這樣的認識”[25],是理解古人道德觀的一個重要路徑。五倫關系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西方理解的那樣由超驗意義上的神憑空創造的。每一個人都處在一個變動不居、錯綜復雜的連續性關系之中,通過真切實在的能為人把握的直接經驗而在自己與家庭、社會和國家以及萬事萬物的關系中不斷地成長。只有從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國家的互相依賴的關系中才能把握到五倫道德觀真正的內涵。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曾指出,“我的生命不是維持這種關系的一種手段,這種關系就是我的生命,而不是某些外在于我的生命而讓我為之服務的東西。我生活中的每一種這樣的關系,如果它確實是一種真正人性化的關系,那么它就會構成我的生命,因為正是通過生活在這么多的關系之中,我才獲得一個更加完整的人的生命”。[26]因此,可以說“‘道德’的人的最基本現實乃是…社會的相系,眾人乃至萬事萬物皆是在社群生活的大環境接受各自的、相對的位置。人自身是個抽象觀念,是從社會的現實情況中抽象出來的一系列復雜特征的組合;而社會現實不是抽象觀念,而是不可取代的具體現實”。[27]
這也即意味著道德只能從社會的相系、不可取代的具體現實中去理解和認識。它并不是抽象的、源自上帝的特殊規定和賦予。沒有脫離于人之外的仁,也沒有脫離君臣之外的義,等等。只有進入到人與人、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關系之中時,才能生成真正的道德。這種道德如杜維明所說,“以人為關系網絡的中心點,而這個中心點落實在每個活生生的人身上,同時有開放性,逐漸的展現,能夠和宇宙大化連在一起,這是我們真正能夠安身立命的地方”。從這個層面上而言,古人的宇宙觀、認識宇宙的方法及其思維方式、道德觀是一以貫之的,徹上徹下貫通天地人三者。從儒家角度看,也即在彼此互系的基礎上達到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境界。杜維明先生曾指出,人的生存形式不是以人類為中心的,而毋寧是天人交感的;在人類世界與宇宙秩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相互影響、持續溝通和活力交流。
這才是一以貫之之道,也才是作為內在于傳統文化核心的儒家精神的價值體現。作為一個延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的核心——“道”是古圣先賢對人類經驗的一種重要解讀和詮釋,它從根本上有異于西方那種超驗原理的單向價值觀和道德觀。“道”是一個不斷延伸和拓展的生命體驗,因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人們在這個過程中通過不斷的體察和感悟而效仿天地化育的生生之德來塑造自己。正是在這種能動性的推動下,人們不僅僅看到了天地萬事萬物之間內在的聯系和相互依存性,更在其中發現了茍日新,又日新的自我完善的可能和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