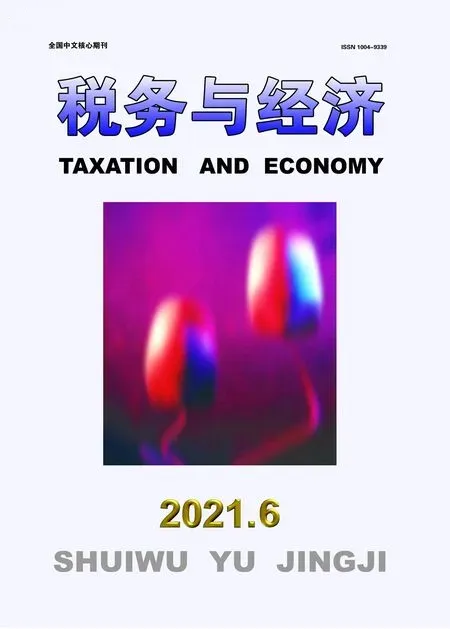多邊公約視角下我國對“一帶一路”非居民財產收益課稅問題研究
林星陽
(廈門大學 法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5)
經濟全球化的三大特征之一是以“共同的國際治理規則為基礎的多邊合作”,良好的國際貿易、投資環境亟需普遍認可的多邊合作來消減包括稅收在內的多種國際貿易壁壘。[1]雙邊協定曾在應對國際重復(不)征稅中一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因僵化和滯后性致使其在應對層出不窮的國際稅務新問題時逐漸失去功效,而逐個更新又顯得漫長而冗雜。國際治理的終極原則及目標在于世界為全人類所共有,“人類命運共同體”描繪了共同發展的愿景,對此,需轉化為具體的機制共識性原則。[2,3]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在2018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指出了優化國際稅制的方向,即“完善國內稅制、加強雙邊合作、建立多邊合作機制”,前二者是不言而喻的,而在經濟數字化、金融化的時代,多邊合作機制的構建就顯得愈發重要。
2015年10月OECD發布BEPS(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行動計劃最終報告后,2016年預示著國際稅收邁入“后BEPS時代”,BEPS所涉多項最低標準在《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多邊公約》(Multilateral Convenion to Implement Tax Treaty Related Measures to Prevent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MLI)中被具體化。盡管國際稅法界對當前國際稅制環境在適用多邊合作機制方面如多邊工具等持積極態度,但因“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國情、稅制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加之多邊工具本身如MLI第9條“關于轉讓其價值主要來自于不動產的實體的股權或權益取得的財產收益”(以下簡稱財產收益)課稅的規定具有復雜性,故給其簽署實施造成了重重阻礙。因此,以MLI第9條為規則指導我國對“一帶一路”非居民財產收益(capital gain)的課稅問題,首先,要了解該規則出臺的時代背景;其次,在明確規則內容的基礎上,挖掘我國內陸地區與BEPS、MLI第9條類似的規則及其實施情況,為修改建議的提出埋下鋪墊;再次,比對中外MLI立場書,尋求條約修改適用CTAs的可能性,若可行,則得出避免雙重征稅協定(Double Tax Convention,DTC)相應條款的修改結論;最后,對于條約錯配,即沿線各國所選MLI條款無法在兩國間生效并修改原DTC的情況,則綜合DTC相關規則的修訂趨勢、稅收法定與多邊主義及我國國內法規定等多個層次,從我國的立場出發,探尋全面解決“一帶一路”非居民財產收益稅收協調問題的路徑。
筆者是從MLI維度出發,探討我國對“一帶一路”非居民財產收益的課稅問題,而MLI第9條僅涉及“轉讓權益為不動產實體所取得的收益”一種情形,其他形態的非居民財產收益的課稅問題未在MLI規制范圍內,仍遵照舊有DTC規定,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一、MLI第9條財產收益課稅規則的立法背景及規則內容
多邊機制藍圖的構建,特別在應對瞬息萬變的數字化稅收時代,該機制允許盡可能高效地對全球現行3000余份雙邊協定進行批量修改,但其運行具有一定的困難性。[4]正如IBFD稅務主管維克托·范·科默先生所言,以多邊公約為代表的多個行動計劃實施起來非常復雜,而一國法律的權威性與公信力最終需要通過法律實施來體現,其必要前提是要求稅務機關深諳相關法律制度。[5]這對于2014年起轉型為資本凈輸出國的中國而言,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中尤其重要。“一帶一路”倡議為我國對外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激發了“更持久的發展動力”,我國要在維護自身稅收權益與支持發展中國家合理訴求間力求平衡,在確保我國稅基不受侵蝕的基礎上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6-8]
(一)MLI第9條財產收益課稅規則的立法背景
1.MLI第9條旨在具體落實BEPS第6項要求
MLI第9條濫觴并落實BEPS第6項最低標準的要求。倘若公約相關條款反映了BEPS第6項規定的最低標準,一般須遵照規定執行,換言之,只允許在有限情形下不適用最低標準的規定。BEPS第6項行動計劃最終成果報告《防止稅收協定優惠的不當授予》(Preventing the Granting of Treaty Benefits in In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提出判別跨國無形資產所得的經濟活動發生地或價值創造地的最低標準,《MLI解釋性聲明》(第128段)闡釋了上述報告(第44段)建議修改OECD協定范本第13(4)條適用的情形。
MLI第9條不完全遵照BEPS第6項最低標準要求。根據MLI第9(6)條及《MLI解釋性聲明》(第136段)中指出,鑒于為符合最低標準并不要求規定有關轉讓其價值主要來自于不動產的實體的股權或權益取得的財產收益的條款,第6款第1項規定允許公約締約方選擇整體不適用第一款。另外,第2項和第3項規定允許締約方分別選擇不適用第1款第1項或第2項規定。其含義有二:一是當被覆蓋稅收協定(Covered Tax Agreements,CTAs)規定完全符合轉讓權益性質,即“有關轉讓其價值主要來自于不動產的實體的股權或權益”時,應當遵照最低標準所設轉讓時間、權益比例執行;二是當所轉讓權益性質與上述條件完全不同或部分相同時,可以對第9(1)條采取完全保留、部分保留,此外還可參照9(1)條自主協商擬定協定條款。
2.MLI第9條為嚴格規制非居民財產收益避稅行為
MLI第9條下的財產收益,是指締約國一方居民從轉讓其所參與實體的股權或其他權益取得的收益,該股權或其他權益的超過一定比例的價值源自位于締約國另一方的不動產(或該實體超過一定比例的財產由不動產組成)。針對上述情形下的財產收益賦予課稅權,可在該締約國另一方征稅。
參照了BEPS第6項的OECD、UN協定范本(2017),相較OECD協定范本(2014)而言,一是除規定受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轉讓實體股權的情形之外,還多加了類似權益轉讓的情形,如合伙、信托中的權益轉讓;二是受益所有人轉讓50%以上權益,所得在締約的來源國一方征稅的條件增加了365天的最低持有時間要求。[9]后者旨在防止非居民納稅人在轉讓權益之前的任意時間節點人為稀釋實體中源自不動產的價值的占比而將資產投入該實體,利用來源地稅收優惠政策達到規避稅收的目的。[10]MLI第9條財產收益課稅規則不完全采納了方案,即引入一項測試期限和擴大相關權益范圍。[11]
(二)MLI第9條財產收益課稅規則的具體內容
由MLI第9條規則可知,該條款內容囊括實質性規范與技術性規范,前者涉及實體條款,后者包含兼容、保留、通知三類條款。根據實體、兼容、保留條款選擇適用組合的不同,結合相應的通知條款,將對CTAs產生四種不同適用結果。[12]

表1 MLI第9條規則歸納表
實體條款包括兩類具體規定,其一是第9(1)條的規定。其將持有股權或權益的比例交由締約國各方自行協商決定,另又下設轉讓時間和轉讓權益類型的規定兩項。締約國同樣可以自主選擇適用其中的1~2項規定;其二是第9(4)條規定,其通常與第3款共同作用。與前種情形不同的是,該條款將權益類型作了限縮,規定所轉讓權益須為與股權類似的權益,并且將權益類型、權益比例及轉讓時間規定在同一條款中,且條款下不設項,以此對實體內容明文確定,盡可能減少締約國締約時的分歧和締約后的爭端。此外,第9(1)條和第9(4)條是排斥適用的關系,與二者對應的成套兼容、保留、通知條款同時也呈排斥適用的關系。
技術性規范包括兼容、保留、通知三類條款,此三類條款無法單獨適用,須與實體性規范結合使用。在兼容性方面,當實體條款與CTAs條款之間存在類似規定且相互沖突時,其旨在明確何者規定優先適用以協調該沖突。具體而言,第2款規定是為解決第1款a項與CTAs間關于轉讓時間規定的沖突,明確了當CTAs規定的轉讓時間與第1款a項最低標準不符或CTAs不存在轉讓時間的規定時,第9條第1款a項替代CTAs相關條款適用或增設適用。同理,第5款規定是為解決第3、4款與CTAs間類似沖突規定或CTAs缺失相關規定時第4款規定替代或增設適用的問題;在保留條款方面,由于MLI第9條僅部分遵照最低標準之規定,所以第6款建議締約國各方根據具體情況,對第1款、第4款采取完全保留或對第1款a、b兩項采取部分保留的方式;在通知條款方面,同樣地,第7、8款需分別結合第1、4款加以適用。締約國各方需根據通知條款的要求對實體條款作出保留、適用,并將此結果通知所指向的CTAs清單。
二、MLI第9條財產收益課稅規則在我國的具體實施
明確MLI第9條財產收益課稅規則在我國的具體實施問題,即是理清在我國多邊工具、稅收協定與國內法間的關系。MLI與《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32條下的國際公約有所區別。我國雖已于2017年簽訂了MLI,但目前仍處于未生效、未執行狀態,此外,我國雖已根據MLI遞交了立場書,但該立場書只是表明我國單方面選擇MLI條款并適用于我國所列的CTAs的意向,而僅當締約他方也就相同MLI款項選擇并通知我國時,原DTC條款才能在雙方合意下修改并產生效力。據此,MLI立場書與DTC相比對于國內法不具有優先性和強制力。此外,通說認為DTC與國內法的關系有四種,我國將簽署生效的DTC直接納入并作為國內法的一部分,且國際條約優先于一般國內法條款,即“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13]這一點在“2002年北京市高院審理泛美衛星公司稅案”的裁判依據中可得到印證。由此可見,一是對于多邊工具、稅收協定和國內法之間一般遵循稅收協定優先國內法適用的原則,二是經轉化成功匹配并作用于稅收協定的多邊工具可獲得優先于國內法的地位,否則適用國內法的規定。
盡管MLI第9條規則暫無法在我國直接或轉化適用,反觀我國國內法已有相類似的規定。在國內法方面,我國現行法律規定與MLI第9條內在沖突明顯。我國對于MLI第9條款項的適用尚為保守的原因可能還基于對現行規范性文件的權衡和考慮,如維克托·范·科默先生所說,我國國內法及實施已然超出了BEPS規定的最低標準。[5]現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稅收協定中財產收益條款有關問題的公告》(1)《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稅收協定中財產收益條款有關問題的公告》第三條:根據“國稅發〔2010〕75號所附條文解釋”規定,公司股份價值50%以上直接或間接由位于中國的不動產所組成,是指公司股份被轉讓之前的一段時間(目前該協定對具體時間未作規定,執行中可暫按三年處理)內任一時間,被轉讓股份的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位于中國的不動產價值占公司全部財產價值的比率在50%以上。該規定所述及的公司股份被轉讓之前的三年是指公司股份被轉讓之前(不含轉讓當月)的連續36個公歷月份。(以下簡稱STA公告〔2012〕59)第3條對權益類型、權益比例、轉讓時間作出了較全面的解釋和界定,唯一與MLI第9(1)(a)、9(4)條差別甚遠的是該公告對“轉讓時間”規定為“三年”,即“被轉讓之前(不含轉讓當月)的連續36個公歷月份”,而非365天或12個月。換言之,非居民在轉讓之前連續36個公歷月份內的任一時間在我國持股低于50%,根據規定我國作為所得來源國都無法獲得相應稅收。可見,我國國內法關于轉讓時間的規定實際上要遠遠嚴于BPES第6項最低標準和MLI第9(1)(a)和9(4)條的規定。
三、MLI第9條下我國與沿線國家的條款選擇及匹配情況
(一)MLI第9條下的條款選擇結果
通過對MLI第9條規則的解讀、梳理與適用分析,在此基礎上又將實體、兼容、保留和通知條款的可拆分項作進一步拆分,并在相關條款之間聯系適用,得出以下樹狀圖:
根據圖1,總結出條款選擇及適用情況如下(由于兼容性條款是為說明實體條款與CTAs相關條款之間的內在關系,與條款適用及匹配無直接聯系,故在此不予列明):

圖1

表3 MLI 9第(1)條的選擇及適用情況表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條約適用的6種結果(見表2、3的第3列)。

表2 MLI 第9(4)條的選擇及適用情況表
(二)MLI第9條下我國與沿線協定國的匹配情況
狹義上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有64個,具體包括東南亞11國,南亞8國,獨聯體、格魯吉亞及蒙古8國,中亞5國,西亞北非16國及中東歐16國,在此64國中已與我國締結DTC的國家有56個。 廣義上的“一帶一路”諸國還包括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和地區,如德國的杜伊斯堡等都是“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者。[14]由于廣義上的“一帶一路”諸國呈現不確定性增多的態勢,為方便研究,本文僅限于狹義范圍內的討論。
在上述64國中,已簽署MLI并提交立場書的國家有34個,依據34國各自在MLI立場書第2條中所列國家情況,與我國達成整體上相互認可并適用MLI的國家有30個。在此基礎上,結合表2、3的適用規則,各國MLI第9條的適用結果及與我國匹配情況歸納如表4所示。

表4 沿線27國與我國MLI第9條適用結果及匹配情況統計表
由歸納信息可知,從沿線30國立場上的條款選擇結果有三種:(1)整體保留適用9(1)條并通知中國,如馬來西亞、土耳其、格魯吉亞等15國;(2)選擇適用9(4)條并通知中國,如俄羅斯、亞美尼亞等11國;(3)選擇適用9(4)條并作出通知,但未通知中國,如哈薩克斯坦、波蘭等4國。從中國的立場上,我國選擇適用9(1)(b)條并對除芬蘭等7國之外的23國作出通知,之所以就選擇條款排除對芬蘭等7國的適用,是因為此7國原DTC無相應條款可供覆蓋。
結合前述分析,從沿線30國立場上,對應條款選擇結果所產生的效果有三:其一整體排除9(1)條的適用,其二適用9(4)條規定,其三以MLI第9(4)條替換原DTC中與之沖突的條款。然而,由于9(4)條和9(1)條是互不兼容的兩個實體條款,又根據MLI第9條遵循BEPS第6項下的不完全遵照最低標準特征,對沖突條款有選擇地部分而非替代適用(效果三),事實上也是間接地選擇適用9(4)條并整體排除對9(1)條的適用。結合中國立場可知,上述效果與我國條款選擇結果間均為互斥關系,致使條款選擇的不匹配。因此,盡管各國均對條款作出選擇并通知,MLI第9條在我國和沿線30國間仍無從適用。
四、MLI第9條下我國對沿線非居民財產收益課稅問題的全面檢視
(一)回溯:適用CTAs舊有規定的紕漏與不足
對于與我國達成整體上相互認可并適用MLI的沿線30國,這些國家與我國在MLI第9條具體款項的選擇與適用上均構成了錯配。由前可知,30國條款選擇結果分別產生了排除適用9(1)條、適用9(4)條、以9(4)條替換CTAs中與之沖突的條款三種效果。其中,通知我國“排除適用9(1)條”情形具體又分三種:一是單純排除適用9(1)條,二是排除適用9(1)條并適用原DTC條款,三是排除適用9(1)條同時原DTC亦沒有類似規定;通知我國“適用9(4)條”情形分兩種,分別是在原DTC有類似規定或無類似規定的情況下通知我國重新適用9(4)條;而對我國以9(4)條替換原DTC中與之沖突條款的情況也存在兩種,分別是在原DTC有類似規定或無類似規定的情況下通知替代適用。
由于BEPS第6項允許MLI第9條在不完全符合規定條件的情況下,參與國可根據本國實際自主選擇有別于最低標準要求的條款,故在上述條款錯配的情況下,并非要強制回歸適用最低標準的要求。綜上所述,MLI第9條財產收益課稅規則在“一帶一路”國家之間被排除適用。由此,“錯配”即意味著兩國之間拒絕就此合意適用某一款項,而不論是三類錯配下七種情形中的哪一種均指向一個結果,便是適用原DTC相關規定。如此一來,由于既有協定簽署時間從1985~2016年不等,個中規定冗雜不一且難以適應現實需求,對雙邊協定的逐個修訂工程巨大,適用多邊工具批量修訂相關條款的愿景再度受阻。
(二)反思:舊協定向新協定過渡之修訂趨勢
條約錯配結果對多邊工具的實施提出了質疑和挑戰。對此,不妨暫且擱置適用上述規則,轉向我國與56個“一帶一路”協定國所締結的DTC之上(截止2019年8月25日)。
1.DTC相關條款規則的演進及其特征
從表5可知,我國與56個沿線協定國所簽署的DTC中財產收益課稅規則的歷史演進呈三個階段,特征如下:(1)1986~2006年。除敘利亞這一非典型國家外,此期間的規則特征表現為或回避制定、或采取含糊保守的規定,缺失對轉讓時間、權益類型、權益比例的具體規定,且將轉讓不動產股份限于“公司股票”一種。(2)2007~2016年。此九年間的規則制定從保守、回避轉向出現新的規定:一是權益類型的擴大。從刪去“股票”使用較為寬泛的“股份”表述到“股票或其他權益”、“股份或可比權益”的類型化擴大,再到適用“公司或其他實體的股份或任何類似權益”這一規定。二是增設權益比例條件。增加了“50%以上”、“50%(不含)”的轉讓限制性規定。(3)2017~2019年。適逢BEPS成果、MLI先后出臺,雖然這一階段我國并未與沿線64國新簽署或修訂DTC條款,但在與非沿線他國即肯尼亞、加蓬、剛果(布)、阿根廷先后簽署的DTC中,除完善規定權益類型、權益比例之外,還增加了轉讓時間的限制,如“轉讓前12個月內的任一時間[2017肯尼亞14(4)]”、“轉讓前365天內的任一時間[2018阿根廷13(4)]”等。通過三十余年的努力,對相關課稅規則的不斷補充和健全,使得新簽的DTC條款更接近MLI第9條(1)、(4)款的實體規定。

表5 我國與56個沿線協定國DTC相關條款匯總表
2.新簽DTC條款與30國立場的多數耦合
從表4可知,遞交MLI立場書的30國中有15國選擇適用MLI第9(4)條以部分或完全替代原DTC相關條款,而30國均保留適用9(1)條之規定,可見絕大多數沿線國家拒絕9(1)條、且半數沿線國家支持9(4)條之規定。此外,9(4)條對于轉讓時間“轉讓前365天內的任一時間”、權益比例“超過50%”的表述,恰好反映了BEPS第6項要求的最低標準,而從2017年后我國對外新簽署的協定可知,我國事實上正有意識地支持并接近BEPS第6項最低標準及MLI第9(4)條的規定。綜上,我國對外新簽DTC條款與MLI的27國立場存在多數耦合,均傾向于以MLI第9(4)條為標準制定規則。
(三)前瞻:適用MLI第9條規則解決相關稅收問題
一方面,靈活應用現有機制是“一帶一路”倡議得以推行并興盛的力量之一,我國積極加入多邊公約的磋商,有力地反駁了一些學者認為的中國尋求“建立中國秩序的大國野心”及尋求“自身優勢最大化”的觀點,表達了我國對多邊合作規劃解決全球性問題的“美好愿望、耐心和決心”;[15-18]另一方面,對轉型為資本凈輸出國的我國來說,正確選擇財產收益課稅規則不僅有助于消除和防止我國與“一帶一路”非居民財產收益的重復(不)征稅和偷漏稅問題,而且是我國對外就財產收益行使來源地征稅權的制度保障。MLI下的課稅規則的選擇并非單向意志,需在締約國間產生共鳴方能適用。通過對協定、法規的反思或可得出,盡管不易,但適用多邊工具仍是現有國際稅收規則下兼顧與批量修訂沿線眾多DTC的最高效方法。
1.修訂立場書及法規條款以適用MLI第9(4)條規定
適用上述規則解決我國與沿線國家的相關稅收問題,應利用好多邊工具、稅收協定與國內法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就我國選擇并通知的MLI第9(1)條來說,相較新簽DTC、MLI第9(4)條在轉讓權益類型方面有細微差異,即以“參與實體的其他權益”替代“類似權益”,以此更廣泛地適用被9(1)條修改的CTAs的現行條款,但不擴大這類涉及權益的范圍(b項的規定除外)。以上增設規定是為盡可能多地使CTAs對應條款符合修改條件,但轉讓權益類型仍局限在9(1)(b)條之內,與9(4)條規定無異。
另一方面,從我國對外新簽的DTC不難看出,我國適用MLI第9(4)條規則已是大勢所趨,并且這是“一帶一路”沿線多數國家的選擇,為避免日后逐個修改DTC條款的繁瑣,應從根本上修訂條款。對此,有兩種途徑可供選擇:其一,是將我國對MLI第9條的立場由9(1)(b)條修改為適用9(4)條規定并通知CTAs,從而與沿線多數國家選擇一致并匹配;其二,倘若暫不修改立場書,次之的方法對STA公告59〔2012〕第3條轉讓時間的規定由“被轉讓之前的三年”修改為被轉讓之前的365天或12個月。
2.MLI第9(4)條下沿線國財產收益課稅規則的統一
稅收法治原則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與稅收制度建立中最重要的一項原則,法律的不確定性如適用繁雜等,會產生貿易壁壘,國際稅法體系的穩定性、確定性和一致性,將對跨境企業的貿易和投資的增長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1,19]我國的國際稅收合作重心在黨的十九大后逐漸轉移至服務“一帶一路”建設。[20]筆者認為,由于“一帶一路”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南亞、中亞的發展中國家立法技術良莠不齊,強調在稅收法定主義下區域稅制的明確、統一,如國際商會“建立一致國際稅收體系”的做法,將在極大程度上提高稅收確定性和稅收政策可預測性,促進稅收征管與稅收效率,并為全球化稅收積攢經驗。[21]
以落實稅收法定主義為前提,在財產收益課稅方面,MLI第9條和以OECD協定范本(2017)第13(4)條規則為模版的眾多DTC條款均為BEPS第6項下的成果。我國與“一帶一路”64國在適用MLI第9(4)條課稅規則下的統一,應包括:(1)對于MLI出臺前的56個沿線協定國,其中原DTC存在相關條款的43國,不論其是否提交立場書,中國均需在我方立場書第9條中將適用MLI第9(4)條的結果通知上述43份CTAs;(2)對于尚未簽署DTC的沿線8國, 以及原DTC無相關條款的13國,建議參照MLI9(4)條內容修訂STA公告59〔2012〕,并以此為依據考慮日后新簽或修訂DTC條款問題;(3)上述(1)中的43國,若有無意加入MLI但有重新修訂DTC相關條款共同意向的,可參考MLI第9(4)條規定處理,若無此意,則我國可適用修訂后的國內法協調今后的相關課稅問題。
五、總結與展望
“一帶一路”倡議輻射地域廣、國家多,由于參與國國內稅收法律制度、協定網絡、文化背景等方面差異明顯,作為助推沿線貿易和投資的動力工具之一,統一的國際稅法體系是必要的。倘若缺失統一的國際稅法體系,適用或解釋規則條款時可能出現無所適從的爭議,比如提交MLI立場書的國家對于第10條常設機構相關問題各國的表態不同,此即各國對于MLI第10條的不同解讀所致。
稅收法治原則要求稅法規定具備明確、簡易性特征。以一致化國際稅法體系為目標、稅收法定主義為基本原則,MLI第9條規則下我國對“一帶一路”非居民財產收益課稅及相關雙重(不)征稅問題中,由于現階段的我國與沿線30國MLI立場書相關條款的選擇和適用結果均導致了錯配的效果,MLI第9條因此在我國與30國之間無從適用。我國與30國適用條款爭議集中在9(1)(b)條與9(4)條之間,盡管發生錯配,但通過對我國對外簽署DTC條款演變、國內法的深入剖析,可以得出我國適用9(4)條規定是應然趨勢,這亦與30國中的多數國家的選擇耦合。由此,通過系列修訂,從而使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適用多邊工具解決相關稅收問題成為可能,并在MLI第9(4)條規則下完成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