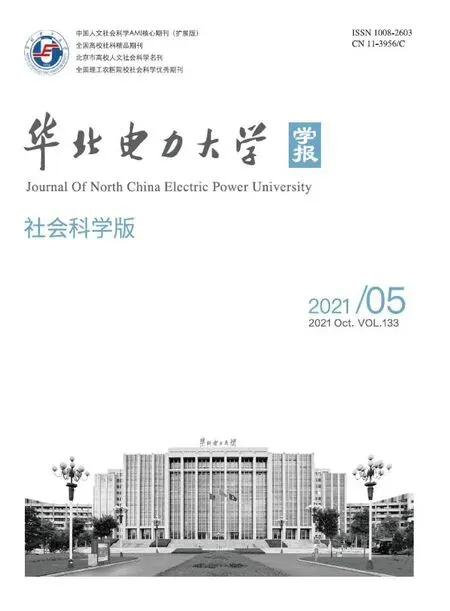我國庭審直播制度的三重理論基礎
金飛艷
(北京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1)
在新一輪司法改革中,國家將司法公開作為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司法改革大力推行了立案公開、庭審公開以及執行公開等信息化相關措施。其中,庭審直播這一制度引起社會重大關注。為何要將庭審過程尤其是刑事案件審判過程直播?直播庭審的正當性基礎在哪里?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今天,我國庭審直播制度可以發揮什么樣的司法效能?筆者嘗試對此進行探討。
一、庭審直播的傳播學基礎:第三人效果
(一)什么是第三人效果
第三人效果,又稱之為“第三人效應”(the third-person effect,THE),是指基于個人偏見,人們更傾向于認為,相對于本人,大眾傳媒對其他人產生的影響更大。故而,由于這種看法,人們傾向于采取行動來抵消傳媒信息的影響。第三人效果通過過度夸大傳媒信息對他人的影響或者低估傳媒信息對他們自己的影響而表現出來。這兩種感知源于自我激勵的社會期望(免受傳媒消息影響,實現自我促進)、社會距離推論(選擇將自己與可能受影響的其他人分離)以及可感知的信息暴露(其他人選擇受說服性溝通的影響)。[1]第三人效果還存在其他的說法,如“第三人感知”或者“互聯網第三人效果”。“互聯網第三人效果”出現于2015年,主要是存在于社交媒體、媒體網站、博客以及其他一般意義上的普通網站。[2]
社會學家菲利普斯·戴維森首次于1983年闡述了第三人效果理論。這一理論解釋了他在1945年到1950年觀察到的現象,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日本人嘗試勸阻一名黑人士兵在硫磺島戰斗中不要散發傳單。戴維森強調,在傳單事件中,日本人沒有和黑人士兵發生爭吵,他們放棄了爭論并直接離開。雖然沒有跡象表明傳單事件對士兵有任何影響,但事件發生之前,軍官中間進行了大量的崗位輪換;第二天,這個小分隊也被調離硫磺島。[1]
隨后幾十年,不斷有社會學家或者心理學家對第三人效果理論作出自己的貢獻。而對哪些因素促進第三人理論的發展,直到2009年,佩羅夫(Perloff)教授對這個問題作出貢獻。他認為,促進第三人效果主要存在兩個因素:對消息可期待性的判斷(judgments of message desirability)和可感知的社會距離(perceived social distance,又稱之為社會距離推論“social distance corollary”)。
在對第三人效果研究進行的基礎分析過程中,來自中國的三位心理學家發現,消息的可期待性是影響第三人效果的最重要因素。[3]當人們認為某個消息不是特別受歡迎,也就是說當群體認為“這個消息對我來說可能不太好”或者“承認自己受到這個媒體節目的影響似乎失去品味”時,第三人效果尤其明顯。實踐與這些預測一致的是,人們認為那些通常意義上被理解為反社會的內容(例如,電視暴力,色情,反社會說唱音樂),對他人具有比他們自己更大的影響。[4]的確,許多研究者也已經發現相關證據表明:不良信息,如暴力和仇恨信息,產生更大的第三人效應。[5]另一方面,當消息是人們所期待的時候,人們就不容易表現出第三人效果。根據佩羅夫(Perloff)教授的研究,第一人效果(the first-person effect)①第一人效果,即,媒體對本人產生的影響更大這種推論,往往發生于人們認為自己受媒體信息影響是可以接受的情形。Innes和Zeitz在1988年首次記錄了這種現象,當時他們注意到暴露于暴力信息之下的參與者表現出了傳統的第三人稱效果,而那些接受公益廣告的人則表現出相反的效果。故而,他們描述了這種相反的效果,不過只是稱之為“類似于第三人稱效果”。Innes J.M; Zeitz H.The Public's 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Mass Media:A Test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88(5):457–463.或反向第三人效果(reversed third-person effect)對于期待的消息更常見,[6]并且經常在積極認同某一消息以及某種程度上涉及個體識別時出現。根據自我激勵理論(the self-enhancement view),如果第三人效果是由于捍衛自尊所驅動,人們更傾向于認可符合社會期望的、無害的或對自己有好處的大眾消息。[7]對大學本科生的調查顯示,他們更偏向于認為:相比較自己,其他人更容易受到香煙廣告的影響,他們將更多地受到反煙草和反對醉酒駕駛公益廣告的影響。[8]
影響第三人效果的另一個因素是自我和比較方之間可感知的社會距離。根據社會距離推論,隨著自我和比較方之間可感知的社會距離增大,自我和比較方的差異也隨之增加。[9]雖然社會距離不是第三人效果發生的必備條件,但是增加社會距離卻能夠使得第三人效果加大。在他們的基礎分析(meta-analysis)中,安薩格(Andsager)和懷特(White)得出的結論是:那些以自己為參照系的人,認為受到說服性信息的影響比其他人要少。[10]
(二)庭審直播的第三人效果分析
為何要將庭審情況通過各種媒體途徑向外界公布?這樣利用現代通訊技術的制度設計有什么樣的司法意義或者政治效果?通觀全球,并不是所有國家都這么做。因此當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分析的時候,筆者認為,根據影響第三人效果的兩個主要因素,對庭審直播的第三人效果可以作以下分析。
第一,從消息的可期待性角度來看,庭審直播對社會群體②未使用“社會公眾”一詞是因為社會公眾的內涵只包括民眾的集合體,而“社會群體”一詞含義更為豐富,包括正式群體(政府、企業、工廠、學校班級等)和非正式群體。的影響非常大。從總體上來看,庭審直播公布的信息不是犯罪案件就是侵權違約抑或行政違法。這些信息對于一般人來說,產生的都是負面影響。①即使各類型案件的判決結果總會對某一方有利,但是公眾并不確定其是哪一方。因此。社會群體更傾向于認為:這些犯罪行為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不會涉及侵權違約行為以及他們不愿意成為違法的行政機關。故而,社會群體會盡量避免成為利益(被)侵害人(同時認為,他們之外的人更可能成為受害者②如公眾通過庭審直播觀看了故意殺人案件審判過程,往往認為自己不會成為被害人,其他人成為被害人的可能性更高。或者加害方)。為了保證其利益不會被損害,社會群體就會盡量確保其行為符合社會規范:如避免自己成為暴力犯罪被害人,盡量遠離那些具有暴力傾向人群;為減少卷入民事糾紛的概率,民事主體在簽訂合同或者作出其他舉動之前,了解相關事項的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時,會盡量關注本機關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避免成為行政案件被告人。這樣,庭審直播傳播的審判信息在可期待性上就實現了第三人效果。
第二,可感知的社會距離也表明庭審直播產生的影響不比親自旁聽庭審過程小。舉例來講,甲和乙相約參加旁聽某搶劫案件審理過程。基于趨利避害心理暗示,甲認為搶劫案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要比發生在乙身上的可能性要小。但是,如果甲和乙是通過觀看庭審直播視頻獲悉某處發生搶劫案件,二人的心理狀態更可能是兩人出門在外都要謹慎一些,避免被搶劫犯盯上,并尋思著對方被搶劫的可能性更大。庭審直播增加了自我與他人和信息源之間的距離,進而也加大了第三人效果。
二、庭審直播的政治學基礎:公眾參與原則
(一)公眾參與原則的含義與特點
公眾參與原則(public participation principle)主要是一項政治原則或者政治實踐,也可以理解為一項權利(公眾參與權)。“公眾參與”這個術語,通常會與“利益相關者參與”(stakeholder engagement)或者“大眾參與”(popular participation)這些概念互換使用。一般說來,公眾參與尋求并促進那些可能受到決策影響或者對決策感興趣的人的參與。這可能與個體、政府、機構、公司或者其他影響公共利益的組織有關。公眾參與原則認為,受決策影響的人有權參與決策作出過程,即意味著公眾的意見在制定決策過程中發揮實質性作用。[11]公眾參與可被視為一種授權手段,也是實現民主治理的重要組成方式。就智識管理層面而言,一些學者認為建立可持續的參與性程序可以促進基于整個社區或者社會的參與而產生的集體智慧和群體包容。
公眾參與原則是過去三十年來在西方文化中涌現出來的“以人為本”(people centred)或者“人文中心主義”(humancentric)原則的一部分,并且在教育、商業、公共政策以及國際援助發展等方面發揮作用。公眾參與由人道主義運動發展而來,其可以視為“以人為本”(people first)范式轉變的一部分。就這一方面而言,公眾參與原則可能會對“大就更好”(big is better)概念以及集中式等級制邏輯形成挑戰,從而推進“集體智慧優于獨斷主義”(more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這些替代性概念,并堅持公眾參與原則可以維持高效持久的變革。
公眾參與原則在經濟發展和人類進步方面發揮的作用,被寫入《1990年公眾參與發展與變革非洲憲章》(the 1990 African Charter for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1990年,為了回應日漸增長的公眾參與需求,推動者們建立了國際公共參與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建立協會這種實踐做法在全球推行很順利,現在在全球范圍內均設有國際公共參與協會的分支機構。[12]
公眾參與原則的含義非常豐富,如公共政策、參與式預算、公共信任、問責制和透明度、參與式發展、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公眾參與權等。在與刑事審判庭審直播相關的內容,主要是問責制與透明度(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和公眾參與權(right to publicparticipation)這兩個內容。
公眾參與原則也可以視為升級版的問責制。支持的依據在于公眾參與可以作為投身于此的公眾使得行政機構對其實施行為負責的手段。[13]透明度這一做法源于英國。在英國,將議會的會議過程予以完整記錄,并冠以“國會議事錄”進行出版,這在威斯敏斯特議會中提出了一種部分形式上的透明度做法。雖然會議可能涉及未頒布實施的法律,但是因為法律草案和最終文本都已經公布于眾,所以并沒有什么不妥。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許多國家的立法機構決定在互聯網上公布其會議記錄和通過的文件。然而,公布法律草案的初始文本和與這些法律相關的討論和協商過程,一般說來,很少發生在那些透明度非常低的機構委員會和政黨中間。此外,考慮到國家頒布的成文法存在邏輯和語言上的復雜性,盡管會議具有最基本的透明度,公眾參與仍然很困難。透明度的要求也存在于政府財政和公共經濟等領域。[14]
在某些司法轄區,通過成文法規定了公眾參與的權利。某種意義上來說,公眾參與權也可以視為基本人權,或者作為結社自由和集會自由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從中世紀以來,荷蘭、德國、丹麥和瑞典就已經在其法律中規定了公眾參與權和信息自由權。以民主制度和集會自由為顯著特征的民主社會將公眾參與權納入其法律體系的做法有幾百年的歷史。例如,在美國,請愿權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內容。①“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西蘭的許多法律(例如涉及衛生、地方政府和環境管理等方面)要求政府應該在作出決策時,要與可能受到其決策影響的人進行溝通協商,并考慮利益相關人的意見。
有效的公眾參與依賴于公眾能夠獲取準確和全面的信息。因此,關于公眾參與的法律常常涉及知情權、獲取信息權和自由傳播信息權等問題。公眾參與權也可以在有關平等權和群體性權利語境下討論,以確保特定人群—如殘疾人—在社會決策中享有平等權和充分參與權。
(二)公眾參與原則在庭審直播中的體現
拉斯基曾講過,人民不能過問之權力,乃以人民為工具,不以人民為目的之權利也。[15]公眾參與是司法民主的體現。司法民主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參與案件審理,共同享有司法審判權,這無論是現代社會還是理想制度設計,均不具有可行性。
公眾參與原則,除了傳統意義上的陪審制度,諸如公民扭送這樣的制度設計,也莫不如此。相比之下,若論及庭審直播中的公眾參與,可以將之概念化為公眾參與原則的間接形式(見圖1)。在庭審直播這一制度中,社會公眾直接通過電視或者網絡觀看庭審視頻,知悉法院審理案件過程。與直接參與庭審(旁聽或者是一方當事人)比較而言,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在庭審直播中,間接的公民參與,使得獲取庭審信息的受眾更為廣泛。因此,除了可以達到宣傳法律的要求,發揮刑罰威懾之功能,該制度想要實現的司法透明、司法公開目的即可成就。其二,庭審直播還有效地節省了大量司法資源和公眾資源。相較于參與旁聽審判,國家要提供大量的旁聽空間資源與安全檢查資源。公眾通過觀看直播視頻,同樣可以了解相關案件審理過程,熟悉國家相關法律規范。不但節省了公眾為親自參與旁聽投入的時間成本與經濟投入,也達到普法宣傳的效果。其三,庭審直播作為間接的公眾參與手段,還保證那些因種種因素(如距離較遠)一時難以參與案件審理,但是又想關注案件進展的社會公眾。如對于被告人所在社區、被告人所在單位以及其他人員,他們可以通過觀看庭審直播,最直接地了解被告人犯罪行為以及主觀惡性等。如果可能,上述主體會盡力為被告人創造有利其回歸社會的條件。

圖1 “直接公民參與”與“間接公民參與”路徑比對
三、庭審直播的法學基礎:審判公開原則
(一)審判公開原則的多角度解讀
貝卡利亞在其巨著《論犯罪與刑罰》中言及:“審判應當公開,犯罪的證據應當公開,以便使或許是社會唯一制約的輿論能夠約束強力和欲望;這樣,人們就會說:我們不是奴隸,我們受到了保護。”[16]拉德布魯赫也曾說道:“現代刑事程序重新采用了為中世紀所拋棄的公開審判。司法的公開性不應僅僅為了監督。民眾對法律生活的積極參與會產生對法律的信任······”[17]
審判公開原則(open trial)或者說公眾審判原則(public trial),是指一種面對公眾開放的審判。與秘密審判相對應,其不應該與表演性審判(show trial)混淆。審判公開原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審判過程的公開,體現在允許與案件結果沒有利害關系的公眾到庭旁聽,允許媒體采訪報道庭審過程;另一個是審判結果的公開,即庭審作出的判決內容應該公之于眾。存在不同觀點的是,有的學者認為,審判公開原則還包括應該將犯罪的證據公開。[18]這不難理解,法院作出判決書,從不說理到簡單說理再到要求充分說理,使得判決書為公眾所接受的可能性越來越高。[19]而秘密審理是指法院對案件秘密審理,不允許公眾旁聽審理過程。如果沒有特殊法定理由,僅僅是向當事人公開。這也不屬于現代司法意義上的公開審判。
審判公開的積極意義在于:一方面可以防止法官和公訴人專橫,遏制司法不公,增進法院工作透明度,提升其公信力;[20]另一方面還可以向當庭陳述之人施加心理壓力,促使其如實回答相關問題,提升庭審質量和效率。但是審判公開也存在某些弊端:如可能會過分損害被告人的羞恥心,不利于其悔過自新;可能會對公眾造成恐慌,尤其對于需要證人出庭作證的案件,可能會對證人造成心理壓力,不利于推動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有效運行。[21]。
美國的審判公開是規定在其憲法第六修正案中,內容表述為“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a speedy and public trial”,但是并不絕對公開。在特殊案件中,可以存在例外。法官可以根據是否會對公眾利益造成損害決定是否不公開審理。但是不論利益為何,對該利益造成的危險性必須滿足“實質性可能”標準(substantial probability test)。[22]以下類型案件可能滿足上述要求:有組織犯罪案件(涉及社會安全)、強奸案件(有關道德問題)、少年案件以及涉及敏感或者特定信息的案件(有關沉默證人規則①沉默證人規則(the silent witness rule)是指美國法院公開審判案件時,涉及敏感信息,使用替代指稱的做法,首次出現在1987年美國訴澤特爾案件。后來也在其他案件中使用,但是存在很大爭議。United States.v.Rosen(2007).或者特定信息程序法)。
加拿大的做法是,根據審判公開原則和相關立法,法庭審理案件的過程一般向公眾和媒體開放。《安大略省法院法》(the Courts of Justice Act(Ontario))第135條第1款規定了“所有法庭審理過程應向公眾開放”的基本原則。
在蘇聯,“公開審判”(open trial)和“公眾審判”(public trial)有所不同。“公開審判”意味著公眾可以旁聽審判活動,而“公眾審判”則意味著有目的的向公眾介紹審判進程。公眾審判的案件廣泛引進媒體,同時庭審過程中也安排了更多的聽眾。盡管蘇聯的公眾審判通常和斯大林時代的表演性審判(show trials)—如莫斯科審判—聯系在一起,但是在俄羅斯文化中,“公眾審判”這個術語,并不具有負面含義。因為表演性審判的主要特點體現在蘇聯時期,國家對于信息公開存在特別嚴格的限制。“表演性審判”這一術語通常對應著俄語中的“пoкaзнoйпpoцecc”—意為出于政治目的,對被告人進行指控,審判具有宣示性質。
因此,綜上,可以對審判公開原則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解讀。首先,從國家角度而言,一般來說,是指司法機關②不同的國家,司法機關所包含的范圍并不完全相同,比如說在中國,司法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含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及其領導的律師組織、公證機關、勞動教養機關等,而在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司法機關僅指法院這一裁判機關。在審判案件過程中,吸收民眾和媒體參與。堅持審判過程公開,有利于整個社會接受其作出的司法判決,在公開的過程中,公眾能夠感受到法官如何采信證據與說理判決的過程。“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在公開的情況下,司法機關枉法裁判的概率會大大降低。其次,就整個社會公眾而言,審判公開原則從側面實現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司法行為的憲法監督,根據心理學理論之“隧道視野”(tunnel vision)、“證實偏差”(confirmation Bias)、“信念堅持”(belief perseverance)、“情感附著”(emotional attachment)、“動機偏差”(motivational bias)和 “目標追求”(goal pursuit)等理論,公眾相信本人親眼看到的,親耳聽聞的,以及在此基礎上論證的結論。而審判公開,恰好為此提供客觀的判斷基礎。司法機關的中立屬性決定了司法機關若喪失權威性,其判決很難得以執行。“不公開-不中立-無權威”這樣一種惡性循環會摧毀司法機關存在的合理性基礎。再次,對審判公開設定例外條款并不影響該原則的廣泛適用。就當事人,對于特殊類型的案件,比如涉及個人隱私、商業秘密以及未成年人案件,不適宜公開審理的案件,可以作特殊規定。一般類型案件,只要符合公開審判的條件,即應當公開審理。最后,就其他訴訟參與人而言,公開審理也會產生很多有利的影響。以律師參與刑事案件辯護為例,在中國刑事訴訟案件中,刑事案件有辯護人的比例一直不高,③根據東南大學王祿生教授的統計,2015年刑事案件辯護率約為21.2%,律師辯護率約為19.9%。貫徹審判公開原則,在媒體與公眾在場旁聽的情況下,有利于激勵律師真正發揮辯護人作用,充分表達其辯護意見。這不僅會實質上增強與控訴方的實質對抗,實現有效辯護,[23]也使得刑事辯護律師找到其辯護角色的真正定位,實現其辯護活動的主體地位。④盡管中國人民大學刑事訴訟法學者李奮飛教授認為存在律師過度利用法庭辯護,本質上并沒有實現辯護功能,只是表演給當事人及其近親屬,以及社會媒體看。李奮飛.論“表演性辯護”——中國律師法庭辯護功能的異化及其矯正[J].政法論壇,2015(2):77-92.
(二)庭審直播:審判公開原則的另一種實現方式
為了給證人出庭作證提供必要的便利,許多國家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錄音錄像設備的使用做了嚴格的限制。①日本,旁聽人員做筆記也會受到嚴格限制,對于通過電視或者網絡直播案件審理過程,多數國家也持謹慎態度。通常情況下,由法庭指定的素描人員通過素描完成法庭審理場景的客觀再現。英格蘭地區對新聞媒體報道犯罪情況以及司法審判活動也作了嚴格的限制。美國對此規定雖然沒有英國嚴格,但是根據慣例,大多數法庭也不允許媒體從業人員在法庭審理過程中進行拍照或者錄音錄像,只有極少數州允許以電視轉播方式對庭審過程予以公開。
因而,盡管不少國家對庭審直播作出限制,但是庭審直播作為實現審判公開原則的另一種方式,能夠解決許多問題。具體好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將審判過程進行直播公開,可以解決絕大多法庭旁聽席位數量不足的問題。一般情況下,除了那些特別重大案件使用特殊場所(如會場)審理,普通案件使用的審判庭空間都不大,如此一來,就會剝奪其他想要旁聽案件審理過程的人的權利。法院主動將案件審理過程進行直播,就向這些人提供了了解案件審判過程的渠道。
第二,審判公開原則的關鍵要求是審判過程公開。有些案件,在開庭審理的時候,會有一方當事人因某種原因無法出庭。這時,對該案件進行庭審直播,可以使得當事人親眼目睹自己案件的審理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庭審直播為當事人提供了直接了解自己案件的機會,避免了因當事人不在場但法院判決對不在場當事人不利當事人不服的情形。
第三,因將審判過程進行直播產生的數據,一般來說是存儲在數據庫中。因此,不會因為庭審直播結束就丟失,可以通過回放來查看以前的庭審案件。所以,這就為那些想了解案件庭審過程的人創造了知悉情況的機會。如,某一案件審理過程在當時并沒有很多人關注,但是后來發現該案件的審理結果有待商榷。那么,該案件當事人或者其律師就可以通過觀看庭審直播視頻,客觀全面獲取有關該案件先前審理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