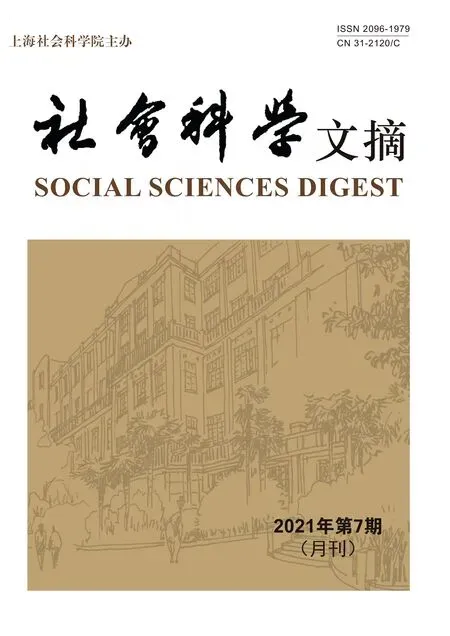生活儒學與“哲學訓詁學”建構
文/張小星
儒學的現代轉型必然蘊含著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型。但到目前為止,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的相關思想資源被建制化地劃歸入文學、史學等學科中,其現代轉型并未真正實現。從學理上講,徹底的現代轉型必須深入到存在論(the theory of Being)層級,即揭示“經典詮釋”作為前主體性、前存在者活動的意義。換言之,對于“經典詮釋”相關問題的探討必須納入存在論層面才是透徹的。而這一轉型的具體展開,既要有效吸納西方“哲學詮釋學”的有益思想觀念,又要充分考察中國本土的經典詮釋傳統,挖掘中國訓詁學所蘊含的經典詮釋資源。就此而論,生活儒學的“生活論詮釋學”為我們提供了啟示。本文意在從生活儒學的思想視域出發,展開對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型問題的思考,進而勾勒出一種新的詮釋學形態:“哲學訓詁學”(Philosophical Exegetics)。
“經典詮釋學”評析
在“中國詮釋學”建構思潮方興未艾、各種詮釋學形態不斷涌現的當下,一些學者試圖建構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經典詮釋學”。盡管這些建構嘗試是在梳理中國(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基礎上展開的,卻各以西方某種詮釋學歷史形態作為其指向性目標,因而在理論旨趣上呈現出不同樣態。其中最突出的有兩種形態:
一種是強調“中西之異”,旨在建構作為現代中國哲學方法論的經典詮釋學,以景海峰的論述為代表。他認為,中國哲學經典詮釋方法的現代轉化,應當是從傳統訓詁學轉為經典詮釋學。在他看來,中西經典詮釋傳統具有明顯差別。西方詮釋學不僅有作為語言工具之技藝性層面的向度,而且有作為認知工具之哲學化向度;而中國訓詁學則缺乏哲學之思辨性和認知功能上的獨立性,而且隨著中國學術范式的現代轉型,尤其是傳統經學的解體,原來附庸于經學、作為解經工具的“小學”現在被安頓于語言文字學之中,使得訓詁學與作為精神性的哲學相去甚遠,加之義理之學被歸入哲學,這就導致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建構在方法上依賴于西方。因此,我們需要重新理解“詮釋”的意義,通過打破傳統訓詁的界域,邁向新的經典詮釋學,從而為中國哲學的創造性發展奠定方法論基礎。另外,吳根友的相關論述也可歸屬于這一類型,其具體做法分為兩步:首先是以西方詮釋學作為參照,通過闡述清儒戴震的經學解釋實踐原則,進而將其歸結為一種“經學解釋學”;然后再將此“經學解釋學”思想泛化到對中國古代經典的解釋過程中,從而將其提升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現代“經典詮釋學”,在由訓釋文字、分析語言而到解讀經典意義的過程中,實現認知水平與思想境界的雙重擴充,從而為“當代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提供新方法與新視野。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經典詮釋學”本身不僅未能提出具體而有效的方法,也未能從建構現代中國哲學的實際情形出發來探討“經典詮釋”作為方法論原則的合法性所在,于是成為一種抽象而空洞的口號,而缺乏應有的實質性內容。此外,就詮釋學形態的歷史演進來看,方法論范式的詮釋學形態已經因其內蘊著“認識論困境”而遭到解構,如果以此作為參照鏡像,那么,這種“經典詮釋學”本身將同樣面臨被解構的危機——“經典”的客觀性意義何以可能?
另一種是強調“古今之變”,旨在作為建構理解理論的存在論基礎的經典詮釋學,以傅永軍的論述為代表。與上述方法論向度形成對照、強調“中西之異”不同,傅永軍主張由“古今之辨”轉為“古今之變”,即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型所應完成的基本任務應當是從“經典注釋學”轉型為“經典詮釋學”。在他看來,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籠罩在文獻學、語文學、歷史學之下而缺乏哲學自覺意識,“經典詮釋”主要被理解為一種解經的技藝學,表現為一種以文字訓釋和文本考據為中心的注疏之學。而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型,必須借重西方詮釋學的刺激,實現從文獻學—語文學—歷史學到詮釋學的現代轉型,在中西經典詮釋傳統的對話中完成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詮釋學轉向,進而建構一種擺脫方法論定位而作為理解存在論的經典詮釋學,也就是關于理解本性以及理解如何可能的理解理論,此乃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現代轉型的優選路徑。
顯然,這種詮釋學的問題意識源自海德格爾,尤其是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伽達默爾說:“我們一般所探究的不僅是科學及其經驗方式的問題——我們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經驗和生活實踐的問題。借用康德的話來說,我們是在探究:理解怎樣得以可能?這是一個先于主體性的一切理解行為的問題,也是一個先于理解科學的方法論及其規范和規則的問題。我認為海德格爾對人類此在的時間性分析已經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屬于主體的行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它標志著此在的根本運動性,這種運動性構成此在的有限性和歷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經驗。”因此,伽達默爾事實上延續了海德格爾的矛盾:盡管“此在”被海德格爾認為是“使一切存在論在存在者層次上及存在論上都得以可能的條件”,“我們在此在中將能贏獲領會存在和可能解釋存在的視野”,由此而獲得突入存在本身的優先性,但“此在”依然屬于某種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因此,伽達默爾詮釋學的矛盾在于:既然“理解”不屬于主體性的行為,那么其本身又何以成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呢?對于作為理解存在論的經典詮釋學來說,“理解”依然屬于一種主體性行為,而問題在于——這種主體性本身何以可能?
“生活論詮釋學”思想
詮釋學史表明,任何一種詮釋學理論都必然奠基于某種存在論形態,而此詮釋學理論出現問題則反映了為之奠基的存在論本身的困境,因而需要建構新的存在論,并在此基礎上重建新的詮釋學理論。上述“經典詮釋學”范式之所以不徹底,根本原因即在于為之奠基的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不徹底。這意味著,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型,首先需要一種更為透徹的存在論為之奠基。筆者以為,生活儒學提出的“生活存在論(Theory of Life as Being)”,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注生我經”為核心觀念的“生活論詮釋學”,為我們的思考與討論提供了理論指引。
具體而言,這種“生活論詮釋學”的建構內在地遵循了生活儒學“破解—回歸—構造”的致思進路。
首先,所謂“破解”,是指一種在“破壞”中的“解釋”,這種“解釋”就是通過“解開”而“釋放”,即通過解構既有的詮釋模式,進而釋放出建構新的詮釋學的可能。簡而言之,這種既有的詮釋模式就是“主體性詮釋”,表現為作為主體的詮釋者對于文本或經典的理解與解釋,其實質上是一種以主體性預設為前提的詮釋觀念。上述“經典詮釋學”亦屬于這種詮釋模式,它不僅長期主導著中國前現代的古典詮釋觀念,如陸九淵所謂“六經注我”和“我注六經”,而且至今仍存在于諸如“中西比較”“對話倫理”“東亞儒學”等關乎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詮釋經驗中。這種詮釋模式的問題在于,其內在前設的“主—客”思維架構難以避免胡塞爾所指出的“認識論困境”,也就是認識如何能夠確定它與被認識的客體相一致、它如何能夠超越自身去準確地切中它的客體的問題,這就導致“主體性詮釋”本身面臨追問:我們如何可能確證一個文本及其意義是客觀實在的呢?我們如何可能通達、理解這個客觀的文本及其客觀的意義呢?進而言之,這種詮釋模式本身難以闡明——詮釋者的主體性、文本及其意義的客觀性何以可能?
然后,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回歸”,即回溯到生活—存在視域,亦即“還原”詮釋活動的“事情本身”。“生活存在論”認為:“生活”乃是一切的本源,而生活本身并非某種主體的生活,即并非海德格爾所謂“此在的生存”——“特殊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先行于任何主體性、任何存在者的存在本身,“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別無所謂存在”;生活本身作為“事情本身”,總是如此這般地顯現為“有事無物”的生活情境,即無分別的“境遇”,而“境遇”正是一切作為存在者的“物”得以生成的本源;生活本身呈現為“在生活并且去生活”的結構,“在生活”表明生活本身作為“事情”總在發生著,而“去生活”則意味著生活本身總在超越著,“事情”本身總是蘊含著向前運動的可能。就詮釋活動而言,所謂“注”亦即“詮釋”正是生活本身所顯現出來的一種生活情境,盡管這種情境總是表現為主體在理解與注解文本,但其本身也同時在生成著新的主體性,以及新的文本客體。
最后,“破解”與“回歸”的目的在于“構造”,即建構一種新的詮釋學理論,來闡明“注”亦即“詮釋”活動本身如何塑造著新的存在者。對此,生活儒學提出“由言而成”,即“言說”給出了新的存在者,此即儒家所講的“不誠無物”,“誠”本身說的是一種本源性的言說,講的是由“言”而成。存在者成為存在者,他們是怎么被給出的呢?由言而成。“注(註)”正是如此這般的“言說”活動,孔穎達《毛詩正義》講“注者,著也,言為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文義著明的過程同時亦是主體實現自我理解與自我解釋的過程,新存在者就生成于這種“注(註)”之中。由此,生活儒學提出“注生我經”的詮釋觀念:“注”本身是生活的一種顯現樣式;所有實體性、存在者性質的東西,包括“我”“經”以及“主—客”思維架構,都是在此事情當中生成并顯現出來,從而不斷地展開并實現自身超越。
“哲學訓詁學”構想
為此,在上述生活儒學“注生我經”觀念的啟發下,這里嘗試提出“哲學訓詁學”(Philosophical Exegetics)的理論構想。需要申明的是,所謂“哲學訓詁學”并不是要建構一種有助于文本解釋的方法論,即并非那種為哲學研究與哲學創作提供一種方法的所謂“訓詁哲學”,而是一種存在論性質的研究,即通過揭示“訓詁”的存在論意義,而探討“訓詁”活動如何生成新的意義世界的問題。
所謂“訓詁”,最初指“解釋古語”,如《說文解字》講:“訓,說教也。”段玉裁注:“‘說教’者,說釋而教之。”《說文解字》:“詁,訓故言也。”段玉裁注:“‘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隨著后世語言研究的發展,凡是對古代典籍上的語言進行解釋說明的活動,皆可稱為“訓詁”;而這種活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可見“訓詁”原是一種常見的“生活境遇”。按上文生活儒學存在論的觀念,“訓詁”活動可被視為生活—存在本身的一種顯現情境。在此意義上,所謂“通之”便不是存在者層級上的主體在溝通“古今異辭”和“南北異言”,即孔穎達所謂“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而是生活—存在本身給出存在者,即訓詁活動生成“古今”(時間)“南北”(空間)“注者”“物”等存在者觀念的過程。
事實上,訓詁本身也是一種“不誠無物”“由言而成”的過程。無論是孔穎達所謂“釋”“通”“辨”,還是黃侃所謂“語言解釋語言”,皆屬于“言—說”活動。此“言—說”活動的發生,既確證了“言說者”自身之主體性,即“(我)言,故我在”,同時又生成了“被言說者”之對象性。在此意義上,所謂“通辭”“辨物”并不是對所謂文獻詞義、名物的訓釋與考證,而是“物”本身之生成(“人”本身亦歸屬于“物”),即“存在者”的生成,而作為“言—說”的“訓詁”在此意義上即成為一種前主體性、前存在者的活動。
“訓詁”生成存在者的過程,也是一個構造新的意義世界的過程。盡管當下發生的訓詁活動表現為主體對經典及其語詞的訓釋與考證,但這種活動事實上卻構造出一個新的意義世界,在此世界中,主體被賦予新的主體性,經典文本被賦予新的經典性。具體來說,由“言語不通”引起的理解障礙使得“訓詁”成為必要,這種障礙表面上體現在語言文字方面,但實際上是作為主體觀念中的事情而歸屬于“讀者”自身,所以“訓詁”實則是在消除主體之于文本意義所形成的“疑惑”,而掃除語言文字障礙的過程便展現為對主體自身之疑問的“疏釋”過程;“訓詁”完成即讀者之“疑惑”得以“疏釋”,使得讀者自身實現了自我觀念的更新,即實現了自我超越而贏獲新的主體性,從而成為新的主體。與此同時,經典文本也被賦予新的意義,即讀者經由“聲訓”“形訓”“義訓”等“疏釋”方式而賦予經典以新的意義,亦即通過語言文字之意義的擴充,經典文本的面貌得以煥然一新,從而生成為新的經典。這就是說,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正是被歷時性的“訓詁”活動所塑造的,經典文本由此而不斷獲得“去存在”的可能性。
比如說,在當前儒家哲學現代轉型進程中,古代儒家經典之所以具有現代性意義,正是被當下的詮釋活動所賦予的。例如,生活儒學對于《周易》經傳的重新解讀,并不只是使得“生活儒學”理論自身獲得了新的充實,更為重要的在于賦予了《周易》經傳本身以現代性意義,促進了易學哲學的現代轉型,闡發出一種包含三個層級內容的現代性易學哲學形態。一是關于建構現代社會倫理和價值的形而下學,即以探討社會制度規范賴以建構的正義原則為核心的正義論。黃玉順認為,《易傳》事實上提出了兩條正義原則。第一是正當性原則,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第二是適宜性原則,如:“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是關于絕對主體性的形而上學本體論,即將“變易”視為形而上之本體的“變易本體論”。在黃玉順看來,《易傳》提出的作為本體的形而上者并非某種固定的實體,而是一種流動的“變易”,此即《易傳》所謂:“《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三是關于如何描述主體性得以可能的本源存在論,即《周易》古經之本源情感論。在黃玉順看來,作為形而上者的“變易”本體源于陰陽交感觀念,而這種陰陽交感的觀念則是源于咸卦、觀卦古歌所顯現出的生活情感,其本身乃是生活感悟的存在者化、本體化、形而上學化的結果,所謂“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而這種“訓詁”活動,亦即對于古代經典的解讀與詮釋,無疑歸屬于現代性的生活方式,亦即當下生活的一種顯現。
以上即“哲學訓詁學”的初步構想,旨在立足于中國特有的訓詁學思想資源,為中國(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型探索一種切實可行的理論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