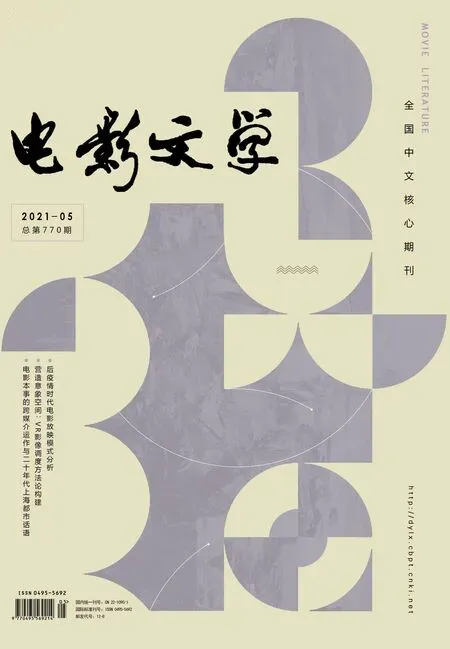《花木蘭》之殤:好萊塢的東方迷思
王 誠 鞠 斐/Wang Cheng Ju Fei
由美國迪士尼公司制作的真人版《花木蘭》在2020年9月11日登陸了國內的各大院線,這部被國內觀眾期待已久的經典動畫電影翻拍,經歷了多次檔期調整之后,終于與全國觀眾見面。從1998年動畫版《花木蘭》上映至今,中國社會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變遷,如今國內觀眾對于真人版《花木蘭》的期待除了源于對迪士尼作品一貫高品質的認同之外,更在于對該片抱有的個人層面與集體層面的認同期待,即在中國經濟、文化領域競爭力日益高漲的今天,西方世界如何再次演繹《花木蘭》這個中國古代傳奇故事。但是隨著這部影片在國內各大電影評分網站上的表現持續走低,國內觀眾對這部迪士尼的“誠意之作”,似乎并不買賬。
電影《花木蘭》從本質上來看是東方故事的西方化呈現,在這個被西方文化重構的文本中,電影自然就不會再以民族文化的立場去講述。動畫版的《花木蘭》得益于動畫手段本身的虛擬性和娛樂性,讓故事中內在的西方價值觀模糊在戲耍和打鬧之中。但是在真人版中,原先用于遮蔽的動畫手段改為真人實景的畫面內容后,電影的喜劇色彩被弱化,轉而以一種深邃和崇高的形象出現,這令電影本身的意識形態內容難以遮掩。影片大體上遵照了原始文本的人物設定,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這部被西方重構的中國民間故事充斥著大量的文化誤讀現象。電影似乎在致力于將《花木蘭》這個傳統的中國故事改寫為一種迎合全球觀眾口味的世界文本,淡化文本之中的民族文化印記,這反而令影片形成一種既非東方也非西方的異域性。這部影片在國內市場的滑鐵盧,代表了當下國內觀眾審美心理已經發生轉型,也向企圖進入中國市場的西方制片商表明,應當謹慎審視今日中國觀眾的審美傾向與其背后的文化因素。
一、文本轉譯中的文化誤讀
電影《花木蘭》的投資體量,無疑是好萊塢大片的標準,從選角到特效制作,皆保持了好萊塢電影一貫的高質量。但該片被觀眾詬病之處在于影片所描繪的古代中國,與國內觀眾所熟悉的景象差距過大,這是源于片中充斥著由于文化誤讀而造成的奇異景觀。理性來看,文化誤讀在文本的跨文化轉譯過程中是難免發生的。正如研究者所說:“電影的意義是由形式系統生成,由解碼編碼相互作用、共同建構的結果。而編解碼過程中的差異,本質上是由于主體差異導致的。”作為編碼主體的迪士尼公司,在信息的生產時必然帶有鮮明的主體文化立場。在《花木蘭》這部電影當中,跨文化的誤讀主要體現在行為誤讀、場景誤讀與概念誤讀三個層面。
電影《花木蘭》中,人物的一些關鍵性行動在國內觀眾來看都頗具奇觀性,例如片中花木蘭被媒婆安排相親的情節,花木蘭的臉上被涂滿了白色和黃色的顏料,這種妝容類似日本藝伎和印第安人的面部涂繪。這個細節的處理是《木蘭辭》當中“對鏡貼花黃”這句的影像呈現,且不言此處是否符合歷史真實,僅從這種圖譜式的妝容處理,就令人難免聯想到好萊塢以前拍攝的關于東方的影片,例如電影《現代啟示錄》中,涂著白色怪異臉譜的野蠻人;再如,電影《藝伎回憶錄》中,涂著白色臉譜的日本藝伎。《花木蘭》中的這種妝容處理與傳統好萊塢電影中對東方文化的描繪似乎沿用著相同的路徑,這種奇觀化的影像處理,似乎在刻意標記出現代的西方文明與愚昧的東方文明之間的顯性差異。
敘事空間是電影的敘事載體,不同的空間選擇,決定著整體的敘事風格。《花木蘭》在敘事的過程中,對空間的處理帶有深刻的文化偏見。例如在影片中,花木蘭從小生活的環境,被設定為土樓,這是一種圓形的群居建筑,分布在我國的東南地區。而《木蘭辭》的背景是發生在南北朝時期,花木蘭生活的地域具體在何處,并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影片此處對花木蘭的生活地域進行的一個定性,明顯是來源于對中國“家”文化的一個形象化誤解,將中國的“家族”比同為印第安人的“部落”,認為中國人的“家”是一個封閉群居的概念,所以用閉環的圓形建筑土樓作為東方“家族”的能指。除此之外,在對于皇城的描繪上,《花木蘭》則完全架空了歷史的實際。片中的皇宮形象,大量使用了唐朝的建筑風格,這種集體的唐朝化,正是來源于西方對于古代中國的刻板想象,可以看出盛唐在西方文化視野中就等同于古代中國,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讀。
如果說行為與空間的誤讀引起觀眾感官的不適,那么電影中對于概念的誤讀,則觸動了觀眾的精神層面。首先,片中主要人物一直強調“家族榮耀”這個概念,這也是整部影片人物行動的精神源頭。例如,電影中花木蘭決心放下梳子替父從軍,就是因為自己無法以常規的婚姻手段給家族帶來榮耀,所以選擇從軍來實現自己對家族的貢獻。這種對“榮耀”宗教般的崇拜,是對中國傳統倫理的一種嚴重夸張,似乎迪士尼想通過強化“家族榮耀”這個概念,來為花木蘭決心從軍建立一個觀念的合理性,但是這樣反而抽空了親情這一中國傳統倫理中最重要的情感基礎。
電影中的文化誤讀體現出以迪士尼為代表的西方電影在處理跨文化文本上的不足,但這個現象的出現是合乎情理的,不同的文化主體在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成果時,必然會刻上主體文化的印記。《花木蘭》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誤讀,是導致影片在國內遭遇口碑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國內觀眾對于影片《花木蘭》當中民族性內容的期待落空,則是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二、類型敘事消解民族特質
《花木蘭》的故事最早源于北朝時期的一首樂府民歌《木蘭辭》,講述了一個名叫木蘭的女性英雄,代父出征的故事。在歷史上,花木蘭的故事不斷地被重述,不同的時代,木蘭被賦予不同的故事背景。“在歷代的詩歌和民間傳說中,木蘭生活的朝代和地點各有不同,直到明代才被冠以‘花’這個姓氏。”在1998年時,該故事曾被迪士尼公司翻拍為同名動畫電影《花木蘭》,在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花木蘭的故事從古至今,一直是中國文化中“巾幗不讓須眉”的典范。這個角色承載著中國人家國同構的心理結構,表達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忠義思想,這是這個文本當中蘊含的內在維度。而歷史上以花木蘭作為原型而進行的改寫則數不勝數,例如明朝徐渭創作的雜劇《雌木蘭替父從軍》,該劇目收錄在雜劇集《四聲猿》當中。徐渭創作這部雜劇的背景正值明朝后期理學的衰退,心學的興起,所以劇中帶有一些思想解放的色彩,譬如對封建禮教的批判和對婦女命運的同情。在抗戰時期,歐陽予倩等人在上海創作了電影《木蘭從軍》,在當時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影響,在這一特殊時期的再度改編正是希望通過古代英雄故事來激勵當時人們的抗日熱情。所以對于花木蘭的改編在歷史上從來都沒停息過,花木蘭成為一個承載不同歷史時期社會價值的藝術符號,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時代內容,這是這個文本的外部維度。但是,歷史上所有的改編都貫穿了“忠義孝”這個精神內核,即家國一體的敘事邏輯。
好萊塢電影一直是類型電影的代名詞,在20世紀30年代就進入了類型電影的成熟期,至今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套極其成熟、完整的類型電影敘事模式,而這套模式的根基,就是觀眾。正如一位學者所言:“類型電影敘事建構了一個擁有堅實的觀眾基礎,貼近大眾的藝術趣味和情懷,靈活多變且不斷追求藝術創意的敘事成規系統。”服務于絕大多數觀眾的興趣愛好,是商業導向的好萊塢電影生產的鐵律,“它是以觀眾的喜好作為敘事建構的出發點和著眼點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迪士尼在創作《花木蘭》時,從來都沒有將其看作一個民族文本,而是當作一個徹底的世界文本去對待,它所對應的觀眾群體,并不是中國觀眾,而是包含中國觀眾在內的全球觀眾。迪士尼是一個非常擅長拍攝跨文化題材的好萊塢公司,例如《阿拉丁》《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等。迪士尼一直在從全球搜尋民間故事、童話故事來豐富自己的素材庫。這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源文本,必定帶有深刻的主體文化印記。迪士尼公司習慣于從不同的文本中探尋符合“美國價值觀”的“通用主題”,例如,女性獨立、親情、友情、救贖等主題的故事,這些全人類共通的價值理念,自然可以跨越文化邊界被全世界觀眾所接受。那么在強調這種共通價值的過程中,必然會弱化掉文本自帶的民族文化印記,例如,《花木蘭》中,影片的主要內容集中在了花木蘭的個人成長,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天賦,憑借一己之力拯救了自己的國家,為家族帶來榮耀。這是一個好萊塢常見的個人英雄主義的題材,這與美國社會強調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相呼應。但在《木蘭辭》當中強調的是家國同構,個人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迪士尼為了突出花木蘭的個人魅力,抽空了關于國家的內涵。另外,迪士尼的作品一直擅長使用正邪絕對對立的二元敘事法則去架構影片,《花木蘭》也不例外,二元敘事的最大弊端是抹除掉了文本自身的多義性,譬如原著中的花木蘭替父從軍背后繁雜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背景,在片中直接就被虛擬掉了,用“很久很久以前”概括了故事發生的背景。所以說迪士尼拍攝的《花木蘭》就是一部完全被成熟類型敘事規訓后的好萊塢文化商品。
民族性的內涵在跨文化傳播時必然會造成轉譯的困難,所以好萊塢運用自己成熟的類型敘事邏輯,強勢改寫了《花木蘭》的文本內容,將本土性、民族性的意義改寫為文化通行能力更強的“通用價值”。以個人奮斗和女性獨立為外殼,將美國式的個人英雄主義注入影片的血液中,完成了主體價值觀的傳達。而國內觀眾對于民族性內容的期待,在迪士尼商業化的類型敘事模式中落空,導致電影在國內遭遇了口碑崩盤。
三、形式轉換導致意義誤差
迪士尼公司的同名真人動畫改編電影是其旗下的王牌產品線,為迪士尼奠定了在全球動畫電影領域的霸主地位。根據迪士尼近幾年生產的真人版動畫改編電影來看,大體上可以將其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僅保留原動畫的人物設定與部分故事架構,電影的情節與原版動畫基本毫無關聯的影片,例如《小熊維尼》《沉睡魔咒》。第二部分則是完全沿用早期動畫作品的情節設定,僅有極小幅度的內容調整的影片,例如《獅子王》《阿拉丁》等。而此次上映的《花木蘭》屬于后者。2020年上映的這部真人版《花木蘭》翻拍自1998年迪士尼創作的動畫版《花木蘭》,電影在基本內容上與原版無異,但是在動畫版的虛擬性語言與真人版的寫實性語言的轉譯過程中,原版一些人物和場面是無法通過真實性的電影語言進行復現的。例如原版中的動畫人物小蟋蟀和小木須龍,在真人版中就被移除。這種內容的調整使電影原本的趣味性、童話性和游戲性被消解,變為一部嚴肅的個人成長史詩,電影的整體風格也由輕松愉悅變為莊重深厚。
在這部真人版《花木蘭》的改編過程中,歌舞元素的刪除對電影風格的形成影響最大。歌舞段落是好萊塢類型電影敘事庫中的一個重要表意手段,歌舞的使用是假定性意境營造的有效方式,例如電影《歌舞青春》當中,運用了大量的歌舞表演,來對青春期年輕人充滿活力的形象進行描繪。在動畫版《花木蘭》中,求愛、戰爭、爭執等情節通過歌舞來進行表現,強烈的內心活動被充滿動感的肢體動作外化后,情節本身蘊含的現實邏輯被神圣化,主人公的選擇和行動不合理性便被掩蓋,因為觀眾的視野被一種充滿煽動性和幻想性的畫面元素所占據。而在真人版本的《花木蘭》中,則刪除了全部的歌舞元素,原本可以被游戲性的動作和表情掩蓋的劇情矛盾之處,隨著歌舞元素的退出,變得無可遁形。例如在動畫版本中,花木蘭與最終的反派單于決斗時,木蘭用折扇雜耍般地搶奪了單于的寶劍,然后木須龍用煙花將單于擊飛,在一場絢爛的煙花中打敗了反派。這種游戲性的影像處理將生死決斗變成了舞蹈,動作感十足卻又充滿童趣。反觀真人版《花木蘭》,迪士尼由于實景拍攝的掣肘,放棄了動畫版本的歌舞和雜技段落。電影倏然完成了嚴肅敘事的轉變,搏斗與廝殺、戰爭與死亡等暴力場面被赤裸裸地展現在觀眾面前,這也是該片被美國劃分為PG-13的原因之一。
另外,動畫電影轉譯成真人電影后,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在于影像表現,這包括了人物的表演、場景的呈現兩個方面。動畫人物的表演與真人表演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尤其是在情感的傳達上,動畫人物的表演最大的特點是可以超越人體動作的肢體極限,例如在動畫版《花木蘭》的結尾高潮段落,花木蘭和伙伴們潛入皇宮中,一連串充滿童趣的打斗動作,肢體的運動幅度已經超過了現實人體的極限,但正是這種夸張的整體呈現才能消解掉搏斗和殺戮帶來的負面影響,因為該片的主要受眾還是以全年齡段為主,必須考慮到低齡兒童的觀賞需要。反觀真人版《花木蘭》,演員更換為真人演出,在片尾同樣的橋段,花木蘭和伙伴們殺入皇宮拯救皇上,這里的人物動作就是以真實的肉體搏斗和刀尖對拼為主,畫面的觀感也更加嚴肅和崇高。而在場景的呈現上,虛擬性的動畫造型天然就比實景拍攝的真人版在表現方式上更加自由,例如煙火炸彈、祖先顯靈召喚木須龍等戲劇性場面,在動畫版本當中就非常容易實現,而在實景拍攝時,這種反現實的場景是無法出現的,因為真人實景拍攝還是以現實邏輯的思考為主。那么隨著影像表現能力由于形式轉譯而導致的縮水,盡管電影保持了動畫版本的劇情內容,但是仍然會使觀眾感覺到不適,這是因為原本被動畫的神圣邏輯所中和的違和之處,在真人版當中被無限放大,尤其是情感表現方面的不足使得電影的一些關鍵情節無法自洽。例如花木蘭留梳離家這一段落,動畫當中,父親極其悲傷,在大雨中撲倒在地,而真人版當中,父親卻非常冷靜,沒有絲毫的情感波動,這自然難使觀眾產生情感的共鳴。
在形式轉換的過程中,雖然內容大體上與動畫版保持了一致,但電影的藝術風格隨著形式的轉換而發生形變,從童話般的女性成長故事變成了嚴肅的個人奮斗史詩,這令已被動畫先入為主的觀眾產生一種心理落差。電影敘事文本中的某些缺乏現實邏輯的內容由于失去了動畫這層甜美的緩沖之后,其不合理之處便被赤裸裸地展現在觀眾面前。尤其是帶有嚴重的“東方主義”色彩的內容,令國內觀眾產生嚴重的陌生感。這種“西方文化中心”的論調,在不符合本土文化邏輯之余,也會使觀眾對電影制作方的傲慢產生厭惡感。這可能是該片在國內票房、口碑雙雙遇冷的核心原因。
《花木蘭》作為迪士尼后疫情時期在中國市場投放的野心之作,其慘淡的票房表現和低迷的觀眾反饋,基本宣告了企圖消費后疫情時期中國觀眾的民族自信的計劃宣告破產。探究其遇挫背后的原因,不僅是一個產業問題,更重要的是源于內部的文化因素。《花木蘭》在中西方文本跨文化互譯的過程中產生的文化誤讀,導致了國內觀眾對其營造的情節畫面產生陌生感,而迪士尼以好萊塢成熟的類型化敘事模式,抹平了《花木蘭》這個文本當中的民族特質。真人版的《花木蘭》進行動畫向實景拍攝的翻拍過程中,電影沒有處理好動畫敘事與實景敘事之間的意義轉換問題,導致影片產生了難以彌合的邏輯誤差和文化隔閡。《花木蘭》在國內市場的折戟,其經驗教訓不僅對于企圖消費中國文化的外國制片商來說有參考價值,更是對于今后即將走向世界的中國電影提供了一個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