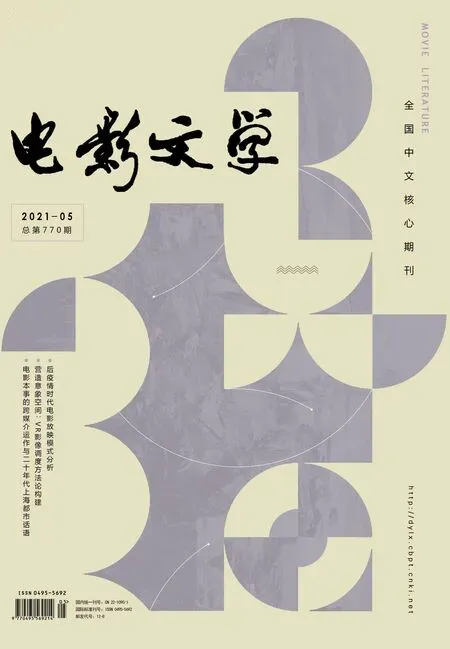“現代”女性與電影機器:1950年代陜西女子放映隊考察
原文泰 溫金陸(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藝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000)
一、陜西流動電影放映與女子放映隊
電影流動放映在陜西由來已久,20世紀30年代以前,陜西地區電影文化發展較為遲滯,這一時期的電影放映多數經由商販由外地帶入西安,以在各類公共空間流動放映的形式將電影這一現代性事物帶至西安。1938年中共成立的第一個電影機構——延安電影團,除了攝制影片,其另一項重要工作便是巡回放映,“并且在左翼電影工作者的影響下,逐步擴大農村電影放映的規模”。而其流動放映工作,除了讓陜甘寧邊區的人們接觸到電影之外,更重要的是“為新中國成立以后電影在全國各地的廣泛傳播奠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陜西的流動電影放映,從政策支持、放映規模以及所取得成效等方面,自然也在這一歷史傳統的脈絡之下。
新中國成立之后,塑造一個社會主義新國家的宏大圖景是應有之義,對處于意識形態領域的各類藝術形態進行重新改造是此圖景實現的重要步驟。于電影業,除了將電影制片收歸國有之外,電影放映行業也發生了相應變化。從宏觀層面來看,流動電影放映根植于廣大的農村地區,旨在借助流動放映這一形式以及電影的宣教功能,形成一種實用的意識形態機制。一方面對農村地區進行文化上的改造,最大限度加速農村地區的現代化轉型;另一方面也便于開展并深入對鄉村社會的控制。
1949年10月22日至11月6日,文化部電影局主辦并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電影發行會議,確立了“要在全國范圍內擴充放映隊,要使電影的教育教化作用得以更大地實現,放映隊的工作要與工農兵接軌,繼續深入農村加強電影放映功效”的方針。在此政策背景下,1950年6月,文化部電影局在南京舉辦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影局放映訓練班。培訓要求學員掌握系統的電影理論知識,以及機器操作、維修等關鍵技術,學員結業后在全國范圍內成立了700個電影放映隊伍。1953年到1956年4年間,“全國范圍內,總共增加了4000多個電影放映隊,200多個電影院,700多個劇團和630多個劇場。有大量增加的電影院、劇團和劇場分布在新興的工業城市。其中電影放映隊更是經常活動在各地工礦區和農村,為廣大職工和農民服務”。
自然,陜西省亦積極響應國家政策要求,在全省范圍內推進放映隊的組建工作。“1953年,國家文化部下達了《關于保證一九五六年電影放映網的建設和完成放映任務的幾項措施》的通知,決定在1956年前完成成熟的電影放映網建設,根據此通知,陜西省在1953年擬定了《陜西省電影放映隊及電影俱樂部登記管理辦法》”。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陜西省放映單位的數量迅速增加。“1953年全省只有37支隊伍,到了1955年,已有139個電影放映隊。”到了1956年,陜西省電影放映隊的數量達到了新的高點,“連原有的農村電影放映隊共計173個”。放映隊數量的快速增長仍然與直接的政策趨向相關,陜西省文化局黨組小組于1956年制訂了未來兩年放映隊的發展計劃:“1956年,預計增加100個新隊,至少需要放映隊干部250名,1957年預計發展140隊,至少需要490名放映隊干部。”
女子放映隊作為陜西電影放映隊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正是在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下出現并成長了起來。1953年7月17日,真正意義上陜西的第一支女子放映隊成立,“受陜西省放映大隊及長安縣委宣傳部及文化局雙重管轄”,“該隊共有五個同志,她們都是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一般都具有初中程度的文化水平”。該隊成員包括了“隊長盧樹坤,隊員有袁秀英、李晶瑩等人”,盧樹坤、蔡雅貞、袁秀英、李晶瑩四人同是師范班的學生,在師范速成班畢業后被分配到了放映隊,也是她們初次接觸電影放映工作。吸收了此前流動放映中所遇問題的經驗,女子放映隊隊員在正式進入工作前,都在電影放映三隊“由四個師父分別帶著四人進行放映技術的學習”,又“連續在西北俄文專科學校、省文教處等地進行了實習放映”。并于當年8月開始了正式于長安、咸陽等地的流動放映工作,首批影片包括了沈西苓的《中華兒女》。
女子放映隊的成立肩負了多重的政治使命,“女子放映隊是一個獨立工作單位、政治宣傳單位、群眾工作單位,也是財經上的獨立培養單位和文藝工作單位”。首先,進行流動電影放映是其本職工作,同時由女性放映員來放映電影,也讓她們成為全國流動電影放映這一歷史潮流的效果體驗主體。將女性群體直接置于現代與傳統文化沖突的主戰場中,而女子放映隊的放映實踐形成了女性的在場,亦為女子放映隊塑造了一種現代的女性形象。在這個過程中,女子放映隊取得了顯著的工作成績,“在不斷的摸索后最終五人確定了通信、放映、發電等各個方面的明確分工,在這其中,女子放映隊隊員袁秀英在發電崗位完成了200多場安全放映的成就”,這份成績在當時的各放映隊中也是相對少見的。從1953年12月起的半年時間內,女子放映隊與其他流動放映隊一起,“在陜西五十一個縣市中配合政策總路線宣傳,在農村放映了共三十一部影片,共放映了約七百五十場,觀眾達七十九萬人次”。
女子放映隊在1957年便結束了其歷史使命。在這四年多的時間內,先后共有13名女放映員曾在女子放映隊進行放映工作,分別是盧樹坤、蔡雅貞、袁秀英、李晶瑩、高鵬、姜亞蘭、于文葉、于鳳霞、李秀榮、陳佩英、李春榮、李鳳霞、劉慧芝等人。1955年10月,女子放映隊第一任隊長盧樹坤因懷孕離開放映隊,隊長一職由袁秀英代替,剛從陜西放映訓練班畢業的于文葉、于鳳霞二人被調入,成為加入女子放映隊的最后兩名女性放映員。1957年,“隊員姜亞蘭因為解決夫妻分居問題調至安康地區,由男子隊員張學華替補21隊成了男女混合隊”。放映隊也由原來的省第21放映隊更名為長安縣第一電影隊,至此,純粹的女子放映隊便宣告結束。
二、與機器結緣:女子放映隊成立因由
顯而易見的是,流動放映對隊員的體力、技術等素質要求較高,從體能層面似乎更適合男性,尤其深入鄉村的放映工作,由于路途、條件上的艱苦,對女性而言更是構成全方面的挑戰,而且流動本身所帶著的不確定性也與很多女性對穩定生活的追求產生矛盾。在這種復雜的境況下,解決為什么是女子放映隊這一問題,顯然有助于增進理解陜西女子放映隊在特殊歷史語境下的時代價值。
正如十七年時期的大多數文藝運動一樣,宏大歷史時期的政策趨向是女子放映隊成立的主要推手。1950年出臺的《婚姻法》為男女平等這一性別理念提供了法理依靠,政策的逐級落實使得女性成為新的社會生產關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社會地位和社會角色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意識形態角度,新中國推進男女平等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塑造社會主義式的女戰士、女革命者以及女強人等形象,將社會生產領域中勞動女性的身體進行多樣化描繪,包括其自然身體和政治身體等多個層面,于是各行各業的女子第一人響應政策紛紛出現:“1952年8月新中國第一支女子測量隊成立”,1953年2月26日,“《群眾日報》第一次對新中國第一個女推土機手胡友梅進行宣傳”,以及對“新中國第一個女火車司機田桂英和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的官方宣傳,這些同質新聞報道聚集出現,對主流輿論進行議程設置,嘗試在社會中廣泛引發“女子第一人”的熱潮。具備生產能力的女性,成為新中國建設初期的標桿,其所體現出的吃苦耐勞、積極進取以及努力提升自我的身份標簽,某種程度上便是體制所認可的社會主義新主人翁們所應具備的品質,“事實證明,她們是能干的,有本事的,不比男人差。女戰斗英雄郭俊卿、新中國第一個女火車司機田桂英,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還有紡織、卷煙業的新工作法創造者郝建秀、張淑云等好多婦女,都是很好的榜樣,所以婚姻法上就規定婦女和男人一樣可以出來工作”。而建設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則是新中國藍圖中的重要圖景。
這一時期,重建社會主義新中國宏大圖景的重要方面還包括動員女性參與社會主義建設。1953年1月14日,陜西省召開了第二屆婦女代表大會,會上重點討論了婦女如何積極介入生產勞動等問題。如男性一樣進行生產,成為新中國構建女性新身份的具體措施。對新中國的女性而言,唯有當她們進入社會生產并由此完成了自我社會身份的建構之后,其從一個普通的婦女向社會主義新女性轉變的現代化進程才能最終完成,從而實現恩格斯所言之“婦女解放”。而這項工作由已經經過改造、地位獲得提升的女放映員們來進行,則既是意識形態工作的現實需要,也是合理調配女性生產資源的重要舉措。某種程度上,女放映員成為意識形態工作的一種樣板。而且,新中國意識形態工作的一種重要策略,便是將全民卷入建設和生產熱潮。女放映隊員不再單純是歷史背景下的必然產物,更是創造新歷史、新生產關系的重要主人。
另一方面,女子放映隊員們的電影放映過程,又在女性與沉重、冰冷的放映機器之間,形成了一種跨越性別溝壑的職業實踐。女放映隊員參與到技術探索的現代進程之中,盡管過程緩慢,但仍有可能成長為社會主義新空間下的新婦女。而與在工廠進行固定生產的女工相比,女放映隊員們與機器的關系更為親密,她們不僅要在放映點進行機器操作,在放映前后還需要對機器進行檢查與保養,往返于放映點的過程同樣需要將放映設備進行搬運。顯然,放映設備其自身所蘊含的機器精密性,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現代和文明,當女性利用自己的身體,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并在這種機器與意識形態宣傳之間進行了勾連的時候,一種社會主義式的共和國寓言就被構建出來了。這份寓言包含了幾個層面的意義:其一便是新中國的婦女不論出身,都可以在自己的勞動中獲得價值;其二便是新中國的女性也得以突破技術的藩籬,在生產實踐中掌控機器甚至改造機器;另外,女放映隊員的性別身份,一定程度還成為一種稀有的欲望鏡像,她們身著工作服并進行勞動的場景極具象征意義,即新女性與現代機器之間的曖昧關系,也成為意識形態深入鄉村地區,動員婦女、改造婦女的視覺切入點。
女放映員的價值實現也被包裹于制度需求之中,在這種運行機制下,女子放映隊成為新中國現代化圖景的顯要符號,是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性的重要標志。1954年6月25日至7月5日,陜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廳“在長安縣五星、細柳區由我省電影放映隊第二十一隊(女子隊)舉行了科學教育影片試映”。這次放映工作的特別之處在于其國際性質,蘇聯專家斯道爾良斯基專程到場觀看并舉行了座談,會上蘇聯專家斯道爾良斯基贊揚了影展的舉辦并講述了蘇聯的電影事業和農村電影放映情況。這樣一次重要的、面向外國專家的電影展映,選擇女子放映隊進行具體任務執行,除了女子放映隊過去優異、幾無瑕疵的放映成績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性別/婦女的框架恰恰為在農村社區言說國家的現代性提供了語匯”。女子放映隊這一群體的社會意象,成為女性平等以及女性進入勞動生產領域的表征,進而成為這一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圖景的重要代表。由此,在外國友人面前,由女性來操作機器進行電影放映便充滿了進步的意識形態色彩。
顯然,陜西女子放映隊正是地方決策者受宏觀政策、對社會主義新圖景建設熱情以及現實需求等多重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產物。而此時,除了十七年時期中國電影從影像內部開始構建起女性覺醒、社會主義新圖景以及現實主義敘事之間的親密關系之外,由女性來進行電影放映這一新機制與新場景,亦成為從電影創作外部進行勾連的景觀呈現。
三、女子放映隊的放映困境與自我成長
但這種新場景的實踐過程并非全然順利,自身踐行著性別平等并且肩負傳播社會主義現代理念這一政治任務的女子放映隊,在鄉村的放映實踐遇到了一系列的難題和困境。盡管在當時的城市生活中,傳統的性別格局已經在逐漸瓦解,越來越多的城市女性進入生產空間,但時年中國多數農村地區則是不一樣的景象,男尊女卑、內外有別仍然是主要的性別秩序。女子放映隊員進入這些場景空間,則必然面臨著文化和身份認同上的沖突。
在農村文化改造的初期,村民們對如男女平等一類的新思想有明顯抗拒,認為男女平等違反歷史規訓,他們深信女性地位的提升不僅會削弱其男性地位,并且會導致“反過來,來欺負男性”的現象。這種思維模式在《婚姻法》在陜西地區的初期宣傳中也有所體現,有的農村群眾認為:婚姻法是欺凌男性的法規,“某些男干部或群眾說婚姻法是‘婦女法’,有時只宣傳婚姻法的部分條文:如只說離婚自由,保護非婚生子女等”。顯然,農村這種保守的性別觀念的確為女子放映隊的工作開展帶來了挑戰,一個典型現象就是這些年紀輕輕的女放映隊員被村民們稱為“諞干板的電影婆娘”。村民們認為正經的“一個大姑娘是不會干這種事的”。由此,伴隨著女放映隊員在鄉村空間的身體移動,其所面臨的困境之一便是其身體不得不處在一種被不斷凝視的時空場所之中,而且由于她們的放映行動在傳統性別權力上的僭越,難免會面對來自男性權力的羞辱。女子放映隊隊長盧樹坤曾在采訪中講到過她的一次親身遭遇:“我到第五村去,推著車子,拿著話筒,拿著糨糊,拿著海報貼。貼完了海報以后,人家一個傳一個,小小一個村都來了,都到村中間。我就拿著話筒在那兒喊,我們今天晚上在姜村演什么電影的。剛一喊完,過來一個惡狗,一下子撲過來,在我腿上狠狠地咬了一下。把我疼死了,疼得簡直跪在那兒都起不來。結果那群眾都哈哈大笑:‘這下子把電影婆娘給咬了!’把我難過的,我眼淚都出來了。”
另外,放映隊員還面臨機器帶來的考驗,“僅發電機便有四百多斤重,每一次裝車都往牛車上裝,我們八個人狠勁兒地往上抬,轉一個點要抬上抬下”。機器也常常臨時給她們制造難堪,第一次現場放映狀況就是由發電機的損壞引起,補演后不久,發電機再一次宣告罷工、漏油。女放映員們盡管學習了如何放映電影,但對技術的鉆研還是有很大欠缺,“只會個拆洗零件,其他的什么也不會”。
放映工作流動性帶來的問題還包括食宿以及心理上的困境。流動放映所至地區往往條件艱苦,隊員們大多數時間住在村子的學校里,偶爾還會打地鋪,但“跳蚤、蚊子咬得不得了”。女子放映隊在長安縣共負責22個放映點,這也讓她們疲于在各個放映點之間趕場,“頭一天晚上放完電影,收拾完都十一二點了,有時候甚至更晚,而袁秀英則要提前一兩個小時騎車去安排好放映場地、食宿、售票點、分發廣告”。日常的奔波也讓很多隊員產生了離家的愁緒,尤其對一些已經成家的女性來說,就有了更多的牽掛,社會上也出現“認為電影隊是無家可歸的人”的消極輿論。
這些現實問題的存在,給女子放映隊員們造成了一定困擾,也讓她們偶爾質疑自己職業與身份的價值所在。但在宏大的國家話語和政策褒揚之下,多數放映隊員產生了一種不甘為人后的拼搏精神,她們深信新中國所構建的男女平等圖景,認為自己被這些負面言論打敗是非常丟人的事情,既對不起國家的培養,也顯得工作能力不如男性。這也激勵她們更努力地工作,在不斷的放映實踐中對性別邊界進行著試探,從而獲得放映群眾與來自官方的雙重認可。
由此這些難題不僅沒能阻礙女子放映隊的工作,反而成就了女放映員們作為個體的一種主體覺醒。女子放映隊進入農村進行放映實踐,盡管背負著意識形態宣教和政策執行的多重任務,但女性特質也必然會在放映實踐中產生影響。如前所述,宏觀層面的制度并不能順暢地在農村地區實施,女子放映隊隊員成為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媒介,這就意味她們需要充分地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去更好地落實政策和完成宣傳任務。于是,生產領域中的女放映隊員們會以其特有的方式去應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法,甚至會由此衍化出比男性更為突出的工作能力,并最終獲得個體的成長。顯然,宏大的制度框架催生了個體化的思考,放映隊員們考慮到了如何以女性身份去更好地實現電影放映效果,如何更好地落實鄉村文化改造這一重任。
具體層面上,女子放映隊隊員們想出了很多策略來提升放映效果,充分發揮了女性心思細膩的特質,與男放映員相比,她們“愛護機器,定期清理放映機器,并手工制作了特有的保養工具”。為了使放映機器可以安全進行放映并且不致過度損壞,女放映員們會定期清理汽缸,去除汽缸積碳。考慮到“廣大農村受眾過去沒有看過電影,對于電影藝術的表現手法并不熟悉,需要電影放映員們做好影片的宣傳解釋工作,來幫助農民群眾看懂電影”。為了貼近村民的知識和欣賞層次,她們用當地人相當熟悉的秦腔和豫劇作為映前宣傳的方式,“根據運動中心內容自制幻燈片在映前放映,或是通過時事政策演講來擴大宣傳效果”,從而“使群眾得以更好地接受她們”。
冬天天氣寒冷,她們還會用自制的棉包包裹住放映機器,保證其溫度以便于放映期間工作。此外,還會手工制作露布和幻燈片,并提前熟悉影片內容,進行映間講解。“因為電影藝術不像戲劇那樣把每一件事件、事情都給觀眾交代,也就造成了農民觀眾不易理解,在這時女子放映員們就要自己解說電影,在放映過程中,做好影片宣傳解釋工作,像演員刻畫角色那樣細心琢磨每一個鏡頭畫面的情節和整部影片的中心思想,隨著每個鏡頭的變化進行宣傳解釋,做好映間講解。”為了避免出現突發的放映事故,放映期間她們恪守職責不離開發電機,處處體現了女性的細致認真和吃苦耐勞。映后,她們仔細整理放映設備,與同時期男性放映隊偶爾丟失銀幕等狀況,形成了態度上的鮮明對比。從某個角度來看,放映隊員們懂得適時利用自己的女性特質,這種主動的性別策略,實際上也是放映隊員主體性逐漸增強的一種體現。
隊員們的努力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肯定,既有來自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可,“區干部在召開電影座談會時,經常夸獎女子放映隊,對女子放映隊隊員如此能吃苦表示贊揚”,亦有來自民眾的積極反饋,“群眾的觀影熱情越來越高,甚至在極端天氣下仍然會堅持觀看電影”。這種正向的反饋也鼓舞了放映隊員們繼續努力工作的熱情,形成了良性的循環。“參加女子放映隊,對業務技術、人事關系、為人處世和搞好群眾關系有極大幫助”。女子放映隊所獲得的,不僅是榮譽層面的成績,還有自我意識的覺醒,她們能夠清醒地認知到,男女平等并不是只靠官方的宣傳政策就可以得到實現,而更多的是需要女性自身爭取,通過努力、學習以及對國家政策的響應,女性同樣可以獲得優異的工作成績。大部分女放映員們離開女子放映隊后仍在電影系統內的其他崗位上發揮余熱:1956年2月陜西省文化局提出為計劃大力發展電影、藝術、社會新聞出版事業,“并決定在陜西省電影放映干部學校,培養電影放映干部來帶動廣大群眾開展文化工作”。盧樹坤一直在校內從事教育工作直至1992年退休;蔡雅貞結束在西北訓練班的培訓后便遠赴蘭州,在東崗電影院工作;李晶瑩在西安市長樂劇院工作至退休;“高鵬在電影放映訓練班改為學校后一直擔任教務干事;于文葉被調至渭南電影公司從事檢片工作;李春榮被分配到三原放映站售票;姜亞蘭在1957年被調至安康縣電影隊,1980年調至臨潼中國電影資料館西安電影資料庫”。
結 語
從特定角度而言,無論怎樣凸顯女性的獨特價值,這一時期女放映隊員們仍然處在革命父權的話語支配之下,女子放映隊的主要目的仍是通過放映實踐傳遞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女性身體成為一種宣傳工具,“權力與人的肉體存在密切關系,權力往往將肉體作為操控對象,而肉體則往往是權力展現的最佳場所,也就變成了所謂的政治肉體”。表面上,通過對女性身體的策略化宣傳,使其體現出新中國的先進性,即與男子一樣的勞動能力、權利和收獲。但事實上,與男子一樣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異樣的平等,忽略女性自身的生理特征,以及女性在家庭、社會中的特殊地位,正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及的,這種思維下的女性標準本質上仍然是男權社會規訓和定義下的“女性氣質”。由此,女放映隊員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實現是被安排的,是“在正確世界觀的領導下,選擇已被界定的女性平等道路”。而且,即便一些放映隊員并不擅長或者真正熱愛放映工作,她們也必須“保證勞動熱情和革命干勁在藝術這種特殊的意識形態上得到它應有的反應”。在進步/落后的二元語序當中,個體就常被裹挾進意識形態的洪流之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女子流動放映呈現出一種復雜的語義,女子放映隊以電影放映為傳播載體,在鄉村性別觀念的沖擊下不斷地完善自身,并靠著自我努力逐步改善鄉村受眾對于女性的認知,彰顯了極富群體色彩的進步性。她們的電影放映活動,一方面體現出女性也可以擁有如男性一般的生產能力,同時又充溢著與女性特質有關的相應策略。“男女平等的觀念不僅是一種公共的政治理想,它更觸及變革人們生活中最私密的空間和相處方式”。宏大政策的設計與推行在農村地區的空間關系再生產,正是借由女性放映隊員這一群體實現了冰冷的制度與豐富的日常生活之間的溝通,關乎性別平等、農村文化改造等現代性話語;也正是基于女放映隊員利用電影、放映機器等所進行的身體實踐,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新圖景的有機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