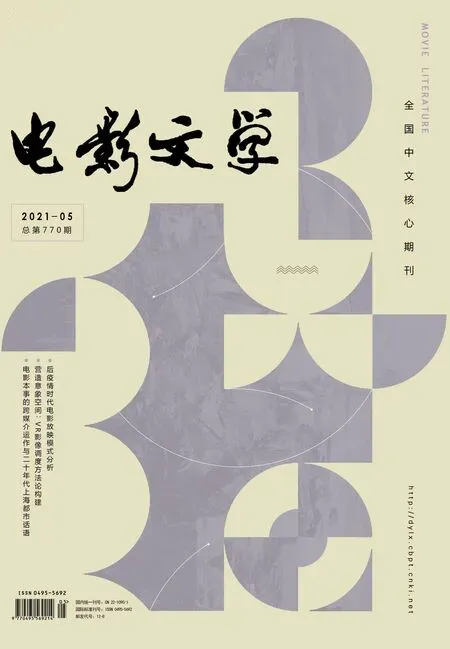電影本事的跨媒介運作與二十年代上海都市話語
劉真真(南京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在現有的研究中,電影本事一直被視為電影與文學文體互滲后所產生的電影文學形式之一。周曉明的《中國現代電影文學史》與周斌的《中國電影文學的傳統與貢獻》都將電影本事視為一種新興的文學樣式:電影本事兼具小說的敘事特點與電影的蒙太奇思維,它既可以是劇情梗概,也可以是電影劇本的雛形;《中國無聲電影劇本選》甚至直接將電影本事作為缺失劇本的替代品。魯勘、程景楷等人的《中國電影文學形式的形成與發展》補充了電影本事與文明戲的關系,但也只是一筆帶過:“早期的電影本事……在情節安排上有點像戲劇,但無對話或很少寫對話。”以上著作與論文都將電影本事置于文學與電影、文學史與電影史的交互與重疊之處進行研究,也有學者試圖進一步分析電影本事中電影與文學互動的實踐過程,如黃勇軍等人的《20世紀20年代中國電影小說的濫觴與發展鉤沉》,談潔的《從本事到小說:電影劇本在早期電影雜志中的形態變遷》與李道新的《電影本事的文體互滲與跨媒介運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道新在其論文中點明了電影本事跨媒介運作的特點,這就使對電影本事的研究跨出了僅限于電影與文學這兩門學科的狹隘,開始注意到電影本事與其載體——不同媒介的互動關系。他指出:電影本事是電影同小說、戲劇問題之間相互影響的產物,它一方面吸收了諸如劉吶鷗、穆時英等新感覺派小說家作品中的“視覺化”與“通感”描寫,又在小說文本與話劇劇本重視故事情節的影響下開始注重情節架構與人物關系。不過李道新并未就此深入下去,仍然停留在對不同媒介中文本的孤立分析上。
不容忽視的是,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印刷文化的興起密不可分,而話劇和電影的演出、放映活動同樣也是都市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對電影本事的文體互滲與跨媒介運作的研究必須將其置于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背景之下。約翰·菲斯克指出:“在媒介文本從文化方面制造意義的過程中,互文性起主要作用。文本同時與其他相似的或不同的文本關聯,通過這種方式為觀眾制造意義。”彼時的上海都市文化,正是東西方文化匯聚于上海時的碰撞——在舊倫理與新觀念、舊文體與新文體,作為媒介的雜志、報紙與作為媒介的電影、戲劇之間的互文中誕生的。因此,電影本事不僅是“文體互滲”,更是“媒介互滲”,不同的媒介給電影本事帶來不同的敘述策略:報紙與雜志上的電影本事與電影說明書上的相比更偏重宣傳,有些還帶有評論的性質;由于媒介間的互相滲透,電影本事的敘述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它力圖采用一種視覺化的敘述方法,既使讀者轉變為電影觀眾,也使閱讀快感過渡為視覺快感。在以上的論文中,電影本事時常被視為影響的結果,事實上電影本事的敘述也在影響著新聞報道的敘述。電影本事既被上海都市話語建構,也同樣是都市話語的積極建構者。
一、《閻瑞生》電影本事與上海都市想象
“文體互滲”不僅使電影本事兼具文學與電影的敘述、修辭特點,同時也使讀者的閱讀習慣從印刷媒介過渡至較為陌生的電影媒介。從電影史的角度來說,電影本事同樣是歷史經驗的一種表述,借由互文性這一概念分析作為史料的電影本事,我們或許可以重新審視1920年轟動一時的“閻瑞生事件”。這樁殺人案因其離奇的情節、受害者妓女身份的艷情色彩迅速成為街頭小巷的熱議話題。按照絕大多數論文的觀點,正是靠上海紙媒大力宣傳造勢,才催生了一批以案情為原型的舞臺劇,乃至將其搬上銀幕。這些論文不約而同地將電影對原事件的呈現視為一個社會事件發酵的最高潮,其中暗含著一種歷時性的、“媒介進化論”的觀念——在所謂“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紀實性”“逼真性”的驅使下,各種媒介中的文本次第不斷復原案情的現場,直到它從報紙新聞變為舞臺劇本再進化為電影(電影顯然是最具有以上幾種性質的),即典型的“本原”歷史主義式表述。然而《閻瑞生》電影本事并不能簡單理解為“閻瑞生事件”這一歷史的最終形態,可以說,從創作者們選擇“閻瑞生事件”為電影素材的那一刻開始,就是以滿足、還原觀眾的視覺性期望為目的,這也正是在該片的宣傳策略中總是強調電影對真實場景高度還原的原因。因此,《閻瑞生》電影本事的誕生是共時性存在的不同媒介中文本互文的結果,所謂的逼真性、紀實性只是其表面的一種偽裝,它并非要還原所謂事實真相,而是要將這樁殺人案上升為齊澤克所謂的社會征兆,且電影本身的放映也并不意味著文本跨媒介運作的結束。
海登·懷特在《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中指出:“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歷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過壓制和貶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視別的因素,通過個性塑造、主題的重復、聲音和觀點的變化,可供選擇的描寫策略,等等——總而言之,通過我們一般在小說或戲劇中的情節編織的技巧——才變成了故事。”當楊小仲創作閻瑞生電影本事之時,他無意識地將自己代入為歷史學家卻有意識地對原素材做了增刪,他需要用一個特定模式來整合自己的敘事,從而將這件令人震驚的案件——一個類似“泰坦尼克號沉沒”那樣的社會征兆迅速納入已有的文化范疇之中,當然,一部分“震驚”是必須保留的,它是《閻瑞生》吸引力的主要來源。因此,《閻瑞生》電影本事對原有報道素材的取舍正表明了作者對敘事模式與修辭形式的選擇。我們首先來梳理一下報道素材:《申報》在1920年6月19日開始了對閻瑞生一案的報道,它是以王蓮英父母對真兇的懸賞的形式出現的。1920年7月2日,《申報》上開始出現《花國總理蓮英被害記》的出版通告。1920年7月5日,《蓮英慘史》《閻瑞生秘史》與《蓮英被害記》在《申報》上發表了出版通告,而官方審理《公共公廨審謀斃蓮英案》直到1920年8月20日、21日及27日才見諸報上,盡管此案犯罪者與受害者都為國人,但會審官、律師甚至探目俱是西人,審案所用語言也為英語。自9月14日起方才在內地法庭(護軍使署)審理。審案中所遇到的問題,其一是此案審理權屬公共公堂審理還是內地法庭(事情的起因在租界,但謀殺行為是在非租界處發生的),其二對第二被告吳春芳的罪責的裁定究竟參考國內法律還是租界法律,其三即閻瑞生與吳春芳口供不一致(閻稱自己只想麻暈王,用麻繩勒死王是吳所為,吳則稱自己只是為閻等放風并未殺人)。8月28日,閻瑞生與吳春芳解護軍使署,報道特別記錄閻、吳二人之穿著:閻身穿麻布衫佩戴十字架,吳身著白夏布衫。11月24日,《申報》報道了11月23日閻、吳二人執行死刑之過程,因為閻瑞生的天主教信仰,執法者特別安排了牧師;吳春芳本無宗教信仰,卻也和閻采用了一樣的懺悔方式。在前往刑場的途中,兩人狀態完全不同:閻瑞生閉目,而吳春芳如傳統小說中“草莽英雄”一般破口大罵王蓮英復又高唱西皮二黃。1920年11月25、26、27、28、29日,《申報》連載《補錄謀斃蓮英案之軍署判詞》,對整個案件進行了比較完整的梳理。
《閻瑞生》電影本事主要參考的應當是《補錄謀斃蓮英案之軍署判詞》,作者刪除了一些與吳春芳有關的細節,并增加新的情節,從而重塑了吳春芳這一人物形象。原素材中,閻曾給吳大洋一元洗澡剃頭并購買繩索,吳花完一元后又向閻乞洋四角以購買繩索,這個細節實際上充分揭露了吳的流氓習氣。在行刑過程的報道中,吳口供“直爽”,前往刑場之時大罵王蓮英,高唱西皮二黃,由此可見,吳春芳是個頗具江湖氣的混混,他參與犯罪,未必完全是因為金錢,也可能有身為混混的粗魯、膽大與殘忍,甚至可能是出于“江湖義氣”。而在電影本事中,作者讓閻瑞生與吳春芳成為共同為金錢、債務苦惱之人:閻與吳相遇是在閻自跑馬場賭輸之后,吳向閻“狼狽稱貸”,閻借吳一元。在此處,編劇將促使閻吳二人共同謀劃的多種可能性簡化為一致的金錢短缺,至此吳春芳的人物形象得到重塑:一個中國傳奇式的草莽人物消失了,取代他的是受過西方教育的閻瑞生的跟班。這個改動是極為意味深長的——在《閻瑞生》電影本事的敘事邏輯中,原先身為江湖草莽的吳春芳成為“異質”的存在,原素材與電影本事分別體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模式與社會觀念。
《閻瑞生》電影本事實際上由兩段敘事——欠債殺人與逃亡組成,第一段敘事最關鍵的兩個場面“見財起意”與“謀殺王蓮英”分別發生在城市(妓院)與鄉村中,從而構建出充滿誘惑的銷金窟——現代都市上海與法外之地——鄉村之形象。在電影本事的敘述與描寫中,都市呈現出流動的特征,其一是金錢的快速流通。閻瑞生穿梭在不同消費場所,他從大世界出來后便直奔小花園蓮英處,向題紅館借的鉆戒又很快被置換為賭資并在賽馬場輸得一干二凈,閻遇吳時吳也為債務所苦,促使二人合謀的主因正是因金錢快速流通所致的拮據,而閻瑞生殺人搶奪首飾之后又回到題紅館處(消費)。其二是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主人公輕而易舉地在鄉村與都市之間往來,而閻瑞生殺人后乘坐輪船、火車逃亡的行動更是強調了一種獨屬于現代都市的時空的流動性。與城市相比,鄉村顯然相對閉塞,閻瑞生只在殺人和逃命時才來到這里,其岳父得知殺人之事還是靠著原始的口耳相傳(派遣乳母去城里探聽)。繩索不僅殺死了王蓮英,更在閻瑞生逃命時發揮了重要功用,最終閻瑞生也被“繩之以法”,繩索與汽車作為勾連起兩段敘事的重要符號,同時也暗示著中國/鄉村不再閉塞,在現代法律與刑偵系統面前它已無法成為閻瑞生等犯罪者的庇佑。
第二段敘事明顯受到了20世紀20年代在上海大行其道的偵探片之影響,閻瑞生逃亡過程中,曾潛入松江奈山教堂向神父求救而“神父斥之”,這段情節并未出現在《補錄謀斃蓮英案之軍署判詞》中,應當是根據前文提到的閻瑞生之天主教信仰改編而成,卻又呈現出強烈的道德訓誡色彩。在電影本事的敘述中我們絲毫不曾感受到原審判過程中東西方在法制與語言等上的差異,也沒有任何關于語言和法律的討論,在緊張的抓捕過程后影片毫無黏滯地進入了正義審判的結局,結合前文中對吳春芳的重塑,編劇試圖改寫并整合東西方的生活經驗、法制、宗教/道德觀念,緩和現代化進程中所經歷的社會矛盾。通過對上海各區域的銀幕再現,上海也由單純的地理空間轉變為影像中具有復合含義的文化空間,從而讓觀眾更好地縫合進電影所構建的幻象——一個現代的上海之都市想象中。
“歷史本身在任何意義上不是一個本文,也不是主導本文或主導敘事,但我們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敘事模式體現出來的歷史,換句話說,我們只能通過預先的本文或敘事建構才能接觸歷史。”換言之,“閻瑞生事件”或許和真實的上海略有出入,但它構建了1920年上海的都市想象:現代性以一種不可逆的、必然的意志將整個中國連同它古老的鄉村都卷入這勢不可擋的洪流中,盡管令人不安的流動性帶來了犯罪與死亡,但縱情聲色與金錢的誘惑仍使人們對都市趨之若鶩,而這一欲望以對罪人的道德與司法審判粉飾。《閻瑞生》電影本事使觀眾安全地觸碰到原本生活經驗與文化中的禁區,它與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現代都市生活一起帶來了有別于以往的新奇快感。
二、電影本事的跨媒介運作與新聞的視覺化敘述
電影本事往往被視作電影與文學相互影響的結果,事實上,電影本事也在跨媒介運作中積極地影響著新聞的敘述方式,《申報》1921年3月23日的一則新聞足以證明這一點。這篇名為《哈埠逆倫巨案始末記》的報道,講述吉林省某團長之子因與父親不和最終選擇與弟弟一同弒父的不幸故事。雖然標題中“逆倫”一詞表現出寫作者仍然受到舊倫理的束縛,但整篇報道并不以傳統的新聞文體寫就,反而更近似于一篇驚險刺激的“電影本事”。該新聞的主人公曹佩雄在弒父之前曾前往電影院,觀看了一部偵探長片,這部影片“情節戲文,均臻佳勝,唯佩雄毫不在意,坐立不安,影戲未完,即不耐坐,昏悶回家”。曹佩雄選擇觀看偵探片,或許是試圖通過他人英勇的冒險故事來麻痹自己緊張的神經,獲取膽量,但偵探片的常規結局一定是偵探偵破案件、抓獲罪犯并彰顯正義,因此即使情節生動的影戲與電影院構成了一個使人暫時忘卻現實的世界,作為潛在殺人犯的曹佩雄卻對此毫不在意,甚至坐立不安(此處描寫從側面也表現出寫作者對電影的觀念:電影對人的心理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如果曹佩雄不是要殺人,他很有可能和其他觀眾一樣沉浸在電影情節之中)。曹佩雄并未看完這部偵探片便離開了影院,這個“未結束”的故事在敘事中以曹佩雄本人的殺人行動繼續發展著,因此,主人公從影院的離開只是情節的開端,它將一樁殺親案與偵探電影的情節結合起來從而增加了敘事中的戲劇性,也暗示著電影這一視覺奇觀最終會演化為現實世界的災難,電影的運鏡方式與敘事方式也平滑地逐漸加入后續的敘事之中。
影戲院顯然是一個具有現代特征的空間,在影院中坐立不安的曹佩雄試圖進入父親的住所——一個傳統、強硬的軍人(隨身攜帶一柄手槍,坐臥不離)所統治的倫理空間,這里的門每晚都要落下七重鎖,并有士兵徹夜帶槍守護,而曹佩雄被禁止進入這個空間,即使進去了也只能住進客房,從主人公的處境來看,他處于開放、享樂的現代生活與封閉、禁欲的傳統生活的沖突當中。主人公以拿東西為借口成功進入這個堡壘一樣的住所,在他進入住所之后,整個敘事伴隨不同視點的切換以交叉蒙太奇的方式進行,并為讀者描述一連串驚險的殺人場面:曹佩雄與弟弟持槍一前一后潛入父母的房間,曹佩雄突然心生猶豫,在弟弟的催促下開槍,倉促之下不僅沒有命中,還驚醒了熟睡的父母,寫作者隨即轉向曹母的視角,她驚叫著向丈夫求救,曹父亦呼喊求救,在一片混亂中曹結果了父母的性命。混亂結束之后寫作者如此描寫道:“佩雄回身時屋外廊下電燈照耀,唯屋中已熄火,佩雄回身屋外后見廊下有人影,又一槍擊之中,往視則其弟佩遠也。”房中并無燈光,而屋外一片光明,身處黑暗、緊張而驚恐的佩雄誤殺了自己的弟弟,這個全程以曹佩雄主觀視角描寫的場面極富節奏感、戲劇性與視覺沖擊性,對比曹佩雄擊殺父母的激烈氣氛,這次安靜而快速的誤傷重擊了曹佩雄脆弱的神經,光明和黑暗的色彩隱喻也意味著曹佩雄就此滑向了命運的深淵。
在這場誤殺之后,曹佩雄因子彈用盡,回到臥室取子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殺死了妻子和孩子。這段敘事以妻子的視角開始:因曹常將洋服和子彈放在一起,曹妻今日為丈夫取洋服時便隨手將子彈放在桌上,此刻她正與女傭在房中逗弄孩子,因此置于桌子上的子彈——這一不祥的意象顯然與逗弄孩子的溫馨氛圍格格不入,但她又是軍人家庭的女眷,子彈對她而言或許只是家中常見的事物之一,當曹佩雄闖入這個溫馨的空間拿起子彈填充時,曹妻與女傭因對此習以為常而并未有任何情感與動作上的變化,在“整理衣服與子彈,逗弄孩子”與“拿起子彈填充”之間形成了類似交叉蒙太奇的閱讀體驗,從而營造出噩運即將來臨而主人公渾然不覺的緊張感,并使曹妻之死帶有飛來橫禍的悲劇意味。
如果我們將這一故事視為電影本事的話,以“戲中戲”存在的、未結束的偵探電影最終在現實世界中完結:殺死家人、精神錯亂的曹佩雄最終被守護在“堡壘”邊的士兵們抓住,送上法庭并執行死刑。這個游離于現代與傳統生活之間的年輕人最終受到了現代法律的審判,他的罪過也被舊的道德觀念定性為“逆倫”。行文似乎暗指了電影這一現代媒介對人精神與心理的巨大影響,模糊自身與電影的界限,并錯用這種力量會帶來災禍,但同時電影敘事的方式卻足以激發具有視覺快感的閱讀體驗。此種觀念與敘事方式在上海中西文報紙中都有體現,1913年9月7日的上海《大陸報》(The
China
Press
)刊載了一則名為“Loves labors lost in the movies”的新聞,講述德國一名渴望婚姻與家庭生活的勞工迷戀上了報紙上一名相親女子的肖像,他不滿足于簡單的照片,以至于寄錢要求女子拍攝她的生活影像,甚至不惜包下整座影院只為欣賞這部自己“訂制”的電影,兩人見面后男子失望地發現,那張相片與影像均是女子的偽造:她花錢雇用了一名電影女演員,并讓她在照片和影像中出鏡。作者花費大量筆墨描寫女子的照片與影像,還特地為文中情形繪制插圖,而這不幸人的故事看上去也仿佛是一部愛情悲劇的電影本事。甚至,上海此時此刻之風物亦可以“銘刻”進影像,并作為一種噱頭在報紙上刊載,1925年1月5日的《申報》報道了一則聯華電影公司的拍攝花絮:前日上海下雪,明星公司的張石川便攜演員鄭小秋等前往徐園拍攝雪景,這段雪景也將插入公司正在攝制的電影《好哥哥》之中。報紙的敘述強化了電影對日常的“銘刻”以及它對真實生活的“戲仿”,當下的瞬間與成為歷史的永恒之間的界限被打破了。“正是在原創與復制、真實和幻想、模仿和被模仿著之間的虛擬空間中,人們能夠掙脫疏離和破碎的現實世界的牢籠,暫時性地享受一種不同尋常的身體化感受并重新獲得‘體驗’的能動性。”對于中國讀者來說,視覺化的敘述方式不僅使熟悉報紙媒介的市民逐漸習慣電影的敘事方式,更強化了觀看電影是現代都市生活必不可少的成分。不過,一切的快感體驗必須置于法律與倫理道德的雙重統治之下。三、電影本事與電影評論
電影本事,尤其是外國電影本事并不是單純的劇情簡介,它們不以本事而是以評論的形式見諸報上,在上海特殊的都市文化背景之下,它們亦成為不同生活經驗與文化體驗沖突與交流的場域,在作者對外國電影本事的翻譯、記錄過程中也包含著對“他者”的評論與審視,以及對主體的再認識。《申報》1920年12月11日羅漢素所寫的一篇觀影隨筆中記錄了一個頗為有趣的場景:作者預備去上海大戲院看一部名為《高槐田斯》的電影(“高槐田斯”是電影名稱的拉丁文音譯,其本意是指“你往何處去”),并與朋友發生如下對話。
作者:你往何處去?
朋友:到上海大戲院去看《高槐田斯》(《你往何處去》)。
作者忽而發覺此言與上海人之無聊對話十分相像。他用如下對話來舉例。
甲:儂來買點啥?
乙:是。
甲:買點啥?
乙:買點啥?
借由兩種語言的類比,陌生的語言和生活經驗并入上海都市之日常生活中,同時也劃分出了都市階層——接受過西方教育的文化精英與普通市民。顯然,在作者為彌合兩種經驗進行的類比中蘊含著新的分裂——文化精英的“往何處去”與普通上海人之“買點啥”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軌跡,即使在作為民主之象征的公共空間電影院中階級的差異也是明顯的:正如《尼伯龍根的指環》與其中文譯名《斬龍遇仙記》背后耐人尋味之不同意蘊,翻譯粗略的電影本事(電影說明書)在普通觀眾與文化精英之間顯然具有不同的意味。羅漢素認為看電影絕不是為了簡單的娛樂,而是為了“讀世故人情、明了人類現實生活的所在”,因為電影比記錄人類歷史的文學作品更淺顯也更易在閑暇時觀賞,有自身獨特的藝術性和教化功用,他對《你往何處去》翻譯粗劣的電影說明書翻譯感到不滿,因為它并不能完全體現這部由偉大名著改編電影的深邃內涵。羅漢素還詳細記述了觀看這部電影所獲得的視覺享受,如羅馬貴族奢侈的生活(他生動細致地描寫了影片中羅馬貴族早起時的沐浴與享樂)、羅馬人(電影演員)強健的體魄,并希望中國也能如羅馬那般“轟轟烈烈”地鬧一場,誕生出如尼祿、黎基維等英雄與藝術家。“五四”的啟蒙話語帶來了線性的時間思考方式,在將中國和西方分為過去與現在的同時也使知識分子自身獲得了一種世界主義者的身份,“在中國語境中,這一跨越國界的中介性的‘世界主義意義上的主體性’也就自然帶上了幾分受世人尊重的文化權力色彩,因為這種新的文化資本形式僅僅屬于那些已經‘受到啟蒙’的少數人”。然而在談論到影像中作為西方文化具體表現的羅馬人生活、身體與藝術之時,作者——這位文化精英不自覺地流露出了帶有窺私欲、羨慕、憧憬與沮喪的復雜心態,結合克拉考爾描述在鏡頭前的身體呈現所用的術語“大眾裝飾”之雙重特性——“既存在官能解放的烏托邦性質,也潛伏著對身體能量進行意識形態剝削的隱患。”這種混合著殖民地居民種族焦慮之心理與文化精英世界主義之心態間的矛盾不言而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者在這篇簡評中重寫了《高槐田斯》的電影本事。值得注意的是,《高槐田斯》雖然充滿濃郁的基督教色彩,卻改編自現代波蘭小說家Sienkiewicz之作品,作者在文中寫道“……內容是借著基督教半神話的故事,描寫希臘羅馬文明衰頹時候的社會狀況和基督教的精神。”或許作者自己也感知到銀幕中的本事與上海當下新舊激烈交替的時勢間存在隱秘的互文關系,他在文章結尾處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與疑問:“可是中國的尼祿、黎基維……一類的大英雄、大豪杰、大藝術家,什么時候可見希望產生呢?”在對電影中羅馬人的描寫中寄托了作者對自身與民族的想象性自我指涉,一個烏托邦幻夢,然而作者對此表示懷疑,這個問句恰好表達了“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又失去了政治解決的視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之彷徨處境。
對外國電影電影本事的“改寫”或“重寫”大多出現在“述評”中,即在劇情記敘之中夾雜著點評。1924年12月25日的《申報》刊載《斬龍遇仙記之短評》可視作是“改寫”的典型案例,作者黃道扶直接將《尼伯龍根的指環》類比為《西游記》,而代表女性強大力量的布倫希爾德則被簡化為“悍婦”:“……余應友人之約,曾一睹之,此片劇情,臻為離奇,頗類我國之《西游記》……蓋此婦兇橫無比,國王不敵也,后卒賴少年之助,如愿以償。”而該片視覺奇觀之刺激在于男主人公遭槍尖穿胸的場面遠勝中國京戲中之武打,“劇情光陸怪離,少年為其仇人刺死時,以槍尖穿其胸,血涌而出,極逼真,遠非中國京戲中之所謂真刀真槍者所可比也”。這則短評可以視作一種簡略的比較研究,以及對《尼伯龍根的指環》改譯進中文語境的嘗試。而1925年1月1日由仇湘創作的《斬龍遇仙記》影評,盡管分析角度與黃道扶不同,兩者在評價的立場上卻呈現出有趣的相似之處——一種基于小市民道德觀念的簡單解讀。仇湘寫道:“全篇情節,處處伏因果,雪格之刺蛟龍也,龍正渴飲于池,雪先以劍刺其右目,蛟龍乃致不敵,及后雪既行獵郊外,忽覺口渴,因就飲于池,詎為盲一右目之海根所刺,循環報復,正予以吾人以絕大教訓也。”中式倫理觀中的因果、報應等概念,與西方悲劇中的命運觀念并不一致,正如《趙氏孤兒》有別于《哈姆雷特》,如果仇湘閱讀過《俄狄浦斯》或者《安提戈涅》,那么他多半不會發出此等議論。
還有一些電影本事會在敘述中加入對男女主人公之面容、裝飾、表情與演技的點評,可稱之為第二類“改寫”案例,如1925年1月3日之《新片〈女皇艷史〉述評》。作者嚴月池在女演員的美貌與演技上頗費筆墨:“琶娣姄兒絲飾女皇示巴,冶艷動人,貌絕肖芭芭拉瑪(演《風流債》《花情蝶義》之女主角)表情做作亦如之,允稱雙璧。當伊姝那米吸士遭挨馬皇擄去,杏眼圓睜,握拳透爪,憤懣極矣。嗣親愛妹遺骸,狀若癲發,撫尸大慟,并立誓為妹復仇,大義凜然,使人起敬。晉宮見皇一幕,靚妝艷服,珠繞翠圍,欵步輕移,拾級而登,眼含秋水,臉呈笑容,極意蠱惑挨馬,俾令墮于彀中,而手刃挨時,一種勇敢果決之神氣尤為佳妙。”第一類作為一種“文化移植”更多地體現出小市民階層面對現代大都會紛至沓來的新文化、經驗保守的接受態度;而第二類則更接近于導賞與宣傳,在作者的敘述中,迷人的男女演員身體構成了新的都市景觀,作者還教導觀眾如何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借助表情與肢體語言欣賞和理解外國影片,享受這種都市文化特有的新奇視覺快感,以成為一名“合格”的上海市民。
結 語
過去對電影本事的研究一直局限在電影與文學的視域之中,從而忽略了電影本事與其誕生的背景——上海都市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電影本事見證了20世紀20年代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它與戲劇、報紙等媒介共同構建了上海的都市想象及現代性體驗,讓人們觸碰到舊倫理中禁忌的快感,欣賞由身體、建筑所構建的都市景觀,又使人們陷入新與舊、世界與民族、現代與傳統之間的茫然與無措。電影本事研究要求我們具有跨學科、跨媒介的研究視野,它的豐富意蘊依然有待更深入的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