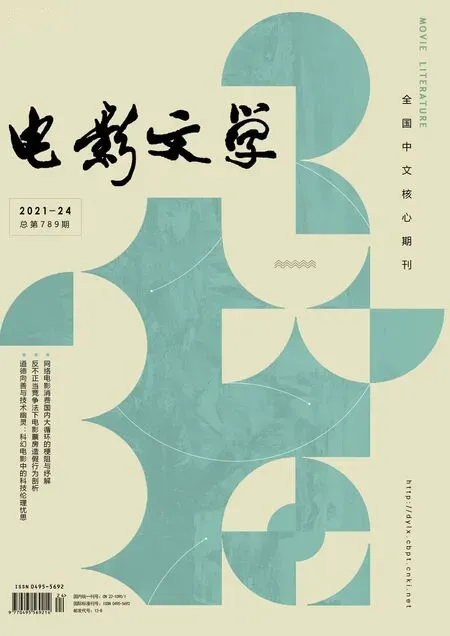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尋漢計》的小人物群像探析
李晉媛
(1.山西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2.山西傳媒學院教務處,山西 晉中 030619)
當下,國產大片往往難以獲得觀眾情感認同,而關注平凡無奇小人物、小事件的低成本電影卻異軍突起,表現出良好的發展空間。由唐大年執導的喜劇電影《尋漢計》,以一個大齡女青年急切為自己腹中孩子找個父親的戲劇性故事,完成了對眾多小人物的塑造,其中的小人物群像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一、《尋漢計》的小人物概況
在電影中,唐大年主要塑造了三類真切飽滿的小人物。
首先是如王招和姥爺老何這樣的勤勞善良者。女主人公,北京大齡女青年王招原是一家公司的內勤,在工作中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是公司中被同事們呼來喝去的“老好人”,曾連續三年在年會中抽到一等獎,但這也招致其他同事對她的中傷。在與他人相處時,王招寧愿委屈自己,也不愿給他人造成傷害和不便。如她一直對姥爺隱瞞自己離婚、懷孕和失業的事等。在前夫并不想對孩子負責時,王招陷入了慌不擇路的狀態中。而姥爺也是正面的長者形象。他對外孫女王招充滿慈愛,與年輕人杜微結成忘年交。對于晚輩的糾葛,姥爺常常裝糊涂,只是盡全力將自己照顧好不給他人添麻煩,而一旦王招遭遇困境,便會表示“你不是一個人,還有姥爺呢”。兩人相依為命,一套簡陋的兩居室房子是兩人唯一的財產。無須諱言,這一類小人物都有一定的缺陷或弱點,如王招助長了他人對她霸凌的討好型人格,姥爺想出給孩子找個“便宜爹”的主意不無自私之心,但兩人都保持了純樸厚道的心。如王招最終向杜微坦白自己已懷孕的真相,姥爺也自感愧疚,一遍遍地對杜微說“對不起”。
其次是如杜微這樣逃脫世俗牢籠的奇人。電影中的杜微是一個摩的司機,平日不修邊幅,和王招原是在游戲中的虛擬夫妻,在相親后,杜微一度對兩人的關系產生退縮之情。不料因為忘年交老何的腳傷,將老何送去醫院并墊付醫藥費的杜微再度與王招相識。盡管外貌、收入平平,但杜微卻始終有著不卑不亢的姿態,關懷他人的意識,以及難能可貴的生活情趣。如在送老何去醫院后,杜微“借”了一盆綠植給老何讓他的病房更有生氣,還為護士們買了水,即使在洞悉祖孫倆的主意暴怒后,依然開車送祖孫倆回家。而更為難得的是,最終杜微看清了王招清澈純真的人格底色,開著“買一送一”的玩笑與王招結婚,對她悉心愛護,在處理孩子父親這一問題上顯得明白而通透。至此,善良者收獲了善良,溫情者得到了溫情。可以說,杜微這一角色承載著唐大年對小人物自由理想人格的探索。
最后則是作為反面例子存在的,擁有市儈靈魂的勢利小人,如王招的前夫侯英杰,王招的母親和王招的同事等。侯英杰在與王招離婚后,依然與王招保持關系,導致王招懷孕,之后完全不想負責,并用“誰知道是誰的”“你不都王招君了嗎”之類的話傷害王招;王招的母親將照顧姥爺的任務丟給王招,本意是避免姥爺的房子落到舅舅手上,而王招的汽車、電視等,母親則隨時進行索取,并美其名曰這是在“幫助”王招;王招的同事則不斷地利用和貶損王招,如彼得這樣的人甚至一直在對王招進行性騷擾,隨后又讓王招被開除。這一類小人物在身處底層、所占有資源有限之際,不斷對他人造成傷害,他們雖然并非極其陰險狠辣之人,但他們的自私涼薄、唯利是圖、丑陋鄙俗依然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公園里明碼標價、自以為是的相親者們,烤羊肉串的小販,姥爺的鄰居等,也都是出場不多,但身段臉譜鮮明的小人物,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幅當代北京底層的眾生相,讓整部電影充滿煙火氣息。
二、《尋漢計》的小人物建構價值
就在一個個小人物登場的過程中,《尋漢計》完成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故事的講述。王招、侯英杰等小人物聚合而成的群像,具有舉足輕重的文本意義。
(一)主題表達的深化
《尋漢計》并不僅是一部以尋愛為中心的“小妞”式都市愛情電影。在電影中,王招的生活盡管和觀眾熟悉的“小妞”們有一定的重合性,如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開闊的視野,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保障等,但是王招自始至終尋找的并非愛情,并非與愛情相關的精神享受和情緒滿足,而只是一個婚姻對象,得到杜微的愛情對于王招而言是一個意外結果。電影所要借王招的道德倫理困境探討的,正是女性彼時面臨的一個問題,即非婚生子女不能登記戶口。正因為王招和她的主要社會關系都是小人物,她無力逾越這一規則,才不得不另辟蹊徑,甚至踐踏自己的良心。她相親“騙婚”的喜劇行動是典型的小人物行徑,其背后其實隱藏著悲劇性的潛流。對此,杜微安慰王招時說的:“這就跟堵車一樣,有別人的道,就有你的道。”實際上是充滿無奈的。并非所有的“王招”都能遇上心胸開闊的“杜微”,而更多社會地位還不如王招的女性,只會面臨更為尷尬、悲慘的結局。觀眾盡管能最終在看到王招將頭伸出車窗欣然微笑時,為她感到釋然,但也會產生某種若有所思的沉重。
電影實際上引導觀眾審視和反思這種普通人生存空間受到限制的情況,反觀其存在的,依然對女性充滿不公的社會環境。正如在文牧野的《我不是藥神》中,正是人物的小人物身份,才有了程勇抱著圖財的初心走私藥物,有了如呂受益、彭浩、劉思慧等病人或病人家屬為了延命的不擇手段。和《我不是藥神》類似的,在《尋漢計》的結尾,電影以字幕的形式交代了困擾主人公的問題最終得到解決:“2016年,國家出臺相關規定,經親子鑒定后,允許非婚生子女戶口登記,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一樣的合法權益。”如此,小人物的窘境得到化解,觀眾也得到稍許安慰,但這種對于主人公而言“遲到”的、于事無補的變化,又更反襯出了主人公遭際的無奈。
(二)后現代意識的凸顯
相對于解構意識和后現代主義思維明確的寧浩、管虎等人而言,唐大年并沒有在《尋漢計》中標舉解構主義,但這并不意味著電影沒有后現代意識。在電影中,英雄完成了徹底的“退場”,小人物占據了整個審美舞臺的前景,和《瘋狂的石頭》中的包世宏、《斗牛》中的牛二一樣,屬于世俗和底層的小人物替代英雄展現了英雄精神。只不過包世宏等人的英雄精神體現在一種永不言敗、愈挫愈勇的韌性上,而杜微的英雄精神則體現在一種超然、豁達的生活態度上。正如尹鴻所指出的:“后現代文化對那種矯情的貴族意識的嘲笑、對那些虛偽的道德寓言和價值觀念的瓦解,以及它那種進退自如、寵辱不驚,超然于勝利與失敗之上的人生智慧,都為中國電影帶來某種生機,帶來了某種脫離了教化傳統的自由和輕松。”杜微正是一個進退自如、寵辱不驚,能始終保持平衡心態者。在這一人物身上,觀眾很少看到自我懷疑與自我否定,相反,他最終不僅不再為自己的職業感到自卑,也根本不再介意所謂的“綠帽子”“喜當爹”等話語邏輯,他也并不居高臨下地以拯救者的身份面對王招,他對王招的選擇實際上是遵從了自己內心的情感指向,于他而言,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在人物的達觀下,這些主流的、對女性并不寬容的意識和話語不再構成傷害。在此,“大人物”們主張的如“男性尊嚴”等“虛偽的道德寓言和價值觀念”便顯得黯然失色。
三、《尋漢計》小人物群像與國產電影創作
小人物電影的迅速發展與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國電影受眾主體的自我文化覺醒,同時也表現了電影受眾的自身價值映射。《尋漢計》的小人物群像設計,實際上反映出了某種國產喜劇電影以貼合觀眾心理需求為目的的人物設置模式。即一方面,電影中的小人物必須植根于現實,是在快速變化的時代中的無可奈何者。人在統治秩序面前的被動感,人成為他者附庸的無力感,都必須是真實的,由此觀眾才能將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主人公的身上,將銀幕上的故事視為現實生活的鏡像;另一方面,小人物電影中,人物關系,人物命運等往往又是顛覆傳統的社會認同的,甚至在電影人的夸張下,劇情的展開有著近乎鬧劇式的娛樂表達,觀眾的獵奇心理由此得到滿足。例如在寧浩《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中,國際大盜麥克、職業殺手察猜、臺灣烏龍幫等,都陰差陽錯地栽在了本土“笨賊”的手上,狼狽不堪。小人物往往是權威的戰勝者與分解者,這能迅速地獲得觀眾的欣賞悅納,電影的泛娛樂化傾向也由此形成。
在《尋漢計》中,同時承受著來自職場、原生家庭和破裂婚姻的王招,在35的年紀曾墮胎兩次,因此無論如何也要保住這一個孩子,但是又無法為其解決戶口問題,試圖相親卻又作為被物化者而處處受挫。她的進退失據便是能讓當代觀眾共情的,而最后,杜微主動向王招傾吐愛意,突破了觀眾的生活經驗,消解了傳統對于兩性關系的定位,人物獲得了一種在根深蒂固陳規面前的豁免權,這充分宣泄了觀眾的郁積。并且,在小人物的外表和言談舉止中,電影也極為注重笑料的設計,以平衡主人公霉運連連帶來的壓抑感,確保了喜劇效果。如相親時兩個老頭“你是男的女的”“我是女的”“我也是女的”的對話,對急于將子女推介出去的家長進行了調侃;又如杜微對其他摩的司機說:“開摩的是我們有錢人接觸社會方方面面的一個小窗口知道嗎?”馬上被另一個司機問道:“大款,你這個月低保領了嗎?”小人物樂觀自嘲、苦中作樂的一面被展現得淋漓盡致。當小人物能夠充分滿足觀眾的娛樂需求時,觀眾便不再介意大人物與宏大主題的離席。
同時,小人物群像的塑造,實際上又是電影展現自己底層立場和人文關懷溫度的重要手段。正如卡西爾所說:“最偉大的喜劇詩人決非給我們一種悠閑的美(Easy Beauty),他們的作品常常充滿了極大的辛辣感。”小人物們在現實生活中跌跌撞撞,暴露出自己人性中的明與暗,展現出自己民間智慧的局限性,也反映出了諸多社會陣痛。如《尋漢計》中單親孩子的戶口問題、老齡化社會中老人的贍養、陪護與遺產繼承問題、職場中女性面臨的“透明天花板”與性騷擾問題等,都借由王招“尋漢”的掙扎和自我拯救故事得到披露,觀眾能在其中觀盡人生百態。類似如周星馳的《喜劇之王》、馮小剛的《甲方乙方》等電影的魅力正在于此。容易被忽視的小人物們奮力活著的面貌被電影人搬上大銀幕,激發著觀眾在現實中對他人回饋善意,也推動著社會的變革與進步。
唐大年的《尋漢計》通過王招、杜微等形形色色、各具苦惱的小人物,為觀眾展示了社會一角,讓人看到了女性在兩性關系與戶口規定下的被動與無奈,同時也對杜微所代表的、消解了傳統男權話語權威的達觀通透人品進行了肯定。而縱觀包括《尋漢計》在內的當代國產喜劇片不難發現,小人物群像的塑造,既便于審丑和黑色幽默手法的運用,這確保了電影的喜劇性,同時,小人物群像的“接地氣”,也有利于電影對底層者寄予溫情的關懷,和對裹挾小人物的社會問題進行觀照,這又確保了電影的深度。對于中國電影人而言,《尋漢計》這種對小人物的聚焦,對普通人現實問題的關切,無疑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