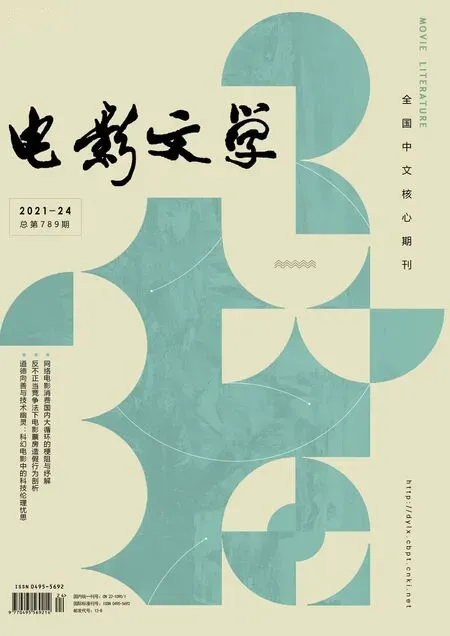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大地》:城市文化圖譜掩映下的人域困境
許鵬云
(重慶城市科技學院,重慶 402167)
一、避世——資本社會下的人群精神危機的逃逸
美國在進入21世紀之后,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文化分野,以2003年的九一一事件和2008年引發全球金融海嘯的次貸危機為轉折點,美國當代的流行文化自分兩條道路,一條指向的是美國的流行與娛樂的審美傳統,資本和流行文化的制造者們將原本世俗化的娛樂更加表面、更加夸張地表達出來,像《加勒比海盜》系列、漫威和DC超級英雄系列電影,用超能力者來滿足人們對生活日漸失控的無力感。另一支則逐漸走向隱逸、逃避或言之曰思考的窠臼中,譬如《荒野生存》等,這些電影嘗試提供給人們以一種生活方式,電影里的主角在大都市和高度資本化的社會之中感到無所適從,主角們隱居山林荒野或貧困的第三世界國家,過上一種簡樸的、自然的生活,從而發現生命的真諦。
當然,從十年后的今天來看,《荒野生存》和《美食、祈禱、戀愛》此類型電影,實際上還是尚未脫離一種中產階級審美的層面。主角對資本社會的厭煩大多都來自一種無法逃避的人際關系和一種對原本生產—消費的都市生活感受到的無意義。這類電影里的社會底層往往以一種“他者”的身份出現,他們身上具有一定的閃光點,主角觀察他們或者與他們成為朋友,最后在與此類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者的對比或“學習”中感受到資本主義世界的處境仍然是“過得去”的,于是完成“療愈”,再次回歸原來的世界。從某個層面來說,這一類故事敘事仍應該被限定于一種自我意淫式的高水平的資本主義消費者的文化安慰。但是在最近的十年里,這類自我放逐、自我和解式的小品作品有了更深入的探索。在這種從主動走向被動流浪的敘事線路中,電影敘事的集中視點也出現了偏轉,自然與生命中不可回避的傷痛,形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連接。因此這一類美式“自然主義”電影也進入到了新階段,也就是“在自然中獲得療愈和拯救”走向“人為何要看向自然”的階段。
當這一類自然主題電影走向新階段后,以編年史的視野去重新回歸美國近二十年的自然主題電影,不難發現《大地》的特殊性。《大地》的結構非常簡單,女主角伊迪在遭遇了音樂廳槍擊案后,失去了兒子和丈夫,她決定一個人進入山林,后遇到了土著居民米格爾,并學會了打獵技能,最終生存了下來。《大地》中有很多不能免俗的元素,如觀眾經常在此類電影里看到的象征著大自然殘酷的北美黑熊;象征一個人走向獨立生活的劈柴和打獵活動;展現隱居生活美好的篝火夜談等,但這些流俗的元素沒有遮蔽電影嘗試討論的內核——即主角逃離大城市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逃避是否是真正行之有效的辦法。
影片在靠近結尾處,用一種祛魅般的言說將逃避都市生活與重新構建人與人之間的聯結相互勾連。伊迪獨自一人在山間小屋快要死去的時候是土著居民米格爾的相助才使得她活了下來,也正是米格爾的拯救,伊迪才重新發現了生命的意義。從這種角度來看,電影制作者似乎并不愿意將真正的逍遙與自由寄托于21世紀前一個十年獨立電影塑造的某種幻覺——離開都市,獨自進入大自然就能獲得解脫。羅賓·懷特作為曾經嬉皮士流行文化的符號,借由《大地》這部電影,恰恰反對了《美食、祈禱、戀愛》式的資本主義消費式開悟的拯救。這不啻于一種對流行文化的反叛,但同樣也是一種對現存的城市文化圖譜掩映下的人域困境的消解路徑的一重影像式探索。
二、土地——對抗后現代工業化語境的標的符號
如果將近些年歐美獨立電影的“隱居”或“自然”主體,看成是一場都市人對現實生活的逃避和幻想,那么多少有些偏頗。美國獨立電影中“隱逸”的傳統實際上發端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本質上,美國當代流行文化的血液里就流淌著對于土地和自然的依戀。在杰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和《達摩流浪者》這一類嬉皮士文學中,就能看到今日這些自然主義電影的發端。因此,刻意將工業與農業、現代社會與隱居生活相對立,某種程度上只是對此類自然主義的誤讀。
在《大地》中,這一類誤讀同樣被搬上臺面,提供了一種影像景觀式的討論閾。電影中,伊迪為了回避喪夫喪子的痛苦,也為了實現兒子在俄亥俄山間旅行時的夢想,她獨自一個人搬進了大山,選擇一個人獨自居住在山間簡陋小屋。電影以一種隱秘的方式揭露了伊迪所面臨的窘境不過是人為設置的某種障礙,護林人在送伊迪到小屋后,伊迪要求護林人找拖車將她的休旅車拖走,護林人感到詫異。這是提示了伊迪被一種流行的隱居文化所誤導后幻想的不真切與非現實,顯然伊迪此時仍然沉浸在某種都市敘事的幻想中,忽略了在殘酷自然中生存與看似休憩的悟道與療愈的差異。直到影片中伊迪第一次遭遇黑熊,某種現實與想象才達成了一種連接性的共識。因此大自然的威力此時更像是某種解構工業性、解構資本主義都市生活的一把鑰匙。它摧毀了都市人對自然界某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將主角和觀眾一起拉進更深領域的自我提問之中——人生存的意義是什么。
《大地》相對溫和地在電影域內給予了解答——伊迪是為了緩解失去親人的痛苦,才自我放逐。她進入殘酷的自然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逃避對人為何生存這一問題的終極懷疑。在隨后的情節里,伊迪頗具象征意味地將印刷精美的銅版紙《野外求生指南》,作為冬夜取暖的材料一張張燒了;伊迪儲備的罐頭在被黑熊搗毀之后,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其分量只夠當作宵夜,工業社會組織帶來的力量和安全在殘酷的自然中十分脆弱。自然解構后工業時代人類所謂的文明、人工產品在自然環境中不堪一擊,卻能夠帶給人某種安全和舒適的錯覺;伊迪作為從資本主義社會退縮逃避到自然中的現代都市人,她所面對的窘迫實際上是一種脫離了大地生存的人群的窘迫。因此,聯系結尾中,伊迪自述逃避自然的原因——她的至親在音樂廳被人槍殺。因此某種元素上的循環就因循形成了。工業制造了伊迪原本舒適的中產階層生活環境,工業時代的文明(槍支)同樣毀滅了支持伊迪這樣一個都市人生存的精神根基。人在工業中的異化與被異化就此得以一窺。
土地以及土地背后所象征的則是某種泛靈論的自然主義,在電影里也有符號化的體現。在伊迪瀕臨絕境死亡的時刻,米格爾來山中打獵,回程的過程中米格兒發現小屋的炊煙滅了,因此才前來查看,米格爾是一個印第安土著居民,他熱衷打獵、唱歌、積極助人,仿佛是某種自然界萬物有靈的隱喻。影片不落窠臼,兩人打獵的一段鏡頭設計得非常有特點,在米格爾教授伊迪打獵時,鏡頭畫面用無人機俯拍,觀眾以一種鷹的視野,俯視自然和打獵的兩人。然而當鏡頭切換到兩人休息時,米格爾提到自己是給土著居民基地送水的工人,而伊迪從事的是城市里營銷策展工作時,萬物有靈這樣的神諭性的描摹又被塞還都市與自然的二元論之中了,伊迪對此的表現是大喊:“你怎么可以在網絡上搜索我!”這種反應昭示著伊迪仍然被困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關系網內,并深感痛苦,與之對應的也是她正在學習打獵的一段,打獵和逃避過去,兩方抗衡,實際上是自然與工業社會的二元對比,影片在段落上安設的對比相當精妙。
三、自我的困境——資本工業城市環境與自然鄉野隱逸的兩重抉擇
所有自然主題的電影,最后都將指向更深刻的目的,《荒野生存》最后指向的是人究竟應該怎樣看待生命;《在西伯利亞森林中》最后指向的是人應該如何看待人際社會對人的限制與支持。《大地》也不例外,《大地》最后指向的是資本社會創造的人工環境與大自然環境的對立與同一性。
電影在開場十分鐘內,嘗試用畫面展示伊迪的困境。當她失去了丈夫和幼子之后,她感到整個工業社會都是那么不可忍耐,她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社會依舊像個設計復雜且精密的儀器不停旋轉,她的悲痛并沒有被社會理解甚至是接納。伊迪去找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只能面無表情地告訴她:“我理解你的悲痛。”事實上心理醫生并沒有與伊迪共鳴。這種巨大的悲痛的同情必然建立在蒙受同樣損失的二者之間,米格爾和伊迪的友誼正是建立在共同都有過喪親經歷的基礎之上,才能夠形成如此緊密而可靠的聯結。心理咨詢的關系與伊迪和米格爾自然生發的友誼在此又是一組對比,電影里與咨詢師的交談是由伊迪的妹妹愛瑪牽線搭橋的,是一種人為催發的結果。而妹妹作為伊迪最后在世的親人,她逃避了作為至親填補伊迪空白的情感責任,轉而用代為付費的方式,付費邀請心理專家幫助姐姐解決心理上的痛苦,實際上也是一種逃避。在電影中多次作為伊迪內心情感支柱的愛瑪其實只是伊迪內心情感依賴的幻象。心理咨詢并沒有起到預想的效果,而伊迪避退深山,與土著居民米格爾的友誼中獲得了療愈與安慰,米格爾在此又和代表愛瑪出現的心理醫生形成了一組對比:情感的親緣與工業化;友誼的自發與天然性。兩組對比,展現了兩組現代人情感意識中的不可回避的矛盾,以及在商業環境與自然環境中,人們對于負面情感消解方式的態度差異。
《大地》始終是一部情感傾向十分明確的電影。米格爾因為癌癥,將小狗托付給伊迪,并就此消失。伊迪久等老友不至,最終決定打破當初進山的諾言,離開山間小屋,去尋找米格爾的蹤跡。伊迪發誓永遠不離開山中小屋的誓言是為了死去的兒子而發的,換言之,伊迪所面臨的困境并非僅僅是外部施加的壓力,更大的則是一種自我幸存的愧疚。在伊迪離開城市的時候,伊迪也自我剖白:“城市讓我發瘋”,實際上并非是城市使人發瘋,而是人群使人發瘋。特別是以金錢代替責任、以責任歸屬代替親情的人際關系使人感到發瘋。伊迪的背誓是內心得到療愈后的平復,為了了解失蹤多日老朋友的動向,她離開了過去幾年一直居住的小屋,再次來到人群聚居的城市。不是不慌亂,但更多的是為了老友忍耐下的不安。影片末尾在米格爾病床前的一番談話,伊迪終于解開心結,從人與人的困境、人與自然的困境轉化為人與自然的和解、人與人之間的和解。電影在末尾并沒有再試圖將伊迪放置于人域困境的張力之下,相反,她開始與過去的自己和解,同象征著城市文明的世界和解。她主動與妹妹愛瑪聯系,并在多年之后第一次報了平安。手機和車象征著文明世界的回歸,也象征著伊迪從都市人走向自然人,發掘自我之后再次社會化過程的完成。因此,《大地》可以被看成是主角伊迪個人成長的故事歷程,又能夠被看成是在如今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人自我創設的人域困境的符號化討論。《大地》中對自然環境的態度保持的中立性,使得其獨立于美國其他借由自然風光闡發中產階級消費品位的電影作品,展現出相對清新流暢的自然主義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