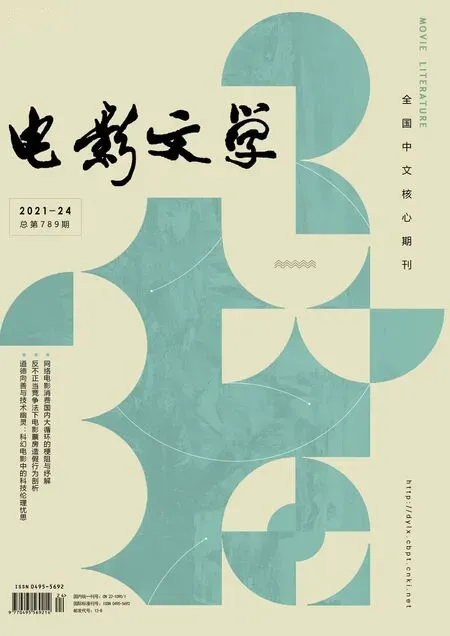從革命到后革命:新主流電影《1921》的情感結構
李冰雁
(惠州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廣東 惠州 516007)
革命歷史題材片一直是中國電影的重要類型,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電影工業化模式的成熟,融合政治性、商業性和藝術性的新主流大片收獲了不俗的口碑和票房,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揚以及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都起著積極作用。作為建黨100周年獻禮片,《1921》(黃建新,2021)將觀眾耳熟能詳的中共一大進行合乎“美的規律”的影像表達,上映4天票房破3億元,不少網友表示“被觸動到了”。導演黃建新在訪談中提到,《1921》通過創造“感性的氛圍”,激活觀眾的“潛意識”,是一種高于共鳴共情的審美體驗。李道新在論文中指出,這種“潛意識對位”以及“激活潛意識”達到“通天下一氣”的效果,“開啟/延續了一種整體思維的中國電影新模式”。趙衛防認為,《1921》將“敘事的宏大性和日常性結合、對歷史人物的個體化描繪、國際化視野的拓展”以及“新穎的電影語言”等方面實現對以往建黨題材影視劇的超越。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1921》對革命歷史題材的創新表達激活了觀眾的“集體無意識”,激發了觀眾的家國情懷和愛國精神,其敘事模式及影像特點值得進一步研究。
在“后革命”時代,主流電影如何將過去歷史精神和當下社會文化進行對話,活化抽象的理論,喚醒不同時代觀影者的革命精神和歷史崇高感,以一種當代年輕人能夠接受的“后電影”形式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里不妨借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唯物主義”中提出的“情感結構”概念,即認為“情感結構”有助于將社會關系模式識別為歷史表達模式,它旨在闡明人們在特定歷史時刻對事件和情況的協調反應網絡。對威廉斯來說,過去總是被作為一種工具來閱讀現在,一種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性的方式。簡言之,“情感結構”有助于實現當下與過去的理解與對話,成為歷史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擬以《1921》為例,考察新主流電影如何在“后革命”語境下塑造“革命式”情感結構,使歷史、記憶與審美經驗在銀幕上合而為一,獲得中青年觀眾的情感認同,從而使革命精神在當代得到傳承和延續。
一、從物理時空到精神時空的跨界敘事
新主流電影集商業性、藝術性和歷史性為一體,往往需要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增強戲劇性,提高影像的表現力。有鑒于此,在講述歷史的過程中如何把握限度和意識就顯得格外重要。畢竟,在短短兩小時內對歷史進行全景式掃描容易流于碎片化敘事。例如,同樣為獻禮片的“建國三部曲”,即《建國大業》(韓三平,2009)、《建黨偉業》(韓三平,2011)、《建軍大業》(劉偉強,2017)對歷史采用“全景式”掃描,由于人物過多、歷史事件繁雜,導致敘事主線不夠突出;枝蔓太多沖淡了主題。尤其是許多重要事件以旁白的形式介紹,沒有最大化地實現影像敘事的功能。
跟以往的新主流電影相比,《1921》從敘事和影像方面都實現了一定的創新,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將電影還給電影”。影片充分利用“影像的力量”深刻展示了一批青年志士對共產主義思想的探索,對革命道路從朦朧到清晰的過程。例如,影片開場透過獄中陳獨秀眼睛的大特寫插入一段蒙太奇組合段落,每個畫面和細節都透著“想象的能指”:飛機盤旋下,一群人在故宮落荒而逃,鴉片戰爭爆發,直觀地展現出當時清政府腐敗無能、中國內憂外患的情景;接著展現李大釗與青年學生的五四運動,再到他生命中各個瞬間的閃回片段,表明一代人尋求救國救亡道路的艱難歷程。影片尾聲,陳獨秀再次入獄,此時的他在鐵窗前怒吼,與片頭構成敘事呼應。重大歷史事件以蒙太奇形式切入,使時代成為“背景”,人物成為歷史舞臺上的“主角”,他們的人生選擇和命運遭際就具有主觀能動性,從而使人的主體性得到凸顯。
《1921》另一個著名蒙太奇段落是青年毛澤東奔跑的場景。在毛澤東的視點中,法租界里的法國國慶慶典流光溢彩;此時從花園里的視角切入,俯視鏡頭下是一群被拒之于門外的中國人,他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兩個視點切換,兩組畫面形成鮮明對比,使觀眾與毛澤東共感共情,一種屈辱和憤慨油然而生。隨后,毛澤東沖出人群,以一種夸張的大步伐一路奔跑,背景以一種廣角旋轉鏡頭呈現出租界商業街燈火通明、高樓林立,暗示著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繁榮對比,中國落后就要挨打。此時插入毛澤東的回憶段落,展現他的心路歷程——在湖南鄉下反抗父親出走。父親,象征封建家長制;出走,意味著與強權和舊勢力的決裂。這場“奔跑”蒙太奇使影像具有豐富的情感指向,盡管有藝術化的虛構和渲染,但其傳達的情感結構喚起當下觀眾的家國情懷和歷史使命感。正如電影海報所言“一百年,正青春”,“奔跑”既服務了電影敘事主題,又有多重意義指向:一方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青年人肩負著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的重任;另一方面,預示著即將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將領導中國人民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新征程,奔向嶄新的世界。
《1921》的敘事場景游走于不同時空,除了講述北京、上海、廣州等早期共產黨成員組織(參與)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上海工人罷工運動外,還交織著兩條副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擺脫歐洲反共勢力和租界密探的監視;日本特務對來滬日本共產黨員的追捕。副線的加入不僅豐富了劇情,還與主線構成互文性敘事。隨著共產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工人階級有了“人民”意識,罷工運動取得階段性勝利。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從孕育到誕生的過程,罷工運動從側面證明無產階級革命在中國不僅行得通,而且必將取得勝利。難能可貴的是,影片并沒有美化革命,而是指出革命必定要經歷艱苦卓絕、流血犧牲。例如,李大釗在北京被處以絞刑,鏡頭切換到罷工運動現場,黑白畫面中成千上萬的工人整齊肅穆,鴉雀無聲,仿佛隔空為革命烈士默哀;接著畫面出現色彩,一面面紅色旗幟凸顯出來,人聲沸騰。這種虛構性的詩意表達預示著經過革命者的浴血奮戰,民智得到開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電影中,地理空間成為指涉具體之物的空間,通過不同空間的排列組合產生新的所指。就敘事模式而言,《1921》從城市到農村、從國內到國際的跨界敘事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精神時空”,即時代大形勢下個體對人生道路的共同抉擇。在共同的歷史使命感和革命信念的引領下,碎片化的歷史片段得到具有向心力的黏合,獨立的物理時空組合成符合歷史邏輯性的精神時空,從而實現敘事功能。精神時空一方面在敘事層面標記歷史記憶,使抽象的文化變得具體可感;另一方面,通過同一個物理時空打通現當代精神時空,形成共同的情感結構,使當下觀眾對歷史人物產生同情和理解。
從電影語言層面來看,由于場面調度和剪輯的選擇,使具有歷史指向性的物理空間從“過去”轉化為“現在”,將不確定的、抽象的“歷史”變得清晰、穩定,可觀可感。地理空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當下和歷史聯結的紐帶,從而喚醒人們潛意識深處的文化鄉愁。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印刷語言以三種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礎”,在新媒介時代,各種媒介以不同的形式重構民族意識,激起人們的家國情懷和民族認同感。從這個角度來看,新主流電影較好地發揮影像敘事的長處,能夠以一種當代人接受的方式講述歷史,使當下與歷史的情感結構相通,從而喚起人們的情感共鳴。
二、革命、青春與電影類型的表達
新主流電影在講述革命歷史的過程中融入青春、愛情、懸疑等元素,溝通了從“革命”到“后革命”時期人們的文化心理。在威廉斯看來,“情感結構”是歷史上某個時期出現的特定思維方式,它出現在政策和法規的官方話語、對官方話語的大眾反應及其在文學和其他文化文本挪用之間的差距。也正如此,在講述歷史的過程中,通過或顯或隱的細節就能管窺全豹,交織著多元的歷史敘事。《1921》將恢宏的歷史背景以蒙太奇形式穿插講述,通過留白手法展現歷史細節,還原人物相對真實的思想和性情,使當下觀眾易于理解人物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的行為和選擇。例如,影片通過簡約的對白描摹了劉仁靜、王盡美、鄧恩銘等青年形象,以對話和蒙太奇畫面呈現劉仁靜參加五四運動的情景,同時也刻畫了他們年輕好玩的一面,對大上海充滿好奇;而李公博、周佛海則偕女眷流連上海的繁華世界,兩人都中途退出會議,為他們后來的人生選擇埋下伏筆。這些場景和細節蘊含豐富的歷史信息,刻畫出真實鮮活的人物形象,并對他們此后革命道路的選擇提供人性化闡釋。這些歷史敘事結合了正史和野史、真實和想象,將宏大的歷史簡約為生活細節,從而貼近觀眾的現實生活和真實性情。
在新主流電影中,革命的宏大敘事往往與個體的情感敘事有效縫合在一起,從而使革命情感結構與個體情感結構實現同一性。例如,《懸崖之上》(張藝謀,2021)中“烏特拉”行動以犧牲革命者的生命為代價而取得成功,最終烈士的遺孤被送回母親身邊,大雪消停,黎明的曙光到來。同樣,在《1921》中,李達和王會悟、毛澤東和楊開慧的愛情幾乎與建黨事業同步:受進步思想影響的男女青年一邊組建小家,一邊宣傳革命思想,籌備中共一大會議;隨著一大順利召開,他們的小家也迎來愛情的結晶,也預示著革命終將取得碩果。在影片尾聲,毛澤東和楊開慧的愛情也令人動容,在楊開慧犧牲的那一刻,鏡頭插入兩人雨中送別的場景,暗含著革命與愛情、信念與理想合而為一。
《1921》在對革命歷史的講述中,將家國情懷、革命理想與個體經驗、人類的普遍情感聯結在一起,使革命歷史的情感結構與現代情感結構一致。威廉斯認為,“文化不是凝固不變的,尤其是對文化的描述,人們習慣于用過去的經驗來表現。文化的形成關鍵是如何將經驗直接或規范地轉化,這涉及將過去不斷運動的特質投射到當代活動中。在文化不斷被評估、被建設的流動過程中,文化的生產過程不斷在官方話語/明確的意識形態與實踐經驗之間取得動態平衡。”簡言之,文化是在歷史沉淀中逐漸形成的,人們在重述歷史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投射了當下的觀念和文化。事實上,將革命置于現代性語境下,摒棄假大空的宏大敘事,沿用“主旋律+”的敘事模式是新主流電影的特色,從最早“主旋律+愛情”的《黃河絕戀》(馮小剛,1999)、《紅色戀人》(葉大鷹,1999)、《云水謠》(尹力,2016)到“主旋律+懸疑”的《風聲》(高群書,2009)、《懸崖之上》再到“主旋律+動作”的《湄公河行動》(林超賢,2016)、《戰狼2》(吳京,2017)、《紅海行動》(林超賢,2018),以及將革命變成全明星視覺盛宴的“建國三部曲”等。愛情、懸疑、動作等是各種類型電影的基本元素,新主流電影吸收各種電影類型的特點,在豐富電影敘事性的同時提高審美性,同時引進眾多一線明星參與演出,實現藝術性和商業性的統一。
《1921》也在電影類型方面進行創新性表達。影片突破以往主流大片人物臉譜化的弱點,以豐富飽滿的細節、立體的人物形象還原歷史現場,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加入冒險、動作、諜戰、愛情等各種類型元素。例如,在租界中發生的那場追捕戲,巧妙地利用汽車和公交車作為道具,鏡頭快速切換,剪輯流暢,懸疑、動作、節奏和緊張氣氛都得到恰當處理,呈現出電影商業性的一面。多元化的電影類型表達既是電影敘事的內在要求,也滿足觀眾的觀影期待,使觀眾與電影文本進行深入的參與和互動。畢竟,每一種類型電影都有相應的形式和契合的主題,每一種類型都釋放出新的敘事能量,開拓新的可能性。作為商業性的電影,尤其是革命歷史題材片,融合其他類型的形式和風格,在符合歷史邏輯的視野下講述新的故事,帶給觀眾新的體驗,滿足人們對電影的娛樂性需求。
情感結構是否能得到成功喚醒還與代際有一定關系。正如韋勒克、沃倫所說,“在某些歷史時期,文學的變化無疑是受一批年齡相仿的青年人所影響的,如德國的‘狂飆突進’運動或浪漫主義運動等都是明顯的例子。”簡言之,青年一代對社會或文化變革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推動作用,他們對同為青年人的行為更感同身受。同樣,我們可以看到,《1921》起用黃軒、劉昊然、倪妮、王仁君等50余位優秀青年演員,凸顯“青春力量”,力求演員和歷史人物的神似和形似,達到形神兼備的效果,同時也符合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齡為28歲的史實。青年演員的加盟再次呼應“一百年正青春”的主題,也容易引起青年觀眾的情感共鳴。新主流電影以多元的類型表達重述革命、歷史和青春記憶,以現代性敘事使傳統故事呈現出與當代人共通的情感結構。
三、后革命時代的情感認同
近年來,新主流影視劇一度火熱“破圈”,接受者從中老年群體擴大到青年人,贏得票房口碑雙豐收,成為重要的文化現象。《戰狼2》《紅海行動》《我和我的祖國》(陳凱歌,2019)分別以56億元、36億元、31億元占據中國電影票房排行榜前10位。在電視劇方面,繼《大江大河2》(李雪,2020)、《山海情》(孔笙,2021)等主旋律電視劇獲得高收視率后,革命歷史劇《覺醒年代》(張永新,2021)還不停被年輕觀眾“催更”,并登上微博熱搜,在豆瓣上超過36萬人打出9.3高分(滿分10分)。
在毛尖看來,主旋律影視劇“破圈”的文化邏輯在于“青年文化和主流文化從來沒有形成對立或對抗關系,基本是平行而動,而當代的情況則更加特殊了。這些年以B站網友為代表的年輕人,反而是主旋律的護旗手”。那么,當代年輕人為何成為主旋律的“護旗手”?新主流影視劇受到年輕觀眾的追捧,顯影了當代中國怎樣的情感和文化指向?王杰曾以《刺客聶隱娘》《戰狼2》的社會反應為例,指出中國當代時尚的基本情感結構是“紅色烏托邦”和“鄉愁烏托邦”的“雙螺旋結構”,它在某種層面上是將“過去”理想化并且具有面向未來的情感和價值指向。“雙螺旋”結構指出中國當代情感結構的復雜面向,既有賡續傳統文化、延續革命精神的一面,也是審美現代性的表征。然而,將“過去”理想化并不能真正打動人心。正如20世紀50—70年代從“紅色經典”到“革命樣板戲”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他們的人生歷程表現出歷史的必然性,時代和社會賦予他們神性的光環,與當下主流文化始終“隔”了一層。縱觀近年來的新主流影視劇,可以發現在大寫的歷史下,小寫的“人性”得到凸顯,在時代浪潮下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也值得被銘記。例如,《集結號》(馮小剛,2007)、《八佰》(管虎,2020)等戰爭片,場面恢宏、視覺震撼的同時,也展現出歷史人物由于種種“偶然”所帶來令人唏噓的下場。他們和任何時代的普通人一樣,在歷史的舞臺上沉浮,渺小、脆弱甚至不由自主。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下新主流影視劇展現了時代激流中人物的人生軌跡,投射出現代性倫理,包括國與家、集體與個人和歷史的偶然等關系。在銀幕上,一個世紀前和我們同樣年輕的一代人,他們在動蕩的年代同樣遭遇對人生道路選擇的彷徨、對理想和信念的苦苦探索、對前途的悲觀和焦慮。他們也有青春叛逆期,也要應對伴侶的不理解,也有革命道路上遭受挫折的痛苦和犧牲。在《1921》里,青年毛澤東的革命道路以對封建家長的反叛開始;王會悟埋怨李達干革命還要自己墊錢;陳獨秀多次入獄,將《新青年》編輯部撤退到廣州,還四處討要教育經費。最終,李大釗上了絞刑臺、楊開慧被槍決、何叔衡跳崖、鄧恩銘遭受酷刑等。在《革命者》(徐展雄,2021)中,經過流血的慘痛教訓,李大釗明白了光有主義和理想還不夠,革命需要真槍實彈,否則只是讀書人無謂的犧牲。革命不再是詩情畫意,不再是書生意氣、揮斥方遒,而是隨時可能的流血和犧牲。更難得的是,當時的他們并不知道這樣的選擇是否會有結果,是否值得,是否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希望,但他們仍然堅持下來。
更進一步看,受“996”“007”“內卷”“躺平”不斷刺激的當代年輕人,他們被新主流影視劇所召喚的情感結構還在于對多元化社會/生活方式的向往。正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單向街》英文版導言所提及:“本雅明作品經常出現的隱喻,如地圖和圖表,記憶和夢想,迷宮和拱廊,狹景和全景,都喚起一種獨特的城市幻象,喚起一種獨特的生活。”從這個角度來看,銀幕上的“歷史”被賦予現實與虛構的雙重隱喻,講述了一個烏托邦、一種鄉愁,從而照見個人生活經驗和情感記憶。換言之,新主流影視劇以一種當代年輕人能夠接受的方式敘述過去的經驗,其呈現的歷史空間、精神空間乃至歷史敘事中所出現的真實與表象、回憶與夢想與當代年輕人的情感結構相通。通過情感認同,喚醒一代人對歷史事件的反應、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對沉淀在舊時空的感情,以及植根于其中的對現實的批判、對未來的激情與失敗的可能。
不容忽視的是,情感結構是一個歷時性的動態結構,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將當下與歷史情感結構的融通,不僅需要對過去情感、文化進行現代轉化,還需要審美主體的主動介入。新主流影視劇之所以能受到年輕人的積極參與,很大程度上跟這些作品豐富的審美內涵有關。從敘事層面上看,獨特的敘事視角、符合歷史的敘事邏輯、飽滿的歷史細節、立體的人物形象都是亮點。從電影語言層面上看,由具有表演功力的演員擔綱,加上精細的場面調度、多樣化的鏡頭語言、好萊塢類型電影的視覺元素,造就了年輕觀眾易于接受新主流影視劇類型模式。
綜上所述,新主流影視劇在情感結構和類型表達等方面的創新和突破,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豐富了中國電影的影像表現力。正如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媒介即訊息”,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將歷史和經驗影像化,消除歷史文本的“固化”,使歷史記憶縫合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結構中,預示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