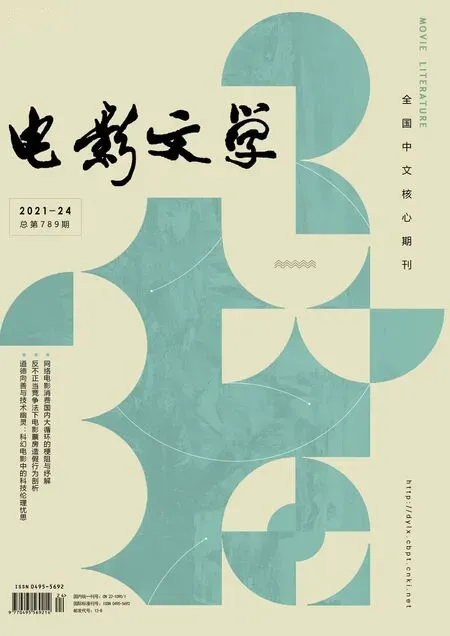張藝謀歷史記憶影像敘事的倫理反思
姬 婷
(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重慶 400715)
電影作為記載民族歷史記憶的媒介,通過影像化的書寫來達成公眾道德感的建立以及歷史的紀念和反思,并在對信息的編碼和公眾的解碼中完成了一場極具儀式化的記憶傳遞。電影中的歷史書寫通過個人在特定時期的遭遇完成反思/批判,遺忘/再現,還原/虛構。張藝謀作為第五代導演代表,對于歷史的關注更多在于個體如何生存、生命如何堅韌。時代語境的變遷注定對歷史事件的表述不再局限于主觀化情感的宣泄或對戰爭的控訴,而是從社會歷史的宏觀視野出發形成新的創作理念,轉向更為冷靜客觀,也更具歷史深度和高度的影像文本創作,是更具歷史責任感、使命感的人性化反思。它用影像表現個人的精神和心理,用隱喻式符號展現個體命運的斷裂與修復,從而達成點連成面的宏觀性歷史呈現。張藝謀將特定歷史背景作為素材相繼創作了《山楂樹之戀》(2010)、《金陵十三釵》(2011)、《歸來》(2013)、《一秒鐘》(2020)、《懸崖之上》(2021)等電影。本文試圖討論張藝謀這幾部電影是如何在私人記憶建構和歷史的跨度中以一種特有的視角完成歷史記憶的影像敘事;如何將歷史記憶共享,從宏大的歷史層面達成私人記憶與公共情感的共鳴,并由此形成歷史記憶影像化的倫理敘事策略。
一、私人記憶影像化敘事的倫理合理性
以色列學者阿維夏伊·瑪格麗特在《記憶的倫理》中闡釋這一概念、主題的思想根源在于“我們有義務記住過去的人或事物嗎……誰是那個有記住義務的‘我們’,‘我們’作為集體還是‘我們’作為某種集體的構成型要素使我們有義務記住集體中的每一個人嗎?也就是說,對于歷史,我們該記憶什么?誰有義務去記憶?”并引出“道德見證人”這一概念。道德見證人既是苦難的受害者也是觀察者,他們需要以正確的敘述立場對過去事件賦予情感意義,并且要具有特殊的道德權威。張藝謀用影像“做見證”:再現歷史,反思歷史,用一種道德立場去講述歷史。在電影中,他用極具時代特征的符號還原歷史真實面貌,用真實的平民人物悲歡展現時代一隅,用個人悲慘命運的設定指向戰爭的殘酷。個人化的記憶再現雖然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但是容易陷入帶有個人傾向的主觀判斷,甚至出現偏離現實的情緒化敘事。因此,關于張藝謀歷史記憶的影像化,要從記憶倫理的角度去判斷和厘清由他言說的歷史采取怎樣的方式或者說視角去講述的:以何種形式記憶?表明了怎樣的倫理立場?是探究私人記憶影像化合理性的主要問題。
首先是以何種形式記憶?張藝謀在電影中選擇關注以一種平民視角講述歷史,小人物的鮮活形象和坎坷命運成為主角。這種設定帶著一種對歷史的反思以及對人的關注,不再僅僅是對災難的呈現和時代的指責,而是以影像的方式進入歷史,把他當作一個人性的展示空間進行全面立體的陳述。《山楂樹之戀》中的老三和靜秋、《金陵十三釵》中的歌女與學生以及《懸崖之上》中的特工張憲臣和張蘭;這些普通人的名字被觀眾記住,人物的經歷和情感與觀眾在關愛中建立起深厚的關系并由此確定倫理責任。如此,這種記憶的建構才有意義。人們才不會在不斷重構歷史的同時將真實的歷史遺忘。張藝謀沒有一味地重現歷史或是揭露戰爭傷痛,影片對這種個體倫理的表達集中在對人性的深層挖掘,通過人性的本真展現歷史中的鮮活個體,通過影像進入歷史從而引起反思。《山楂樹之戀》講述的是普通人老三和靜秋的愛情故事。他們的愛情以老三重病去世終結。靜秋去醫院看望老三卻被趕出來,老三隔窗望著坐在醫院門口的靜秋。兩人的愛情也被門窗阻斷,門窗作為一種符號將病癥、時代的阻礙具象化,凸顯普通人命運的悲慘以及相愛的本能,記憶的影像通過平民視角完成歷史敘述的真實感和代入感。就連戰爭時期的英雄也只是大時代下的普通人。《金陵十三釵》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展現軍人和戰士在炮火連連的戰場上奮戰犧牲。教堂里被困的女學生在面臨危險時,不被世俗接受的風塵女子選擇赴死救人。她們沒有槍炮卻甘愿用生命換來他人的安全。《懸崖之上》中投身革命的四位特工將個人情愛融入抗日戰爭這一重大歷史題材,為了任務和使命在必要時犧牲自我。正是這種微觀的個人角度切入,才拼湊出完整或者鮮活的時代記憶,關于傷痛或者戰爭的歷史才有更加深刻的記憶回溯或者記憶生成。
其次是道德見證人的倫理立場。道德見證人的立場應該是以一種積極的倫理態度來構建公共記憶。這種積極的倫理立場,一般包括“人道”“向善”對“仁愛”的追求和宣揚,對主流審美價值觀“真”“善”“美”的推崇。所以,私人記憶在通過影像進入公共話語空間時,訴說者必定傳達了一定的倫理態度。張藝謀作為見證人,其影像的最終指向是對“人”價值的肯定、苦難中希望的堅守以及犧牲戰士的英雄性歌頌。張藝謀沒有一味地表現沉悶與昏暗,而是選擇對人性、生存價值做了更深一層的表達。《山楂樹之戀》影片最后的山楂樹明亮起來,昭示的是一種對未來的期望以及人追求純粹愛情本性的宣揚。這種光亮和色彩,是告別悲傷和痛苦的記憶,告別過去,在新的歷史高度上重新前行,走向開放,獲得一種文化自信和自覺。這是一個恢復人性、反思社會,帶有回望和恢復歷史意義的,蘊寓政治、經濟、文化含義的故事,也是一場熾熱而又美好的純愛故事。《一秒鐘》傳達的倫理態度也是充滿希望和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影片最后范電影、張九聲和劉閨女三人因為情感上的共鳴得以聯系,所以范電影冒險將定格膠片贈給張九聲;張九聲在劉閨女面對危險時挺身而出;一心為弟弟找膠片的劉閨女也被張九聲對女兒的愛打動,將遺失在沙漠中的膠片撿起。在送膠片、洗膠片、晾膠片、放電影等一系列具有儀式感的程式化敘事中,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情感也在不斷的擦拭清洗中得到升溫。活著的人帶著苦難繼續生存,相愛的人雖然歷經艱辛也終于團聚,張九聲失去女兒卻在某種意義上被劉閨女的情感補償,無論是親情還是愛情最終都獲得了某種意義上的大團圓結局,影片最終仍然是美好而充滿希望的人性指歸。張藝謀在集體失憶的現實情境下將私人記憶影像化,用冷靜客觀的態度反思,并在積極的美好結局中表現出創作者的倫理價值指向。《懸崖之上》里的特工們最終順利完成任務,即使付出代價。最后被戰爭破壞的生活秩序逐漸恢復,被分離的母女/子也得以團圓。無論是個人的命運悲劇還是戰爭時代的生存悲劇,張藝謀從控訴時代轉向深刻的人性思考并表達出鮮明的倫理創作傾向,即電影的正義性或者善的指向。
二、歷史記憶影像化敘事的“公共”倫理性
同時代幸存者生于集體又通過敘述的方式重塑集體。正是因為共感所傳達的道德秩序、倫理規則、情感蘊含和主體之間產生的精神互動,對歷史表述者和記憶接收者的精神活動都產生了影響;這種體驗構成了主體之間的情感互動和共鳴。記憶的公共性建構體現在倫理秩序的一致、情感價值判斷的共感,如對于悲劇的同情、對于純愛的向往。這些傳統認知在影片中完成了秩序和情感的統一,也正因此,歷史的、私人的、戰時的記憶才在影像化中獲得認同,并在情感共享中完成這種記憶的公共性建構,個人的歷史經歷聚集組合形成記憶的社會性框架。
首先,公共性基于傳統人倫集體認同的基礎。通過夫妻、父女、母女關系撕裂,轉向自我人倫指認。《〈說文解字〉注》言:“倫者,道也,理也。粗言之曰道, 精言之曰理。”倫理秩序是在一定利益基礎之上結成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客觀交往關系及其規則系統 。“一般呈現為某種形式的社會公共倫理規范、日常生活準則、社會風俗習慣以及社會成員或國家公民的公民美德等具有公共特性的倫理文化體系。”從《山楂樹之戀》到《懸崖之上》,張藝謀將大時代下的普通人作為主體,人是倫理規范邏輯和歷史的起點,通過人與人關系的崩塌與重構得以完成倫理性的社會反思。人與人的倫理秩序在家庭關系中體現為儒家提倡的父、子、母構成。儒家提出親親,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倫理。這幾部作品都涉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山楂樹之戀》中的愛人、《金陵十三釵》中的姐妹、《歸來》中的父/母女、《一秒鐘》中的父女/子、《懸崖之上》的母女/子。這種關系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影片通過傳統關系秩序的毀滅塑造出受害者形象,并將這種悲劇的原因歸結于多種元素。在民族的、個人的記憶達成一致情緒后實現倫理秩序的恢復和重建,然后傳播,并引發悲劇之源的深層反思。《歸來》中的三口之家也是典型的傳統家庭結構。這種基本構成被認為是一種較為穩定的家庭結構。這種傳統秩序的顛覆體現在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沖突中。首先是丹丹和父親陸焉識,她試圖和父親斷絕關系。“和他沒關系,服從組織”的立場以及堅毅冷漠的態度消解了父女親情。在舉報等一系列行為后,直接導致自己父母的被迫分離。這種大義滅親式的行為合乎法理卻違背了傳統親情人倫,也由此導致和母親的情感淡化甚至對立,孝道和尊老的傳統被顛覆。在知錯就改中重新完成家庭結構的彌合,通過分裂和修復的倫理關系指向深層次的歷史。而《一秒鐘》更多的是展現特定歷史被破壞的親情倫理是如何重新建構的。當父/母女的家庭結構只剩下父親或者孩子,傳統秩序瓦解,張九聲只剩下再看女兒一秒鐘的執念,劉閨女要承擔起不屬于這個年紀的家庭責任。漫長歷史上的一秒,從親情的角度橫向切開,呈現出難忘動人的父女親情。作為家庭人倫關系構建的紐帶,既可以是血緣至親的家人,如為了女兒瘋狂尋找膠片的張九聲,也可以是非親血緣的親人。這種倫理關系的連接不是依靠血緣,而是在大時代下人與人之間彼此依賴而產生的親情。痛失女兒的張九聲和流浪兒劉閨女都來自不完整的家庭結構中,他們都有自己的生存目標也有著悲慘的命運,并由此產生聯系。兩人在矛盾相處中日漸消除隔閡,建立起了非親血緣的父女之情。這種特殊的父女情超脫了常規的煽情式表達,而是在特定的敘事情景中完成被顛覆后的重建,更具有歷史的特殊性,有著跨越時空的影響。《懸崖之上》中也有基本的人倫關系。張憲臣和王郁既是革命戰友也是夫妻,并有兩個孩子。戰爭破壞了家庭秩序的和諧,小家的構建依托于大家的穩定,也以大家為先。投身革命的父母在選擇大家的同時必定舍棄了小家,在最終任務順利完成后孩子才得以回到母親身邊,家庭秩序由此恢復。
其次,公共性基于統一情境的情感共鳴基礎。由于個體所經歷的時間和所處空間的有限性、單一性和不可回溯性,我們無法親身全部經歷無窮的倫理生活實踐。但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價值判斷所依托的“具體環境”卻可以在敘事當中被“安排”出來。并在藝術化的歷史現實呈現中,觸動內心從而引發情感的共鳴,在統一的情境感受中完成歷史記憶的“公共”性建構。
對悲劇的同情。《歸來》中父女關系解構,母親馮婉瑜和女兒丹丹決裂。在一種含蓄留白式的敘事倫理中,仍是對人物苦難命運的控訴以及對人的渺小、情感的脆弱的赤裸書寫,以對倫理秩序的瓦解和個體生存狀態展現對歷史格局的追溯和反思,以此來挖掘潛藏于歷史表象之下的傷痛經驗和悲劇意味。《金陵十三釵》的震撼性正是在于以命換命的無奈選擇。正是因為犧牲,因為14個風塵女子的奉獻加深了影片的戲劇張力,觀影的情緒感染力也被放大,在悲劇性的人物命運面前傳達出戰爭中個人的無力和悲痛之感。《一秒鐘》呈現了人物不完整的情感聯系。盡管質樸的年代膠片和電影為精神貧瘠的人們帶來很多慰藉。但是作為一部關于電影的電影,《一秒鐘》并沒有著重展現人物對電影的熱愛,只是將膠片作為敘事背景,更多的是關于人情感秩序的混亂以及精神修復。張九聲愛女兒,但是只能在新聞紀錄片上看到,所以他需要那一秒鐘定格女兒的膠片;無父無母的劉閨女姐弟弄壞別人燈罩被欺負,所以需要膠片做燈罩還給別人;范電影的兒子誤食膠片清洗液傷了大腦,堅持放電影只是因為他享受電影帶來的特權。從情感層面來看,他們都是有著悲慘命運的可憐人。影片通過人物命運的悲劇性書寫引發大眾對歷史事件的公共情感認同。《懸崖之上》的結局是美好的,他們順利完成任務并且家人團聚。但是有一些戰士永遠留在了戰場,他們堅韌不屈卻落得被殺害的結局。這種悲劇式犧牲背后指向的是人的選擇的正義性,是戰爭對人以及人們生活的毀滅性傷害由此引發的人的同情。
對純愛的追求。隨著社會文化語境的變遷,消費文化下的愛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主體的選擇趨向物質利益,推崇“唯利是圖”的畸形價值觀。純真的愛情日漸成為現代社會的奢侈品。張藝謀在影像書寫中重新展現了永恒至深的純愛,他借助影像構建美好的情感烏托邦,在一個又一個特定情境中將感人的愛情借助歷史背景的敘事框架得以表達。《歸來》中被迫分離的父親母親最終相遇,雖然病理的因素阻擋了兩人的交流,只能在日復一日的陪伴中等待“歸來”,但是“歸來”本身暗含了一種希望,一種珍貴的不離不棄相濡以沫的傳統情感。除了一起等待歸來的陪伴之情,《山楂樹之戀》中的老三和靜秋作為年青一代,代表的是熾熱而又富有激情的愛情。他們的相識、相知以及戀愛像極了普通男女的愛情經歷,由悸動的情愫到熱烈的情感,甚至忽略了歷史背景的特殊設定,沉浸在對人物愛情走向的期待和好奇中。死亡使這段愛情戛然而止,老三和靜秋生死相隔,兩人在悲痛和無奈中表現出對彼此的愛,這種愛情超越了時間和空間,戰勝了疾病和死亡并得以永恒。死亡在愛情中通過跨越時空的情感延續完成愛的偉大這一主題的表達。《懸崖之上》中的四人特工隊分別是兩對愛人。只是他們的愛情表達得極為隱忍含蓄,只是從只言片語中拼湊出完整的人物關系以及情感走向。他們舍小家為大家,將個人情感融入革命事業成為無私偉大的戰士。在愛人面前他們又將自我生死置之度外,只為換取愛人生存的機會。這種充滿犧牲的沉甸甸的情感也是因愛而生。《金陵十三釵》中的風塵女子也有愛情。豆蔻被女學生辱罵,因為身份和潑辣的性格被嫌棄。在教堂避難的幾天里,她和受傷的王浦生朝夕相處互生情愫。在日常相處中喂飯、彈琴,然后私訂終身。為了彈出絕美的樂曲給奄奄一息的王浦生,豆蔻冒著生命危險尋找三根琴弦。即使她知道兇多吉少,但是仍然選擇義無反顧地冒險。戰爭或者極端情景更能考驗人性,也更能照見愛情的本質和純真。即使每對愛人的生活經歷不同、個體記憶不同。他們在漫長等待中陪伴,在生死相隔中堅守,因戰爭犧牲小我,為了愛人甘愿冒險。這些私人的記憶包含了公共情感——愛。基于此,私人的言說就有了公共基礎,并得以構建并傳播。
愛情的純潔、愛人的堅守以及愛的偉大與永恒,這些情感不再局限于某段歷史或記憶中,而是在影像化后將個體的經歷與情感上升到新的高度,進入公共話語空間,將私人記憶升華為公共認同的道德價值和普世情感追求。差異性的個體在倫理敘事的框架中融合為一個倫理共同體和情感共同體,最終實現記憶共同體。它呼喚人類共同的文化記憶,倫理敘事的文化意義要求體現傳統倫理敘事的價值,通過共同價值觀或者倫理認同完成對私人記憶的言說。
三、記憶公私域轉化的影像敘事倫理策略
電影用視聽的形式將個人記憶記錄下來,其鮮活性和傳承性遠優于文字,而當個體的記憶以影像的形式固定下來,當這些個體記憶進入公共意義的領域時,觀眾通過觀看這一形式成為潛在共享者,個體記憶由此得到傳承,又因為事件本身的普世性,人類的共同記憶由此形成。在表現苦難和反映歷史方面,沒有比影像更加直觀深刻的手段。如何將歷史合理化敘述,必須以真實歷史為倫理底線,以倫理道德為導向。張藝謀這幾部關于歷史記憶的電影遵循了記憶影像敘事的倫理策略。
第一,表達歷史的敘事重反思而不重記錄。歷史敘事被視作個人和集體生存經歷的再現,歷史敘事通過保存歷史真相、認識理解過去,見證著歷史事件中人類的脆弱和渺小,起到了情感宣泄和修復傷痛的作用,構成了獨特的敘事特征。歷史記憶所喚起的震驚、恐懼等感受往往并非來自事件本身,而是人們所賦予它的“意義”。歷史敘事不以個體經歷的歷史事件為表現重點,更重要的是以旁觀者/觀察者的態度重新講述歷史記憶。因為記憶具有私人性特征,每個經歷者對同一事件的講述角度、側重點都不相同,因此力求對真實事件的完全恢復是無意義的,甚至是不切實際的。即使文字、圖畫、影像等媒介對歷史的記錄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這種看似客觀的記錄,仍然不是對歷史真實的復刻。所以,當歷史事件發生,公共記憶的構建就不再只是圍繞事件本身。張藝謀的電影也只是把歷史記憶作為敘事的背景,通過講述時代下的個體去反思歷史,而不是對事件的描述。所以,他的某些情節只是符號化了特定語境:穿著旗袍的風塵女子、具有年代感的建筑等。當歷史事件淪為敘事背景,對生命的追尋、人性的歌頌以及歷史的反思才更有超越歷史事件的價值。
第二,以堅定的倫理立場為前提重寫歷史。私人記憶影像化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個體創作者的倫理指向。作為道德見證人,他們有責任和義務將見證的記憶共享,但是也必須滿足堅定的倫理立場這一條件。電影作為媒介承載著意識形態的輸出功能,影像的傳播也對受眾的道德倫理有著重要影響。所以,以何種立場和方式言說,是歷史記憶倫理敘事的又一重點。張藝謀以倫理道德的視角介入,轉向對客觀事實的冷靜呈現,消解了歷史/戰爭的災難意味,將重點放到對歷史語境下個人命運的關注。這種關注不是一種悲劇式主觀態度,而是通過個人生存的困苦掙扎表現生的力量和愛的堅韌。這是創作者或者歷史言說者應該注意的原則,即使歷史記憶是私人的,是可塑的,但是基本的倫理立場應該明確:不歪曲、捏造歷史事實,也不過多地美化、夸張。在尊重歷史真實性的基礎上,進行正向倫理指導的合理化藝術創作。
除此之外,創作者還注重對記憶的媒介再造中融入道德倫理觀念。張藝謀對歷史記憶影像敘事仍然以倫理表現為內核。所以,展現了被撕裂而又縫合的人倫親情,被阻斷而又彌補的情感本性。將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人性倫理融入歷史的影像化表達中,私人記憶的公共化有了共同的精神根基。因此,歷史倫理秩序的破壞和恢復才更具言說的力量。
第三,私人記憶和公共記憶的倫理性轉化。哈布瓦赫說:“個體通過把自己置于群體的問題來進行回憶,但也可以確信,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并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也就是說,私人記憶通過媒介構建共享成為公共記憶,并在解碼和編碼中影響每一個接收者,從而完成私人記憶和公共記憶的轉換。因此,張藝謀的知青下鄉經歷成為他創作素材的重要來源,但是藝術的真實或者媒介的介入必然會消解歷史的真實,在私人記憶的媒介再造中融入個體情感態度和倫理意義,如生的追求和愛的純粹。然后電影創造了新的記憶,以一種更加冷靜的反思態度和公共倫理價值認同影響了后來者對歷史觀望的態度。
消費主義浪潮中公共記憶重建—共感—分享的過程,也是私人領域的個體記憶轉向公共話語空間的過程。這使得沒有地域或經歷關聯的觀眾在此媒介敘事中獲得了相同的文化記憶。但是藝術的真實不等同于歷史的真實,公眾更傾向于選擇直白的影像講述而非歷史學者嚴謹的追溯去了解歷史,再沒有比影像了解歷史更加直白的方式了。它通過虛構的藝術、人性的真實、價值的認同去使公眾感同身受,產生共情。一旦歷史記憶進入公共空間,影像化再現記憶的過程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藝術“標榜”下的主觀臆想和不切實際的夸張甚至扭曲,歷史的原貌或者說記憶的真實,在娛樂化語境下被戲謔、惡搞,用商業元素的拼貼,最后歷史記憶淪為敘事的背景,只剩下符號堆砌的歷史外殼,消解了歷史記憶的嚴肅性和現實反思意義,這是私人記憶轉向公共文化所必須警惕的倫理問題和道德底線。
在數字影像取代了膠片的融媒體時代,張藝謀通過影像喚醒人們的記憶,用一種觀望式的冷靜去重新審視歷史。比起社會悲劇,他更關注的是個人命運。即使沉重的大門最終關閉,虛妄的期待終會落空,美好的事物也轉瞬即逝。張藝謀仍試圖在這種遺憾和反思中向和過去告白,與自我和解。言說者/見證者敘述歷史的意義正是將一段被沉淀的記憶重新撿起,在回溯和反思中自省:記憶不應該被遺忘,無論它們是好還是壞,見證/記憶不僅是一種責任,也是倫理要求。通過歷史記憶影像化以及倫理的崩塌/重建去提醒當下的人們在反思中達成對歷史的回溯以及倫理秩序的規循,這是歷史記憶影像化的意義,也是公共創作者將創作置于傷痛或者戰爭記憶中敘事的倫理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