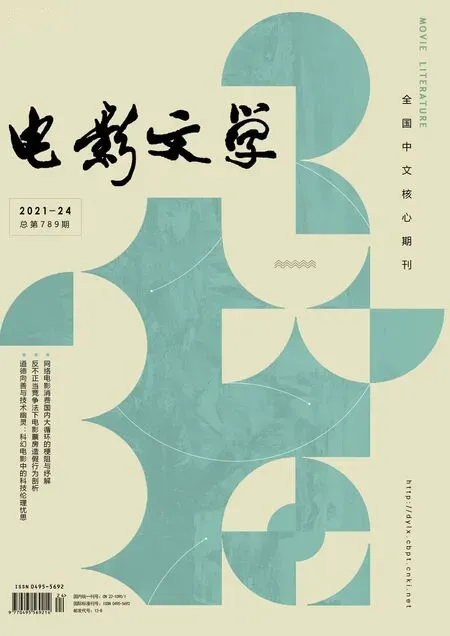西北邊疆題材劇中的“懷舊烏托邦”意象
王 月
(伊犁師范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學(xué)學(xué)院,新疆 伊寧 835000)
“存在坐標(biāo)上的兩個維度——時間和空間是不可割裂的,兩者在審美中達(dá)到完全的同一。時間藝術(shù)也展開了審美空間。”面對現(xiàn)代化的文化焦慮要找到釋放的出口,其中一條路是指向空間,而另一條路則指向時間。社會發(fā)展太快,身體及理性被裹挾向前,但心靈卻不一定跟得上城市化與技術(shù)化的速度,人就不免會向往自己曾經(jīng)熟悉、適應(yīng)和舒適的精神地帶與想象時空。新世紀(jì)以來,以《戈壁母親》(2007)、《在那遙遠(yuǎn)的地方》(2009)、《大牧歌》(2018)等為代表的主流西北邊疆題材電視劇借助話語主體的話語實踐,在邊疆想象的構(gòu)成中夾雜了對于舊時“好時光”的追憶,青春敘事與紅色編碼的心靈史被反復(fù)開啟,“好時光”也催生了“好地方”的誕生——集體主義與個人生命的“黃金時代”恰與張開雙臂亟待開拓的邊疆熱土作為某種烏托邦的時間與空間的兩種維度達(dá)到同一。懷舊的集體文化心理因邊疆想象而被“撩撥”和撫慰。
在時間上,劇作多定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到改革開放初期之間,且“文革”前多為敘事重點時段,呈現(xiàn)了帶著紅色印記、理想豪情的“激情燃燒的歲月”。厚重的年代感形成了該類劇作的懷舊調(diào)子。從經(jīng)濟角度來看,邊疆仿佛代表著某種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出發(fā)點和起點,苦地、險境、絕域的景觀不容忽視,它代表著現(xiàn)代性上的欠發(fā)達(dá)狀態(tài);但從心理層面來看,劇中則從空間到時間塑造了一個歸宿與家園的形象,尤其是普遍的“過去”的時間定位和對過往詩意化、美化處理及深情追憶代表了創(chuàng)作者和多重文化場域共同的話語選擇。這種選擇是一種共謀,或說是不同話語不謀而合的相遇,不同話語主體和文化場域“懷”的是不同的“舊”,“懷舊”卻同時滿足了國家話語、精英話語與民間話語的表達(dá)和價值需求,在具有強烈時間特征的空間上形成了話語的交織。
一、國家話語——以“政治學(xué)的浪漫主義”承載主流意識形態(tài)
劇作“身份”是決定其話語特征的重要因素,主流媒體作為阿爾都塞所說的生產(chǎn)社會關(guān)系與價值觀念的“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國家意志的重要載體。“火紅年代”的“紅色”故事因歷史敘事的厚重感、英雄的藝術(shù)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本雅明)及其深入人心的前經(jīng)驗與前文本具有非凡的優(yōu)勢。
不論是解放軍的剿匪衛(wèi)國、來自天南海北的軍墾戰(zhàn)士的拓荒事業(yè)、雪山之巔的邊防衛(wèi)士感人至深的壯舉,還是響應(yīng)“到邊疆去,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號召的有志之士在農(nóng)業(yè)、牧業(yè)、醫(yī)療、石油、核工業(yè)、藝術(shù)事業(yè)中的偉大貢獻(xiàn),其核心內(nèi)容都在于:展現(xiàn)國家艱苦卓絕的成立和發(fā)展歷程及教化人心的崇高的民族精神和崇高品質(zhì)。歷史往往是永久的可再生資源,在主流話語中,它的重要價值在于以真實的時間觸感和時間的演進(jìn)性來形成民眾共同的國家記憶,從而佐證政權(quán)的歷史合法性。“歷史寫作過程……必定具有達(dá)成意識形態(tài),甚至原型政治的功用。”相對于時間上的點狀敘事來說,橫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和包含千錘百煉歷程的敘事使得政黨、政權(quán)更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國家機器自然會將時代性的故事——這一重要的符號資本和文化遺產(chǎn)“納入民族國家的新文化傳統(tǒng)”。在電視劇已經(jīng)成為紅色文化的主要傳播陣地之時,主流話語在電視劇中的“懷舊”是一種必然。
政治性的動機要實現(xiàn)于電視劇中,少不了藝術(shù)化的處理和感性的建構(gòu)。多部劇作所呈現(xiàn)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以及“十七年”時期的中國大地上,曾經(jīng)“悲哀的人民”由于經(jīng)歷了長久苦難終于迎來了一個嶄新時代,所以有著難以抑制的捍衛(wèi)和建設(shè)新生政權(quán)的激情,彌漫著一種時代性的情緒,這樣的情緒具有恒久力量。“火紅年代”的精神力量與邊疆獨具特色的“廣闊天地”一經(jīng)結(jié)合,再加上其充滿潛力的處女地特征,讓邊疆大地成為一片巨大的共產(chǎn)主義熱土,洋溢著掩蓋不住的浪漫主義氣息。這是一種與反思現(xiàn)代性、擔(dān)憂現(xiàn)代文明會消解人文精神的解構(gòu)和批判性質(zhì)的浪漫主義不同的浪漫主義,它更多的是為階段性的政治斗爭服務(wù)、表現(xiàn)為“英雄主義”、泛“夢想的實現(xiàn)”“獻(xiàn)身精神”等要素的“政治學(xué)的浪漫主義”。主流價值觀增加了感性的因素和審美的向度,從而在精神層面對民眾產(chǎn)生有效的“詢喚”效果。
二、精英話語——緬懷“精神”占據(jù)文化主導(dǎo)的時代
成立和建設(shè)新中國時期,萬象更新,把“小我”奉獻(xiàn)于這樣的時代,是精英知識分子曾經(jīng)為之澎湃之理想和義無反顧之事業(yè)。“理想”“精神”“情懷”“信仰”曾是一個時代的文化關(guān)鍵詞,且不管是官方還是大眾都曾對這些價值極其尊重與推崇,曾是引領(lǐng)時代思潮的主要價值觀。“那個年代”四個字,包含了家國情懷、俠肝義膽、奮不顧身和對具備遠(yuǎn)見卓識的創(chuàng)世英雄的想象,是一個在記憶中被詩意化的時代,被勾勒為“精神的黃金時代”,是“實用主義、商業(yè)主義和消費主義大獲全勝之前”的讓人深情回首的“理想”時代。
從人物上直觀地看,從新世紀(jì)20年來的西北邊疆題材電視劇中,知識分子的人物地位、性質(zhì)及數(shù)量在發(fā)生微妙的變化,“過去”的人物成為精英文化對自己的想象性構(gòu)建。如果說在《西圣地》(2006)中知識分子還是襯托農(nóng)民出身、軍人和工人身份的主人公楊大水的次要人物,《戈壁母親》(2007)中知識分子程技術(shù)員是一直被壓制的悲劇性角色的話,那么到了10年后的《馬蘭謠》(2016),從浙大和哈軍工畢業(yè)的林俊德等人就已經(jīng)成了劇中的靈魂人物,《大牧歌》(2018)中上海大學(xué)畜牧專業(yè)畢業(yè)的林凡清也是全劇的核心。不僅如此,主要人物的形象、行為和語言等方式往往也投射出知識分子的情趣與風(fēng)格,再如《沙海老兵》(2018)中進(jìn)疆先鋒隊——英雄團團長在傳統(tǒng)軍人形象基礎(chǔ)上多了一層儒士風(fēng)采——會作詩,并出人意料地在迎接女兵的聯(lián)歡會上嫻熟地拉起了手風(fēng)琴。知識分子角色的數(shù)量變多,占據(jù)更重要的位置,多精通音樂、文學(xué),愛好閱讀,語言文雅。
丹納認(rèn)為,“要了解一件藝術(shù)品,一個藝術(shù)家,一群藝術(shù)家,必須正確地設(shè)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精神和風(fēng)俗概況”。黃書泉教授認(rèn)為,“中國20世紀(jì)的精英文化產(chǎn)生、形成于近代啟蒙主義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幾經(jīng)蹉跎,到改革開放標(biāo)志的新時期重新形成自己的格局”,“20世紀(jì)90年代至今,在政治和經(jīng)濟雙重擠壓下,一方面從整體上走向社會邊緣,另一方面產(chǎn)生分化——這一切使得精英文化已不再是曾經(jīng)那樣的社會精神思想的中心”。而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與文化建設(shè)在市場經(jīng)濟和國家治理中展現(xiàn)出越來越重要的功能,國家話語、經(jīng)濟話語和社會話語逐漸提高了對知識分子的重視,這也成為邊疆題材電視劇(以及傳統(tǒng)文化類、科普類等節(jié)目)中有關(guān)知識分子的表述微妙變化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之一。而且,在國家主流文化的保護(hù)下,這些劇都堅守了較為高雅、深刻、持穩(wěn)的文化質(zhì)地,沒有在商業(yè)化引誘下如同一些所謂的“新紅色經(jīng)典”一樣將人物“痞化、野化、俗化”,堅持了知識分子的審美和文化底線。
再往深處看這些劇的敘事層面。創(chuàng)作者的首要任務(wù)是完成傳遞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使命”,于是電視劇中的新疆故事選取了解放邊疆的剿匪故事、支援邊疆的知青故事、守衛(wèi)邊疆的邊防故事、建設(shè)邊疆的火熱事業(yè),這些題材顯然都是在主流話語框架之中的。而在這樣的命題框架中,精英話語也在“紅色經(jīng)典”的編碼和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允許的范疇內(nèi)表達(dá)著自身的思考、情趣、集體情懷與價值觀,劇中深嵌的母題包含個人價值的追尋、愛情親情的浪漫與溫暖、出發(fā)與歸家的抉擇、家國責(zé)任、自由與人性的堅守……這些體現(xiàn)了精英知識分子一向強調(diào)的“人的主體意識、自我價值,以及強烈的責(zé)任感和使命感”,對深刻反思性、獨特的審美旨趣和對終極價值等的探索在多部劇中有所體現(xiàn),這就意味著精英話語在進(jìn)行自我的文化表達(dá)。
相對于“當(dāng)代劇”,“老故事”里有許多值得精英話語發(fā)掘的敘事資源和動人的情懷。電視劇所建構(gòu)的美好的往日時光里包含著知識分子的一種精神寄托,它試圖彌補物質(zhì)時代與大眾文化成為“當(dāng)代社會的最大文本”這一語境中知識分子淡出主導(dǎo)地位的失落感。其修辭策略是“火紅年代+廣闊天地”下的“理想”與“情懷”,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都使得這種“理想”與“情懷”顯出不一樣的浪漫主義和烏托邦色彩。
儒家認(rèn)為,君子的人生追求為“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句話也很好地總結(jié)出歷代知識分子的個人理想、社會理想、政治理想及至審美理想。劇中人物身處往日時光,卻表達(dá)著當(dāng)下精英文化的精神訴求。個人理想上:人格道德上追求完善,如栗峰一樣義薄云天;人性解放,自由瀟灑,如草原民族般策馬馳騁;能力修養(yǎng)精益求精,挑戰(zhàn)極限,實現(xiàn)極致的個人價值,如林俊德一樣追求科學(xué)真理。社會理想上:愛情自然發(fā)生,忠誠如一,人與人不分民族,不分彼此,幼幼老老,相互守望,如入大同。政治理想上:保家衛(wèi)國,建功立業(yè),對民族興亡、人民疾苦責(zé)無旁貸,信念如磐石般不可動搖,就如同來到帕米爾高原的援疆醫(yī)生吳天云、放棄都市生活的上海知青林凡青……這樣的時代和地方,還意味著審美理想的達(dá)成,自由廣闊,人心純粹,如世外桃源,指向“夢幻式向往”。復(fù)歸這樣的舊時光,即假想式地滿足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政治理想與審美理想的統(tǒng)一,回歸知識分子極為珍視的精神、詩意與情懷。
反觀表現(xiàn)當(dāng)下社會生活的電視劇,如家族倫理劇、情感糾葛劇、青春偶像劇、商戰(zhàn)劇、刑偵懸疑劇……知識分子在其中的身影寥寥可數(shù)且不常成為主角。而在邊疆題材電視劇中的知識分子角色,具有“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特征,朝氣蓬勃,信念堅定,既有國家胸懷,又有人性情懷,這樣的“筆墨”是在緬懷尊崇“精神”與“情懷”的年代,也是精英文化群體主體意識的尋回與強化。
三、民間話語——青春的生命記憶與年代感的視覺消費
對于國家話語,革命年代及昔日激情是論證政權(quán)合法性、凝聚人心、提升感召力的重要思想資源;對于精英話語,以“情懷”之名為“缺鈣”的時代提供思想力量,對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進(jìn)行反抗。這兩層話語都試圖使特定歷史與價值觀重新“附魅”和神圣化,從而發(fā)揮出文化權(quán)力。而對于民間話語,早已盛行著濃郁的懷舊風(fēng),但它并不像前兩者那樣嚴(yán)肅,也并不試圖尋找某些整體性的終極價值,其以“回憶”之名做一次精神還鄉(xiāng),或是實用地消費著舊時光,“懷舊”對于不同的大眾群體有著不同意味和價值。
對于中老年觀眾,“逝去的歲月”鞏固其“存在感”,在懷舊中獲得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軍營生活、支援邊疆的知青生活、熱火朝天的集體大生產(chǎn)、物質(zhì)匱乏但信念篤定、精神充實的歲月;老朋友、老物件、老樣子、老故事;“那個年代”的“詩歌、行走、愛情、生死、別離以及酒、徹夜長談……”這些表意符號構(gòu)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曾經(jīng)的生活方式和獨特氣質(zhì),成為他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構(gòu)成了被特定時代話語編碼的“心靈史”,是不可磨滅的情結(jié),就像汪政所說的,這類故事的生產(chǎn)與接受“是一部分人青春記憶的證明,猶如各地的知青飯店一樣,一個人不能容忍自己的生命曾經(jīng)是空白或被否定”。
電視劇的聲光與敘事藝術(shù)將舊時光浪漫化、詩意化和陌生化了。如諾瓦利斯所說:“把普遍的東西賦予更高的意義,使落俗套的東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東西恢復(fù)未知的尊嚴(yán),使有限的東西重歸無限。這就是浪漫化。”特定的年代、曠野、邊疆生活能喚醒群體的特定回憶,美化的、詩意化的懷舊儀式是“立足現(xiàn)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gòu)”。
電視劇對曾經(jīng)的青春的描繪并不像老照片那般斑駁、晦暗,主調(diào)也更不是平凡、瑣碎、悲哀與凝重,而是五彩斑斕、風(fēng)華正茂的“正青春”,是一代人曾經(jīng)的活力、強盛、意氣風(fēng)發(fā)與英姿颯爽,是兒女子孫們未曾見過的發(fā)著光的生命階段,是引吭高歌的“激情燃燒的歲月”。這樣的懷舊書寫影響著中老年群體的社會定位與自我調(diào)適,使這一群體在大眾媒體平臺上提升了“存在感”。
“曾經(jīng)”并不只有青春記憶,也包含對小時候、母親、鄉(xiāng)土、家園的懷舊。劇中的女性書寫如《戈壁母親》中的劉月季等提供了一種溫柔、寬厚、包容的母體想象,激發(fā)“那些美好幸福的記憶瞬間以及值得肯定的生活細(xì)節(jié)”。而令人心神寧適的自然大地,也往往意指著精神回歸的空間。
同時,在經(jīng)濟話語對社會整體發(fā)揮出越來越強的控制力量的時代,行為標(biāo)準(zhǔn)日趨統(tǒng)一與功利,中下層民眾的失落感與失衡感推動民間話語“順著國家話語對紅色經(jīng)典的推動”,召喚曾經(jīng)的紅色年代,“在一個漸趨多元、中心離散的時代,深情追憶權(quán)威、信念”。而劇作中火熱的共產(chǎn)主義氛圍為“體會著當(dāng)下的失落,懷念迷失的美好”的群體提供了一個“舊夢重溫”和對比當(dāng)下的形象指向,舊時光、青春年代、母體、共產(chǎn)主義氛圍等元素共同形成了一個“黃金時代”的象征空間。
對于年輕人,“別樣青春”構(gòu)成“復(fù)古”時尚。電視劇里有父輩甚至祖輩的“別樣青春”:神圣的權(quán)威、執(zhí)著與純潔、浪漫與奇遇、勵志與成功……也有童年時代的模糊記憶和對舊時代的間接的朦朧認(rèn)知,這些轉(zhuǎn)化為一種對陌生時空的好奇和消費,構(gòu)成一種“復(fù)古”時尚。
對消費而言,影像是否真實并不重要,它能否建構(gòu)出美好想象才重要。對于新生代年輕人來說,新的時代語境使其更傾向于個性化的文化,而上代人精彩的“別樣青春”確實不同于今日之生活,劇作放大了其傳奇性和浪漫性,對年輕人形成了一定的吸引力。與此同時,在全球化浪潮下,國家間的競爭與沖突加速了民眾向內(nèi)的文化認(rèn)同與國家認(rèn)同,國家獨特的歷史進(jìn)程和其中的審美與文化對年輕人產(chǎn)生了一定的號召力。“勵志故事”、青春記憶、歷史符號、邊疆特有的空間震撼感,都成為對年青一代的吸引力。影像細(xì)節(jié)也可成為現(xiàn)實世界中的物化消費(時尚用語為“國潮”)的引子,軍裝、軍包、軍用水壺;搪瓷缸、解放鞋、花臉盆;知青主題的餐館、酒店、博物館;邊疆旅游體驗……時間在這里既可以空間化,也可以物化、消費化。
主流價值借時代敘事與新疆影像“重返當(dāng)代青年情感世界與生活中心”,精英借此影響其審美取向、歷史觀念與文化心理,而年輕人也因為這樣的敘事、符號包括相應(yīng)的“消費”彌合與父輩之間的裂隙,形成代際觀念與經(jīng)驗的交叉。
綜上所述,特定時代情緒的設(shè)定,固化了西北邊疆在觀眾心中的時間屬性與年代傾向,其成為具有年代色彩的懷舊“烏托邦”的想象物。然而文化藝術(shù)層面的符碼建構(gòu)已然在某種程度上“現(xiàn)實化”與“合理化”,多元話語的投射形成了“景觀”與現(xiàn)實的偏離。對邊疆文化的“附魅”和現(xiàn)實的“祛魅”之間,時間的遙遠(yuǎn)化、陌生化處理與現(xiàn)實的真實性之間形成了某種話語的張力。未來對于邊疆呈現(xiàn)的時間維度選擇上,需要更多地反思、修正與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