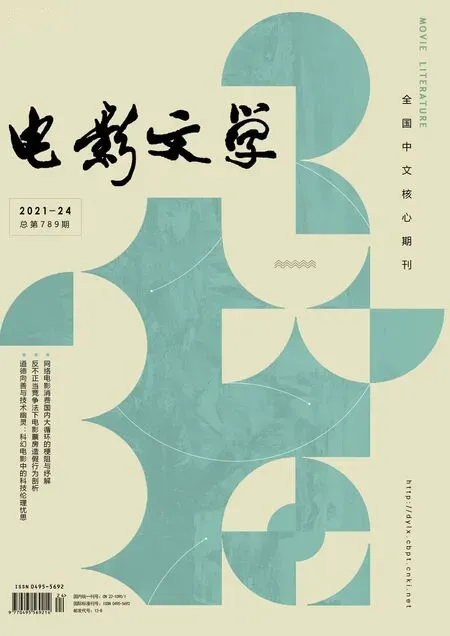道德向善與技術幽靈:科幻電影中的科技倫理憂思
韓貴東 孫欣敏
(1.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遼寧 大連 116014;2.成都體育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面對技術化所帶來的新的秩序問題,著名技術哲學家埃呂爾曾坦言:技術已成為人類必須生存其間的新的、特定的環境。它已代替了舊的環境,即自然的環境。技術成為人類肢體行動延伸范式的同時,也在某些同構化的話語語境中,以同藝術結合的形式,展示出技術背后的倫理困境。威爾斯(H.G.Wells)用“可能性的諸種幻想”(fantasias of possibility)來定位科幻:這些作品“接過在人類事務中的一些發展可能性并對它加工,發展出該可能性的諸種廣泛結果”。在電影數字技術發展日益革新的語境之下,科幻電影的發展凸顯迅猛的勢頭。回顧科幻電影的創作,從早期喬治·梅里埃的《月球旅行記》到2019年度中國硬科幻電影的奠基之作《流浪地球》,無不說明了這一問題。與之俱來的是科幻電影作為充滿藝術與技術雙重隱喻屬性的媒介產物,自然成為人們對于影像文本藝術化的探討焦點以及對技術問題一探究竟的關照對象。與此同時,試圖從技術的角度來管窺科幻電影中所存在的尖銳的倫理問題,則成為對于影像文本中科技倫理道德約束機制現實性建構的必然選擇。
斯蒂格勒的技術觀念一直受到多種思想的影響,從胡塞爾、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考,到西蒙棟和吉爾的技術哲學意義,技術的困擾一直成為諸多思想家反思的關鍵命題。同樣,對于科幻電影中所包含的科技倫理問題能否成為現實世界生活中人類所面臨的科技倫理困惑,在某種意義上盡管不會絕對的實現,但正如激進左翼思想家齊澤克所說:“一小片想象,但經由它,我們獲得進入現實的入口。”這意味著,對于科技倫理現實性的問題癥候,首先要界定科幻電影與現實維度的關聯性,即其與現實之間既構成了某些導向性的問題可能,也在其本質上脫胎于現實倫理的想象與勾勒。畢竟科幻電影“構建了一個框架,通過它我們將世界體驗為連貫與有意義”。此種特殊的技術與藝術、現實與想象聯結路徑,則為我們有針對性地在人類想象力生發的存在之思中,發現當下或者未來諸多科技之中的倫理焦慮,以防患未然或警醒世人。縱觀當下科幻電影中的科技倫理問題,不僅影響了科幻電影中主題內涵的表達,同時對其作品背后映射的現實道德建構意義也是巨大的。對技術極端發展中所面臨的道德危機,人性迷失以及技術批判進行反思,展現技術向善與負責任創新的訴求,一言以蔽之,即如何在科幻電影技術化的路徑中,探討技術所帶來的價值觀念及其本身所蘊含的倫理傾向,則應該是科幻電影研究的重要課題。在對科幻電影的文本關照之外,更需要引起人們所思所想的則是科幻之中技術背后的哲學困擾以及倫理傾向,并關注由此而派生出的集中、激烈、尖銳的倫理道德關照點。
一、去偽存真:科技倫理問題的現實可能
毫無疑問,國家技術的發展與科幻電影文本最終呈現的技術典型是有密切關系的。現實技術的應用不僅為科幻電影的發展賦魅,更得益于科幻影像文本中的技術想象,為人類生活所帶來的技術幽弊預警。科幻電影的一個內核,便是“未來主義”(futurism)。這種對人類生活中所可能發生的基于技術所生發出的倫理選擇性問題,在科幻電影的角色行為刻畫中顯露無遺。
從異形出現到人工智能、基因改造人、逆熵人、賽博格世界,“忒修斯之船”的悖論故事似乎早已變成現實,并引發諸多與之俱來的技術恐慌。一系列技術問題的困惑擺在倫理道德的面前。這些科幻的技術想象力如此之豐富地為觀眾建構起一個“未來主義”與“恐慌格調”兼具的影像景觀,是否也意味著這些驚悚的技術想象僅僅是主觀性的思考表達,并未對現實造成可怕的推測?從拉康主義的觀點來看,此種態度與視角顯然是值得商榷甚至是否定的。科幻電影之中的科技想象,讓人們短暫逃離“現實世界”的同時,進入技術想象的“非現實”之中,卻恰恰以想象的“未來主義”讓現實生活之“現實性”變得更為現實。當下現實生活中諸多的技術問題被加以過濾或者遮蔽,留給我們的只能是“望技興嘆”的不知所措與技術遭遇之下的無可奈何。面對此種問題,科幻電影有力地刻畫了技術性同現實社會性、群體性之間的對抗關系,重新將人們的現實遭遇與選擇串聯起來,賦予人們技術主動權。而技術背后的倫理向左走抑或向右走則成為觀眾影像觀閱后的行為選擇示范。倫理的選擇意味著技術困境背后之“愛”,正如齊澤克所言:“是一個關于真實的不可預見的回答:它從‘無處’(nowhere)出現,當我們拒絕任何指引與控制其進程的嘗試之時。”從具有“救世主”般的“愛”到技術倫理選擇中的“愛”,恰好將科幻電影中科技倫理的意義加以詮釋并指明科技倫理的發展方向。
當我們翻開世界電影史冊,在科幻電影的類型發展中,新舊好萊塢、各種先鋒主義、新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電影浪潮的交替出現為我們呈現出了在歷史性敘事之中的諸多科幻典型。伴隨著技術化電影的迅猛發展,也將科幻電影中的倫理問題為我們一一呈現,從生物技術、溫室生態、人工基因編輯到預測性警務、面部識別、社交媒體數據隱私以及人工智能AI的具體應用。這些新興技術的出現,也正向我們提出了復雜的科技倫理問題。
二、道德困境:科技倫理的問題導向
科幻電影中的科技問題為倫理的選擇指出了具體道德困境的意義,即引導或指正生活中技術的多重可能性。科技作為一把“雙刃劍”,如何通過科幻電影別有意味、極具指示含義的影像藝術形式,表現出科技背后的憂思,促使科技工作者或普通大眾具備科技倫理的意識,才是其背后的重要考量。海德格爾曾說:“從‘我思’出發,人和世界就分裂為二,這必然導致主體性的極度膨脹,把人當成控制存在者(亦即客體、對象)的尺度和中心,成為判定存在者之存在的法庭,從而開始了人對世界的征服進程。”人類自身欲求的無限制增加和技術使用的泛濫與過度依賴,促使當下諸多問題如阿喀琉斯之踵一般困擾著我們的日常生活。
阿爾貝特·史懷澤在有關“敬畏生命”的倫理思想中指出:“倫理學如果只是人與人的關系,那是不完整的……當所有的生命,不僅包括人的生命,還包括其他一切生物的生命,都被認為是神圣的時候,才是倫理的。”而面對科技倫理中的基因編輯問題,1993年好萊塢大片《侏羅紀公園》,則為我們展示了技術濫用背后災難性的生態困局,并在技術欲望的倫理控訴中透露出時代理性的吶喊。出于欲望與名利的追求,影片中的主人公約翰·哈蒙德博士試圖通過基因編輯建造出最成功的恐龍主題公園。電影之中,觀眾看到了強大的基因工程,復活滅絕物種災難背后那些荒唐而短視的人性弱點問題。影像以跨時代的意義,對不計后果的研發新技術的行為提出了倫理警示,并贊頌了自然界的美好,以此來展現出了人類與自然界環境之間應該保有和諧統一的倫理關系。“喪鐘為誰而鳴?”在電影上映數年后的今天,人類依舊貪婪地使用一切技術來行使所謂“引導自己走向美好生活”的權限。“切爾諾貝利之殤”,不僅是一場悲劇性的災難事故,更是在無數個科技造就的神話面前,經不起推敲的一次人性倫理實驗,其結果無異于作繭自縛。
從羅蘭·艾默里克導演的《哥斯拉》開始到今天改編、翻拍依舊在院線上演票房神話的亞當·溫加德版本的《哥斯拉大戰金剛》,充滿貪婪與欲望之心的人類組織換了一個又一個,但最終卻仍舊讓我們反觀電影中人類本身有違道德倫理的生態悖論以及出于自我保護而人造“機器哥斯拉”的倫理道德怪圈。其根深蒂固的思想不是“和諧”的生態觀,更像是滿足自我私欲的“征服心”。羅爾斯頓坦言:“無論從微觀還是宏觀的角度,生態系統的美麗、完整和穩定都是判斷人的行為是否正確的重要因素。”毫無疑問,自然界在漫長的自我進化中,始終是以守恒的自然規律為依托,在這層意義上任何主觀性的利益行為均是以打破自然世界平衡為前提來牟取暴利、滿足私利。也就在原本和諧統一的生態系統中,由于某些人為的干預釀成了最終的生態悲劇。此類案例不勝枚舉,經常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喟嘆于生命例外狀態之下的人類群體之痛,更像是不計后果摧殘自然自我演繹的結局,結果固然痛心疾首,但經自我審視之后,根由依舊是倫理選擇的困局。從這個角度而言,《侏羅紀公園》《哥斯拉》《哥斯拉大戰金剛》等一系列基于環境生態或是基因編輯而言的科技背后倫理則成為人類生活的“警世通言”與“喻世明言”,讓人類反思自我行為的同時,為人類生活行動發出預警信號,無異于提供了一種結局性的道德審視與倫理思考。
三、“道”技之魅:技術背后的倫理選擇
“具有人類心智屬性的計算機程序,它具有智能、意識、自由意志、情感等,但它是運行在硬件上,而不是運行在人腦中的。”人工智能技術顯然具備類人化的特征,與此同時,人工智能體與人體也構成一種差異化的實存,其雖由人類發明卻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具備自我辨識的主體意識。一旦人工智能體在技術異化的環境中,出現自我的意志,很可能伴隨技術的過度使用而出現難以管控甚至僭越人類行為主體的倫理觀念變化。這種合理化的科幻影像想象均展現出了現實問題中的技術倫理病癥,正如2021年上映的《哥斯拉大戰金剛》中阿派克斯公司醞釀許久的陰謀,即所謂以保護人類自我為目的制造出基因克隆后的“機械哥斯拉”在最終電影程序控制失控的條件下,其不僅將阿派克斯的BOSS一網打盡,更是喪失理智開始毀滅性地破壞人類世界,與金剛、哥斯拉展開大戰。這種科幻電影的視覺呈現不是突破邊界漫無目的地放飛自我想象意識,而是為我們確證了人工智能背后的現實倫理問題,即“人”“機”關系矛盾等錯綜復雜的困擾。
人類試圖對自然界完成主宰式的控制,對于自然的人為干涉已經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后果,“這類干預的結果將是難以預料的”。在人類對自然資源大肆攫取與爭奪的同時,以技術為主導的人工智能體不斷投入新的實驗中;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則使得人工智能倫理的問題成為現實的焦慮。
人工智能背后的倫理幽弊,不僅是這幾年科學家空想的結果,更是早在現實人工智能技術之前,就已經奠定了技術背后倫理選擇的基調。2002年由21世紀福克斯影業制作的電影《少數派報告》,為我們呈現了AI人工智能預測技術在判斷人性“好壞”方面的諸多倫理問題。影片中基因變異的“預測人”能夠預測犯罪,執法部門據此提前逮捕有可能犯罪的罪犯,但這套系統并不如人們料想的那么可靠,因此而引發了諸多的社會亂象并造成一系列的現實問題。影片中展現的許多技術推動了現實中的技術創新,但并未完成科技倫理之中“負責任的創新”命題,因此造成了技術使用背后道德邊界被打破的結果,并且其基因變異的“預測人”屬于藝術想象中合理的“科幻”成分。誠然,影片呈現了在預測、履行犯罪動機方面的難題。與現實世界相比,在人類今天生活中的技術如AI人工智能、大數據天網等,則更有可能解決這些難題。影片在展現技術發展時,也為我們提出了“負責任的技術創新”的科技倫理觀點。
人工智能體與人類之間,在“人”“機”關系的命題中倘若難以達成平等一致的關系權限,是否會產生人工智能體對身體行為的超越抑或是侵害,這本身就是一個倫理選擇問題。本質上來講,人工智能體由人類設計師設計完成,當然帶有人類道德倫理的標準,因此,“智能體道德根源于人類倫理體系”。但是,盡管人工智能可以以人類的道德倫理完成自我約束,是否就代表所有的設計工程師可以在程序開源的關節上從善負責?如果人工智能對于人類偏見和智識的了解不斷深入,甚至可以為了自身利益操縱人類,這又將為我們帶來何種困境?曾在2014年上映的科幻電影《機械姬》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趣的視角,同時幫助人們思考未來科技發展的一種可能性。一位自私且操縱欲強的成功企業家創造出一個智能機器人。機器人通過大數據芯片的預設,學習人類行為及思想。隨后企業家驚訝地發現機器人開始違背他的意愿,并由此引發一系列的現實問題。人工智能學習、模仿人類,但同時并不會局限于人類自身認知偏見以及負面價值觀。電影引發觀眾思考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利用人類弱點與人類為敵。而這其中的人工智能倫理問題與2019年中國科幻電影扛鼎之作《流浪地球》如出一轍。
《流浪地球》作為中國硬科幻的代表作,其意義與價值往往被指認為是電影技術化革新的代表。既然有其技術化的運用,自然存在技術背后倫理反思的可能,“在‘人’‘機’關系空間生成的同、異質場域中,人工智能形式化指向與意向性生成機制就成為其技術問題背后的現實倫理焦慮”。電影的成功不僅反映出了中國科幻小說發展的趨勢,更展現出了中國硬科幻的技術思考,盡管電影并未徹底實現在影像故事沖突與視覺景觀建構上“大快朵頤”的審美接受可能,卻將中國硬科幻中對于自然界生態規律平衡的議題,以東方文化語境的思維加以探討,完成了基于中國電影工業美學之中的故事生成。并“在對人性的‘我思’之中逐漸展現真理去蔽的真情內容,執著于藝術化的審美與哲學化的物我思考”。從而開啟了建構中國式科幻電影大幕的序章。
進一步而言,科幻電影的內容表達不單是視覺影像文化的營造與體現,更是將藝術創作者內心中的倫理思辨加以探討。科幻作家與科幻導演在小說文本以及電影創作中,均有差異化的倫理體驗,也就意味著時代發展中的倫理問題以文學藝術化創作的方式加以放大。尤其是將現實生活中人的“利欲之心”與“理性思考”相對立,以一種有解的“悖論”形式向讀者或觀眾加以呈現。尤其是在科幻電影中的“人工智能”倫理探討,往往是將“人”“機”關系問題以二元對立的矛盾形式具象化地說明,在文學與電影的主題中體現“和解”的可能性。
科幻電影中的人工智能體身份往往是從“被制造”到“服從命令”再到“自我意識覺醒”等經過一系列階段性變化可能的。這種AI的角色大都是科學家內心功利心的產物。而其對于主、客身份的迷失以及確證過程,即是在場者與他者身份的思考。歸根結底,如若賦予人工智能體以人性的情緒審美與思考感情,則意味著人——本身主體身份的僭越與喪失。但從某個層面而言,給予人工智能體以功能價值的人類本身是否又可以尋求到本我主體的位置,而不是利欲遮蔽的異化表現,這是值得警惕的問題。電影《流浪地球》中導演郭帆做了一次有意味的藝術與技術形式探討,他將充滿技術功效與人體意識思維的MOSS,放置在電影的角色行為選擇之中,即MOSS本身是人類科技的智慧凝聚體,作為智能化的客體存在,它是整個火種計劃的具體執行人和監控者,這一人工智能體原則上是沒有感性可能的,唯有理性的算法命令執行,畢竟其背后擔負的是整個人類轉移的使命。但是電影中頗有意味的沖突正是來自電影主人公劉培強中校以個人主觀情感化的行動,將MOSS這一充滿理智的AI執行者加以毀滅。這種戲劇化的“人”“機”矛盾處理,讓電影中的這句臺詞發人深思,即“讓人類永遠保持理智,確實是一種奢求”。俄國科學家維爾納茨基和法國人類學家德日進認為:“人生活在由人工創造的文明世界中。”而我們不難發現,AI人工智能體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無論怎么去革新,其都充滿著人類主體的標簽與表現,實際上正是人工智能倫理中二元對立的“人”“機”關系問題,其討論的背后恰好是關于人類自身命運的倫理憂思。
四、負責任之善:倫理堅守的原則
將《流浪地球》稱之為中國硬科幻電影元年開啟的奠基之作,得益于《流浪地球》在“硬科幻”作品的技術創新與藝術文本的兼顧之中達到了有效統一。而我們細數以往的“華語軟科幻”電影,實際上也呈現了諸多的倫理道德焦慮。這其中既有社會倫理、家庭倫理的問題,也出現了生態倫理與醫學倫理的矛盾爭議點,而與此同時,這些華語科幻的倫理共性則具體指向“負責任的道德向善”這一倫理的原則。
科幻電影對于“社會倫理”的具體想象表現在人們對社會的責任感。通過展現科幻電影中人物的情感意志,人生觀與價值觀等,來展現諸多的道德評判。在華語科幻電影的創作案例中,就有許多展現社會倫理層面的優秀作品。這些電影試圖通過故事的講述與典型人物的塑造,來為我們呈現社會責任感的重要性。毋庸諱言,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對于社會責任的表達是眾多的,從家國同構的理論到王陽明的“一體之仁的大我生命觀”,皆體現出了家國共情的倫理情懷,因而早期的華語科幻電影中,將科幻的標清外化為一種糖衣,而其內在的藥用機理則是我們普遍具有的社會情感觀念與具體的責任倫理。
香港導演泰迪·羅賓在1987年拍攝的影片《衛斯理傳奇》,以追查“龍珠”作為主要的敘述線索,通過對“龍珠”這一道具的使用,講述了外星人將太空船啟動器遺落在地球的故事。而影片也圍繞著衛斯理這一主人公在與黑幫團伙爭奪“龍珠”的具體事件中,塑造了充滿社會責任倫理情懷的人物角色。顯然這部影片是具有時代特色的,也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文化色彩。而黃建新導演在1986年所拍攝的科幻電影《錯位》,就已經將機器人的人工智能敘事放置在特殊的時代之下,影片將虛構的科幻想象與現實的生活相結合,以一種針砭時弊寓言式的影像風格,表現出對某些社會問題的批判意識。以對社會現實發展的某些具體批判,來展現對于社會發展、生活變遷中人們欲求增減的責任關懷。
在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家國同構”的責任理念影響深遠,在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曾把“人類家庭”當成是一個微觀的倫理實體存在。因而在國產科幻電影中的家庭倫理問題就成為電影創作者置入在電影中的規范準則。不僅是華語科幻電影對于家庭倫理問題的關注,放眼到整個中國電影的發展,都可以看出對家庭倫理的問題探討是十分普遍的。楊小仲導演在1938年所拍攝的科幻電影《60年后上海灘》,以科幻電影的講述視角,為我們呈現出一個在中國傳統倫理視野下與“家”有關的故事。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因為家庭經濟拮據,但生活放縱,歲末除夕夜之時,兩人尋歡舞場,后被妻子發現,便萌生了改造家庭、變換世界的想法。從故事的預設中我們不難發現,改造家庭的想法正是影片成為科幻電影中探討家庭倫理問題的劇情標配。而同樣因為技術的問題,這部電影也成為軟科幻之中,將科幻或奇幻色彩一筆帶過,而重中之重則是探討家庭關系緩和與否的倫理主題。與早期華語科幻電影所不同的是:新世紀以來伴隨著技術的發展,國產科幻電影在展現家庭倫理問題時,更多的是將“中和之美”的溫情探討為觀眾呈現出來,在對現實主義美學接受的基礎之上,將時代精神內涵與傳統文化的批判融合在一起,表現出了家庭之中的父子或父女的關系問題。電影也常常借助兒童視角,為我們展現出童真、童言之下的家庭矛盾。例如1988年導演宋崇所拍攝的科幻電影《霹靂貝貝》以及周星馳導演在2008年拍攝的《長江七號》,這兩部電影都以兒童科幻片的視角,為我們呈現出了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內心的孤獨與周遭關系的矛盾。在處理父子關系時,更為我們增添了諸多現實主義的溫情關懷,從而呈現出了親情之間的偉大。這與《流浪地球》之中劉培強中校與兒子之間成長關系的矛盾設置也是不謀而合的。如此看來,華語科幻電影中,對于家庭倫理責任問題的探討往往是必然的,也能夠通過電影的視覺想象為現實生活提供更多的倫理關照。
康德說:“你的行動,要把你自己的人格中的人性和其他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是目的,永遠不能僅僅看作是手段。”人既然作為目的,而非手段,自然應該以人的完整作為日常行為的參照標準。在華語科幻電影的發展中,對于人類生老病死的醫療問題也表現出了東方化的倫理視野。近幾年對于電影中的醫學倫理問題,已經引發了人們對于科學與技術的再思考。例如在2005年獲得77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由導演亞利桑德羅·阿曼巴執導的電影《深海長眠》就將“安樂死”這一醫學倫理話題放置到了觀眾的關注視野中。而醫學技術的進步不僅可以造福人類社會,同時也因為其技術的發展使得貪圖權欲的不法分子通過醫療技術而牟取暴利。當我們在探討人類生存的終極命題——生與死的存在狀態時,醫學倫理便成為不可不說的倫理議題。在華語科幻電影中探討醫學倫理而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的作品,通常是可以引發人們深思并由此思考醫療為人類帶來便利的同時是否剝奪了生死的權利。1991年由張子恩導演的電影《隱身博士》就為我們展現出了醫學技術日益革新的前提下,所引發出的諸多社會生活亂象。借此,可以看出生命價值指出的道德倫理顯然成為醫學生命倫理遵從的最高標準與范式依據。在科幻電影中對于醫學倫理的探討,不應該只落實在影像的虛構中,還應當放置在現實生活負責任態度的醫患關系中。
環境倫理或稱之為生態倫理,其指向了人與自然生態之間的關系是否建立在倫理道德關系的屬性之上,當然,環境倫理問題確證了人與周遭世界尤其是自然界與自然物之間的道德標準與道德框架。也就是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納入了倫理問題的討論之中。毫無疑問,人類作為自然生態這一系統整體存在的部分構成,而自然生態也成為人類自身存在的具體條件。在社會生活中作為主體而存在的人類,對于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道德關懷,從最根本上來講,即是對我們人類自身倫理規范的要求與關照。1990年由導演馮小寧所執導的作品《大氣層消失》以及2016年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則通過對工業化的景象設定,展現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對于生態資源過度開采所引發的諸多環境污染問題。影片也表現出了導演對于人類生態破壞的批判性思考,控訴了為既得利益而破壞生態環境的非人道行為,對于無視生態發展關系的人進行了譴責,同時也表現出了影片對于生態倫理的探討。對與人類相伴的生態環境資源大肆攫取與無底線的毀壞,只能使人類最終走向喪失自我意義與存在可能的絕境。正因如此,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與“和諧共生”的倫理原則,則為我們在稱賞科幻電影之余,提供了更多的生態倫理想象和審美期待。“負責任的向善”并非一味地只照顧到“善”的緣起,而忽視具體個人的責任擔負,這是雙重命題中的雙向選擇而非單向度的現實臆測。科幻電影中的科技倫理不單是負責任之善的表現,更是現實倫理問題的新面向。
五、人的“目的”與“倫理”責任
對于科幻電影的關照,不應該僅僅停留在既定的影像藝術想象視野之中,更應該對科幻電影創作與探討中所涉及的具體科技問題提供一種合法性的倫理道德約束機制。即一種“為人之目的”而參照的“負責任向善”的標準。馬克思·韋伯在1919年曾經提出“責任倫理”的概念,他認為“我們必須明白,一切倫理性的行動都可以歸于兩種根本不同的、不可調和地對峙的原則: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當然,伴隨著技術的發展,對科技倫理問題的探討,則成為科幻電影情感訴求背后倫理道德選擇的一條路徑,正如海德格爾“人充滿勞跡,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的“喻世明言”一般,借以期待充滿“人文主義”關懷與“技術詩性”關照下的科幻電影繼續走向倫理選擇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