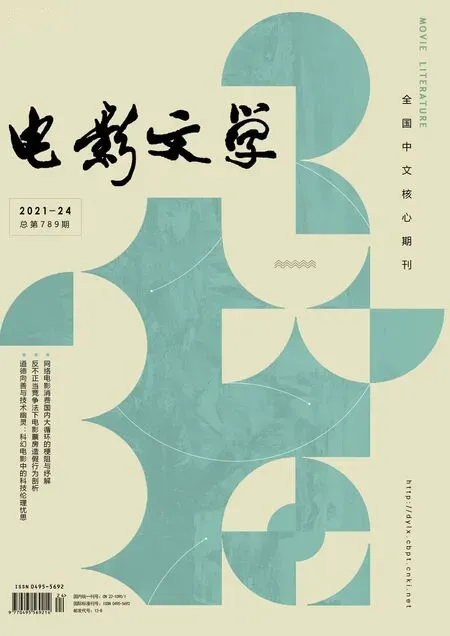對近年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的日常生活批判
李 巍
(惠州學(xué)院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廣東 惠州 516007)
近年來,中國電影涌現(xiàn)出一大批現(xiàn)實(shí)主義佳作,讓曾經(jīng)退居邊緣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重新回歸觀眾的視野。不過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內(nèi)涵和外延向來十分寬泛,因此,很多電影都可以被囊括在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標(biāo)簽之下,甚至在后現(xiàn)代主義嬉鬧式的解構(gòu)中,一切電影皆可以是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有學(xué)者稱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為硬核現(xiàn)實(shí)主義,它早已式微;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是變形后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有粉紅色現(xiàn)實(shí)主義、軟核現(xiàn)實(shí)主義以及二次元寫實(shí)主義三種。有學(xué)者則將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視為與類型片相結(jié)合的新現(xiàn)實(shí)主義,即兼顧商業(yè)和批判兩重維度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還有人將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區(qū)分為日常現(xiàn)實(shí)主義、詩情現(xiàn)實(shí)主義以及奇觀現(xiàn)實(shí)主義三種。在這些分類標(biāo)準(zhǔn)中,很多“不那么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電影也被歸類為現(xiàn)實(shí)主義。如果以此來斷定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強(qiáng)勢回歸就顯得有些理據(jù)不足難以服眾,現(xiàn)實(shí)主義應(yīng)該有一個(gè)基本邊界,跨出此邊界的是帶有現(xiàn)實(shí)因素的電影而不是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界定無須長篇大論,亦可從最簡單的事實(shí)開始,韋勒克在《批評的諸種概念》中指出,“現(xiàn)實(shí)主義是對當(dāng)代社會現(xiàn)實(shí)的客觀再現(xiàn)”。由此及彼,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應(yīng)該是以影像為基本媒介對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的客觀再現(xiàn)。如果參照早期的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那么“現(xiàn)實(shí)”二字不僅體現(xiàn)了當(dāng)下這一時(shí)間指向,也意味著對社會矛盾一面的展示,客觀則意味著電影中的故事或人物在當(dāng)下社會中可以找到真實(shí)原型,或者說它們就來自新聞故事。盡管如此,但其他學(xué)者關(guān)于現(xiàn)實(shí)主義變形的說法也是必須承認(rèn)的。在意大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的發(fā)展中也曾出現(xiàn)類似情況,“那些延續(xù)喜劇風(fēng)格一脈的新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被稱為粉紅色新現(xiàn)實(shí)主義”,與好萊塢的警匪片、西部片等類型結(jié)合的電影被稱為折中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近年來,中國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的確類型化和商業(yè)化了,這使得它們不僅在藝術(shù)上獲得了認(rèn)可,在票房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諸如《我不是藥神》《老炮兒》《南方車站的聚會》《無名之輩》《暴裂無聲》等影片。除此之外,以《夏洛特?zé)馈贰妒芤嫒恕贰镀皆系南穆蹇恕窞榇淼南矂∈浆F(xiàn)實(shí)主義逐步成為影院主流,它們將嚴(yán)肅的現(xiàn)實(shí)批判與喜劇藝術(shù)形式進(jìn)行了不錯(cuò)的融合;以《過春天》《少年的你》《嘉年華》為代表的青春類現(xiàn)實(shí)主義也日漸被大眾注意;以《烈日灼心》《江湖兒女》《追兇者也》等為代表的犯罪懸疑類現(xiàn)實(shí)主義也有不俗的表現(xiàn)。這些電影昭示著現(xiàn)實(shí)主義適應(yīng)時(shí)代的強(qiáng)大生命力,在當(dāng)下它依然能觸動普通大眾的心弦。
它們的成功在于敢于突破和創(chuàng)新,這能從《秋菊打官司》《小武》《蘇州河》等既有的敘事范式中掙脫出來,轉(zhuǎn)向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shí)和當(dāng)下的日常生活。這讓它區(qū)別前30年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也與改革開放前30年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保持區(qū)隔。這并不意味著此前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屏蔽了底層人物或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只是它們的敘事還局限在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視角中。底層人要么是英雄的要么是反英雄的,說到底這都是創(chuàng)作者心目中的底層生活,反英雄的一方受到后現(xiàn)代主義和先鋒派的影響,力圖建構(gòu)一種無中心非英雄的敘事,如賈樟柯的《小武》。同樣是小偷,小武那種過度的非英雄生活反而顯得比周澤農(nóng)(《南方車站的聚會》)更不真實(shí)。另一方則是對傳統(tǒng)英雄主義的重塑和革新,如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秋菊是新的法治社會條件下的底層英雄,是底層中的底層,因?yàn)樗€有一層女性身份。近幾年的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盡管有商業(yè)化和類型化的妥協(xié),卻更接近于當(dāng)下的底層現(xiàn)實(shí)。底層人的傳統(tǒng)英雄生活的確垮塌了,但并不因此就墮入徹底的反英雄狀態(tài),他們無時(shí)無刻不在渴望英雄生活的重建,大倫理、高道德乃至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贊語依然是底層人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因素。底層人不是小武,仿佛領(lǐng)悟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精髓并洞悉了生活虛無的本質(zhì),進(jìn)而放棄了一切英雄沖動;底層人也不是秋菊,憑借微弱之力和頑強(qiáng)的毅力便可以重建公平正義;現(xiàn)實(shí)可能更多的是兩者的奇異結(jié)合,近年來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對準(zhǔn)了這種真實(shí)的日常生活狀態(tài),展現(xiàn)了底層人重建英雄生活的渴望和重建之不可能的沖突。
一、新時(shí)期底層人在大銀幕中的非英雄化與個(gè)體永恒的日神沖動
底層人的英雄生活似乎是一個(gè)悖論式陳述。實(shí)際上對底層人的英雄敘事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和電影中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它最早產(chǎn)生于馬克思對現(xiàn)實(shí)主義和工人階級的論述,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是第一批真正意義上踐行這種英雄敘事的文學(xué)。《鐵流》《恰巴耶夫》《毀滅》展示了底層無產(chǎn)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的歷史能量,底層的勞苦大眾在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和社會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文藝中始終承載著最高意義和最高價(jià)值。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fā)展理論中,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是世界上最先進(jìn)的階級,是引領(lǐng)社會和時(shí)代走向共產(chǎn)主義的根本性力量。在這樣的歷史觀主導(dǎo)之下,歷史的發(fā)展不再由模糊不定的天道主導(dǎo),也不由萬能的全能神把持,更不能寄希望于少數(shù)魯濱孫式的人類英雄,唯有工人階級代表的人民大眾才是正道。新時(shí)期之前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都具備這種特征,在改革開放后,主旋律電影依然以此種方式描述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直到當(dāng)下亦然。不過解構(gòu)和祛魅在20世紀(jì)80年代也逐漸開始,解構(gòu)是在文學(xué)和電影兩個(gè)層面同時(shí)發(fā)生的。由于文學(xué)作品與電影之間的親緣性關(guān)系,因此,文學(xué)在80年代末的祛魅敘事勢必影響到電影對底層人的銀幕展示。祛魅最先是在新寫實(shí)主義小說中展開,由作家池莉、劉恒、劉震云等領(lǐng)銜。
王蒙曾概括了新寫實(shí)小說的特征,其中幾條是:“他們回避神圣與崇高,用調(diào)侃的態(tài)度對待一切,消除崇高與卑微的區(qū)別;他們大體上避免寫大人物,而多寫沒有地位也沒有使命的小人物;他們反對執(zhí)著,有的干脆說做不到像民族英雄、革命先烈那樣英勇不屈。”新寫實(shí)小說最大的特色便是對個(gè)人零碎日常生活的無修飾暴露,底層個(gè)體的身體與精神都完全陷入日常狀態(tài),非日常的藝術(shù)、革命、政治以及宏大的歷史走向都與他們徹底脫鉤。過于日常化讓新寫實(shí)小說中的人物暴露出一種徹底的反英雄姿態(tài),1998年上映的電影《小武》將此種姿態(tài)更進(jìn)一步。新寫實(shí)小說的影響并非一時(shí)一地,而是具有長久性和持續(xù)性。“新寫實(shí)對普通人物的還原,對原汁原味生活的再現(xiàn)都給后來文學(xué)的發(fā)展提供了參考,也引領(lǐng)了后來文學(xué)發(fā)展的潮流。在后來作家的筆下,幾乎沒有過去那種革命式理想式的小人物,特別是在農(nóng)民和工人群體的刻畫上。轉(zhuǎn)而變成新寫實(shí)般原原本本的小人物。曾經(jīng)轟轟烈烈的新寫實(shí)大潮早已散落在后來者廣袤的文學(xué)天地中,雖然不再明顯突出但已經(jīng)融入后來者的血脈之中。”新寫實(shí)小說在某種程度上扭轉(zhuǎn)了中國文學(xué)乃至整個(gè)文藝界對底層個(gè)體的展現(xiàn),強(qiáng)勢且先進(jìn)的革命階級逐漸退化為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他們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光澤。由于一些新寫實(shí)主義作家與電影界的密切互動使得此種祛魅敘事很容易傳導(dǎo)到電影創(chuàng)作領(lǐng)域。諸如劉震云的《一地雞毛》在1995年被改編成電視劇,《1942》《我叫劉躍進(jìn)》《我不是潘金蓮》等作品也先后被改編成了電影。小說與電影的時(shí)差非常小,可以說是無縫對接,不得不說后來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始終都彌漫著一層新寫實(shí)主義底色。
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對底層人的神性祛魅不單是因?yàn)樾聦憣?shí)主義小說的強(qiáng)勢影響以及新寫實(shí)主義作家群與電影界的親密互動。解構(gòu)還來自中國電影理論和電影創(chuàng)作自身的更新和發(fā)展,其中巴贊的新現(xiàn)實(shí)主義理論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早在1984年邵牧君就指出了巴贊的強(qiáng)大影響力:“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思想解放的步子加大了,在電影界也開始聽到了回響。其中最惹人注意的回響之一,就是巴贊和克拉考爾的電影理論在電影界得到了傳播、引起了議論、發(fā)生了影響。人們談?wù)撾娪八囆g(shù),已不再言必蒙太奇,引必愛、普、杜,紀(jì)實(shí)性、長鏡頭、多義性等新詞匯流行起來了。我們一些同志鼓吹的‘電影新觀念’云云,實(shí)際上就是對巴贊和克拉考爾的電影照相本性論的采納。和克拉考爾相比,巴贊的影響似乎還更大些,至少人們在談?wù)撔掠^念時(shí),提到巴贊的時(shí)候要更多些。”巴贊的新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理論并不是在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才被人們所發(fā)現(xiàn),早在十七年時(shí)期,巴贊這個(gè)名字已經(jīng)被電影界知曉,但當(dāng)時(shí)的政治風(fēng)氣以及隨后而來的十年動亂不可能讓電影自足自為地去踐行新的理論,反而讓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朝著“三突出”和樣板戲的方向快跑。直到20世紀(jì)80年代電影界才開始自覺地應(yīng)用巴贊的相關(guān)理論,第四代導(dǎo)演創(chuàng)作的《紅衣少女》《鄰居》《沙鷗》《見習(xí)律師》等影片是最早的一批代表性作品。到了第五代導(dǎo)演,巴贊之于中國電影已經(jīng)如同新寫實(shí)主義小說之于中國文學(xué)一般,廣泛地融入后來者的血脈之中,他們甚至還表現(xiàn)出一種突破巴贊的創(chuàng)作傾向。“不拘泥于巴贊的長鏡頭理論或愛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論,而是力求從所要表現(xiàn)出來的思想出發(fā),從民族文化傳統(tǒng)中,從外國文化中吸取營養(yǎng),開拓視聽語言的新領(lǐng)域。”當(dāng)?shù)谒拇⒌谖宕鷮?dǎo)演努力將這種理論轉(zhuǎn)化為具體作品時(shí),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的審美模式差不多完成了一個(gè)整體轉(zhuǎn)向。巴贊的新現(xiàn)實(shí)主義理論為什么能夠在80年代對中國電影進(jìn)行整體重塑,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學(xué)者認(rèn)為80年代“在思想上電影工具論轉(zhuǎn)變?yōu)殡娪氨倔w論,在美學(xué)上影戲美學(xué)轉(zhuǎn)變?yōu)橛跋衩缹W(xué)”,是中國電影接受巴贊理論的重要語境條件。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巴贊的理論適合被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認(rèn)識論所改寫。不管怎樣20世紀(jì)80年代巴贊電影確實(shí)參與了中國電影的重構(gòu),其中最為重要的重構(gòu)便是底層人的神性敘事被拋棄了,而這與巴贊理論本身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
巴贊的新現(xiàn)實(shí)主義理論是從二戰(zhàn)后意大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中提煉出來的,代表性影片有羅西里尼的《羅馬,不設(shè)防的城市》《游擊隊(duì)》,德·西卡《偷自行車的人》,維斯康蒂的《大地在波動》等。巴贊認(rèn)為羅西里尼們追求對現(xiàn)實(shí)的一種真實(shí)展現(xiàn),“意大利電影的一大功勞就在于它再一次重申,藝術(shù)上的‘寫實(shí)主義’無不首先具有深刻的‘審美性’”。所謂深刻的審美性其實(shí)指向了所謂的現(xiàn)象學(xué)現(xiàn)實(shí)主義,巴贊與現(xiàn)象學(xué)以及存在主義的密切關(guān)系是眾所周知的事實(shí),僅從他的理論主張中便能辨認(rèn)出二者深刻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諸如“新現(xiàn)實(shí)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攝影影像本體論”以及“電影的存在先于本質(zhì)”等。現(xiàn)象學(xué)的相關(guān)理論始終滲透在他的電影理論之中,現(xiàn)象學(xué)追求意識的純粹還原,一種未被各種理論和理念把控的意識還原,在還原的過程中不存在先入為主的現(xiàn)實(shí)。巴贊認(rèn)為存在先于含義,電影應(yīng)該首先呈現(xiàn)各種現(xiàn)實(shí)片段,這些片段的含義并不能在電影開拍之前就被準(zhǔn)確定義,那是好萊塢和商業(yè)電影的故事套路。他強(qiáng)調(diào)鏡頭的“畫面—事件性”,而不是故事性,他欣賞意大利導(dǎo)演們臨時(shí)增加的一些電影情境,這種拍攝技巧使得電影和現(xiàn)實(shí)具有同樣的實(shí)在密度,即完整的現(xiàn)實(shí)。片段的現(xiàn)實(shí)或一個(gè)單獨(dú)事件的含義唯有在與另一個(gè)事件或片段現(xiàn)實(shí)連接起來之后才能被逆推出來,而不是事先決定于某種戲劇性邏輯中。在現(xiàn)象學(xué)的影響下,巴贊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的本質(zhì)并不是典型所能把控的,那是一種人為選擇的現(xiàn)實(shí),它本質(zhì)上并不是真正的現(xiàn)實(shí)。現(xiàn)實(shí)的原生態(tài)要通過一種現(xiàn)實(shí)的直面才能被揭露出來,現(xiàn)實(shí)的本質(zhì)是不確定性,朗西埃在《歷史的形象》中持有相同看法。不確定性必須通過情境的營造而不是故事的敘述來展示,電影不能有道德和倫理神話摻雜其中,它們將影響電影的真實(shí)性。因此,巴贊的新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理論要求在展示人的時(shí)候,首先去掉各種先在的神性敘事。人不僅包括個(gè)體也包括群體,尤其是群體。演員本身也是人之展現(xiàn)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么新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尤其青睞非專業(yè)演員,至少是一種專業(yè)和非專業(yè)的混搭。人的出現(xiàn)是在現(xiàn)實(shí)的情境中,而不是戲劇場景中,非專業(yè)演員能夠更好地將自我融入日常情境之中,專業(yè)演員反倒容易進(jìn)行一種特殊場景的設(shè)想。對人的祛魅和情境化展現(xiàn)促成新現(xiàn)實(shí)主義成為一種真正的革命人道主義,“這種類型的革命人道主義不受政治局勢所左右,它的根源同樣在于對個(gè)人的重視,而很少把群眾當(dāng)成社會的積極力量。即使描寫了群眾,通常也是與主人公相對照,表現(xiàn)他們的破壞性和消極性,被蕓蕓眾生包圍的人就是它的主題。”群眾不是革命群眾,只是蕓蕓眾生,個(gè)體是蕓蕓眾生的普通一員。美國學(xué)者邦達(dá)內(nèi)拉在分析《偷自行車的人》時(shí)指出:“里奇以外的人群對他來說是威脅而不是令人安心的力量,影片很難充當(dāng)描寫無產(chǎn)階級同仇敵愾和階級意識的電影符號。”新現(xiàn)實(shí)主義理論的影響在中國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中隨處可見。如鏡頭樸素,較少外在燈光和構(gòu)圖的修飾,人物服飾日常生活化,角色之間使用方言對話,啟用非專業(yè)演員等。因此,即使沒有新寫實(shí)小說的助力,僅巴贊的電影理論也足以促成底層人物在大銀幕上的神性祛魅。
然而將底層人和普通人的生活還原為日常生活的“一地雞毛”就是真正的現(xiàn)實(shí)嗎?正如巴贊所說,最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藝術(shù)也不可能把完整的現(xiàn)實(shí)捕入網(wǎng)中,它必然會漏掉某些部分。其中最大的遺漏便是大多數(shù)底層人實(shí)際上一直處在一種英雄生活的幻景之中,這便是尼采所說的日神精神以及悲劇精神。即使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家不斷抨擊當(dāng)代資本主義的消費(fèi)意識形態(tài)將人單向度化、片面化以及異化,但他們依然不能否認(rèn)這種意識形態(tài)背后包含了“虛假的自由”“虛假的需求”以及“虛假的理想”,它們依然是日神精神,不過是一種特殊的變種。沒有對自我的英雄信仰或日神沖動,個(gè)體在世存在的本體性依據(jù)便會動搖。“我們不妨設(shè)想一下不和諧音化身為人——否則人是什么呢?——那么,這個(gè)不和諧音為了能夠生存,就需要一種壯麗的幻覺,以美的面紗遮住它自己的本來面目。這就是日神的真正藝術(shù)目的。我們用日神的名字統(tǒng)稱美的外觀的無數(shù)幻覺,它們在每一瞬間使人生一般來說值得一過,推動人生經(jīng)歷這每一瞬間。”叔本華的生命意志論也肯定了這一點(diǎn):“只有作為審美現(xiàn)象,人生和世界才顯得是有充足理由的。”日神沖動在不同時(shí)代表現(xiàn)為不同的英雄生活,改革開放前的歷史英雄是引領(lǐng)時(shí)代走向共產(chǎn)主義,改革開放之初傳統(tǒng)英雄沒落,隨之而來的是創(chuàng)業(yè)英雄的崛起(諸如萬元戶為代表的創(chuàng)業(yè)者),他們是新一代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者。如今,21世紀(jì)的第二個(gè)十年,傳統(tǒng)英雄和創(chuàng)業(yè)英雄都式微了,消費(fèi)英雄的崛起才是更為顯要的日常體驗(yàn)。近幾年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的成功之處正在于捕捉了此種轉(zhuǎn)變,底層人的困境在于日神精神已經(jīng)更替,但絕大多數(shù)人卻無法跟上。
二、近幾年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中的消費(fèi)英雄以及消費(fèi)英雄的排他性
傳統(tǒng)的英雄倫理在底層人的日常生活中逐漸消退,而日神沖動或悲劇沖動又是個(gè)體的本體沖動,這勢必導(dǎo)致民眾對新日神精神的強(qiáng)烈渴求。在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或消費(fèi)社會(這個(gè)詞在20世紀(jì)60年代之后便成為標(biāo)定西方社會現(xiàn)實(shí)的新術(shù)語)中,唯有消費(fèi)英雄才是名副其實(shí)的真英雄,其他英雄都是偽英雄。近年來各種類型的影視劇都能夠提供充足的證據(jù),從滿身高科技裝備的超級英雄,到都市言情劇中的霸道總裁,再到從一擲千金的武俠英雄或仙俠英雄,不管是中國還是世界,消費(fèi)英雄才是無可置疑的時(shí)代真英雄。新的主流日神精神與底層無關(guān),底層人想要重拾英雄身份只能是追隨于主流而無法創(chuàng)造主流。近幾年的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深刻地揭示這個(gè)消費(fèi)英雄的世界,它們向觀眾展示了這種英雄生活的排他性,底層人根本無力進(jìn)入,底層人的現(xiàn)代悲劇恰恰在于這種想進(jìn)而不得的生存狀況。恰如卡夫卡《城堡》中的K先生,城堡近在咫尺卻總也進(jìn)不去,哪怕見一見跟城堡有關(guān)的人都異常艱難。消費(fèi)英雄不是馬克思主義下的革命英雄,也不是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之下的宗教英雄,它沒有那么寬大的胸懷來容納所有的普通人成為英雄,也無法將所有人的日常生活轉(zhuǎn)換成英雄生活。但它始終都提供了一個(gè)顯而易見的誘惑,一個(gè)近在眼前的城堡,也許在本雅明看來它們還是一種類似拱廊街的透明城堡,它再也不神秘了,即使底層人也能遠(yuǎn)遠(yuǎn)看見,從而激勵(lì)他們一步步邁向它、靠近它。
在《老炮兒》中小飛所代表的新一代“混混”跟老炮兒六爺?shù)纳钍澜缤耆煌★w們在塑造一種全新的英雄生活,門檻極高,底層人不可能憑借某種人格或體格的完美便參與進(jìn)去。這種英雄在古代世界是可以被接納的,他們能夠以“圣徒”“勇士”“孝子”“忠臣”乃至“貞女”的名義被接納。在那個(gè)世界,普通人追求英雄生活有來世或天堂作為堅(jiān)實(shí)后盾。消費(fèi)世界的英雄之舉不會這么遙不可及,一切都是現(xiàn)世的乃至現(xiàn)時(shí)的。小飛和六爺?shù)凝e齬緣于小飛的跑車被六爺?shù)膬鹤觿澚艘坏溃∏∈沁@道細(xì)細(xì)的裂縫暴露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英雄倫理。在六爺?shù)氖澜缋铮推峁蔚袅搜a(bǔ)上即可,能是多大的事,即使需要很多錢,那依然是錢的事,無關(guān)道義大節(jié),它依然不是大事。六爺以為兩千塊錢就能夠解決問題,他沒能意識到補(bǔ)一道小小的裂縫居然如此昂貴,需要自己傾盡全力才能解決。六爺那些仗義的兄弟也持有同樣的理念,好兄弟燈罩仗義相助,意圖私自刮掉油漆而后重新補(bǔ)上,恰恰是這一好心舉動將兩者的矛盾直接激化到無可挽回的地步。至此10萬元可以解決的問題變成了底層人再也無法承受的天價(jià)債務(wù),而這個(gè)天價(jià)對于小飛而言不過是日常生活的一個(gè)小插曲。小飛們通過名貴跑車所營造出來的“現(xiàn)代英雄生活”是完全基于消費(fèi)主義的,他們的英雄之舉并不在于他們的為人和行為,而在于他們能不能擁有跑車,即消費(fèi)時(shí)代最具代表性的奢侈消費(fèi)品。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也有類似真實(shí)的例子,撞上豪車,可能就要傾家蕩產(chǎn)。以至于各種短視頻不斷就此調(diào)侃,看見豪車在前便急忙剎車或保持車距,然后以顫抖之聲來補(bǔ)充說明剛才日常現(xiàn)實(shí)中的驚險(xiǎn)一幕。消費(fèi)英雄們在日常生活中到處制造此種看不見的鴻溝,名車、名包、名表、名牌服飾自帶隔斷功能,讓普通人主動躲閃避讓。
《我不是藥神》中程勇在夜店的英雄救美之舉,同樣體現(xiàn)出現(xiàn)代英雄的消費(fèi)主義本質(zhì)。劉思慧為了拯救患病女兒,不惜在夜店跳鋼管舞。后來,夜店經(jīng)理當(dāng)著眾人為難劉思慧,一定要讓她跳舞,盡管那天她是一個(gè)消費(fèi)者而不是服務(wù)者。然而經(jīng)理知道劉思慧的財(cái)力狀況,他的不屑和傲慢在于判定了對方作為消費(fèi)英雄的不夠格。此時(shí)程勇出面阻止了夜店經(jīng)理的行為,反而讓經(jīng)理甘當(dāng)小丑給大家跳舞。程勇的英雄行為非常簡單,就是將賣藥的錢一沓一沓地砸在桌面,直到對方接受為止。跳鋼管舞的劉思慧以及黃毛和呂受益在剎那間重拾了生活的尊嚴(yán),這一切緣于他們在夜店一擲千金的消費(fèi)。可惜的是,除了程勇之外,其他人的英雄氣概不過是一次短暫的幻覺罷了。《夏洛特?zé)馈分邢穆迨莻€(gè)徹底的失敗者,來參加婚禮的豪車是租借的,進(jìn)門前還要特意多繞幾圈顯擺,結(jié)果還是在宴席上遭到昔日老師和同學(xué)的無情嘲笑和奚落。王老師的記憶偏好也佐證了消費(fèi)英雄的魅力,他對送電視機(jī)的袁華記憶最為深刻,記不住送掛歷的大春,但能夠記住送收音機(jī)的張揚(yáng),夏洛只能以二傻子的奇特身份被記住,成了消費(fèi)社會的笑料。夏洛想要重塑過去只能以消費(fèi)英雄的方式進(jìn)行,他在夢中完成了自己的英雄壯舉,過上了英雄般的生活,這一切都是以成名后的巨額財(cái)富作為后盾。可惜這種英雄生活還不如劉思慧們的體驗(yàn)來得實(shí)在,不過是黃粱一夢罷了。《南方車站的聚會》在這方面顯得尤其卑微,周澤農(nóng)和兄弟們以生命的代價(jià)換來的不過是區(qū)區(qū)30萬獎(jiǎng)金,他們以小偷、妓女等邊緣人的身份徹底彰顯了與主流消費(fèi)英雄的絕緣。成年人的世界充斥著消費(fèi)崇拜,少年的世界又怎能獨(dú)善其身。《過春天》里中學(xué)生佩佩和好閨密JO一心想要到日本去看雪,為了實(shí)現(xiàn)這一審美消費(fèi)愿景,佩佩不得不想盡辦法掙錢,最終變成走私的水客。盡管如此,她依然沒能進(jìn)入那種英雄生活之中。《少年的你》中充當(dāng)霸凌角色的魏萊有著優(yōu)渥的家庭背景,她以此聚集“門徒”欺壓那些家庭條件不好的同學(xué),在霸凌之后又想用錢來解決對方可能報(bào)警的威脅。少年們同樣會聚集在消費(fèi)英雄的周圍,幫助他們排斥擠壓其他少年。如果說前面這些消費(fèi)英雄消費(fèi)的還是有形的商品或有形的服務(wù),那么《暴裂無聲》中的昌萬年則過渡到一個(gè)更高層次,他擁有眾多礦山富可敵國,大口吃羊肉、開豪車以及住豪宅已經(jīng)是日常生活。他不屑于以此來標(biāo)榜自己,他想要的是名譽(yù)和聲望,因此他熱衷于公益事業(yè),給貧困學(xué)校以及學(xué)生捐款,為此受到了學(xué)校師生的熱情接待。昌萬年以消費(fèi)的方式獲得了以往只有完美人格才能承受的英雄生活。
英雄為何在當(dāng)代蛻變?yōu)橄M(fèi)英雄,無論如何英雄都不可能只限于消費(fèi)英雄一種。英雄生活的本質(zhì)是日神精神,是個(gè)體為自我的人生所塑造的前進(jìn)幻想,消費(fèi)只是眾多幻想的一種而已。什么才是英雄生活?費(fèi)瑟斯通認(rèn)為:“英雄生活是可以把生活作為一種整體而當(dāng)作一次冒險(xiǎn),要想此得以發(fā)生,個(gè)人必須在生活的整體性之上感覺到一種更高的一致性,仿佛一種至高無上的生活。也可以說,這種規(guī)定和統(tǒng)一生活、借助更高的目標(biāo)將一種宿命感賦予生活以從內(nèi)部塑造它的能力,就是生活的核心,特別是它符合齊美爾所指的那些‘精神冒險(xiǎn)家’:知識分子和藝術(shù)家。”統(tǒng)一整體的生活感為什么指向了藝術(shù)家和知識分子,費(fèi)瑟斯通為什么把傳統(tǒng)的英雄給排除出去了,因?yàn)檫@是現(xiàn)代性的必然后果,蛻變緣于現(xiàn)代性本身所具有的解構(gòu)性或不確定性。馬克思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揭示過此種現(xiàn)代體驗(yàn):“生產(chǎn)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地動蕩,永遠(yuǎn)地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chǎn)階級時(shí)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shí)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關(guān)系以及與之相適應(yīng)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guān)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美國哲學(xué)家馬歇爾·鮑曼將《共產(chǎn)黨宣言》中的體驗(yàn)替換為整個(gè)現(xiàn)代性體驗(yàn),他比馬克思更進(jìn)一步,至少馬克思還在構(gòu)建工人階級這一新的光環(huán),而伯曼認(rèn)為工人階級將如同他們操作的機(jī)器一樣,同樣是短暫的。現(xiàn)代社會將無可避免地清除一切帶著光環(huán)或神圣性的職業(yè)、個(gè)人以及行為。“光環(huán)將生活分裂為神圣的和世俗的:正是光環(huán),使得籠罩光環(huán)的人物令人敬畏;神圣化的人物是從人類狀況的母體上被剝離出來的,是不可阻擋地從激勵(lì)著其周圍男女們的需要和壓力之中分離出來的。馬克思相信,資本主義摧毀了每個(gè)人的這種經(jīng)驗(yàn)?zāi)J剑静淮嬖谏袷サ臇|西,沒有人是不可碰觸的,生活變得徹底非神圣化了。”現(xiàn)代性破壞了以往一切帶著光環(huán)的英雄生活以及英雄行為。美國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家舒斯特曼認(rèn)為:“由于道德融入審美,因此藝術(shù)也取代宗教成為精神價(jià)值最可靠的核心,藝術(shù)天才取代圣徒和科學(xué)家成為我們的文化英雄。然而,民主意識形態(tài)那不斷增大的力量(無疑地受到熱衷推銷生活風(fēng)格的貪求利潤的經(jīng)濟(jì)的強(qiáng)化),要求我們每個(gè)人都成為自己個(gè)人生活的藝術(shù)家。”
由此費(fèi)瑟斯通定義的現(xiàn)代英雄只能指向消費(fèi)英雄,唯有消費(fèi)英雄能在洶涌的時(shí)代大潮中維系一種脆弱的整體感,重新在生活中凝固一種暫時(shí)的審美幻覺,消費(fèi)英雄并非簡單地購買大量貴重商品,在身邊堆砌金銀珠寶,遠(yuǎn)不止于此。現(xiàn)代消費(fèi)英雄之所以是藝術(shù)家或知識分子,是因?yàn)樗麄兛偸峭ㄟ^有意識的商品選擇來塑造有著統(tǒng)一審美風(fēng)格的生活方式。這是中產(chǎn)階級以上才能參與的游戲,他們通過豐厚的資本將世界上各種生活風(fēng)格囊括其中,生活可以是巴洛克式的、洛可可式的、波西米亞式的、航海冒險(xiǎn)家式的、超級英雄式的,甚至也可以是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式的。只要他們想要,就能通過變更室內(nèi)居住環(huán)境以及相關(guān)的一系列商品來營造出一種帶著強(qiáng)烈“藝術(shù)氣質(zhì)”的人生。“人格美學(xué)已經(jīng)成為一種新的角色模型。在城市里,幾乎所有的事物近些年都被整容一新,至少富有的西方國家是如此。經(jīng)濟(jì)也從消費(fèi)者的新趨好中獲得巨額利潤,這些消費(fèi)者實(shí)際上不在乎獲得產(chǎn)品,而是通過購買使自己進(jìn)入某種審美的生活方式。”一句話:“美學(xué)變成了好的生活的倫理標(biāo)準(zhǔn)。”當(dāng)代消費(fèi)英雄的一個(gè)重要特征便是美學(xué)的倫理化,中產(chǎn)階級主導(dǎo)著這場運(yùn)動,將個(gè)體的日常生活整個(gè)地藝術(shù)化,而這又必須依賴消費(fèi)才能夠被建構(gòu)出來。盡管這種整體感在西美爾看來也是不穩(wěn)固的,很快又有新的時(shí)尚來替代它。但這已經(jīng)足夠了,時(shí)尚至少能維系一種暫時(shí)的整體感和日神幻覺。
佩佩想去日本看雪的愿望,夏洛的傳奇歌手人生,昌萬年的慈善人設(shè),小飛們的飆車與炫酷等無不是利用消費(fèi)來營造一種內(nèi)在統(tǒng)一且具備更高目標(biāo)的生活方式。正如好萊塢著名“007”系列電影中的詹姆斯·邦德一樣,始終以名貴的阿斯頓·馬丁跑車和馬提尼雞尾酒來彰顯現(xiàn)代間諜的英雄氣概,當(dāng)然邦女郎所代表的美女商品才是最高級的消費(fèi)品,很明顯這個(gè)間諜從來不缺這個(gè)。正如詹姆斯·邦德的阿斯頓·馬丁跑車和女郎總是不斷更新一樣,小飛們通過跑車建構(gòu)的英雄生活,也只是暫時(shí)抵消現(xiàn)代生活的碎片性和祛魅性。然而即使如此,大多數(shù)的底層人和普通人也進(jìn)不了這種英雄倫理之中,他們實(shí)際上被逼尋求另一種突破。
三、底層人的消費(fèi)殘缺性與重建英雄生活的悲劇性
日神沖動的強(qiáng)烈鼓動,過高的消費(fèi)英雄門檻,導(dǎo)致底層人只得另尋他路。總體而言,重建方式有兩種:一是拒斥消費(fèi)英雄,從對立的立場重構(gòu)英雄生活;二是跟隨消費(fèi)主義,從依附或追趕的角度幻想英雄生活。無論哪種方式,對底層人而言注定都是失敗的。
所謂對立立場是指被拋棄的傳統(tǒng)英雄,包括傳統(tǒng)的倫理英雄、道德英雄、暴力英雄(戰(zhàn)爭時(shí)代的戰(zhàn)爭英雄,和平時(shí)代是見義勇為的俠客)乃至情感英雄等。《無名之輩》中胡廣生和李海根兩個(gè)匪徒是通過暴力搶劫的方式快速進(jìn)入主流消費(fèi)社會,即使他們搶到了真手機(jī),也不過只值20萬元,每人分10萬元。僅此,李海根便暢想起7萬裝修、2萬彩禮、1萬棒棒糖的美好生活。胡廣生甚至有當(dāng)黑社會大哥的宏大設(shè)想,而這種設(shè)想也帶著傳統(tǒng)倫理傾向,即“一步一個(gè)腳印,做大做強(qiáng)”,這一目標(biāo)當(dāng)即便被殘疾的馬嘉祺嘲笑。但他們的暴力工具是一把土槍,連一個(gè)癱瘓的女人都制服不了,它撐不起對現(xiàn)代英雄的想象;相反,為了全市的文化旅游事業(yè)而舉辦的煙花秀才是真正的主角,土槍不過是絢爛煙花秀的陪襯罷了,只敢在煙花秀盛大進(jìn)行時(shí)誤開一槍,這反而坐實(shí)和加重了兩人的犯罪。武力過人,敢單挑十幾個(gè)混混的馬先勇也曾用土槍威脅過老板高明,想要回買房的10萬首付款,結(jié)果也失敗了。六爺是傳統(tǒng)的道義英雄,道是江湖之道,也是盜亦有道之道,影片開頭六爺阻止小偷扔錢包和身份證的情節(jié)便證明了這一點(diǎn),即使是下九流也要講個(gè)規(guī)矩和原則,這道義的形成緣于六爺常常叨嘮的那句話——“這年頭誰都不容易”,它暗示了傳統(tǒng)道義英雄其實(shí)扎根于一個(gè)物質(zhì)并不發(fā)達(dá)的社會。六爺和兄弟們一直感嘆世道變了,年輕人沒輕沒重,不講規(guī)矩。其實(shí)并不是沒有規(guī)矩,而是規(guī)矩變成了新的消費(fèi)規(guī)矩。父子倆之間的那場談話袒露了兩種規(guī)矩的碰撞,曉波們只在乎自己能不能玩得高興,其他都不重要。很多應(yīng)該遵循的江湖道義現(xiàn)在都成了被嘲笑的古董,老炮兒不愿承認(rèn)自己的落伍,更不愿意接受英武的過往成了可笑過往,最終不惜拼上老命捍衛(wèi)了這種英雄生活。《江湖兒女》中巧巧和斌哥堅(jiān)持的也是類似的道義,斌哥讓手下人在關(guān)二爺塑像前調(diào)解紛爭的情節(jié)極具象征意義,巧巧替斌哥做了幾年牢也是此種情義的體現(xiàn),但斌哥背信棄義拋棄巧巧追隨消費(fèi)英雄而去,結(jié)果落得個(gè)下身殘疾。即使如此,巧巧依然遵循道義接受了他。甚至在《少年的你》中少年劉北山甘愿為少女陳念承擔(dān)殺人罪名的舉動也屬此等道義。《南方車站的聚會》中周澤農(nóng)是道義英雄和暴力英雄的混合體,他的行動動力既包括要替兄弟報(bào)仇的江湖道義,也包括給妻兒一個(gè)交代的家庭責(zé)任,這種道義和責(zé)任都需要極端的暴力手段來完成——人和自殺,于是才有了讓妻子舉報(bào)自己的戲劇性橋段。《暴裂無聲》中張保民通過自己的拳頭和武力來重建底層人的尊嚴(yán),可惜他不僅不能像他的名字一樣保民,甚至連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保護(hù)不了,更不能替他們討回公道。妻子因長期喝受污染的水日益病重,孩子的死也不明不白,連尸體都找不到。相比之下,村長大量購置消費(fèi)的瓶裝礦泉水倒顯得更像英雄之舉,至少它能保護(hù)自己的妻兒老小不受污染水源的侵害。
第二種重建方式是主動追隨,在幻想中完成消費(fèi)英雄的重建。程勇是通過道德來完成英雄生活的重建,但不同于六爺和巧巧們,《我不是藥神》中程勇的重建過程始終脫離不了消費(fèi)英雄帶來的便利,兩者如影隨形般地糾纏在一起。程勇的英雄救美之舉是通過消費(fèi)完成的,利潤和金錢也是他走私仿制藥的初始動機(jī),他能幫助眾多白血病患者用上廉價(jià)救命藥,因?yàn)樗捌诜e累了大量財(cái)富并將這些財(cái)富用于再生產(chǎn)。在電影后半段,程勇的英雄生活能夠得以維持完全依賴于財(cái)富。財(cái)富耗盡時(shí),英雄生活也就結(jié)束了。不同的是:程勇并不是昌萬年式的名譽(yù)消費(fèi),在金錢耗盡之后一切皆空,其英雄行為在未來依然會被認(rèn)可。因?yàn)樗麑τ⑿凵畹闹亟▽?shí)際上是雙重的,是從消費(fèi)英雄過渡到道德英雄,也可以理解為他并不排斥消費(fèi)英雄在道德英雄重建中的作用。《夏洛特?zé)馈分邢穆遄詈蟮闹亟ㄒ部梢员粴w于此類,在夢中他得到了他預(yù)想的一切,實(shí)現(xiàn)了他期望的一切,卻最終發(fā)現(xiàn)深愛自己的馬冬梅才是最重要的,但這份愛情又無可挽回地丟失了。從夢中醒來之后,夏洛重建了一種情感英雄的生活,重拾了對生活的信心。現(xiàn)實(shí)的重建是一剎那的醒悟,夢中的重建則跨越了漫長的半生時(shí)光,一剎那的重拾需要作為消費(fèi)英雄經(jīng)歷一生的磨煉,沒有這種磨煉重建是不可能的,電影認(rèn)可了英雄生活的重建必須經(jīng)歷消費(fèi)英雄的劫難和考驗(yàn)。《無名之輩》中的霞妹、《南方車站的聚會》中的劉愛愛以及《過春天》中的佩佩則體現(xiàn)出對消費(fèi)英雄更為赤裸的依附,她們的努力也反映了女性重建的悖論性,即困難又容易。困難緣于傳統(tǒng)英雄生活本來就沒有多少屬于女性,她們一般是作為男英雄的伴侶出現(xiàn)的,貞潔烈女是最極端的表現(xiàn),這里普通男性的女人也可以成為倫理英雄。因此女性本身很難通過六爺、張保民和周澤龍等人的方式去重建,她們更多的是選擇依附,正如以往的時(shí)代一樣。但消費(fèi)時(shí)代又為女性提供了得天獨(dú)厚的條件,即女性本身就是消費(fèi)時(shí)代最重要的消費(fèi)品,霞妹們可以將自己變?yōu)樯唐啡缓筮M(jìn)入消費(fèi)社會。霞妹在夢巴黎的工作是明確的賣淫行為,劉愛愛也是通過妓女的身份得以參與周澤農(nóng)的英雄游戲之中。佩佩雖未涉足于此,但佩佩的命運(yùn)是母親以另一種形式的賣淫造成的。母親那一代為了獲得留港資格不惜與香港底層男性交往,哪怕對方已有家室。佩佩的跨境學(xué)童身份是母親一手造成的,即使在深圳,母親也一直不停地更換男友,尋求男人的庇護(hù)。佩佩看似以一種獨(dú)立的方式去接近消費(fèi)英雄,但她之所以能夠更輕松地走私最新款的蘋果手機(jī),緣于她利用了自己未成年女學(xué)生的身份,她能入門也得益于男友阿豪的幫助。盡管通過非法的手段來接近消費(fèi)英雄,佩佩依然只能在陽臺上幻想著到日本看雪的情境。正如30萬元并不算巨額財(cái)富,甚至不能讓小飛的法拉利換一次車漆,但并不妨礙劉愛愛和楊淑俊對未來的暢想。
底層人重建的悲劇性始終緣于他們消費(fèi)的不充分性或殘缺性,電影中消費(fèi)殘缺性以人的殘缺性彰顯出來,人的殘缺是無法充分生產(chǎn)以及無法充分消費(fèi)的征象,它包括肉體殘缺和精神殘缺兩種。張保民是個(gè)啞巴,天然的失語者,妻子則身患重病;屠夫李水泉被張保民刺瞎了一只眼睛,看不清世界,盡管他也是一身蠻力。屠夫的兒子自始至終沒有說過話,不是肉體上的啞巴便是精神上的沉默。這些人甚至都不住在城市,而是在偏遠(yuǎn)的農(nóng)村地區(qū),真正地遠(yuǎn)離消費(fèi)世界。《我不是藥神》中到處是無法消費(fèi)天價(jià)醫(yī)藥的白血病患者,程勇一開始賣印度神油的身份也暗示了自身的無能和殘缺性。老炮兒六爺是一個(gè)重度心臟病患者,他的兄弟們都是一幫老弱病殘。夏洛和大春分別是王老師眼中的大傻子和二傻子,屬于智力殘缺,跟袁華全方位的優(yōu)秀比起來,他們甚至在身體上也是又老又丑,這是班級女神秋雅給出的評價(jià)。佩佩的殘缺性在于她未成年,剛滿16的她只有在路邊餐飲店打零工的資格。胡廣生和李海根是“夏洛式”的弱智者,他們不敢搶銀行因?yàn)殂y行有保安,只能搶隔壁的手機(jī)店,結(jié)果只搶到了一堆手機(jī)殼,搶劫的視頻傳到網(wǎng)上被做成了鬼畜視頻,遭到了網(wǎng)友們密集的彈幕調(diào)侃和嘲諷。馬嘉祺則高度癱瘓,完全無法正常行走,連日常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她罵走保姆的行為其實(shí)是徹底將自己與消費(fèi)世界隔絕了,她的死亡就變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如果馬嘉祺是一個(gè)巨額財(cái)富的擁有者,同時(shí)又是一個(gè)癱瘓病人,那么某種意義上她還是一個(gè)理想的消費(fèi)者,因?yàn)樗枰M(fèi)這個(gè)社會提供的各種醫(yī)療服務(wù)以及日常生活服務(wù),但馬嘉祺恰恰只是一個(gè)沒錢的普通人,沒錢也無法生產(chǎn),她的最大悲劇便是沒用,其對自殺的渴望皆來自此,沒有人需要她,她徹底無法重建一種消費(fèi)社會中的英雄生活;相反,即使身處底層的匪徒也還能夠在消費(fèi)社會中生產(chǎn)或消費(fèi)。“身處消費(fèi)社會,馬嘉祺卻因無法行動(甚至無法勞動)成為都市生產(chǎn)者的反面和邊緣人的代表。她無法勞動,無法消費(fèi),無法成為都市生活中健全的消費(fèi)主體,從而不被都市承認(rèn)。她的殘疾不過是這種缺陷的肉身隱喻。煙花加深了馬嘉祺的被遺棄感和局外感。”
近幾年中國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真實(shí)地揭露了底層人當(dāng)下的生活現(xiàn)狀和生存困境,并不斷地提醒觀眾注意英雄生活的多重性。無法否認(rèn)的事實(shí)是:消費(fèi)英雄日漸強(qiáng)勢,并不斷滲透到每一個(g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形成了新的“鐵籠”社會,生活中本該有的其他超越維度都被遮蔽了。底層人在日常生活中重建英雄生活的努力看似是螳臂當(dāng)車,實(shí)則體現(xiàn)了一種頑強(qiáng)的超越意志和生命意志,在日益同一化、單向化的娛樂消費(fèi)社會中,它將是一種革命因素。不同的英雄倫理將促使人們從不同的層面重構(gòu)有機(jī)整體的生活,日常生活本身所具備的多種可能性將被掘開,進(jìn)而有利于實(shí)現(xiàn)列斐伏爾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提出的終極目標(biāo),“這個(gè)目標(biāo)就是改變生活,從日常生活的細(xì)枝末節(jié)之處,改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