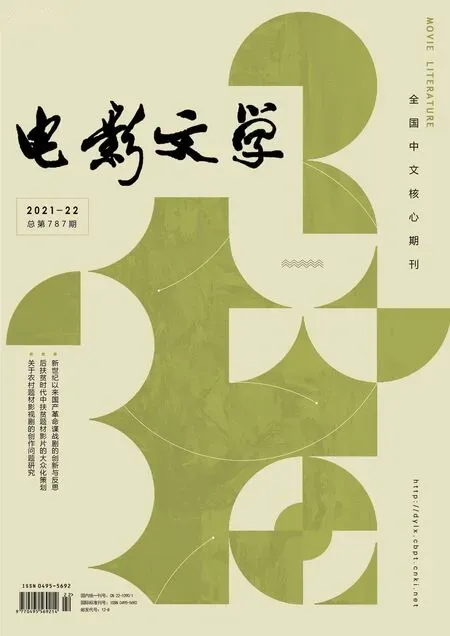影像化儀式:中國女排電影的審美維度
任 和
(首都師范大學燕都學院,北京 100048)
一、五連冠的榮光與中國女排電影的儀式敘事
儀式一直以來都是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基本研究主題之一。通過符號和儀式的運作,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象征形式融合起來,構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意識。在當今社會中,定期舉辦的體育比賽也是模式化儀式之一,具備了互動儀式鏈理論提出的群體聚集、交流互動、有節奏的反饋等要素。體育題材電影也大多有重復性、漸增性、可預測性、懷舊性、象征性等文化特征。然而,有關體育題材電影中儀式敘事的研究相對較為薄弱。而這些文化特征在中國女排電影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因為儀式在女排電影中不僅是特定時期文化的影像呈現,也擔負著電影敘事和文化表征功能,表征著女排電影的意義再生產。
20世紀80年代,中國女排奇跡般地獲得“五連冠”,女排精神也作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被報告文學、紀錄片、電視劇、電影等一系列媒介重復建構。這種互動儀式通過可見的互動情境和數個歷史人物的個體際遇塑造了一場家國神話,也成就了女排電影不變的敘事主題,《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奪冠》和2020年上映的《奪冠》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奪冠”作為自己的電影標題。電影《沙鷗》雖然以女主人公沙鷗的名字為題,但其英文題名為“The drive to win.”(直譯為“勝利的動力”)。幾代女排隊員的奧運征程被放置在頒獎儀式上升國旗、奏國歌的高光時刻的時間段落當中。從女排的風采來表現民族強大、國家崛起的歷程,觀賞女排電影成為一種儀式或集體慶典。電影中的“五連冠”,不僅是重現的集體記憶,更是“女排精神”的群體體驗的再生產。
女排電影圍繞著國家本位、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相結合的敘事途徑,將政治文化符號以直接可見的方式改編進電影文本;片中人物崇尚英雄主義、集體主義與理想主義,并始終圍繞著理想付出行動,甚至有可能這些行動是象征性的,而非日常化的;人物塑造上以承載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內涵的人民英雄為主,最終在銀幕上呈現“奪冠”這一儀式性的情節和場景。沙茨認為,電影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它的文化儀式功能,即電影有能力使自身成為一種文化儀式:“一種神話結構只有被吸收到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去,才能被文化團體中的成員所認識,并對他們有意義。”銀幕上的“五連冠”是一個延續不斷的歷史文化主題,成為國家民族想象的集中投射,成為民族寓言式的故事源泉。
本文將以奪冠為主題的女排電影作為討論的對象,在儀式理論的框架中探討女排電影的審美特征、創作傾向、儀式訴求,在此基礎上探尋女排電影敘事嬗變的軌跡和動因;探討女排電影的創作者如何借文本書寫中國的現代化影像,并以影像構建的“國家的儀式”對建立集體記憶的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豐富的銀幕再現不斷傳播主流價值觀;并嘗試探討女排電影在反映 “五連冠”之余構成的國家民族認同的現實意義。
二、鏡像儀式——集體記憶的影像展現
(一)原版體育比賽資料的鏡像
“儀式中,大到框架的建構、關系的定位、場景的構建,小到符號的選用、動作的展示都源自模擬”,儀式的模擬最直觀的是場景化,“敘述故事的實況,對話和場面的紀錄,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大致相等”。這一特點在許多體育題材電影中都非常明顯,即大量采用模仿比賽的影像,甚至是原版比賽轉播畫面。當這些比賽場景被編織到敘事文本之中,意味著敘事的短暫停頓,觀眾有片刻僅僅沉浸于儀式的狂歡。儀式的狂歡也來源于體育競賽本身,每四年一次的奧運會,是一個周期性進行慶典的神圣國家時間。這是一個舉國歡慶的時刻,比賽現場滿目的紅色彌漫著節日的氛圍。《奪冠》電影中,比賽的解說員直截了當地說:“中國與日本、美國的比賽,從來不是一場比賽這么簡單。”女排的比賽作為一個節日,和中國民族國家的起源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跟“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愿望連接在了一起。
《奪冠》中中國女排的三場比賽,都邀請了外國排球運動員專門重新拍攝了排球比賽的鏡頭,片中觀眾在國內收看電視轉播時,卻看的是當年比賽的轉播鏡頭。電影中中國女排跟巴西比賽時,甚至連場外觀眾的鏡頭都有部分來自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的實況轉播。兩部《奪冠》為了表現真實,特別請著名解說員宋世雄做解說。《沙鷗》中,女排運動員晚上一起學習,電視里播放的也是20世紀80年代乒乓球、排球比賽的真實錄像。現實比賽的錄像成為連接女排與比賽觀眾、電影觀眾的載體。
(二)現實女排隊員和教練的鏡像
女排電影利用瞬間的、感官的歷史人物影像的疊加出場重塑著觀眾的記憶與經驗,制造出一種符合觀眾欣賞趣味的歷史擬像敘事。陳可辛導演表示,在看女排拍攝的時候,他自己都會有一種在看紀錄片的感覺。不同時期的女排電影,故事情節到人物形象再到歷史遭遇總是顯現出了極度相似的特質。
女排電影在集體記憶建構中主要有兩個作用:再現記憶和創造記憶。在女排精神的集體記憶中,郎平是“具象”。一個以拼搏精神成長起來的鐵榔頭主攻手變成了著名教練。鞏俐的“形似-神似”的演繹將郎平的形象進行了再創造,她為當代年輕觀眾對英雄的崇拜創造了一個新的偶像和想象,對“奪冠英雄”這一人物符號進行了很好的理解、使用,繼而創造。除了郎平之外,也有其他廣大球迷很熟悉的女排隊員如朱婷、丁霞、魏秋月等,這些歷史人物本人的參演加劇了電影中人物符號的產生、維系、修正等轉變過程。《奪冠》中的郎平,陳忠和等人物體現了現實中中國女排的團結合作、拼搏向上、堅忍不拔、永不言敗的體育精神,被映射為女排精神的符碼。儀式的循環互動過程中,人們分享著共同的情感體驗。正是這種群體體驗,將符號與神圣的國旗、國歌聯系在一起,使人們的家國情懷得以升騰。
《沙鷗》中,中國隊決賽輸給了日本隊,沙鷗悲慟不已,回國船上將銀牌扔到了大海里。這一行為跟女排教練袁偉民有相似之處。袁偉民在擔任女排教練之前,曾是中國男排國家隊隊員,在捷克世錦賽上榮獲“最佳全面運動員獎”,但袁偉民卻在獲得榮譽后將獎杯砸碎,因為中國男排甚至未進八強,他作為男排一員,不愿意獨享榮譽。電影將人物仿像和場景重現,聯構表征的歷史事件重塑。
電影在集體記憶的形成和民族族群凝聚中有可能起到關鍵作用。不同于紀錄片單純的歷史記錄,女排電影用場景化鏡像重現歷史比賽的原貌,對現實中的女排人物進行特定符號化生產,突出了具有歷史標志性的體育事件,并使其被建構為新時期的集體記憶。女排電影以一種隱秘而成功的鏡像化的視聽成功地確立英雄形象的鏡像化重塑,為觀眾打造了一個現實的鏡像儀式時空。觀眾對“五連冠”這一歷史事件的崇拜,被女排電影提供的移情想象空間喚醒,在鏡像儀式中完成了對歷史社會現象現代化的表述。
三、符號化敘事儀式——國族符號的傳播
符號化也是女排電影的突出表現之一。它抓住了曾經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五連冠”的國人的需求,利用觀眾的集體記憶、社會懷舊心理來建構神話。物品、場景或活動都帶有時代的印記,這些具體的日常符號,是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們所特有的,符號喚醒觀眾對于那個年代的追思,符號成為族群身份認同和個體意識的載體。
(一)標語的符號
視覺影像符號成為女排精神的一種載體,在女排電影中,最常見的可見符號就是各種標語,創作者大量使用符合具有時代特征的符號并加入敘事,強化了電影的敘事效果和敘事深度。以隱喻和象征的方式呼應著電影的主題,往往具有超出自身詞義的深層文化意義。《排球之花》片末,歷經磨難的老教練終于回到了他闊別已久的體育館,女排隊員們齊刷刷地對老教練舉起了手——手掌心貼著紙條“為國爭光”“勇攀高峰”。這些懸掛在訓練場邊紅綢上的標語,寫在了隊員們的手上,也寫在了她們心里。
在《奪冠》中,也有大量的口號和標語出現:彭昱暢飾演的陳忠和第一次進入漳州女排基地,進門的門崗上是“婦女能頂半邊天”;一進體育館,他就被女排隊員們扔出的排球砸到了頭,他下意識地抬頭一看,鏡頭直對著館內國旗下方正中間的“沖出亞洲,走向世界”;女排隊員們跑步時,鏡頭掃過館外“團結 拼搏 敬業 奉獻”;陳忠和一個人在女排基地角落練習單手發球,背面的墻上貼著“團結 緊張 嚴肅 活潑”;女排跟江蘇男排打友誼賽的時候,會場標語是“球場當戰場,排球做鋼槍”;真實的中國女排基地里,同樣懸掛著類似的標語:“同心同德開創體育工作新局面”“全力攀登世界體育高峰”;在女排訓練館里懸掛著一個巨大的世界地圖,其中中國地圖又以等比例大覆蓋在上面,上面寫著“破釜沉舟迎奧運 氣貫長虹戰賽場 祖國在我心中”。女排電影以特定的藝術符號呈現出了儀式的空間秩序,填補了觀眾記憶中的拼圖,緊緊抓住了時代特征,將“五連冠”時空中的影像語言借助視覺化的符號編碼。
(二)場地的符號
奧運主賽場是4年一次的生命循環。作為儀式舉行場所的主賽場,高聳于主賽場中心的旗桿則賦予了主賽場一種神圣性。因此,旗桿作為一種“顯圣物”,是將無序的世俗空間標識轉化為有序的神圣空間的標志物。圍繞著旗桿這一“顯圣物”景觀,在日常空間中開辟出了一個神圣而有序的儀式空間。《排球之花》的開頭和結尾用這個“顯圣物”首尾呼應:開場是全國青年女子排球賽的比賽現場,女排隊員們在場上比賽;結尾是世界青年女子排球賽,中國隊對日本隊,在觀眾的歡呼聲中,老教練的手高高地舉了起來,中國隊獲得了勝利,教練和隊員們站上了領獎臺。
女排隊員在體育館中訓練的場景也是一個固定化的儀式,《奪冠》中陳忠和隔著鐵絲網看女排隊員們訓練;《沙鷗》中隊醫也是隔著鐵絲網看女排隊員們接球。不管是《奪冠》,還是《沙鷗》《排球之花》,他們無一例外采用了“教練面無表情地向女排隊員扔球,讓女排隊員在地面上翻滾接球”的敘事段落,教練都是說:“你們不是身體不行,就是意志垮了!”“沒完成多少個好球就不能停!”“我們的條件不行,就是靠意志!”年輕氣盛的隊員會因為接受不了這么殘酷的訓練而跟教練發生激烈的沖突,說教練是“母老虎”“法西斯”。或是全體隊員在平時訓練的體育場外一起接受各種體能訓練的敘事場景。比賽時,運動館的助威是場地在特定時間最獨特的外在形式,排山倒海的氣勢、歇斯底里的呼喊、勝利后的慶祝和歡呼,都是排球比賽時場館內特有的帶有排球印記的場域儀式。
(三)象征的符號
儀式中很重要的一個現象是象征。儀式通過一些象征符號,模擬并指涉相關的對象,對象常常與要解決的問題相關聯。儀式性的鏡頭常常是電影中高潮性的鏡頭,是最有感染力的。在《奪冠》中,有這樣一幕場景:中國女排第一次獲得世界杯冠軍之后,無數群眾舉著國旗,打著“中國女排行,中國一定行”的標語上街歡呼,高興地把鑼都敲破了,開始敲打臉盆。陳可辛導演在拍攝結束后佩服地說:“看到觀眾看中國女排比賽奪冠時的那種狂熱,都不由得戰栗,這種狂熱遠遠超出了排球,甚至超出了體育本身的”。女排五連冠的象征就是國歌和國旗,通過國家象征物的媒介再現并建構對國家的忠誠感。女排電影以特定的藝術符號呈現出了儀式的空間秩序,緊緊抓住了賽場中傳達出的主旋律,將“五連冠”時空中的影像語言借助視覺化的符號編碼;同時,女排電影在傳播體育文化之余,也折射出了在那特殊時期中國社會的文化形態和價值觀念。在女排精神的激勵下,觀眾的意識形態被積極昂揚的斗志主導,并且重復建構著集體記憶。
女排隊員的隊服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讓其與其他人區分開的標記,《沙鷗》中,正是沙鷗在跟其他隊員一起量體準備裁衣做出國比賽新隊服的時候,發現自己沒有在國家隊的正式出戰名單上,憤而出走;在她退役后,她默默收拾行李離開國家隊,疊衣服時也要將隊服胸前大大的“中國”兩字露在最外面。《奪冠》中,剛來到女排訓練場地的陳忠和始終認為自己是短期借調來國家隊的,所以一直沒有穿上那身印有“中國”的隊服,而是穿印著“福建”的隊服;直到他真心認同自己也是國家隊的一分子之后,才心甘情愿地穿上了那身隊服。
《沙鷗》中,沙鷗一直在積極備戰中國隊對日本隊的比賽,日夜訓練,在第一次得知自己因為身體原因可能再也上不了場時,面對教練、隊友、隊醫、母親等眾人的勸說,她斬釘截鐵地說:“我愿意用我的一生來打這場球!”在備戰時,所有的女排隊員一起看中國乒乓球隊已經獲得世界冠軍的宣傳片,女排隊員們激動地說,“誰不想拿冠軍,就不是好運動員!”沙鷗在自己的賽場失利之后,自己一個人默默地到圓明園的廢墟中,在代表了中國受壓迫和苦難的斷壁殘垣旁,隨著樹葉吹動的沙沙聲,排球比賽時觀眾的歡呼聲又出現在她耳畔,而且越來越大。沙鷗的母親雖然對沙鷗堅持打排球不太支持,甚至到訓練基地請求教練,不要再讓沙鷗參加訓練。但是在給沙鷗準備禮物的時候,仍然親手給沙鷗縫了一個風扇套,圖案是排球躍過球網。這些比賽場外的日常表述和交流同樣解釋著奪冠這一時代神話的象征意義。電影巧妙和隱秘地打造了一個富有20世紀80年代氣息的影像時空,經由“真實—影像—擬像”的符號系統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儀式空間,觀眾對女排運動和奪冠的想象得到了合理化的語境保障。重復再現節日慶典景觀,讓所有人都成為儀式的參與者,構建這種萬人空巷的觀看儀式場景。共同的吶喊和助威,創造了相同的集體記憶,激活了觀眾的共同情感和集體認同感。
四、女排電影能為現在的我們帶來什么
約翰·費斯克曾說,體育“是一個儀式化的行為”,特奧多·阿多諾也曾說過,體育不是游戲,而是儀式。女排電影將觀眾們帶入了一個共同參與、體驗、建構的“儀式”中,觀眾在這場“儀式”中產生了一種虛擬的互動與交往,從而建構起共同的集體記憶,讓大家對那個特殊時代的熱情重新點燃。
這些女排電影,通過蒙太奇話語形塑的敘事儀式系統還原歷史的原貌,重溫那些具有歷史標志性的體育事件,運用這種敘事儀式進行自我言說、自我營銷與自我傳播,建構國家形象,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轉化為國家想象話語生產的權威意義的內在動力。對中國來說,女排不僅是體育題材電影,它是“國家與民族性影像”,具有濃厚的國家、民族性特征,它寫中國,寫集體的記憶,映射了改革開放以來時代的變遷,電影中文化符號的不斷重現,不僅增強了觀眾的族群認同感,還強化了中國體育文化的代際延續,展示了一個國家的文化特征,是構建族群想象共同體的工具。女排電影立足于鏡像儀式和文化符號來表現中國女排的歷史,不吝于用宏大史詩塑造民族吶喊和英雄群像,頌揚進取精神,最后終于匯成了中國女排——無與倫比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