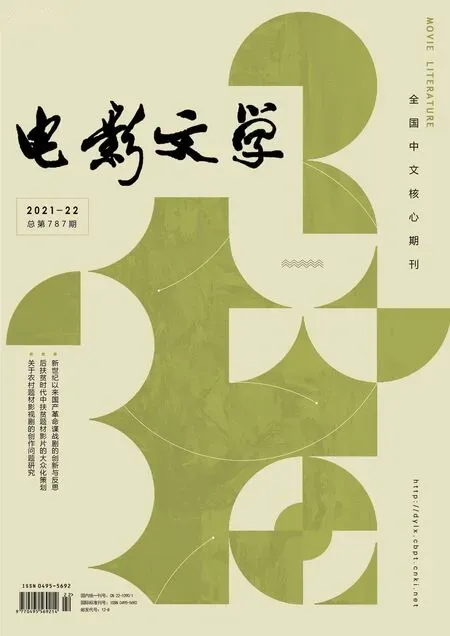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的“愛情敘述”
黃亞利
(北京城市學院國際文化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094)
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在中國電影中有著突出的地位,至新中國建立和改革開放以來,留下了一大批經典電影,同時無論在內容和還是在形式上,也形成了一套與好萊塢及其他國家電影截然不同的敘事模式和表達手法。
愛情在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有著特殊的位置,在這其中愛情所指向的既是個人的愛欲也是社會的理想,既是精神的也是文化的。革命與愛情在某種層面上似乎具有共通性,愛情是“本我”的表現形式之一,指向感性、體驗、浪漫和溫情;革命則是“超我”的重要體現,它指向的是理性、信念、崇高和壯烈。在特殊語境下,愛情則被賦予改革現實的使命,“愛情被看成一種情感威力,內化了社會改革的沖動;那么愛欲或可視為一種生命能量,足以推動終極的革命之輪”,當革命與愛情結合,生命的本能和超越理想在某一時刻重合置換,愛情為人的心靈提供棲息的場所,革命則為理想開拓生命超越的道路。
一、革命與愛情的敘述母題
革命和愛情的結合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的“革命文學”時期,“革命加戀愛”的寫作模式在當時蔚然成風,其中代表人物是蔣光慈。在當時那樣一個波濤洶涌的年代,文學不僅被看作是一種政治行為,也被看作是“情感教育”的媒介。茅盾將當時這一“時髦”敘述模式概括為三種公式:“沖突”公式——革命事業與浪漫情欲之間的“沖突”,小說中的角色往往會為了革命大局為重而放棄兒女私情;“互惠”公式——革命是愛情的誘因,愛情促進革命進步,革命成為影響戀愛成敗的重要因素,戀愛中的男女同心協力共赴革命;“革命至上”公式——革命已經不再是青年男女追求愛情的條件,革命就是愛情。因為時局關系以及左右派政見差異,這種模式在當時也確實引起不少爭論。盡管如此,革命加戀愛卻深深地影響了革命文學以及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范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革命浪漫主義的提出和發展,革命與戀愛的模式再次被重視起來,如電影《青春之歌》則將林道靜追隨革命的理想嫁接在三個具有不同政治理想的男人身上,對于革命的理解和實踐成為影響林道靜愛情選擇最為重要的元素。
改革開放后,革命與愛情這一模式同樣延續在革命歷史電影中。如電影《歸心似箭》講述了抗聯戰士魏德勝在一次戰斗中身負重傷又與部隊失聯,后被寡婦玉貞救起照顧,二人在日常相處中漸生情愫的故事。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大眾對于類型范式審美的習慣性定向解讀逐漸成立與加強,“傳統”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已無法繼續滿足觀眾對于人性考量與社會反思的需要,就在影像與觀眾之間對于“類型”的契約即將破碎之際,一些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在內容和形式上另辟蹊徑,以不斷建構起來的“新”的特質為牽引,拓展了革命形態在內容和形式上的呈現。“愛情”注入“革命”,開發了獨特的“紅色愛情”敘述模式。如電影《紅色戀人》講述了共產黨員靳在革命戰爭中受傷,向往革命的秋秋臨危受命扮演靳的妻子掩護他去接受治療,二人同樣是在患難中將真心托付給彼此,最后靳為了救秋秋被特務機構殺害。《黃河絕戀》講述了美國飛行員歐文在飛行途中被日軍戰艦擊落,迫降在中國黃河邊緣地區,組織特派女衛生員安潔和黑子護送飛行員到革命區。一路上他們歷經波折,他們一行幾人還因為敵人的步步緊逼,而被迫跳入黃河,歐文與安潔在患難中互生情愫,然而安潔為了讓歐文和黑子的孩子繼續存活下去,最終犧牲了自己。她用生命和歐文在波濤洶涌的壺口瀑布前上演了一出可歌可泣的愛情悲劇。
進入21世紀后,在市場化和引進大片的沖擊下,創作者意識到觀眾的重要性,積極尋求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變革之路。例如《云水謠》用個人情感為觀眾講述了一件民族事件,借男女的相思相戀和相守隱喻出歷史浪潮中的國家起伏,那橫跨60年、涉及海峽兩岸的摯情感動了每一位觀眾,也將那一代人的思緒牽引回了當時年代。《秋之白華》講述了革命戰士瞿秋白和楊之華之間的革命愛情,兩人從相識相知、相互扶持,是愛情的牽引也是革命的支撐。這些電影將革命故事和愛情故事交融在一起,把個人的命運、家的命運、國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從點點滴滴的生活細節中表現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堅貞與執著、高尚的情操和人格魅力。革命和愛情運作的成功也為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市場化轉型奠定了基礎,使得主旋律電影類型化創作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二、革命與愛情的敘述公式
參照茅盾對“革命加戀愛”的“沖突”“互惠”“革命至上”三種公式的概括,我們發現當下此類電影中在具體表述上仍舊具有一定的可適性和延續性。《歸心似箭》中魏德勝為了“找隊伍”回到革命組織中去,最后還是忍痛離開了玉貞,為了革命放棄了兒女私情。《紅色戀人》中秋秋與靳因革命而走向愛的結合。《秋之白華》中楊之華愛上瞿秋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瞿秋白的革命覺醒和他投身社會改革的革命信仰,最后瞿秋白毅然為了革命獻身,與愛人生死兩別。不過,不同于20世紀20年代文學中革命與戀愛的搖擺關系,這些電影中的革命與愛情則是互為忠誠的關系,“獻身革命即獻身愛情”。
在《紅色戀人》《紅河谷》《黃河絕戀》《云水謠》等影片中,愛情才是嚴格意義上的主角,革命與愛情不再是對抗的,而是相生相伴的,甚至“愛情決定了革命”。《紅色戀人》中盡管靳和秋秋是因為革命才走到一起,但秋秋的愛是針對靳這個個體本身的,而并非其作為革命者的光芒。即便靳難以忘懷自己的革命愛人安霞,但他與安霞的關系也是先愛情而后革命:“直到她死,我才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最后,為了救秋秋,為了他的愛人,他選擇站出來將自己交到特務機構手里,直至犧牲,是“愛情決定了革命”又是“愛情戰勝了革命”。電影《黃河絕戀》在表現安潔的犧牲時,導演沒有讓這一場景發生在戰場上而是在湍急的黃河水中,安潔中槍后為了不拖累歐文,而剪斷繩子沉入水底,把生命希望讓給了她所愛的人。在這兩部電影中,革命和愛情是統一戰線的,甚至是一體的,既是為了革命也是為了愛情,他們為了信仰而戰,為了愛情而死,表現出愛情和信仰同樣可貴,這在革命+愛情的模式中成為一個突破點,也深深地影響著后期關于革命和愛情的表達。
但是,這些電影又不約而同地都表現了愛情的“分離”、愛情的“悲情”。正如電影中儀式化情境的使用,“英雄受難”是革命者一般會經受的一個考驗,與愛人的分離不管是來自主動還是被動,革命者都承受了與愛人分離的痛苦。《南昌起義》中的雙喜和黑姑是一對令人艷羨的革命夫妻,南昌起義當晚雙喜不幸陣亡,黑姑忍受著愛人離去的痛苦接過雙喜手中的紅旗繼續沖到戰斗中去,將痛苦化為革命的動力。《建軍大業》中毛澤東同志多年輾轉于不同地方進行革命運動,每次與妻子孩子的分離都是一次心靈上的煎熬。結合革命與戀愛的互文關系,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這一表現,一方面,在革命與愛情的敘述公式里,革命者為了革命大義舍棄個人愛欲,將個人的愛升華至對真善美的愛,對家庭、對社會、對民族的愛;另一方面,心靈受難的儀式過程中,鍛煉并彰顯著革命者更為堅定,以公共福祉為重的革命理想。愛情的行為因此轉變為社會化的意識形態產生意義,而延續了它存在的必然性。
三、革命與愛情敘述的延續和變奏
電影始終是文化的構造物,相信這種觀點今天來看已經沒有任何異議,它的生產與接受最終會指向與時代背景相應的文化語境。盡管革命與愛情的公式是延續的,但在語境上卻有著潛移默化的變化,這不僅包括外在語境,也包括內在語境的變化。
一方面,新時期之前的此類電影中,革命是絕對主體,愛情依附于革命,成為突出革命、證明革命的一個途徑,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靜之所以放棄于文澤而追隨盧嘉川、江華的直接原因即體現在他們身上的“革命”信仰,他們作為老師、朋友引導著林道靜在思想上的啟迪和價值追尋。事實上,影片中沒有明確地表明他們之間的“戀愛”關系,這是因為“十七年”革命電影中的愛情直接或間接化身為革命情感和階級情感,其中兩性私密的內涵被隱匿起來。新時期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大眾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影響下,人性、情感等人的特質被認同,如果說以往是在革命主題中加入愛情敘事,那現在則是愛情主題中加入革命敘事,愛情的敘述逐漸越過革命成為主體,革命則作為某種元素襯托愛情,愛情中的情欲特質則重新回到銀幕上宣誓著她的主流性。如電影《紅色戀人》《云水謠》《秋之白華》的主角是愛情而并非革命。《云水謠》實際上已然是一部標準的愛情類型電影,在傳統的三角戀關系中融合疊加了革命歷史、戰爭、風光片等類型電影的重要元素,形成一種新式的“革命題材”愛情電影。
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內部語境上的延續和變化。在以往的革命與愛情的敘述中,二者最突出的關系是“沖突”,“戀愛妨礙革命”或者“革命決定了戀愛”,即以革命與戀愛的沖突和決斷,表現為革命犧牲或斬除個人愛欲的阻礙,帶有強烈的為集體舍棄個體的社會屬性。新時期以來的諸多革命歷史電影中的革命與愛情不再是沖突的,而是相生相伴的,甚至“愛情至上”。電影《云水謠》至始至終都在講愛情的堅守和尋找,愛是人物動機的源動力,愛情才是電影中故事情節發展的動力,也是影片的意義所在。革命和愛情是統一戰線的,甚至是一體的,既是為了革命也是為了愛情。
四、革命與愛情敘述的現實語境
革命與愛情放置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創作者在主流意識形態范圍內創作的慣性和規約。同時隨著時代語境的轉變,當下電影的教育意義與娛樂意義在功能上發生了轉變,政治化的宣傳手法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即便是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也應當遵循美學原則,再加上當下的主要受眾群體是青年受眾,愛情敘事更為符合大眾的需求,也就促成了革命與愛情的敘事方式在延續中持續地變奏。
對于電影而言,青年觀眾是主要的受眾群體,愛情元素所具備的通俗特質有著天然的吸引力。要知道,此時的電影文化生態已然發生變化,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已然是不爭的事實,不同于此前八一、瀟湘、北影等國有電影制片廠對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集中生產,民營公司、國際團隊紛紛開始進駐到電影市場中去,參與著電影的生產,推動了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類型化。
那么為什么要在愛情中設置革命的背景?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創作者在主流意識形態范圍內創作的慣性和規約。革命所帶有的現代意識和社會性內涵,以期喚醒更多的年輕人銘記歷史,走出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鶯鶯燕燕中,去探索更有價值的人生意義。
電影《云水謠》即用“愛情”對主旋律電影進行了類型化的改造,將主流意識形態自然融入一個愛情故事中,將三個人的愛情故事放置在一個動蕩復雜的時代,愛情故事背后跨越了二二八事件、抗美援朝、隨軍援藏等歷史事件,跨越了臺灣、西藏等極具歷史意義的地方,“一面將主導意圖浪漫化,一面將情感傾訴現實化”,突破了以往主旋律電影意識形態濃厚的風格。電影在愛情類型的基礎上融合疊加了革命歷史、戰爭、風光片等類型電影的重要元素,形成一種新式的“革命題材”愛情電影。類型元素的轉換、更迭,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影片的敘事和視聽,滿足了大眾文化下的觀眾口味,革命背景的加入也延展了愛情電影的歷史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