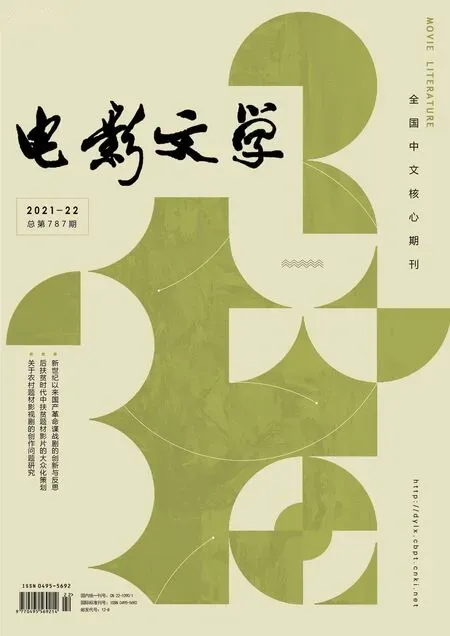隱喻中國的路徑
——當代藝術電影“中國空間”敘事研究
黃 燦
(長沙學院影視藝術與文化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22)
新世紀以來,中國藝術電影進入多元發展的軌道。伴隨著21世紀初多項電影產業改革政策帶來的產業化加速,藝術電影告別了第四代、第五代導演辨識性強的代際特征。注資方式的多元化,讓創作者能有更自由的視野關注中國當下的現實,審美表現上由單一化向雜糅化發展。
而當下中國現代化進程呈現出驚人的豐富性。一種總體性的歷史元敘事已不復存在,在這種元敘事中,對歷史的思辨占據壓倒性優勢,歷時性特征(時間敘事)大于共時性特征(空間敘事)。不妨對比第四代導演吳貽弓《巴山夜雨》與“新生代導演”楊超《長江圖》,兩部優秀作品同樣發生在長江上,但前者對空間的呈現只不過是作為一種歷史“傷痕”與“反思”的背景,并未特別凸顯,后者卻將長江通過隱喻人格化,以“這是我的長江”為題眼,探討歷史文化與個人記憶在真實空間和精神空間中的融合。
這種區別具有某種代表性。從畢贛“走不出的凱里”,到張猛對于廢墟的迷戀,從李睿珺對西北故鄉的反復吟哦,到張大磊對國企大廠的細繪精描,在當代藝術電影中,對某種地方性空間的關注,已成為普遍性趨勢。段義孚在分析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這一組詞匯時指出:“空間比地方更為抽象,最初無差異的空間會變成我們熟識且賦予其價值的地方。”顯然,出現在當代藝術電影中的影像空間,是對具體而微的“中國”的自我賦值,而這些獨立而又隱然聯系的空間影像,像完成拼圖一樣,正在逐漸形成當代“中國空間”的影像表達。
這樣的影像時空體,較之文學時空體有明顯的區別。在文學中,時空體里的主導因素是時間,正如巴赫金所言:“時間的標志要展現在空間里,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和衡量。”而在當代藝術電影的“中國空間”敘事中,空間要素往往占據優勢,并通過詩性隱喻,構成了時間呈現的基礎。如在藝術電影導演青睞的“工廠電影”中,煙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圍繞煙囪的“立”與“拆”,國企改革、大廠轉型倒閉的時代背景被鮮明地呈現出來,這在《少年巴比倫》《鋼的琴》《暴雪將至》等電影中有同構性的表現。畢贛在《路邊野餐》《世界上最后的夜晚》中,更是將場景的切換,作為時間(記憶)轉換的唯一依據,通過轉場漸漸回溯到記憶深處。比較《陽光燦爛的日子》這樣的經典作品,當代藝術電影的敘事重心,由“具有空間形式的時間敘事”,過渡到“具有時間因素的空間敘事”。這些由空間結構時間的影像時空體,因為同時并置了“自然/城市”“回憶/當下”“神話/現實”的不同意義,因而具有鮮明的隱喻性,構成當代想象中國的三個烏托邦:自然烏托邦、記憶烏托邦和神話烏托邦。
一、自然烏托邦:現代生活的對照物
對自然烏托邦的找尋源于一種哲學上的重建:重建人與空間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藝術電影中,這種重建的主體很少聚焦于都市人,而多選擇鄉野之民。藝術電影“求諸野”,把目光一次次投向中國邊疆自然,在對自然一次次的融入和審視中,將其塑造為與現代生活對立的烏托邦。
對都市主體的不信任暗含了自然烏托邦主題下的兩個分支:“闖入”與“歸家”。
對于近乎于無人區的荒野而言,都市人是闖入者,這一身份不會因為其對自然的“青睞”而改變。人希望借助于自然找尋存在的真意,恰恰證明在現代社會多元結構不斷規訓和詢喚下,人再難確證自我的身份。闖入者的主觀愿望,與自在存在的自然之間,存在著不可彌合的張力。以《七十七天》(趙漢唐,2017)為例,這一旨在還原探險作家楊松柳77天孤身穿越羌塘無人區壯舉的電影,請來李屏賓作為攝影指導實景拍攝,完美還原了青藏高原無人區的壯美與殘酷。但微妙的是,導演本人雖然是戶外探險的愛好者,卻對于“荒野生存”的單一主題并不自信,于是虛構了主人公與女孩“藍天”的感情線,這一條感情線貫穿全片始終,用男女之情平衡生死之事,卻破壞了人與自然對峙、自省的結構性平衡。
《七十七天》引發的爭議,讓我們看到處理都市主體向自然烏托邦尋求拯救主題的困難。作為闖入者,如何拋掉浮泛的拯救論,建立一種更加真實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既是對自然空間的尊重,也是對影像邏輯的尊重。在這方面,《荒野生存》(西恩·潘,2007)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電影并未切斷主人公現代生活的根脈,而是將其追根溯源,慢慢呈現他對于現代生活的抵抗和放棄,逐漸融入荒野,整個過程完整、舒緩而自然,帶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只有當都市主體選擇融入自然而非單純征服自然時,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達成平衡,“空間并不是人的對立面。它既不是外在的對象,也不是內在的經驗”。如此,我們才能擺脫奇觀影像的控制,而將思考更深入地延及人與自然空間的共生共存關系中去。
與“闖入者”相比,“歸家者”的空間敘事受到更多關注。有論者指出:“自然景觀是我國電影對外傳播中標志性的‘在地性’文化符號之一。”進一步分析,自然景觀分為“非人化自然”(如《七十七天》中呈現的無人區)和“人化自然”。在當代藝術電影中,人與自然最重要的關系,是自然作為可棲居的“家”帶給人的心靈感受,以及這種感受的失去與復得。
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無家感”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性體驗,“現代個體在極具差異、經常充滿矛盾的不同社會語境之間游走不定。從生活經歷來看,個體在一系列迥然不同的社會世界之間漂泊。越來越多的個體脫離原有的社會環境;可是沒有新的環境取而代之,成為他們真正的‘家’”。對于廣袤的中國西部地區而言,“家”的感受是與前現代生產方式及其伴生的文化土壤密切結合的。現代性/前現代性的沖突,直接導致了“家”的無處安放,以及“落后但淳樸”與“現代但無根”的二元對立。《塔洛》(萬瑪才旦,2015)與《米花之味》(鵬飛,2017)便是個中代表。
這兩部電影鮮明地呈現了空間上的對立:藏區城市與荒野,上海與云南邊境傣族村寨。對于塔洛而言,兩個世界的交錯讓他義無反顧地“離家”,發現被騙后想“歸家”又不可得,如同出故障的摩托車一樣,拋錨在現代與前現代的旅途中間,進退兩難。在片中,現代生活空間不僅包括小縣城的理發館、KTV,還包括拉薩、北京甚至紐約的一系列想象性能指。而塔洛生活多年的自然環境則粗獷、封閉、靜默,是收音機中播放的“拉伊”(藏族民歌),通過加之于現代生活的古典愛情想象,勾連了兩個世界,也打破了“家”的完整與寧靜。
片尾塔洛的自殘反映了這種對立的尖銳和殘酷,這或許與他多年的獨居生活有關。在《米花之味》中,自然空間具有更多的包容和治愈功能。主人公葉喃雖然從上海返回云南故鄉,也并未放棄現代生活帶給她的理性態度。事實上,與利用故鄉對現代生活進行一味批判相比,《米花之味》中的自然空間可能更貼近中國的現實:即便是在彩云之南風景絕美的竹寨,網吧、手機、機場這些現代性特征,也構成了不可拒絕的要素。現代性與前現代性的混雜,構成了當代自然烏托邦的重要特質。也正因為如此,一種比傳統少數民族電影更為復雜和微妙的空間出現了,葉喃見女兒楠杭晚上不睡覺,“蹭”神廟的Wi-Fi玩游戲,一氣之下關掉Wi-Fi,并說 “佛祖要睡覺了”。“佛祖”和Wi-Fi信號,在這一空間中構成了兩個不可見的在場,共同作用于這一空間內,對立又共享著當代中國的“原生態”村莊。
《塔洛》和《米花之味》為我們提供了當代藝術電影中自然烏托邦“何以為家”的兩種思考:一種是現代空間與傳統自然的極端對立,一種是對立與融合共生。而大部分自然烏托邦敘事都介于兩者之間。如《岡仁波齊》中,朝圣隊伍在路旁扎營,我們既能看到雄渾原始的高原雪山,也能看到蜿蜒的公路如臂膀環繞著他們的帳篷,載重卡車不斷隆隆駛過。少數民族電影兩大經典主題“香格里拉”(未受污染的世外桃源對現代人進行精神反哺)和“最后的草原”(文化留守者悲壯的最后抵抗)固然在自然烏托邦敘事中還時有呈現,但單獨構成全片的主題,已不太現實。更多空間上的思考,源于現代社會與自然世界的融合,以及在這一融合過程中,如何尋求自我的存在之路。
二、記憶烏托邦:重建記憶之墟
現代性進程帶來的“無家感”并非僅限于地緣問題,“尋找逝去的時間”同樣是其重要主題。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進入懷舊潮,老中青導演們紛紛將目光投注過去的時光,而是懷舊90年代、80年代、70年代抑或60年代則因人而異。這一現象耐人尋味,正如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言:“在個人那里,回憶的過程往往是隨機發生的,服從心理機制的一般規則,而在集體和制度性的層面上,這些過程會受到一個有目的的回憶政策或曰以往政策的控制。”從集體懷舊的角度而言,懷舊潮暗合了對現代社會加速發展的不安,對動蕩不居的現代生活中迷失的個人身份的找尋,這種集體無意識在當代藝術電影中被進一步強化,其具體表現方式為,記憶敘事與空間敘事結合構成敘事閉環,形成一個包含著時間因素與空間因素的獨特的記憶時空體。
之所以說這一記憶時空體具有敘事閉合性,是因為這一影像空間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都有明確的邊界,時間和空間的區隔性特征非常明顯。以過去十年來頻出佳作的工廠電影為例,時間上都聚焦于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工人下崗那段時期,空間上則囿于工廠內部。國企工廠“小社會”統管統包的獨有特性,讓影片中的工廠空間具有一種“母胎”隱喻,即所有人物都為工廠容納,又面臨著“脫離母胎”的“出”與“不出”的詰問。在《暴雪將至》(董越,2017)中,多雨陰郁的國營大廠,與主人公余國偉郁火灼心的內心高度同構了。他雖然一直想上調離開工廠,但最后行兇的過程中,他的身影在廠房、管道的映襯下,與追尋的兇手無異。空間,成了人物心魔外化的表征,空間與人血肉相連的依存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與之相比,另一批人則是“出”后渴望再回到“母胎”。《鋼的琴》之所以被認為是時代的挽歌,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下崗工人去而復返的車間廢墟,營造了一個死而復生的“虛假的輝煌”。廢棄的工廠仿佛有某種魔力,召喚著離去的工人們又回到母親的懷抱,熱火朝天回味曾經“共和國長子”的榮譽。這種喜中帶悲的意味,恰似片頭喜樂送葬的祭奠場景。工廠,不僅是一個物理空間,也是身份空間、記憶空間、價值空間,它幾乎賦予了在其中的人們所有社會人應有的文化意義。因而,在剝離這一空間時,失去身份、混亂記憶、抹消價值造成的精神動蕩,便融入一代中國人的無意識,以一種創傷代償的方式,不斷重現出來。
當我們通過“母胎”隱喻討論空間的性別特征時,不應忽視工廠空間“父性”隱喻的一面。如前所述,很多工廠電影都出現了炸毀煙囪的影像,這絕非巧合。煙囪,作為工廠生產力的直接象征,是一個明顯的陽物能指,這與工人階級男性氣質的一面也是吻合的。對煙囪的拆解,工廠失去生產能力,背后亦隱藏著作為男性的閹割焦慮。而同樣不謀而合的是,這幾部電影(《少年巴比倫》《鋼的琴》《暴雪將至》)伴隨著拆除煙囪,主人公都出現了性的困境:路小路失去了自己的欲望對象白蘭,陳桂林結束了與情人淑嫻的幽會生活,余國偉一次次拒絕了燕子的求歡,男性失去性別特征在現實和隱喻層面雙重發生,人物與空間的命運再一次同構了。
無論是母胎隱喻還是閹割恐懼,通過隱喻,影像空間與人的互相浸潤都達到了最大,這在傳統的工廠題材電影中是不常見的。我們注意到影像空間在記憶隱喻的作用下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形,這種變形是通過意義的層層累加實現的。一種齊澤克所言的“視差”(parallax)現象,即因觀測位置變化而造成的客體錯位,發生在這些影像空間中,“建筑學中的視差間隙意味著,如果不征用時間維度,建筑的空間位置就無法得到理解:當我們接近并走入一棟建筑時,視差間隙是我們變化著的時間經驗的印記”。隨著時間的流逝,觀察過去事件的傾角也在變化,來自事件本身的真實感受逐漸為一種震蕩體驗后的代償性懷舊情緒所籠罩,新的“記憶的邏輯”逐漸升起:在記憶之墟中,事件不是用來再經歷一次,而是通過變形,完成對人生傷痛的撫慰。
在這條道路上,畢贛走得更遠。《路邊野餐》中的凱里,是一個四重空間的疊合,它既是地理的、影像的空間,也是隱喻的和現象學的空間。凱里首先是一個地理名詞,少女洋洋背誦的導游詞這樣介紹凱里:“凱里東接臺江雷山兩縣,南臨麻江丹寨兩縣,西接福泉縣,北接黃平縣,地理位置在東經107°40′58″至108°12′9″。”凱里雖然在中國地圖的西南部,但卻是黔東南州的州府,也是片中所提鎮遠縣的相對“中心”(所以才會有洋洋在蕩麥矜持地說自己是凱里人一說),并與鎮遠縣、蕩麥村構成了一個由中心至邊緣層級拓展的地理輻射圈。
影像空間與隱喻空間融合在一起。在片中,當陳升開始讀詩,鏡頭中出現凱里的城市遠景,一個被群山環繞的西南小城。這一構圖兼具了封閉性(被環抱的城市)和開放性(延伸至遠方的群山)的雙重屬性,與詩意隱然呼應。陳升的旅程,是從記憶開始,要經由夢境一般的追尋,從記憶之外的現實再找尋回記憶空間的入口。這也是為何故事的后半段發生在蕩麥,英文片名卻叫Kaili
Blues
的原因,因為陳升的記憶被禁錮在凱里,這也就是一個充滿著“凱里性”的“凱里往事”。這種凱里性,源于詩性主體觀照下,凱里人遠離現代都市生活,卻飽含現代性的一種生存狀態——這些與地方性密切聯系的、飽滿的主體,不知如何對抗命運,卻也從未順從,山水雖遠,人心更大,在貴州幽綠的背景中,時時綻放出灼眼的主體性光華。這種強烈鮮明又未被現代生活異化的主體意識,讓“凱里”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地理名詞,它成為承載“凱里人”的永恒空間。也正因為如此,人物無法左右命運,卻不能忘懷,于是在記憶的交叉小徑中,時時墜入名為“凱里”的夢境。《路邊野餐》雖然是一部關于記憶的電影,但時間因素并不重要,時間是用空間的組合來表達的。去鎮遠、蕩麥,實際上去的是另一處時間打撈往事。要理解這一點,最重要的是要明白,陳升是用詩歌的方式來記憶的。詩歌的隱喻,是一種共時性的替換關系,而非歷時性的組合關系。對他來說,時間并未按照正常狀態前行,而是不斷圍繞“追憶/尋找妻子”內部循環。他無法走出這一時間的閉環,而只能用不斷隱喻替換的方式,通過空間的變換,一次次回到這個主題。這其中,陳升對于詩的理解和畢贛對于詩的理解交疊起來了,我們便不難理解畢贛長鏡頭的意義:通過對空間的極致呈現,讓凱里和“像凱里”的蕩麥成為同一主題的“替換項”,讓時間摧毀、重建、回歸,在不同的空間中,建構出歸屬于同一隱喻的,可以延伸至無窮開闊的現象學空間。這或許是當代中國藝術電影創作中,對于空間問題最為藝術和深刻的認知。
三、神話烏托邦:祛魅與復魅的超驗空間
當代中國藝術電影面臨的空間危機在于,理性主導的中國都市現代生活空間已經高度祛魅了。在高速發展的社會現實中,工具理性的擴張不可避免地帶來一系列“現代性疏離”:人與自然的疏離、人與社會的疏離、人與人的疏離、身與心的疏離、目的與手段的疏離。如果說在《蘇州河》(婁燁,2000)的時代,城市還能依托河流創造普通人的傳奇故事,那么到了《推拿》(婁燁,2014)時,只能把目光更多投注于現實生活之外的“城市異托邦”(盲人推拿院)。同樣的困難也擺在張猛導演面前。在《鋼的琴》(2010)獲得成功后,《陽臺上》(2019)聚焦當代上海城區拆遷工程,面臨著幾無故事可講的困境。“無事可述”當然不是情節空白,而在于被理性化的都市生活宰制的當代青年,已經褪去了理想的人性光芒,只能在卑瑣的些微欲望中茍且度日。
不得不說,為了抵抗空間祛魅,當代藝術電影做出了不斷的努力,并塑造了一系列復魅的空間譜系。從時間向度上而言,“復魅”既指向過去,又指向未來,對應的是前現代性復魅和后現代性復魅。在未來加速逼近的當代世界,技術逐漸趕上甚至超越了后現代性想象,因而,“賽博空間”(Cyberspace)成為最重要的后現代性復魅空間,這在科幻電影中最為常見,少數科幻電影甚至突破了類型片的藩籬,探討真實的邊界、理性的極限和人的存在等更為深刻的問題(如丹尼斯·維倫紐瓦執導的《銀翼殺手2049》)。但在中國藝術電影的視域中,還暫未展開對未來的眺望,而采取了“求諸史”與“求諸野”相結合的方式。
姜文在《邪不壓正》中重建了一個虛實相交的北平城。片中真切還原了20世紀30年代北平正陽門、內務部街、東交民巷、協和醫院等景觀,又浪漫而荒誕地塑造了“屋頂空間”。這一片連綿不絕的瓦屋頂,構成了李天然來去縱橫的自由天地,是他性靈情感盡情揮灑的空間,也構成了一種虛指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的隱喻。地面世界與屋頂世界的雙重建構,使故事的邏輯在理性和感性之間交錯展開。一種細膩而曠遠的感受,如同逝去的老北平的“靈韻”,在自由的屋頂世界慢慢升起。姜文的“任性”在于他總是希望在歷史與現實的感受之間,尋求一種關于人的“當代神話”,一種超越了人“是如此”而走向“應如此”的夢的世界。令人驚訝的是,這一精神烏托邦以一種“外化”的方式從現實世界中割裂出來,人物的臺詞密集,表演刻意,毫無掩飾,如漂浮的能指對空間進行二次注解,仿佛屋頂世界只是表演的舞臺或畫布。這種帶有鮮明作者性的空間“外化”方式,也構成了人們毀譽《邪不壓正》的共同理由。
另外一些導演則選擇了更為自然的“內化”的方式來勾勒神話烏托邦。李睿珺在《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中構筑了逼真寫實的西北農村,但全片一直在尋找現實之外的超驗空間。白鶴象征著傳統文化(神話故事)對現代進程的抵抗,它所表征的神話空間大概也是爺爺這些現代性進程中落伍者的最后歸宿。這一神話空間究竟是否存在于片中呢?導演非常巧妙地將之放于現實空間“背后”,即它一直在被爺爺找尋,而從未現身。
相較于其他類型的影像空間,神話烏托邦的呈現方式非常見功力。在片中,白鶴從未出現,但卻符號化地“在場”,出現在棺材漆畫和動畫片里。作為一個提示符,“白鶴”指引著觀眾順著爺爺的視角,去觀看和尋找神圣化的空間。在這一過程中,有一個現實空間入侵神圣空間的事件,即割槽子湖(割水草)。槽子湖是爺爺心中仙鶴棲居地,但在割湖的過程中卻被割刈一空。導演將攝影機放在泡沫板上,人在水中推著泡沫板滑行,提供了一個貼著湖面飄蕩的低視角影像,仿佛白鶴的靈魂在巡游。這一現代性進程中“祛魅”(鏡頭內容)與“復魅”(拍攝方式)交錯的空間,因而也具有一種激烈雄渾又瑰奇神秘的美感,構成一個經驗與超驗疊合共在,人與神話共存的影像空間。
如同自然烏托邦一樣,一般而言,神話烏托邦是作為現代性進程的對立面出現的,因而往往會有一個明顯的空間上的二元對立。但《長江圖》是一個例外。楊超導演極具野心地將整個長江流域人格化并高度復魅了,這一神話空間的廣度和深度,是其他一些藝術電影難以比擬的。在片中,貨輪“廣德號”逆流而上,循著詩集《長江圖》的指引,開始了追溯回憶和文化尋根的雙重旅程。這一過程,是現實空間、詩歌空間和神話(傳說)空間互相纏繞裹挾向前的。
雖然題材魔幻,但細節卻很“實”。實景實拍,膠片拍攝,對于船艙內外的明暗質感和江面空氣的層次質感有上佳的表現力。寫實主義風格的影像實際上拉遠了經驗世界與超驗世界的距離,也即影像風格和敘事主題之間的張力被拉到最大。在珍珠串線般的故事中,每一個具體空間都是實在的,但合在一起,非實在性會慢慢積累,即安陸在《長江圖》提及的每一個地點現身,并逐漸變得年輕,這件事情是建立在堅實的實在性上的神話,不容置疑。而到了真正點題的時刻,安陸在江邊看著“廣德號”從遠處駛過,大聲叫喊著“這是我的長江”,轉身在江灘上跳起了房子,腳下沙地為稿,刻寫著屈原的《天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在這一空間中,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合二為一,自然與人各自的屬性向對方分流,而詩歌空間悄然間由現代進入歷史。在對最古老傳統的召喚中,一種籠罩長江數千年的超驗感受默默降臨。這種超驗感受支撐著電影“影像”轉換為“心像”:船行宜昌三游澗,天色入暝,豎峰如屏,安陸并未現身,卻在崖間點燃火焰,如山鬼般在黑黢黢的群山間若隱若現。影像沉入中國人世世代代集體無意識的心像,影像空間的邊界漸漸模糊,并融入一個無窮廣袤深遠的神話世界。
作為影像復魅的表征,神話烏托邦建構了當代藝術電影文化尋根最堅實的底座。與傳統有所不同的是,當代神話的建立,是在形式自覺的基礎上,將個體的境遇和感受融入到超驗世界中去的。這種高度個人化的表達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載道傳統,而呈現出一種個人神話與歷史神話交織融合。
結 語
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在后現代思想的影響下,空間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誠如詹姆遜所言:“后現代主義是關于空間的,現代主義是關于時間的。”這一論斷固然不一定完全適用于中國,如對于現實中國來說,是在完成現代性進程中,前現代性、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互相雜糅,在不斷融合、沖突、交替的過程中前進的。但空間越來越成為當代影像關注的對象,卻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空間性表達,摒棄了空間/時間的二元對立,打破了“現代主義=時間性,后現代主義=空間性”的固有觀念,將對時間問題的思考,深深融入空間塑形中,也讓我們對影像“中國空間”的思考,進入更為復雜和細微的層面。
在對一種整體性歷史元敘事進行解構的同時,因為現代性進程而產生的空間落差,構成了當代藝術電影精彩紛呈、錯落有致的空間呈現。從整體上而言,當代藝術電影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品格,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的現代性進程及其后果”。對于列車般飛馳向前的現實而言,藝術電影往往會擷取一個時空片段,這一片段從空間上構成“地方/中心”的張力,從時間上構成“前現代/現代”的張力,完成“中國空間”的影像意義結構。
在這一視域下,自然烏托邦、記憶烏托邦和神話烏托邦,構成了影像中國空間的三個維度,它們共同構成了從自然環境、歷史記憶和神話體驗三個向度對“中國”的想象,以一種具體而微、多元共生、悲喜交織的方式,將各自隱喻中國的空間碎片,拼合成“當代影像中國”這一宏觀而具體的完整空間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