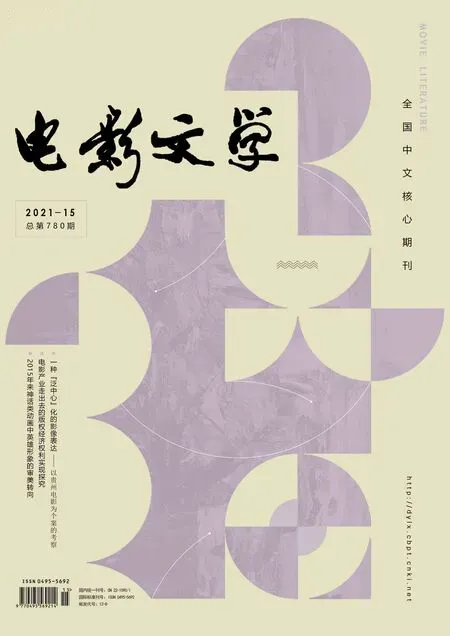一種“泛中心”化的影像表達
——以貴州電影為個案的考察
肖艷華 (貴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貴州 貴陽 550018)
近年來,貴州電影成了當下視覺文化傳播的熱點現象,從歷史的在場缺席,到當下的多維審視,貴州的實在空間與影像空間被不斷地賦予了多重意象的解讀。“依托貴州地理、文化、經濟背景,在中小成本類型電影和藝術電影的生產中佳作不斷。無疑,在高速發展、復雜多變的當下中國電影藝術、文化與工業版圖和‘工業美學’建構圖譜中,這一支中國電影的‘貴州新力量’,有著重要而獨特的意義。”與北上廣等現代性極其明顯的城市空間或其他中西部省域相比,貴州電影的生產實踐展現出了自我空間影像消費特征的美學意識,且極大地彰顯了貴州作為主體在電影作者屬性上的影像書寫。
在考察貴州電影生產的歷史時空中,戰爭特征代表的長征文化影像、少數民族身份書寫的傳統影像、藝術詩意邏輯運行的魔幻空間構筑,不同的影像特征并行使得貴州影像邏輯歸納以及中心影像難以確定。因此,“有必要考慮:并不存在中心,中心亦無自然的位置,它不是一種固定的點,而是一種作用,一種不定點”。借助德里達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視角,解構是一種對成規化法則否定的變革。這種變革性使得貴州電影對原有的影像結構框架有了“調節的轉換”,現有的影像類型與形式規則在貴州的影像符號實踐存在著明顯的“延異”表征,即差異性的鏡像生成:貴州電影的差異性不僅體現在影像符號層面上的差異,更指涉著這些影像符號差異形成的運動過程。差異形成之后的延緩運動使在場者的顯現,即貴州電影的生成,“無意識實質上并不是隱藏著的,潛在的‘自我—在場’;它使自身變化,并延遲自身,這無疑意味著差異的交織”。由此可見,任何影像符號意義都是延異中差異“蹤跡”的交互運動衍生的。
德里達的延異觀不僅使得傳統結構的中心化意識被質疑,在否定決定性、唯一性中心化的同時,相對性、主體間性多元中心點的視角對復雜事物的辨析有了更全面的意義探究。“泛中心”化正是基于“去中心”化的意識上,認為事物唯一的、顯著的中心點被多個并存的、且重要度均化的中心點所取代。正如利奧塔認為,后現代意識的集中表現在對于元敘事的懷疑,“確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敘事”的否定,是對于現實社會中權利、制度、生活方式行為等傳統認知的反認同。在貴州的影像思考中,其繁復在肯定與否定的矛盾之下,既定的影像法則成了無解的意象,由此“泛中心”化的意識成為思考其持續行進的重要路徑之一。
一、有意義的在場者:貴州電影“泛中心”化特征的生成
(一)歷史維度下影像出現的反本土化與去同一性
電影作為一種舶來品,它在中國的誕生與發展有著明顯的本土文化結合特征顯現。“藝術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現在可以更進一步,確切指出聯系原始因素與最后結果的全部環節。”電影的自覺性創作與本民族文化存在著極大的互通傾向,它以視聽符號形式“記錄與承載著各民族文化歷史的變遷,城市的空間展現也往往成為電影媒介中極其重要的民族文化書寫與象征”。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1905)誕生于北京,其與京劇相結合的形式有著明顯的北京傳統意象承載。20世紀20年代中國城市電影在上海掀起高潮,這亦與上海開放性的都市化特征難以剝離。反觀貴州影像的發展歷程,其電影作品的首次出現以及在不同時空中特征的顯現,均并非遵循這一傳統的電影實踐策略。貴州作為少數民族的形象主體是一種現實性的既定認知,但是在梳理貴州電影引發關注的節點時空軸時,卻呈現出了與本土違逆的表征,即并非以民族影像為原初的創作。
貴州電影的開山之作是《密電碼》(1936),這是一種戰爭類型的創作,而并非少數民族文化主體的影像書寫,而后以革命解放為主的戰爭影像表述成為貴州電影中一個極其重要的主旋律符號,也基本貫穿了整個貴州影史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第五代導演的美學隱喻崛起背景下,《良家婦女》(1985)借助女性主義視角透過貴州外化環境的封閉性與差異性,表達了深層次的悲劇意識。新世紀以來,貴州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良家婦女》的藝術風格與形式,還進一步注入了在貴州現代化極其不均衡體驗下的后現代意識,并一再地引發聚焦化。《尋槍》(2002)“選擇以整體隱喻的方式講述人性的異化的物戀悲劇,并以感性跳切的方式展現不無荒誕的生存幻象”。王小帥的“三線三部曲”《青紅》(2005)、《我11》(2012)、《闖入者》(2014),在貴州特殊的歷史在場身份之上,傳遞出了個體命運與社會時代的互文反思。《路邊野餐》(2015)的時空交錯、《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的夢境詩意,不僅在技術影像上新意迭出,且在傳統美學原則上做出了“陌生化”的闡釋。原初影像與關鍵影像的書寫在以往的電影發生上,與本土傳統文化的銜接是固化的習性,但在貴州空間卻出現了在場的脫離,尤其是藝術影像中的詩意邏輯運用在這并不具備開放性意識的空間上,衍生了與后現代最為接近的奇幻意象。
歷史時空的坐標系中,在貴州電影被不斷關注的節點上,戰爭與藝術成了兩個最主要的影像符號書寫,但這并不意味著貴州影像史上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的消隱。貴州少數民族電影從20世紀60年代逐漸拉開序幕,《秦娘美》(1960)與《蔓籮花》(1961)在中國電影史上都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秦娘美》與黔劇結合,演繹了傳統與創新的別樣民族表達:《蔓籮花》以苗族傳說為母題進行了極具神話意蘊的影像書寫。新世紀以后,貴州民族電影不僅在量上逐漸遞增,且在表達上呈現了立足于本土空間的內外視角思考,如貴州籍女導演丑丑的民族三部曲:《阿娜依》(2006)、《云上太陽》(2010)、《侗族大歌》(2017)在自我民族意識內化的主體性表達下,勾勒出了與外在世界存在強烈差異體驗感的心靈棲息地。而他者視角下寧敬武的《滾拉拉的槍》(2008)、《鳥巢》(2008)則介入了更多的外界力量,對貴州封閉的外化與心理空間做了突破界限的審視。
在貴州電影引發關注點的不同時空轉換中,戰爭影像的首創與藝術影像的更迭幻變成了貴州影像發生的特殊軌跡,同時又兼具著民族影像的重點與密集書寫。戰爭、民族、藝術成了貴州影像作為現實在場者的三個關鍵詞,而這三個關鍵詞在類型與風格的傳統判定中,卻又充滿矛盾性與相悖性。
(二)當下貴州影像作品維度取向的復雜性
電影的生產,被默認為是一種有跡可尋的規律式判定,如電影發展中類型化的形成、不同風格化的電影流派成型。人們往往習慣于通過已成型化的規則去理解與闡釋其他影像,但在貴州影像的差異實踐化下,傳統的中心結構變得界限模糊,甚至在意義空間上不斷延伸綿延,形成了多元化的影像在場者。貴州戰爭電影的持續創作,在革命歷史空間上延續著重大歷史事件題材選取的一致性,且進一步對貴州長征文化的傳播發揮了巨大的助力;囿于少數民族省域的社會形象,貴州民族電影的創作日漸密集,少數民族的身份形象也在民族影像的泛化表達中更趨明確;繼而又在藝術電影的特征中,貴州空間亦蔓生出了令人迷幻的詩意之美。基于內容表達的類型化、抑或是風格與受眾取向的商業與藝術涇渭分明,在成規化的電影理論與實踐界域里卻實難辨析與歸置貴州的電影內容與形式。
事物觀念的形成往往是主觀研究的意識中產生,再回歸到客觀中獲得絕對性。電影作為類型的存在就是電影理論視域中一種極為固化的觀念性的存在。類型是電影作品分類的一種主要方式,是電影內外情境中不同參與者達成共識的一種默契存在,“而重復在每部電影中出現的類型公式和慣例,給予了各個類型電影共用的識別規律”。類型的區別主要在于主題與情節模式化的影像實踐,但類型的觀念在貴州電影考察中無法獲得一致性。類型化的生產有書寫歷史革命事件的戰爭電影,也有展示少數民族文化的民族電影,這兩種類型構筑了貴州影像的兩個重要維度,即以內容為取向的戰爭類型與民族類型。但在以詩意為特征的藝術影像中,它的類型取向是缺失的,尤其是在當下,貴州詩意影像在內容上有著極度的自由表述,有紀錄影像下《四個春天》(2018)的日常生活思考美學、有攝取城鎮漫游者的《無名之輩》(2018)現代幻象,還有魔幻現實主義與夢境邏輯指引下的《路邊野餐》與《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迥異的平行時空顯現,這些詩意影像內容的交迭在傳統的影像規則下并未形成終極意義的推出,如何能延展出有效的意義在類型框架上失去了目標地。
即使繞開類型的規則,試圖在形式上仍然無法找到貴州影像統一的原則。形式往往與內容作為相對的概念所理解,但實質中,電影的形式也經常因內容的選取而發生變形。基于內容,形式指向電影的兩大組成部分,敘事與風格。尤其是在風格的形成上,風格模式不僅僅是作品的單一風格,也是導演的創作風格,在法國新浪潮的“作者論”中,風格的延續性常常是判斷一個導演作者色彩的標準之一,像侯孝賢的寫實、賈樟柯的超現實、畢贛的魔幻現實,或集體的風格,德國表現主義、蘇聯蒙太奇等。貴州電影中的詩意影像在藝術的維度里找到了形式與風格的明晰特征,但在戰爭與民族的維度中卻又脫離了形式與風格的定性。
或許我們可以理解為貴州電影是一種從類型走向形式風格的趨勢,但是這一走向性卻并非一元或二元的對應,尤其是在當下的時間的維度里,貴州影像類型與風格并存構筑了多重點的時空意象。如20世紀80年代的《四渡赤水》《奢香夫人》《良家婦女》三者并存的在場。即使在“畢贛現象”不斷引發熱議的當下,戰爭影像與民族影像并未消隱,反而流溢著更強化的類型影像生產,尤其是在2018年至2019年初,《迫降烏江》《無名之輩》《四個春天》《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引發的貴州電影熱潮中,戰爭、民族、藝術詩意同時交互映現,它們風格相距甚遠卻交互復現。
貴州電影的本土化、同一性被各種特征離散,絕對概念、無區別的差異已然被非常規性的邏輯所阻斷,形成了傳統結構下無法釋疑的差異性影像圖景,而這種差異性正是“泛中心”化在場顯現的基礎符號。恰如德里達所質疑的封閉的傳統翻譯書寫模式,“忠實于原作的翻譯也是無限地遠離原作,無限地區別于原作的”。完全比擬的等同翻譯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同真詮釋與轉化,因為文本是沒有可抵達的終極意義的。貴州電影作為一種影像文本的主體書寫,它的能指與所指意義性遠非傳統影像觀念的“翻譯”。因為“所指概念絕不在一個僅僅指自身的充分的在場中靠本身自行地出現。每一概念在本質上被合法地刻寫在一個系列或者系統中,其中以差異的系統活動或者說游戲的方式指涉他者,指涉其他概念”。可見,所謂概念意義的形成并不是先天的,那它的指涉意義就不應該是固化,反觀貴州電影,它也可以突破刻板印象的框架,形成合乎實際化的影像在場還原,或許我們可以更直觀地理解為:電影不應該是影像規則的附屬品,而是影像規則的締造者。
二、原初蹤跡的尋找:貴州電影“泛中心”化生成之因
不同于海德格爾的“在場構建在場者”,德里達認為事物的延異運動過程才是最終在場者的構成,而“原初蹤跡”就是運動過程中起到作用的、可能消失或并未消失的某種因素。“在專門的痕跡(蹤跡)領域中,差異產生了種種要素,并使這些要素構成為文本和痕跡(蹤跡)系統”。貴州電影作為解構傳統的在場者,它的“泛中心”化形成,正是“原初蹤跡”提供了可確立的依據。
(一)貴州文化主體性的缺乏
“文化不是可觀察的行為,而是共享的理想、價值和信念,人們用它們來解釋經驗,生成行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們的行為之中。”任何藝術作品的生產離不開它所依賴的社會環境,因而不同區域的電影影像生成是有著明顯的自帶文化特征的,如上海城市影像與它高度城市化的現代環境息息相關,香港電影里的非理性邏輯與香港后殖民身份的懵懂與迷離相依,臺灣電影的長鏡頭美學有著對故土文化眷戀的詩意隱現。影像的傳統解構是存在既定文化歷史情境下的一些解構姿態,尤其是與居于凸顯意識的中心文化難以抽離,因此大部分的地緣電影文化都基于一種主體性文化而進行影像闡釋。但審視貴州電影的不同特征,卻很難將它們統一對應到貴州文化某一特征上,在戰爭、民族、詩意的影像之間,少數民族文化似乎只彰顯了其中一個符號特征的呈現,且這一民族符號亦存在多種少數民族文化形式的交融。這種文化主體特征的缺失與困惑,可以在溯源貴州作為主體形象生成的歷史中去尋找蹤跡:貴州文化由于其歷史與政治場域的變化,在傳統、記憶、語言上都存在極大的差異與散點化。于此,我們不難發現,貴州影像生成的復雜之因源于貴州自身主體文化的難以確立。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貴州是缺乏先天主體性的。在今天的地理位置上,貴州是一種不邊不內的位置,既不像邊疆省域一樣處于跟異國的接壤邊界,也不如四川、湖南一樣與內陸地區聯系緊密。這種現實的形成,源于貴州歷史上在場感的邊緣性。由于山重水復的復雜環境,在各種封建皇權中,貴州均被視作野蠻荒涼之境,直至明朝1413年,貴州才作為單一省份出現,且基于云南、四川、湖南、廣西等邊緣地域的劃分合并而成。因此,貴州的形成是本身就是一種無中心的各周邊區域的拼圖。在這樣的一種身份形成下,該區域的政治制度也變得復雜,土流并治下各種原生的、氏族的、封建的社會類型交匯,直至進入大環境的現代社會中,貴州的仍存在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各種復雜社會鏡像。
其次是多民族的雜居現象。貴州是一個少數民族元素尤為彰顯的省份,這種彰顯性不僅因為貴州少數民族人口、種類眾多,且成分極其復雜,光世居的少數民族就多達十幾個。此外,貴州還有許多未識別的民族。貴州的少數民族,不僅支系龐雜,還存在極其明顯的同源異化,各少數民族追溯至漢、百越、苗瑤、濮、氐羌等不同族系。眾多的少數民族在貴州山地環境主導因素的影響下,民族居住環境的大雜居小聚居分布格局逐漸形成。但由于“溪峒型”的自給自足生產方式,信息的交流與傳播存在著天然的障礙,并恍如羅盤星布于貴州地域,他們擁有著自身本質的生存方式與文化信仰,又通過與當地本土文化的交融,兼具了多樣化色彩。“溪峒型”地域特色使得貴州文化四處“撒播”,且各自獨立成為貴州民族文化的共生現象,但中心化的民族文化卻至今都處于模糊中,難以確立。
最后是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造就的影像多元根基。貴州建省以前處于相對獨立自主的邊緣區域,不僅遠離彼時行政中心的管束界域,且在漢文化的接受影響上存在較大的間離性,因而這一空間的各民族有著極大的自由性,不同民族的生產方式與文化傳統原真度保存較高。隨著不同朝代的變換,由于其地理位置偏遠,貴州地域成為各朝戰亂年間最佳的庇護之地,加之它本身拼湊而成的缺主體性,因此它在不同民族的融入下更趨開放化,相異民族的原始文化也在主體少數民族的缺乏下,變得更具包容與兼收,并在相互的文化交融之間各自調整與適應,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大走廊。在貴州少數民族中,每個少數民族都有著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這些不同信仰與風俗在本土的泛化與相互認同,衍生出了有貴州本來印跡,但是又各不盡相同的民族文化共存意象。
(二)前現代性、現代性、后現代性不同程度參與下的影像生成
絕對中心意識的懷疑與否定,是德里達對于事物“延異”與“蹤跡”的解構滲透,并通過“播散”的行為進程最終抵達泛中心化之實在境地。“蹤跡是一般感性的絕對來源,蹤跡是顯現外觀和意義的延異。”事物的差異變動是無時無刻的,但是卻又未必具備實在性,但不可否認的是任何當下事物的呈現都不可避免地裹挾著它所經歷的印記。這種感性的蹤跡尋覓跟波德萊爾的現代性體驗有著驚人的相似,“現代性是短暫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藝術的一半,藝術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的”,而這瞬息萬變的元素需要去捕捉與獲取才能真正確定藝術作品的意義性,“因為我們所有的創造性都來自時代加予我們情感的印記”。現代性問題雖然發端于西方世界,但在全球化的步伐之下,它已逐漸嬗變為一種世界現象。“中國的現代性我認為是從20世紀初期開始的,是一種知識性的理論附加在其影響之下產生的對于民族國家的想象,然后變成都市文化和對于現代生活的想象。”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性不僅有著與西方的迥異性,還夾雜著不同區域之間現代化發展程度的斷裂性,貴州影像的生成與復雜性正是源于自身極具差異化的現代性體驗而形成的。“所謂現實都是過去傳下來的,向未來伸展,現實不可能停留在‘點’上,現實生活中沒有零點。”貴州影像的差異分延,就是對現代性差別性感知下不同蹤跡的捕捉。
對于身處西南腹地的貴州來說,它的現代性初體驗是一種不同于藝術審美文化的殘酷體驗,即戰爭被動性的卷入。鮑曼認為戰爭是現代性的固有可能,是“在社會失范——不受任何社會約束的情況下,人們就會無視傷害他人的可能性而做出各種反應”。這種社會約束的目標是外部力量介入中國強加的自私意圖而演變的野蠻殺戮,貴州本在遠離戰爭中心區域之外,但偶然失衡的戰爭格局使得革命空間不斷波及與深入貴州的內部,給予戰爭影像最核心的主題與敘事素材,《突破烏江》《四渡赤水》《遵義會議》等影片都集中凸顯著長征紅色文化的集體記憶。縱觀戰爭影像的生產,被動性的意識不僅體現在內容的聚焦上,且從影像的生產體制上也可窺見貴州作為從屬的非主體立場,歷史上貴州電影制片廠從1958建成至1963年全部結束,短暫的存在并未在影片生產上發揮主導生產力,因此早期的較為有影響的貴州戰爭影像基本上都是由外省電影制片廠出品,如八一電影制片廠出品的《突破烏江》與《四渡赤水》,這是一種依附于外在力量的空間生產,而貴州作為主導力量的出現在戰爭影像中是較晚的,直至2005年以后才逐漸有了貴州本土生產主體的戰爭影像生產實踐參與。
民族影像里的貴州是一種前現代性與現代性的交織體驗。貴州山地環境與“溪洞型”生存狀況使得貴州當下的民族環境中仍然保存著前現代性的景象,原生態世外桃源里的古樸技藝展示、山地環境中的文化景觀、未經商業社會浸染的民族至善都保留著前現代性的痕跡。貴州的前現代性不僅僅有著傳統環境決定論的因素造就,還有著歷史原因造就的民族多樣性下民族文化各自的存留,在民族影像中的原始崇拜、巫儺文化的隱秘原初信仰暗喻的是前現代性表達。但隨著社會現代化的發展,雖然貴州固有的環境劣勢滯緩了經濟與文化在現代化上的普適性推導,但是眾多偏隅一角的原初民族生態系統,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現代性的入侵,寧敬武的《滾拉拉的槍》中獵人生存技能演化為法律禁止的行為、吳娜的《行歌坐月》里杏對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卻最終帶著遺憾回歸故里的唏噓,這些影像書寫對不同時空中傳統與現代的沖突進行了內外視角的思考。
后現代意識往往是在現代化的泛化之下而衍生的新的審美趨勢,并將現代審美的固有界限徹底模糊化,“后現代主義為我們今天的文化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文本——其內容形式及經驗范疇,皆與昔日的文化產品大相徑庭”。貴州作為藝術影像的空間生產被關注,矚目于新世紀以后的第六代導演的關注,《尋槍》用傳統的空間反映了人主體的渙散與物戀的悲劇,繼而王小帥的“三線”三部曲的貴州認同書寫、再到畢贛的黔東南藝術宇宙呈現都是后現代意識與本土文化景觀的相互作用生成的詩意影像表述。這其中,畢贛現象成為藝術影像中被反復闡釋的關注點,“導演在調度空間中重構時間的能力比繚繞的詩意和精工的畫面更令人驚嘆,他在重復、也在延續塔科夫斯基對‘電影最珍貴潛能的思考’”。一種新的詩意美學在貴州的差異空間中不斷被讀取,外化自然的差異空間成了地方生活經驗的內化攝取,成為均質化的城市空間中獨特的美學生產空間。而詩意影像的具化邏輯運用在畢贛的演繹下是魔幻現實主義策略的運行,一種“奇異的現實”在時空交錯的幻象中,正是源于貴州本土部分空間現代化急速完成與前現代性空間殘存的交互感知。
三、解構意義的生產:“泛中心”化下新的西部影像美學形成
縱觀不同區域的電影影像表達,貴州電影特征的復雜與意義多元化是一種已然成立的影像事實:戰爭、民族、藝術的多重交織構筑了貴州電影作為中國電影中具有超越意義的一種個體現象。在當下的區域影像考察中,很難再辨析出如貴州電影般三者截然不同影像的皆存空間,貴州電影呈現出的豐富層次感突破了其他區域電影的一元或二元生產,形成了新的影像審美邏輯判斷的可能性。
貴州電影在傳統的影像邏輯中并沒有呈現出普遍性的類型與形式歸納,因而無法建立中心主體影像特征的唯一性。但這種中心化渙散的意識,并不是虛無主義與游戲主義的思維表述。“解構不是摧毀,而是揭開遮蔽,暴露可能性,關注他者和異域”。“如果一定要確定通過解構人們構建了什么,我要重復我說過的:解構不是否定的,而是肯定的。……如果一定要確定通過解構人們構建了什么……那就是世界的新面貌、人、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新面貌,以及通過解構尋求的新的規則和法則。”正如德里達所理解的那樣,電影系統的開放性使得貴州影像獲得新的美學意義理解。
貴州影像特征的差異性使得傳統的西部電影類型瓦解,新的西部電影美學類型獲得了可行性,中國區域電影的多元化進一步得以深化。在中國的地緣電影劃分中,貴州電影被籠統地歸在了西部電影中,1984年鐘惦棐所提出的中國西部片概念指的是立足于大西北的影像攝取。“中國西部片是一種以中國大西北獨特的自然景觀、悠久的歷史積淀和豐厚的人文意蘊為底色的中國電影類型片。”由此可見西部電影在我國的電影語境中有著雙重意味:一是西部地區出品或長期定居西部的導演所拍攝的電影作品;二是以生動、逼真的影像來展示、敘述、言說“西部”地區的電影,它可以是寫實、表意,也可以是奇觀、戲說、神話等。這一原初的電影類型存在邏各斯的中心意識,貴州電影因其泛中心化而顛覆解構了這傳統的西部類型標志。
從西部電影的概念上來看,貴州的西部意味較為牽強。首先是地理位置上的偏南,導致它的自然風貌“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與大西北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完全不同的自然環境必定無法在影像外化的屬性上形成統一化的風格。其次是從精神文化上來看,貴州是不同省域邊緣區域邊緣文化的拼合,因此貴州本身的巫文化與四周的巴蜀文化、荊楚文化、滇文化、越文化相互交融擴散,在不同文化“雜”交之下,彼此認同、粘連,最終形成文化的多元。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貴州不同于其他西部地區文化的一元性,如四川的漢文化、西藏宗教文化、云南與廣西的少數民族單一主體文化,這構筑了它與其他西部區域文化的別樣性。正因如此繁復的文化載體,貴州的影像表達才呈現出了戰爭電影、少數民族電影、詩意的藝術電影三者迥然不同卻又各自彰顯的意義,如再以傳統西部電影定義去判定貴州影像的創作,顯然已無法與貴州電影的外化顯現與精神內涵相對應。
貴州影像的不同維度特征交融,延長了地緣電影的審美意義空間,創新了西部電影的概念。“西部電影是一開始就確定了要在追尋自身的無限性發展中來確認自身的一個全新的理論概念,它的問題不在于總結和說明,而在于發展和創新,它不是對創造者的總結,而是對創作的參與與創造”。在當下的中國區域電影中,上海電影、北京電影、香港電影、臺灣電影已然成為中國電影的不同中心區域,反觀其他中西部地區,單一省域的地緣電影特征讀取卻稍顯片面化。因此新的影像類型的意義賦予,為以往屬于邊緣影像的貴州話語存在提供了一個更為恰當的空間,一種更多元化的敘事語境。貴州的不同影像在泛中心下達成“共識”的美學意象,“‘共識’不是建立在對一個事物的客觀認知的基礎之上,而是主體之間遵循一定的有效性要求所達到的一致意見”。在更有效地理解貴州影像的生成與發展下,這種共識性的結果就是新西部電影空間的不同主體間性的確立。
結 語
還原到“一切都是影像書寫”的意識里,以解構視域的態度介入貴州電影的思維意義界域里,其差異性、他者性以及新的被遮蔽的意義重新被賦予了在場顯現的能力。“從某種它無法定性、無法命名的外部著手,以求確定那被其歷史所遮蔽或禁止的東西”。貴州電影作為一種不同區域主體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國區域電影多中心播散行為的生產。以“泛中心”化的視域考察貴州電影的具體歷史實踐與現實書寫,其影像的表達已超越普適性影像規則,衍生出了多面的影像交錯。置于社會文化背景的深層動因,可以對貴州電影泛中心化形成得出合理性的依據,這對于其他區域電影的差異性剖釋給予了可借鑒的反向式思維判辯。正是基于這種多重意義場的過渡和躍潛,在區域電影的研究中,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國不同地緣電影存在的合理意圖。于此,中國區域電影不同的影像實現了對位式、癥候式的讀取意識參與、多層次的影像攝取意義趨于完善、非均質化的影像美學個體區域獲得平等化的關注,而這也正是貴州電影個案帶來的超越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