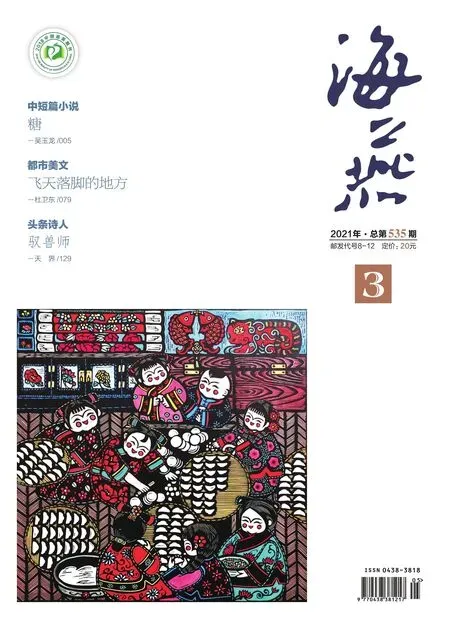遼河月輝映下的女性主義詩學
——論李簞短篇小說集《遼河月》
《遼河月》是李簞近十年創作、發表的短篇小說集萃。翻開小說集,你會訝異于柔美、蒼涼的詩意題名掩蓋下鮮明的女性主義寫作色彩,更會訝異于中國大陸上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走向高潮的女性主義寫作思潮,在遼西一隅五彩盤錦的新世紀回響。
執著的女性詩學意識
李簞小說中卓爾不群的女性意識與其說是一種敘事策略不如說是她的一種性別執念。《遼河月》中的許多女性人物執著于給自己作自畫像。女性主人公往往有一種女巫的氣質,能夠先知式預見自己的命運。小說的敘事策略與人物的氣質相一致,首先采用印象式議論語言對女性命運加以評說,然后才進入敘事環節。《形意》中的我“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狀態,工作也不斷地出錯。”①《聲名狼藉》開篇的詩性絮語“我是一枝尚未盛開就已凋零的花!我柔弱的肩承載著太多的不幸。我濃濃的愛意是漫天飄灑的細雨遮蔽晴日”②仿佛一個女性創傷的呢喃。《偏離》在題記中寫道:“冰雪聰明的女子骨子里往往是透徹的愚蠢!別人一頭霧水時她早已洞明于心,誰都一目了然的淺顯事情她偏執迷不悟。這樣的女人輕易不犯錯,犯錯就是大錯。我就是這種女人。”③《紙畫人生》中白雪以審美客體的形象出現:“白雪半裸著身體,一只美麗的花環攏住烏黑的長發,兩條白絲巾纏繞著身體,一條圍住胸肩,一條纏在腰臀。”④白雪去美院做寫生模特,這一情節與形象是意味深長的。一百年前,丁玲《夢珂》中的夢珂,對抗著人們復雜的笑語和強制的干涉決絕地走進美院的教室,今天的白雪褪去花環和絲巾如同走上生命的祭壇。李然給白雪看了自己的畫,“白雪的心一下子被擊中,她做模特,展露人體,收集自己的畫像,就像喜歡紙畫上的完美,畫家們有意無意地打開了箍緊她的銀圈。”⑤“白雪太漂亮了,盡管她一出生就是殘缺的”⑥,白雪先天的殘缺是“第二性”的隱喻,而她為了獲得完美鏡像的獻祭,所付出的代價正如王安憶在《妙妙》中所寫,女性要完成自我的理想與信念,就得踏著自己的鮮血前進。女性自畫像既是對女性生命意識的張揚,也是對父權制社會挫折回歸的自我撫慰。
與女性相對的男性生命或者如家駱一樣猥瑣,或者如陸文魁一樣無恥,或者如表哥一樣懦弱,或者干脆像表嫂的死嬰和小寶一樣夭折,隱喻著父權制異化下男性生命的委頓與病態,無法像女性一樣獲得生命蓬勃的自由舒展。父權制的歷史重負同樣可以侵蝕女性生命。《花梨紫檀》中的姑母雖然生理性別是女性,但是社會性別已經成為伍爾夫《婦女的職業》中命名的“守護神”。“守護神是男權思維左右下的女性形象,她其實就是男性權威的化身,她的一舉一動都按照男權社會的要求行事。”⑦伍爾夫認為殺死“守護神”“是一個婦女作家職業的一部分”⑧。姑母最后與花梨紫檀這些男權社會價值象征物一起葬身火海,是李簞殺死“守護神”的隱喻,只有殺死“守護神”,女性寫作才能打破男性經驗神話,進入女性獨特經驗的敘事空間。
封閉的女性詩學空間
近一個世紀前伍爾夫曾為女性呼吁“一間自己的屋子”,這一聲沖破父權制壓抑的喊聲在中國大陸獲得了跨民族和跨語言的熱烈回應。上世紀80年代伊蕾的長詩《獨身女人的臥室》石破天驚,引起了女性主義學界的巨大轟動。詩歌創造了“獨身女人”的主體想象,獨身女人成為女性文學的經典性人物型塑,“一個自由運動的獨立的單子”“一個具有創造力的精神實體”奠定了獨身女人的敘事元精神。上世紀90年代陳染的《無處告別》、徐坤的《廚房》都將女性從婚姻中主動或被動抽離,女性主體以獨立的姿態自立于世。而獨身女人的臥室、廚房也成為女性文學的隱喻式空間意象。李簞小說呈現出明顯的對這一浪潮的傳承賡續。到了新世紀,《形意》中的廚房,不僅再現了為心愛的男人做飯的空間諷喻意義,也成為同性關系依賴轟然倒塌之后的避難所。李簞的女性空間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帶有超越于性別之上的普遍人際關系焦慮的時代色彩。《遼河灣》中的南大泡子雖然是開放的自然天地,但這個天地似乎是專屬于“我”的秘密天堂,小寶作為男性生命的象征踏入其間就會斃命。《紙畫人生》中母親臥室永遠緊閉的房門,同樣閉鎖著母女的精神和情感。《數數》中人情冷漠的豪宅雖然寬敞得沒有邊際卻壓抑得讓人窒息。
女性的確獲得了“一間自己的屋子”,可是這屋子并沒有給女性帶來期待的自足,世界正在變得匪夷所思。女性結盟意識的松動使李簞對女性之間的關系持有與審視父權制一樣的警惕目光。《形意》是對女性關系的解構與嘲諷,“我”在醫院最好的朋友,我的小同鄉、小學妹真真竟然隱瞞實情將自己的前夫介紹給離婚的“我”作為男朋友。原本同性之誼是躲避男權戕害的避難所,現在也與這個時代合謀,女性的最后一方天空坍塌,“我”的退路只有廚房——“廚房是女人遁世的最好去處”⑨。廚房隱喻的是一個與客廳的開放性公共空間相對的隔離的自我空間,空間意象在李簞這里獲得了更多的封閉性和可疑性。《遼河月》的人物多是在封閉的自我空間里靜默地成長,經歷著一個女性神秘的生長周期,在兀自開落的日子里于某一天驀然淪陷父權制的陷阱,開始女性生命的創傷歷程,而這一切仿佛與理想、哲學、詩性無關,女性在現實和欲望的泥潭中掙扎無望。
迷人的女性詩學色彩
也許兼擅繪畫與文學有關,藝術性天生地成為李簞小說迷人的色彩與線條。李簞的小說有一種北方文學中罕見的迷離的鬼魅氣質——夢游一般的人物,形同迷霧的敘事氛圍,明暗交疊的心理事實,敘事在真實與夢幻中無障礙出入,鬼氣森然卻欲罷不能。小說幽暗、鬼魅的深層動因來自于作家近于執念的女性意識,隱含著對父權制壓抑下扭曲生命樣態的批判。
《花梨紫檀》鬼魅、幽深的三進院落,心理變態的當家主母,色迷心竅的猥瑣表哥,死嬰的魔咒,月光樹影下被親生母親敲碎的嬰兒腦殼,被鐵匠燒焦的靈蛇……這種審美感受倒是西南邊地的女作家林白、楊映川的美學胎記,卻與遠在東北的李簞這里遙相呼應。《遼河灣》在江北水鄉充滿生命歡愉的靜美天地之間鋪展出一場人世的悲戚。為了將這悲戚渲染得足夠沉痛,作家還給原本的歡愉加上一個趨于圓滿的高潮——五個女兒之后兒子的降生,讓“我”家的幸福達到極致。然而“福兮禍之所伏”,小寶終于在“我”的詛咒之下永遠在葦塘里留下一道草綠色的背影。《紙畫人生》是一篇唯美的女性敘事,在蒼白的布景和人物上淋漓明艷的血的鮮紅,將女性針刺一樣的疼痛書寫到極致。李簞筆下的女性形象無不來自創傷背景,她的小說在痛感書寫上猶見功力,這種痛感讓人不寒而栗。《偏離》是一個女性雙重復仇的故事,辛竹對年幼的麗麗奪走父愛的仇視,人性的自私與陰暗在閃念之間使辛竹付諸謀殺麗麗的行動。此時的辛竹猶如《遼河灣》每日詛咒親生弟弟的“我”,李簞對推進女性極端性時刻到來的緊張與恐怖運用了精到的戲劇筆法。麗麗因為辛竹不徹底的謀殺留下了終身性疾病,而她報復的方式是與辛竹的丈夫發生關系,摧毀辛竹的家庭,同時被摧毀的還有她繼父的生命和親生母親的婚姻。《老二》在陰間——陽界、夢境——現實之間的自如穿梭往返,水粉色真絲內衣的欲望性意象,都生成了小說陰森哀艷的美學特征。
《遼河月》充盈著李簞對女性生命本能般的驚嘆與贊美——美麗而充滿靈性,純良而堅韌勇敢。李簞借助短篇之間的穿插回閃,構建起完整的女性生命敘事:以少女時代——青年時代——妻性時代——母性時代的生命歷程為經,以城市、鄉村兩大地理空間為緯,交織出女性生命時空的獨特畫卷,為女性主義詩學貢獻了兼具獨立性與對話性的遼寧聲音。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⑨李簞:《遼河月》,沈陽出版社2020年版,第64、168、196、53、56、52、75頁。
⑦荒林:《日常生活價值重構——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頁。
⑧伍爾夫著,李新譯:《婦女的職業》,《文化譯叢》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