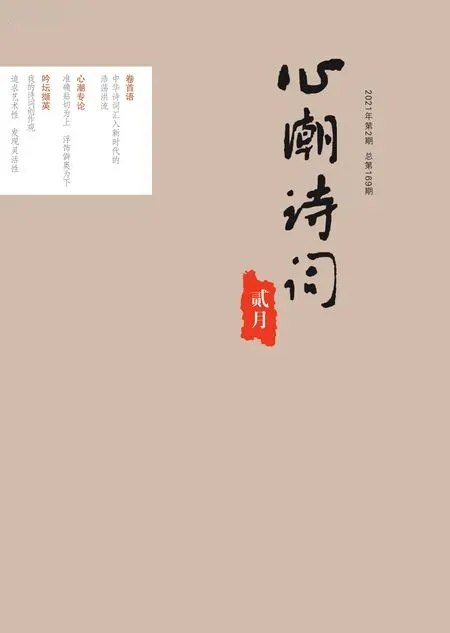從現實生存到理想樂園
——當代田園詩詞的寫實與超脫
曾憲媚 周于飛
田園詩詞在田園的失落和當代多元文化的沖擊之下,已經逐漸退守到文學生態圈和大眾視野的邊緣地帶。面對冷落和輕視,排擠和打壓,它也在思考應該以怎樣的姿態重獲新生。為了追慕失落的田園牧歌而選擇摹仿古語古意,今人唱老調,以致時代骨力軟弱;為了建構新田園詩詞的體式而全力兼容多元文化,主要的特征表現為以大量白話、方言、外語直接進入詩詞,甚至不顧舊體詩詞的規范,使生硬的土洋結合、中西合璧顯得不倫不類……筆者認為蔡世平田園詞的復活形態在一定程度上為明確當代田園詩詞的現實生存意向、構筑其理想樂園提供了兩點可借鑒的方法:一是寫實,即寫當代之實;二是超脫,即主動打破田園詩詞樸實簡淡之境,直面田園鄉土所存在的悲情。
一、田園詩詞與現實生存的關系
筆者選取黎建三的田園詩與蔡世平的田園詞作對比的依據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
面。第一,黎建三所生活的清代,是距離當代最近的受正統詩學制約和儒家正義涵養的朝代,其所固定下來的田園詩詞可以對當代田園詩詞的創作起到規范作用。第二,壯人出身的黎建三因長養在山水蒙昧、正統教育較為落后的南疆,致使其田園詩歌藝術技巧的運用和創新能力都略顯不足,而由于教育體制的變更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導致當代田園詩詞創作也存在相似的問題。第三,黎建三作為一位心懷家國、胸臆赤誠的士人,其田園詩在山水四時、農事民生的描畫中總能顯現出他的時代氣概和剛直氣骨,這正是當代田園詩詞有所欠缺的。
山 中
十尺茅庵折腳鐺,宵深不辨短長更。
狂歌詩句兒童怪,獨坐松根風露清。
浮利虛名千日醉,空山白月一身輕。
巡檐延佇心如水,時聽盆魚煦沫聲。
黎建三是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壯族詩人,他一心為民,一生為國,在官場威逼和現實迫害下依然不屈。這首《山中》是詩人自覺對抗現實丑惡的一曲“狂歌”。尤是頸聯“浮利虛名千日醉,空山白月一身輕”——可見他視“浮利虛名”如鏡花水月,不愿沉醉在以百姓血淚釀成的毒酒所帶來的一時歡愉之中。又以“空山”作骨,“白月”為氣,傲然地挺起自己不屈的脊梁。上下兩聯將“浮利虛名”和“空山白月”進行虛實之間的對比,突出了“利名”寄生于昏毒時代的虛假、“山月”生養于牧歌田園的純真。全詩暗諷了追名逐利、魚肉百姓的時代弊病,表達了對山月田園的思慕,表現了詩人不屈于“利名”的剛直氣概。
對致力于解當代田園詩詞涸澤之困的詩人們來說,以黎建三為代表的舊體田園詩詞創作中蘊藏的時代氣息和時代氣骨,恰如源頭活水,流出一脈生機。蔡世平在遵從舊體詩詞規范的基礎上,借鑒、融合前人創作的時代表達,通過抒寫當代之實——事物的真實、骨力的堅實,來塑造田園詩詞的當代個性,使得田園詩詞在當代現實中能夠與時俱進又獨立自主地生存。
蔡世平的田園詩詞不是一味地模仿古風,吟唱老調,而是將當代鮮活的人事物象用舊體田園詩詞的體式來記錄和表達。他筆下的田園詞在一字一句之間都活著當代的人、長著土里的苗、吹著月下的風、掛著天上的日頭、流著農人的汗水。一切都顯得那么真實而自然,沒有故作風月的無病呻吟,只是在靜靜地講述同時代的田園故事。蔡世平所作的《浣溪沙·洞庭田舍翁》便是對“一九九零年代以來,國家糧食有余,農民有閑,袁隆平功莫大焉”的田園時事見證。一句“才了蠶桑又曬倉。袁公播種我收糧”,筆法簡白,直接流溢出作者和時人心中的喜悅之情。明明蠶桑之事剛過,還未盡享閑情,又迎來稻香滿頃。“才”和“又”用字精巧,乍看之下是隨性的白描之筆,細品卻又有煉字于無形之意,好似只是陳述事實般的隨口一說,但是又明顯帶有對于農閑未歇農忙又至的“無奈”和“抱怨”,正話反說,筆調俏皮,寫出了農人故作“無奈”“抱怨”之態的豐收喜悅。隨之點明豐收之喜的出處,袁隆平先生響應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政策的號召,在田間地頭披風戴雨歷時十余年所培育成功的秈型雜交水稻。“袁公播種”了一顆真實可見的時代糧心,給了今人一份真實可感的安心,可謂前無古人,功在千秋。“我收糧”的喜悅之情也不僅僅是因為豐收,而更多的是因為農民在當今時代下能在自己的農田里找到安全感和歸屬感。
田園詩詞的風格雖多是以沖淡平和為主,但這清風明月、山水四時、農事牧歌之間并非全無氣骨。比如古來詠嘆的蒼松翠柏、傲雪寒梅等,以及黎建三詩中的山骨月氣。而蔡世平對自然、田園有著天然的親切感,又有十余年從軍生活的磨練,二者兩相滲透融合,使得“他的詞有著軍人的豪情、男子漢的血氣”。《賀新郎·說劍》:“石光鐵火銅風起。便造了,河山筋骨,男兒血氣。從此文心懸劍膽,山也橫成鐵笛。怎辜負,吳戈楚戟?不向愁腸吟病句,鑄新篇,還得青銅味。拈劍影,詞心里。”他將河山劍影化作筋骨血氣,自覺地背負起參軍衛國的時代使命,等到“退役瀟湘故里,猶喜田園風色,翻地種青蘿。縱是男兒骨,常要鐵來磨”(《水調歌頭·土器》),亦是不改氣節。蔡世平常持鐵鑄土器,翻地種蘿,以男兒血氣滋養芽苗,自此劍影化作綠意,赤血融為根系,種下一派田園風色,長成一副河山筋骨。此錚錚之骨,軍人脊梁,凜然挺立在他的田園詞中,使得筆下的山河花木、云月風雨,不見絲毫愁病之嘆,沒有半分矯作之態,顯得高潔而又堅韌。正是人有鐵骨,詞生血氣,人詞骨氣相投,故而在蔡世平的當代田園抒寫中,多了一份源于赤血衛國的軍人骨力。
二、理想樂園的塑造與對比
黎建三的田園詩詞,大多都是身仕廟堂心懷遠志卻苦于無力舒展的寄情之作。出于對現實的失望乃至絕望,又無法與其完全決裂,因此往往將個體的憂愁壓制,而選擇在現實之外構建一個桃源式的精神樂園聊以自慰。給予理想一片沃土,將本真之質和清明之心養在山林田間、漁歌午后。
山 中
十尺茅庵折腳鐺,宵深不辨短長更。
狂歌詩句兒童怪,獨坐松根風露清。
浮利虛名千日醉,空山白月一身輕。
巡檐延佇心如水,時聽盆魚煦沫聲。
全詩借以“茅庵”“松根”“風露”“空山白月”等意象構造了一個簡淡幽深之境,這里沒有現實俗世的“浮利虛名”,只有松風山月的田園氣象。遁入此境,詩人可以休憩于茅庵之內,一方草席之上,聽清風于松下,望明月于山間,放聲狂歌,閑逗魚趣,行逍遙之樂事,做一回散仙,管他宵更短長,浮利虛名。可見在黎建三的筆下,他的田園被構筑成一個隔絕世事的桃源仙境,固然美好,卻有著不容于世的脆弱。為了構建一個理想的桃源,一個無憂的仙境,黎建三將所有煩憂哀愁、浮利虛名驅除在外,而將純澈質樸、寧靜安逸的田園幻想盡數傾入其中。但這何嘗不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對自我的封閉和欺騙呢?它終歸只是一個筆墨寫成的美麗傳說,一片由主觀意志幻化的虛無。就像是一場易碎而不實的幻夢,容易做,也容易醒。
追根溯源,黎建三之所以會執迷于簡淡純粹的桃源幻想,甚至于以此回避現實,一方面是因為他所處時代的昏暗與他本心的清明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在這樣的沖突之下,他依然選擇堅持自我、堅守本心,站到了現實的對立面;另一方面是因為他作為封建社會的附庸,王權之下的臣奴,微于螻蟻,自我的意志和抱負不受重視而且還要被殘酷的現實壓制、迫害,故而尤是向往殿堂之外那寧心純粹的田園生活。于是在黎建三的抒寫中,總是有意地將自我渴望自由、追慕自然的意志投入其中,營造一派悠然自得、言笑晏晏的田園風情,意圖與現實的污濁斷絕關系,申明其不屈的心志。可事實上卻是草有榮枯,人亦有悲歡,田園作為一個人與自然的共生之境,榮歡和枯悲同是共存的常數。桃花源式的理想田園不該只是囿于親慕榮歡、描摹鄉色的筆墨抒寫,或是一個用于寄托情志的精神假想,而應該是以直面田園悲情,正視田園所存在的問題,謀求解決之道為主調的現實構建。蔡世平即是如此,他的田園詞就敢于超脫常境,直面田園悲情,從中思考理想樂園在生活的現實里如何構建。
蝶戀花·路遇
序:二零零六年冬去鄉下,路遇村漢呆立寒風中,一臉茫然。妻子畏貧,拋下兩個患白血病的兒子,棄家而去。
一地清霜連曉霧。村漢無言,木木寒風佇。曾是嬌妻曾是母。而今去作他人婦。 世道仍須心養護。豈料豺狼,叼向茅叢處。誰說病兒無一物。還留血淚和煙煮。
蝶戀花·留守蓮娘
序:有“留守兒童”,也有“留守女人”“留守老人”。一九八○年代以來,億萬農民進城務工。夫妻異地分居,乃今日鄉村常見現象。
秋到荷塘秋色染。秋水微紅,秋葉層層淺。人在天涯何處見?秋風暗送秋波轉。 春種相思紅片片。秋果盈盈,秋落家家院。獨對秋荷眉不展。秋容淡淡秋娘面。
以上兩首詞都通過對當代現實問題的揭露來表現田園中所存在的悲情:一是貧病之悲,一是留守之悲。
“曾是嬌妻曾是母”,曾有恩愛曾有慈,可是卻因為無法忍受貧窮和病兒所帶來的困窘,這位嬌妻慈母不愿賠上自己的一生,她棄家出走,“而今去作他人婦”,選擇“重新開始”,重新做一回“嬌妻慈母”,重新組建一個家庭,重新擁有自己的孩子。她解脫了,以對感情、家庭的背叛和離棄為代價。但曾經的家破碎了,只剩下前夫和病兒獨自孤苦,“還留血淚和煙煮”。詞人對此怒道“世道仍須心養護。豈料豺狼,叼向茅叢處”。原來,田園也并非全然是純粹質樸的,鄉人也并不總是樸實重情的,它們都會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人心的復雜而變得復雜。
四時流轉,蔡世平有意讓留守蓮娘活在秋季里。望夫的日子,不若春天般可愛喜人,不似夏天般明媚熱烈,也不像冬天般嚴寒無望,正如接夏逢冬的秋季,萬物將枯待榮,蕭瑟中帶點暖意,沉郁中仍留期待。秋荷映秋水,秋葉畫秋風,秋容秋娘面,秋里盼郎歸。可是盼來盼去,等來等去,“人在天涯何處見”?終究是難以執手相守,因為他們的整個生命、整個生活都好像被鬧人的秋風纏住了,凋敝困乏,疲于生計。留守婦女在這場喪偶式的婚姻里,需要獨自一人去承擔起農事勞作、贍養老人、教育子女的重任,更要忍受無盡的孤獨和漫長的等待。隔著天涯海角,當所有的無奈和孤寂無人訴說之時,她們只有“獨對秋荷眉不展”。可是她們也明白,那都是為了生存,為了讓愛情和家庭在柴米油鹽里能有自己的生命。
可見蔡世平的田園抒寫是當代田園的生活實錄,真實而鮮活,美麗而憂傷。在清風明月、稻香蛙鳴的田園表象之下,也生活著人們的喜怒哀樂。在他的筆下,田園不再是如黎建三所描繪的那般清心寡欲的避世仙境,只存在晨起弄花、對月狂歌的歡情,而是將現實生活滲透進字句之間所幻化的一個有感情、有血肉的世界,在紙上演繹著貧病留守的悲情人生。在這里,云會哭,清風會嗚咽,花兒會死去……蔡世平選擇主動打破田園詩詞的清新簡淡之境,打破黎建三們千百年來的田園幻想,其意并不在于標新立異、嘩眾取寵,而是希望通過展現真實的田園風貌,引起當代人的思考,思考在田園詩詞中建構理想樂園的意向和方法。
綜上所述,通過清代廣西壯族詩人黎建三和當代詞人蔡世平的田園詩詞創作對比,可知蔡世平敢于直面前人有意隱去的田園悲情,秉筆直書真實的田園生活。他的田園詩詞中所使用的寫實和超脫之筆法,對當代田園詩詞從現實生存到理想樂園的建構都帶有現實意義上的思考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