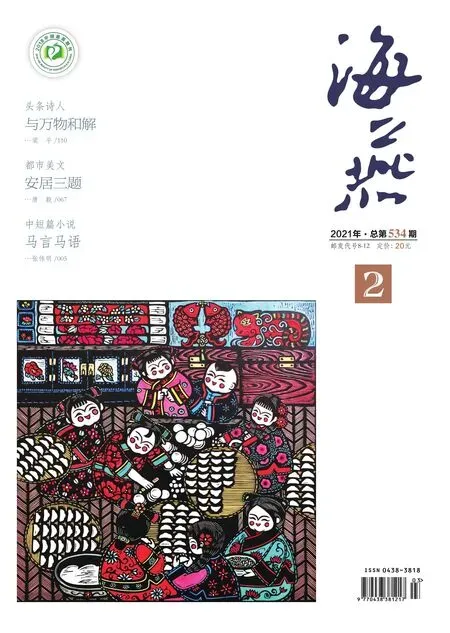蟲 子
文 邢仁宇
我肚子里長了蟲子。
現在我的肚子像是進了一窩活泥鰍,在肚腸里鬧得生疼,疼得我從工位蜷到了地板上。
我吃了打蟲藥,流著冷汗摸到了公司廁所,卻發現廁所門口橫了張桌子,桌子后面坐了個西裝革履的男人,正仔細擦拭著手里的鋼筆。
我半弓著身子趴在桌子上,痛苦地說:“你讓讓,我得進去上廁所。”
男人打量了我一會兒,開口問道:“預約了嗎?”
我愣住了,什么時候上廁所也得預約了?我往廁所里探了探頭,略帶憤怒地擺了擺手說:“別開玩笑了,快讓我進去,我的肚子疼!”
男人看我沒有預約,從手邊扯了張單據給我,說:“現在廁所人滿,你先冷靜冷靜,三十分鐘后來吧。”
我難以置信地看著手里的單據,又看了看男人,那男人身旁不知何時出現了兩名大漢,正朝自己輕拍著手里的鐵棍。
我只得無奈地夾著腿挪回了工位,看著秒針一抖一抖地挪動著位置。
三十分鐘后,我幾乎是爬著到了廁所門口。門口的男人看了看我的單據,側身給我開了門。我迫不及待地跑向蹲位,拉開了一扇蹲便器的門,卻發現里面站了一個大娘。
我愣了愣,勉強擠出了個笑容,對她說:“大娘,您讓讓,我得趕緊上個廁所。”
那位大娘嘆了口氣,說:“你們年輕人啊,就是氣火太旺了。”
我更加不解了,我上個廁所跟氣火旺不旺有啥關系,我摔上門,打算換個坑位,卻發現另一個坑位上也站著同一個大娘。
“你看看,”大娘說,“說你氣火旺你還不信,氣火不旺會不聽人講話嗎?”
我的肚子開始給我下最后通牒,我捂著肚子,額角滲出了一層冷汗,“您行行好,”我對大娘說,“我就想打個蟲子,您就放過我吧。”
大娘仿佛受到了驚嚇,激動地對我說道:“打蟲?蟲子那是說打就能打的嗎?你有沒有點基本的責任心?”
我蒙了,怎么打個蟲子又扯到責任心上去了?
大娘并沒給我辯解的機會,繼續說道:“我也知道你不容易,但日子怎么著不是過啊,一帆風順那還能叫生活?”
我捂著肚子回答:“那我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肚子疼啊,您做個善人,讓我把困難解決了行不?”
大娘又說:“你現在覺得是困難,是累贅了?當初下肚的時候怎么那么開心?我看啊,你就是喜新厭舊了。”
我哭笑不得地回答:“是,我吃東西的時候是覺得不錯,但我怎么知道它里面包著寄生蟲呢?我這是被騙了啊!”
大娘嘆了口氣,“誰還不是被騙了呢?”她說,“剛接觸時只看得見對方的好,處得深了缺點才顯現出來,這換了誰都一樣,不如忍一忍,等習慣了就好了,要學會包容。”
我急了,扶著大娘的肩膀對她喊道:“這是能包容的事兒嗎?我再忍身子都要被作踐廢了。”
大娘把頭一扭,“那不行,”她說,“你們處了這么久了我不信你們一點感情沒有,你只顧著自己舒服,考沒考慮過蟲子的想法?若是蟲子不同意離開,我就不能準許你打蟲。”
疼痛感已經讓我連半個字都說不出口了,我后退兩步,搖搖晃晃地暈倒在了地板上。
再次醒來時,我已經躺在了醫院的病床上,鼻子和嘴都塞滿了管子。
“腸子給蟲咬穿了,”護士頭也不抬的說,“能保住命就不錯,也不知道為什么最近凈是這種事。”說完她收拾好用剩的藥品,離開了病房。
我嘆了口氣,心想,起碼蟲子打掉了,傷就慢慢養吧,卻發現床邊居然坐著一個人。那不是我的父母也不是我的親戚,而是那個大娘。
“你說你怎么這么傻呢,”她抽泣著說,“你要是跟我說了情況有這么緊急我會不幫你嗎?”
我想辯解說自己明明說過很多遍自己情況緊急,但卻被嘴里的管子卡住了。
“這樣,”她抹了抹淚,“等你出了院我就批準你把蟲子給打掉,咱開啟新的生活!”
我傻眼了,看來蟲子還在我肚子里呢!隨著一陣疼痛,我又一次暈死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