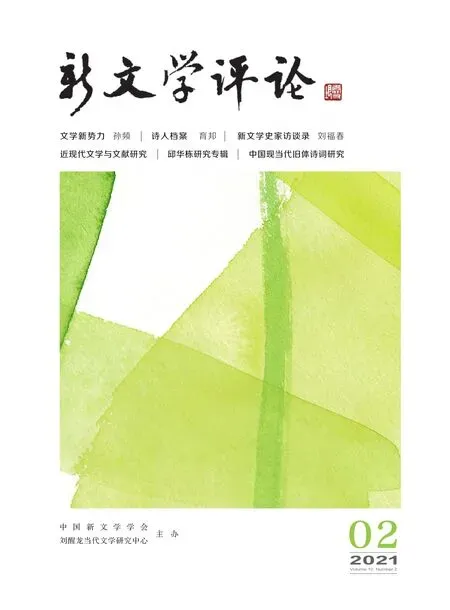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俠”與“詩”的深層共鳴:讀閻志的“江湖詩”
□ 劉詩宇
閻志的詩歌創作涉及很多方面,主題鮮明,包括但不限于詩歌地理、底層想象、往事回憶、歷史人物、自然風物、時代反思、人生頓悟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對文學的一腔熱忱是詩人創作的不竭動力。并且能夠看出,閻志對于詩歌的形式感有著清晰的自覺意識,類似《今天》《挽歌與紀念》等長詩提供的形式實驗耐人尋味。但在眾多作品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卻是兩首“江湖詩”。
《華山往事》寫一個名動天下的俠客,與愛人分隔經年,后來在一次江湖比試中殺死對手,卻發現死者正是愛人。從此俠客郁郁寡歡,陷入了深度的自我懷疑和思念,在華山虛度一生。《空心人》則和《華山往事》形成了一種巧妙的對讀關系,這位修習空心拳的人,死在對手劍下卻乞求不要摘下她(他)的面具,以免認出舊人,不由得讓讀者想到她(他)或許就是前面那位神秘而又狠心的愛人。于是這兩首詩如兩儀般,嵌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對江湖與武俠的想象。
中國文學中有武俠的傳統,這是一個源遠流長的譜系。從唐代的傳奇中我們就能一窺那些神秘、瀟灑而又驚天動地的身影。到了現代文學階段,從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到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仙俠與武俠作為文學類型密不可分),武俠文學蔚為大觀;進入當代文學階段,無論是金庸、古龍、梁羽生、黃易、溫瑞安的港臺武俠,還是鳳歌、易水寒、小椴、步非煙等人的大陸新武俠,武俠文學構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但時至今日,武俠文學正走向式微,這是不爭的事實。在敘事性的視覺藝術尚不發達,文學傳播很受媒介限制的時代,武俠文學為深陷日常生活漩渦的人們,提供了想象光怪陸離的江湖世界的機會。除了飛天遁地、刀光劍影,吸引人們的當然還包括快意恩仇、兒女情長。后者是對人們日常情感的一種偏執化表達——這不難理解,如果我們完全用世俗的標準去判斷,像金庸筆下的那些人物,例如《華山往事》中提到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這“四絕”,幾乎全可以被當成“精神病人”,只有郭靖等少數幾個人在“正常人”的范疇之內;而像古龍的小說里,重要的人物形象恐怕無一幸免,全都應算是稀奇古怪之徒。與此同時,另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是,從語言的風格和作品的結構來看,古龍的作品比金庸更接近于“詩”。
為什么武俠一度風靡如彼,卻又在今天逐漸沒落?影視、動漫、游戲等視覺藝術將人們的思維方式越來越帶向真實的維度,這只是時代的一個側面,視覺藝術和網絡、信息化極度發展下,人們自以為見識過大千世界,會越來越質疑武俠世界中偏執化的行為心理。武俠文學一度被當成青年人的讀物,因為人們下意識將人生經驗的局限和對偏執化情感的追求綁定,但這個時代正在從信息的層面上,讓所有人都“成人化”。當武俠文學的接受土壤正在逐漸瓦解,武俠文學的式微也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然而閻志的《華山往事》和《空心人》卻讓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中國是一個有著俠文化傳統的國度,而詩歌又一度在千百年的文明史中被看作中國文學的象征,這二者是否有結合的可能?類似“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這樣的詩歌畢竟是少數,從表面來看,武俠題材的詩歌十分罕有,雖然武俠小說對中國傳統的詩詞歌賦十分青睞,但畢竟沒有將其作為自己的主要表達方式。但實際上很多流傳千古的詩歌,其中記錄的情感模式,和后來武俠文學中流行的,其實是一致的。無論是穿越時間空間的相思,比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還是銘心徹骨卻又讓人捉摸不透的哀怨,例如“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等,都和后來武俠文學中表現的主題十分近似。
自從那一年的華山論劍
那一劍的溫柔
令天地動容
下了三十六天的雨
江南淹了
有一種柔情也同時被淹沒
…………
我每天都走一遍華山
北峰南峰中峰東峰西峰
蓮花峰三元洞擦耳崖梅花洞
藥王洞五里關五狼谷
下到東山門回到玉泉院
十六年從未間斷
總盼望你白色衣袂能在
華山再現江湖
——《華山往事》
詩歌,是這種偏執卻又動人的情緒的絕佳載體。與小說等文學體裁不同的是,時間在詩歌中是一種可以被隨意差遣的元素。“三十六天的雨”足以讓任何一個地方的文明毀滅,但是沒有人會在詩中苛責抒情主體的想法是否符合現實的邏輯。在這里一月有余的大雨,只是為了形塑抒情主體那漫過一切的哀傷和無助。
是的,華山上有很多洞穴
那也不是什么神仙留下來的
而是我十六年來一個一個鑿下來的
我只是在尋找你的途中
在這些洞里停歇一下
或者避開不期而至的山雨和行人
——《華山往事》
詩歌中的空間亦如時間,在詩人的這一段中,我們大可以想象抒情主體將自己的相思和哀愁灑滿華山的每一個角落。情緒被空間化,空間則被充分地情緒化了。很多人會認為類似科幻、玄幻、魔幻等類型的出現,是武俠文學式微的重要原因。但這個問題的根本,其實是在小說的范疇里,這些新類型相比武俠,找到了諸如時空穿梭、飛天遁地等更自如地調用時間和空間的手段,有了將偏執化情感作更合理呈現的方式。但當小說費盡力氣尋找表達的方式時,這一切在詩歌中不過是最簡單的分行與意象就能解決的問題。
我已在華山坐成了一尊石頭
還是本來我就是片樹葉
在華山深處飄零
雨打也好風吹也好
——《華山往事》
這句是詩中的點睛之筆,寥寥數句,勾勒出了抒情主體的孤獨、迷茫,以及靈魂深處放逐自己的沖動。選擇枯坐,選擇浪費生命中的時間,這是不被世俗生活觀念允許的行為,但卻是在現代詩中經常出現的傾向與體驗。這說明武俠在時常被看成是一種類型文學的同時,與作為嚴肅文學的詩歌有著深層次的精神共鳴。事實上,很多經典的現代詩都寫某種日常生活中沒有的、極端化的情感,而這與武俠文學是相通的。換句話說,也許武俠文化的精神內核,正產生于詩歌所代表的抒情傳統。
江湖看似腥風血雨,令人想看淡一切,但它作為一個虛構空間,正因跌宕、纏綿,才成為無數讀者蹉跎一生,希望尋找到的精神寄托之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思潮進入中國,加之市場化改革對文學的莫大影響,純文學與類型文學、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逐漸變得涇渭分明。于是雖然武俠與詩歌存在著種種契合之處,但大多數詩人還是多少在潛意識中認為武俠這種元素“難登大雅之堂”。也許論及藝術手法和社會影響,閻志的《華山往事》和《空心人》比不上他書寫底層、時代、人生的作品,甚至未必能稱得上是詩人的代表之作,但是詩與武俠題材的碰撞,卻讓我看到了一種通向歷史和未來的巨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