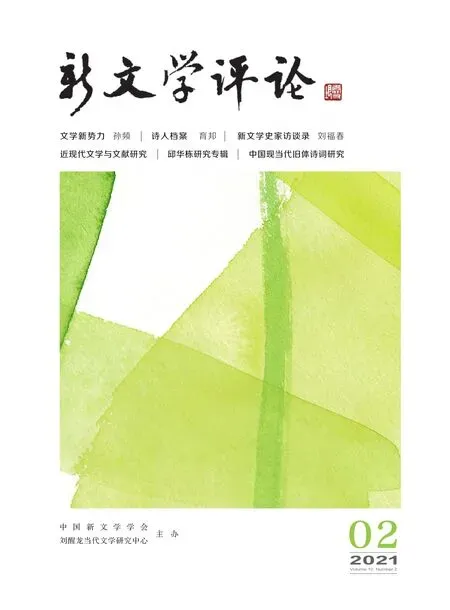懷舊的誘惑與風景:論閻志的詩
□ 張立群
為了能夠從紛繁的作品中清理出一條線索,本文選擇“向后看”的方式解讀閻志的詩。總體地看,閻志的寫作基本呈現了鄉村與城市兩個重要的版塊。這位從大別山以南羅田縣走出來的詩人,如今雖身在城市,但童年的記憶和距離產生的美感,都使其常常在有意無意的回望中將最真摯的情感獻給了那片土地,而從回望的角度看待其正在持續的詩歌寫作,恰恰構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一
也許,在閻志反復書寫記憶、向回漫溯的時候,他就已表達了對當下現實生活的某種疏離感。這一基于其作品文字的判斷,同樣也隱含著情感的甄別。對于城市,他寫過高房價、擁擠的人群,“二十歲前的記憶不屬于這里/在霓虹燈突然閃亮之前/我找不到剛才的自己”(《城市》);還有“一切與感情無關”的利益關系(《生意》),房屋拆遷后“變得無家可歸”的“我們”,只能退到城郊,多年后再次成為鄉下人(《拆遷》);以及打工者的最卑微與最簡單的夢想(《打工》)……對比城市書寫的緊張、直露甚至是冷靜的客觀化,一旦轉向故鄉,閻志的敘述就能讓人感受到一種純真與溫馨,“太陽的照射 蟲草的鳴叫/我不知道少年的我是否還在等待/關于二十歲的約定”(《夏天》);“情感的記憶板上 我們依然潔白”(《秋天》);“看見我的炊煙里的父親/很親切”(《看見》)……盡管沒有通過諸如“創作談”式的文字說明自己為何這樣處理現實和記憶的關系,但閻志已用生動的敘述表明了他的立場與態度,而這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在事業有成之后,依然沒有舍棄或曰有暇顧及詩歌。他將自己詩歌中最安靜、柔軟的部分留給了故鄉和土地,那里自然也成為其愛之彌深的詩意棲居地。
為了能夠加強記憶的誘惑與風景,我們還可以通過詩人面對“未來”時的態度來加以佐證。在一輯名為“遠方”的詩中,閻志首先寫到“明天”:“慌亂的行程/更加接近/更加難以企及”(《明天》);而后是《出發》中有“我們無法尋找 那片原野/那片金黃 從來都不屬于我們”;還有《未來》中的“我”,“一直心存恐懼/憂慮的目光從未游離過未來/一切是如此深不可測”。可以說,無論是出于“未來”的不確定性,還是出于命運的不可掌控,閻志在以詩講述未來時,總是呈現出某種憂慮甚至是一絲恐懼。既然只有不斷地出發才不會停留,既然只有不停留才能無限接近——然而那片原野、那片金色,從來都不屬于我們——那么,對未來的擔憂也會加重詩人完成一次又一次的精神還鄉。在“還鄉”的過程中,那片原野、那片金色,都會因曾經的經歷而與此刻的想象實現一種重合,進而在支撐起詩歌寫作的同時,完成一種心理意義上的滿足。
記憶中的風景當然不是現實,它更多是源于過去的經驗并通過想象完成。重溫過去、書寫記憶往往隱含著懷舊的過程,此時主體通過文字表達的風景其實是經過選擇、過濾之后呈現出來的——她們會集中在某一主題或某一類景象上,并且常常使用感官上的差異以區別不同的書寫。閻志曾經在《春天》里寫到“我想翻動故鄉的泥土/這氣息如此陌生/生長的氣息 如此陌生”;在《落在童年的雨水》《江岸》《平原》《視線》中反復書寫或靜謐或喧嘩的“聲響”,或黑或白直至各式各樣的“色彩”……調動多重感官描寫的手段,以視覺、味覺、聽覺等調節布景的變換。閻志一直渴望能夠寫出故鄉的各個角落和出走經歷的每個瞬間。現實生活的日趨繁華與富足只是加重了他的向往,并營造出他寫故鄉和寫城市時兩種截然不同的敘述風格。“沒有了/彩色的云 彩色的雨 彩色的風/也沒有了/金黃 金黃的麥粒//沒有了 那條通往森林的道路/也沒有了/姐姐們燦爛的歌唱//我的漫步停駐在冷漠的城市里/我的鄉村的行走/沒有了//純白的詩歌在最后響起/像一首安息曲 響起/我們的逃遁/正朝著我們的童年。”無論從題目,還是具體的表達,一首簡單的《挽歌》幾乎包括了閻志詩中的全部秘密。
二
當閻志在《大別山以南》寫下:“大別山以南的語言/來自這里修遠的道路/母親的蒼白/永遠如花朵/我們正是用這種語言來接近世界/并與世界自豪地交談。”詩人同樣期待一種聲音,講述成長的故事,同時他也很自豪地確證了自己的身份,一如他還寫有《我是農民的兒子》的詩篇。聯系詩人出生于湖北羅田縣,我們不難讀出“大別山以南”是不折不扣的實寫:大別山風景如畫,“盛長美麗的青草”,有值得銘記的歷史和現實。大別山挺立在安徽、河南、湖北交界處,為淮河、漢水、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包圍,“越過淮河/越過漢水/離家好遠了/再回首/還是大別山”(《還是大別山》)。可以說,大別山特別是以南的羅田縣,始終是閻志心頭揮之不去的記憶,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可以使閻志流連忘返、徜徉于詩歌之中,獲得心靈的平靜。他的創作總是將此作為寄居地并與此有關,“大別山 你在我走過的每個路口/又引領著我走近你”(《木蘭山發現》),從特定的角度理解,“心安即是歸處”恰恰可以作為其書寫的重要注腳。
顯然,只有飽含深情、發自肺腑,才會寫下那么多關于大別山的詩篇、誕生一本名為《大別山以南》的詩集;才會進一步對寫作加以分類,將90首詩分為11個部分,呈現詩歌表現過程中的深度和廣度。“風物”“山林”“土地”“人物”“村落”“生活”“童年”“傳奇”“鄉居”“豐碑”“故事”,很難說沒有具體主題或曰場景的重復,但這些明顯寫于不同時期的作品卻表達了閻志對于故鄉、鄉土、童年的向往與追慕——
面對純凈的鄉土和情感/我們紙折的思想和詩歌/顯得不堪一擊瘦弱無比/當我放下自我的時候/才發現河水正流入故土/我用鮮嫩的青草去對付/那片紫色的天空和人生情感
然后在春天的河流上/透徹地分析我們的鄉土/把所有的懷念所有的質樸/放進家里/在收獲的日子里我們重新開始/另一種思維方式
母親的炊煙已飄揚得很高很遠/讓我們拾起詩歌與鄉土/與暮歸的牧童和老牛/一起回家 一起回家
——《結局或者開始》
既然結局亦是開始,終點即是起點,那么在一個特定階段完成后,能夠留下的或者說重新開始的只能是返還與歸鄉,能夠推動生命年輪轉動的、進入一個新層次的也只是回家、回家。應當說:“大別山以南”作為現實生活的鏡像及精神替代品,映照著一步步走來的詩人和其坎坷不平、百轉千回的人生,自會對閻志產生源自生命深處的誘惑。雖說具體作品的書寫是在歷時性中完成的,但其呈現方式卻是共時性的:有多少寫不盡的“大別山以南”,就有多少說不盡的風景!
“大別山以南”有父母、兄弟姐妹,有山村、河流和一座座美麗的山峰,有傳說中動人的故事……因為在書寫風景的過程中,親情的嵌入往往會增添詩意,所以那些寫給親人的詩是閻志這一類詩中最感人的部分。“母親是一條船/父親是舷/我是上空那繚繞的云彩”(《蔭》),在另外的書寫中,“父親是山,一座盛長水杉的山”(《父親》),詩人總是用最親切、恰當的比喻,獻給自己的至親至愛的人。“歸途寫在紙上/是一行行寫滿深山的詩句/請原諒我的腳步已走進深秋”,“歸途已寫滿”,而“看不清是我此去的路途”,為此加重了我“沉沉尋你而去,我的歸途”(《歸途》)的程度,同時也加重了歸途的目的地指向。
三
現在說說季節吧——閻志的記憶之詩曾直接以春、夏、秋、冬為題,描述過懷想中季節。通過季節承載記憶、講述風景的變化,詩人顯然想表達一種差異性。像《春天》回鄉尋覓時觸及的“青草的氣息”和“發芽的花朵 含苞的雨水”;《夏天》中“陽光的氣息”與“你”有關,有情感的故事;《秋天》“田野開始荒蕪 疲勞不請自來”,但許多花仍然會在“秋天的田野開放”;《冬天》里則有“黑色的雪 灰色的思念”,廢墟上可以泛起“紅色的記憶”;還有《四季》集中展現四時的風景。沒有什么證據說明閻志書寫季節究竟是為了什么,即使和季節相關的字眼兒不時浮現在他的詩中。這種現象當然可以在集中起來后進行簡單的分析,在不加任何理論術語的標簽之余,我只是想將其作為一種進路,談談時間在閻志記憶之詩中的意義。
盡管由于文體形式的原因,詩歌中的時間不像小說中的那樣至關重要,因為詩歌的跳躍可以讓時間自由穿梭,也可以讓其隱含在敘述背景之后,從而“弱化”了時間的作用。但時間依然是詩歌結構的重要元素,因為時間可以容納更多敘事內容、增加敘事的寬度與空間。在近年來的寫作中,詩人曾這樣理解時間:“與過去永不相欠/與未來相遇。”時間是現實與未來的連接點,確切的時間意味著此刻之前的過去已成為歷史,而歷史是可以用來緬懷的。
從時間在詩歌中的意義看待閻志的季節書寫,我們是否可以首先將其視為簡單而又適當的時間單位?季節包含的時間不長不短,可以融進很多想象與情節,并在一個特定的場景證明詩人回憶時的細節:“在冬天里/每一片落葉/深合心意/綴滿爺爺手心的/不再僅僅是童話/那般單純”(《鄉村的冬季》);季節有流轉的規律,可以形成一個圓圈,無限地循環下去:“在冬季/你開始訴說著春夏秋的道路/那是怎樣一條廣闊的道路//我踏上夜晚/夜晚在夏天激動地抒情/或者歌唱。”(《在冬季》)季節可以是題目,也可以自由的鑲嵌在詩歌的句與行之間,而為數眾多的詩篇就這樣成為可以生長的過去,并在許多場景下實現了“彈性的增長”。
季節雖可以作為解讀閻志詩歌時間密碼的一把鑰匙,但肯定還有許多特殊的內容使其詩中包含更多內容。時間是經歷過的歲月,是記錄生活的重要標識,在回望之間,時間是距離,也是一個個生命的關節點。時間和諸如“大別山以南”的空間支撐起閻志的詩歌世界,時間的含義或曰種類繁多,幻化出不同的往事;時間可以被任意修辭,像以上所述的“季節”那樣可以被賦予色彩、情感甚至是心理原型。而一旦我們從更為遙遠的距離看待這些,一切也許會像閻志在詩中疑問的那樣:“在時間、空間以外/有沒有另一種方式度量我們的過去。”(《老去》)肯定會有這種質素,出自時間、空間并最終獨立于時空結構之外,因為當時空確定后,如何展現內心的情感世界又成為一個問題。“我們失去了許多不該失去的事物/惟獨沒有失去時間//我與你一起走進去/不要回憶/更不要時間/好嗎。”(《老去》)看來,在時間之外,還有一些秘密需要呈現,而此時,我們要做的或許只能是向閻志詩歌中更深的層次進發。
四
在懷舊的書寫中,可以讀出閻志對于詩歌的理解。“寫詩”可以記錄冬天如何變成春天,可以記住一些人的生日和名字,“我要寫詩 正如/我在一張紙上劃下的痕跡/不知不覺的時間啊 了無蹤跡”(《寫詩》)。通過文字的記錄,一些容易被遺忘的或是無法擁有的,可以留下來成為見證,在某一特定時刻重現記憶。但相對于創作主體,詩歌本身是不可捉摸的,詞語也是不可捉摸的,詩歌和詞語的魔力在于常常得意忘言、不可言說,所以,“我是一個失語者”,目睹著許多詩句和詞語在面前逃逸,卻無力留住、全部掌握(《詞語》)。想來被感知的詩遠比被寫作的詩要豐富得多,因為文字只能表達想象卻無法全部展示其妙處。與詩歌相比,語言又何嘗不是如此?通過寫作,詩人道出了古往今來所有詩人的困惑,是人說語言還是語言自己在說?沒有什么固定的法則,所以,詩人最好的表達方式是一直寫下去,通過語言盡力挽留屬于自己的體驗,即使時間無情地流逝,但終究會留下些許痕跡。
詩歌離不開人稱指代,尤其是那個曖昧又令人充滿遐想的“你”,詞語和語言也是如此,它們會因為“你”的出現而呈現出交流、對話的可能,顯出勃勃生機。“我們已經不能完整地表達/大多數事物在融合之后更加強大/唯獨你不是如此”(《語言》),這樣的“你”飄忽不定,但卻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道出了人與語言之間的關系;“你肯定知道/有一些細節被掩埋在落葉之下/少年的詩句 從未被吟唱/所以一切經歷過的/又好像什么也沒有發生/多么了無痕跡的/時間”(《詩句》)。此時的“你”,含義則有些復雜,乍一看來可能指代的是異性,不過因為題目和敘述中都有“詩句”字樣,所以在反復思考后將其理解為記憶或者是客觀的經驗更為恰當。當然,還有更多數不清的“你”,在訴說著古老的愛情故事,在保持著曾經經歷過的最純潔的詩意與想象。
我是在短詩《生活》和《童年的背影》中讀出閻志對于詩歌及語言的期望:他希望以詩歌寫出生活的理想,并以此記下漸行漸遠的歲月。“懷舊不永遠是關于過去的;懷舊可能是回顧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現代的需要所決定的對于過往世代的奇思幻想,對于未來的現實具有直接的影響。”也許,真的是“對于未來的考量”使閻志承擔了對于自己“懷舊故事的責任”。懷舊在向往過去的同時思考著未來,而為此,閻志的懷舊詩篇還有相當大的增長空間。
值得指出的是,閻志雖寫了如此多懷舊的詩篇,但其并為簡單沉湎于自己的世界。他的《挽歌與紀念》就是一部通過書寫記憶,觸及了詩歌作品本身以及環境、道德等很多問題的長詩。閻志懷舊詩的內容當然還有很多,比如,《閻志詩選》之“江湖集”中的《江湖》《華山往事》《空心人》就是對武俠故事的一次懷舊,那里有閱讀中的青蔥歲月,更有年少渴慕的俠骨柔情。總之,通過懷舊書寫過去、面向未來,閻志這位大別山以南的羅田之子應當還有許多往事沒有寫出。相信他還會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而這一點就足以值得我們珍視了!
注釋:
①見閻志《明天的詩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具體包括《明天》《清明》《出發》《未來》共4首詩。
②斯維特蘭娜·博伊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導言”第5頁。
③閻志:《后記·以自己的名義》,《挽歌與記憶》,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