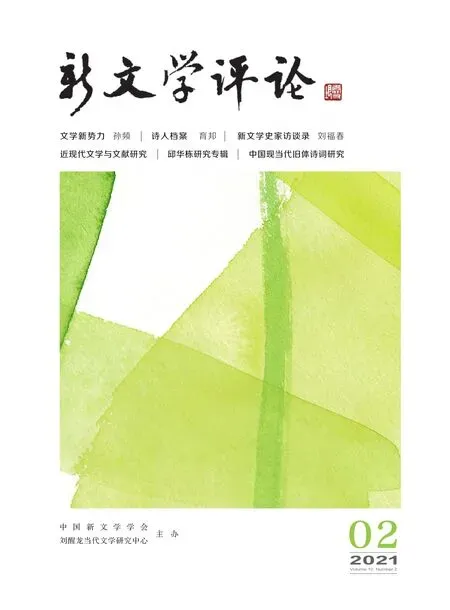主持人語
□ 劉大先
我最初閱讀邱華棟,是他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些以《手上的星光》為代表的描寫北京外鄉人、闖入者的都市題材作品。那些外地來京的青年主人公,內心雖不免忐忑與恐懼,但更多的是搏擊未來的激動與勇氣。嘈雜浮華的景象與糾結復雜的內心相互激蕩,顯示出人們對于現代化大都市的無限憧憬。此后,邱華棟以敏銳的直覺,觀察與描述日新月異的北京蓬勃發展當中出現的新現象與新人,陸續寫出了《時裝人》《公關人》《直銷人》《化學人》《平面人》《廣告人》《電視人》《環境戲劇人》等一系列以“都市新人類”命名的作品。新世紀以來,時代不一樣了,傳統制造業占據的地方,如今全部都變成了現代商業、金融業、傳媒業和網絡經濟業的地盤。這里過去都是一些衰落的國有企業的老廠房,像什么機床廠、木材廠、紡織廠、軸承廠、酒廠什么的,都衰落下去了。現在,老廠子通過土地置換和買賣,把自己置換到郊區去了,繼續茍延殘喘,十多年的時間里,在這些老廠房的地皮上,很快崛起的就是這些新的寫字樓和高級公寓建筑群了。在高級公寓里居住的,是這個社會新出現的中產階級和富人新貴們,他們就是這些新興行業的從業人員,白領、金領、職業經理人、老板和傳媒從業者、藝術家。他又以2007年《教授》這部長篇小說,為一個轉型的時代立此存照。這些作品從宏觀到細部、從建筑到人群、從城市規劃到情感與精神進行了全景圖式的展示,因為有著親歷經驗而具有了記錄城市變遷的史料價值。
那些當然只是邱華棟作品中最受關注的部分,他實際上還寫過一些建筑、電影與文學評論,以及歷史題材小說。他近幾年以歷史上十位俠客為題的中短篇小說集《十俠》在2020年出版,我讀過其中的篇章,覺得是以一種質木素樸而內蘊勁道的筆法在講述那些一再被講述的故事。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過:“人們需要這樣的故事,它們凝結著經過時間檢驗的智慧與經驗,為任何一個聽到的人提供教訓與啟迪,如同偶爾裹進飛蟲的松脂在歲月的沉淀中凈化了雜質,轉變成晶瑩剔透的琥珀,傳遞著久遠時代的信息。那些在故事原生時候的蕪雜、齟齬、荒誕、不合理乃至愚不可及的東西,都在一次又一次講述的過程中被錘煉和洗刷,最后鍛造成精純、堅固而不可磨滅的母題。不同的人們都能夠從中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東西,當他們第一次讀到這樣的故事的時候就感覺似曾相識,再次重讀的時候仍然能夠得到新鮮的見解,如同卡爾維諾所說,這樣的故事其實已經成為經典,它在時光中走過,對于它的闡釋和重述本身也形成了我們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它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對“傳統”的踵事增華與層疊累積的書寫實際上意味著人文的記憶與傳承。新近出版的《北京傳》爬梳史料、文史融合,我認為是一本“北京流變的雅正之書”。
邱華棟是一個吞吐量很大的作家。他成名極早,涉獵極廣,卻并未局限于某種文學批評所賦予的符號化概括(如“新市民小說”“新生代”“晚生代”)之中,而是依然勤奮寫作、多向開掘。面對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巨獸一樣的存在,批評的關注略顯不足,這個小輯約請了幾位青年評論家圍繞邱華棟其人其作就各自感興趣的點自主選題,奉獻給大家。
徐阿兵在全面掌握邱華棟創作歷程與實績的基礎上,重讀了他20世紀90年代的小說,從“人與物的關系的變化”中窺見北京乃至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物質與精神變革。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徐阿兵歸納出邱華棟的敘事風格是以不動聲色的“發現”造成現代性震驚體驗,在此基礎上,再揉入本土化的新奇人事、情緒化的城市經驗以及不失時機的反諷和幽默,從而使作品蘊含著巨大的社會現實與心理內容,并進而認為直至目前為止中短篇小說是邱華棟最高成就所在。我認為這個判斷是自洽而有力的。陳若谷則將邱華棟的北京書寫置諸世界上諸多都市的虛構和紀實的橫闊背景以及北京想象的深厚久遠的歷史脈絡之中予以定位,尤其就《北京傳》的視野審慎地提出了一種在已知與未知之間那種無法規約與范型化的生長性書寫,可以與“空間的生產”相并提為一種文學與觀念的生產。張凡、袁亞冰選取邱華棟作品中不怎么為人關注的地域經驗角度切入,認為他以“在地性”經驗為創作初源,發現并挖掘新疆這一地域文化所蘊含的表達空間,關注風景與生態、生存及死亡等話題。從鄉村到都市、從邊疆到中心的邱華棟,空間上的“位移”使他在當前這個碎片化時代不斷地拓展個人的創作視野和觀照層面,著意自然生態、成長主題以及邊地想象等層面來呈現對地域經驗的追憶與回望。《西北偏北》《夏天的禁忌》等再現了少年成長的灰色記憶,同時表現草原文明遭遇現代文明介入后的尷尬與無奈。基于史料而創作的歷史小說《賈奈達之城》以歷史事件為框架聚焦人物的內心世界,探索戴安娜夫人、賽麥臺等在特定情境下的心靈嬗變,表現對邊地歷史與過去的一種浪漫想象與建構。邱華棟超越性思維積蓄的創作力量旨在呈現一種現代話語表征和文化歸屬感,新疆故事于是也就成了普遍意義上的“中國故事”。江飛以中篇小說集《唯有大海不悲傷》為中心,認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是重審人與自然關系、思考終極價值、探究生態危機的“生態寫作”,從中闡發分析出邱華棟的生態美學:有意識地把“中國故事”由本土城市搬演到了異域山川,試圖確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有限度、有條件地反思和批判了“人類中心主義”,由此重建了人物的心靈境界,提升了小說的生態倫理意識和生態品格,為中國當代生態寫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和啟示。但同時江飛也指出只有認識到“生態的人”是文學表現的中心,生態寫作才有可能真正突破“人類中心主義”的窠臼,才有可能真正解決長期困擾生態文學的難題。
感謝四位作者的支持,相信讀者對于他們的見解與觀點,同意或者不同意,都會有所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