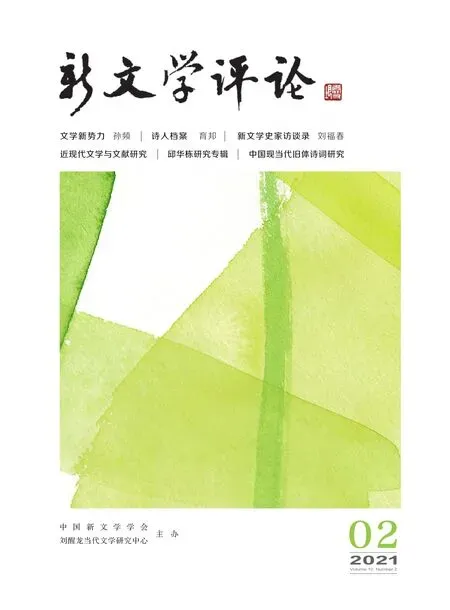主持人語
□ 陳子善 王 賀
比較理想的近現代文學與文獻研究,應該是對此時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不僅有所研究,且能在一定的理論高度,對此二者有所綜合。但長期以來,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弄潮兒所建構的歷史敘述、學術研究范式和價值判斷等因素的影響,“現代文學”在某種程度上被窄化為“新文學”,而“近代文學”儼然是“古典文學”的余緒、代名詞(其實至今仍在不斷發(fā)展,豈可僅以“舊體詩詞”目之?),不免影響了彼此的研究格局、實績。而本輯發(fā)表的四篇論文,既有依據新舊文獻資料,對近代文學尤其近代古典文學作出的專題研討,也有對現代文學文獻的發(fā)掘、整理與研究,皆可見出一定之特色。
王靜博士的《被遺忘的晚清詩人——許宗衡詩集版本敘錄及其集外詩作》,根據其自北京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地所查見的許宗衡詩集版本情況,對存世的五種許氏詩集版本予以敘錄。作者此前曾發(fā)表《許宗衡詞集考述》《許宗衡與晚清常州詞派的詩化問題辨正》等文,此文則聚焦于其詩歌創(chuàng)作,尤其側重版本學、目錄學的考察。此外,該文也整理了其新發(fā)現的許氏集外詩作四題(《春日雜詩》《晴》《感喻》《沈仲復秉成編修織簾讀書圖》),從而使得我們對這位被遺忘的晚清詩人的著述情況,有了更為全面、深入的認識。
趙友永先生的《從葉恭綽友朋信札看〈全清詞鈔〉的編纂歷程》,是依據近年來其參與整理的數十通“葉恭綽友朋信札”,尤其其中吳湖帆、張茂炯等人致葉恭綽信札,圍繞著其中不斷出現的《全清詞鈔》編纂問題所進行的一項研究。該文不僅還原了《全清詞鈔》這一近人所編清詞總集的人員分工、具體編纂流程等細節(jié),同時還指出葉恭綽等人關于《全清詞鈔》緣起、時間的敘述充滿歧突,須予辨正,澄清了其編纂歷程中的一些疑點。事實上,直至該書于1975年由中華書局香港分局正式印刷出版,主事者葉恭綽尚不及見之。也正是由于眾多詞人、學者共襄盛舉,才使得這一總集最終完成,蔚為20世紀詞學史上的一樁盛事。
李杭春女士的《新發(fā)現郁達夫的兩篇“未完稿”》,整理了郁達夫致何勇仁(識夫)函全文及其譯著單行本《勇毅果敢之邱吉爾先生》。前者雖已有研究者考證,指出《汗血周刊》第15卷第7期(1936年10月10日上海出版)刊何勇仁《郁達夫的實干——一封論國防文學的信》,收信人為廣東四會人何勇仁,寫信時間當在1936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之間,但此一刊本并非完璧,而本文作者在《國防文藝》匯刊第1集(1936年出版)發(fā)現了此信全文;后者則是首次公之于世。郁達夫譯著單行本《勇毅果敢之邱吉爾先生》系一“非正式出版物”,雖然其印行時間、地點等不詳,但其中部分文字曾揭載于1940年代初期的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新編《郁達夫全集》亦據此選入其“未完稿”,但該譯著全文的發(fā)現,則對此作出了補充和完善,為郁達夫南洋時期文事再添一注腳,順次作者也糾正了《郁達夫年譜》等論著存在的一些史實訛誤。
徐強教授的《黃裳致范用書信系年推求——〈來燕榭書札〉考釋之二》,系其對黃裳書信集《來燕榭書札》考釋的系列論文之一。作者此前曾發(fā)表《黃裳致楊苡書信系年重考——〈來燕榭書札〉考釋之一》,本文則專門討論黃裳致范用書信作年、編次等問題。正如該文指出,由于種種原因,《來燕榭書札》所收信件的日期標注多所訛誤,因此,該文對此集所收黃裳致范用書信之作年逐一推求、考證,并將各信按其寫作時間重為董理、編次,為理解這批材料的原始面目乃至更進一步闡釋其文獻史料價值,提供了必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