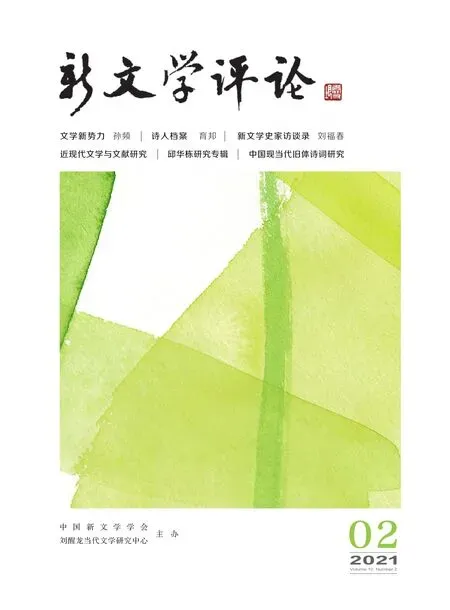作為“專業(yè)”的中國現代文獻學可能嗎?
——劉福春先生訪談錄
□ 劉福春 李 哲
李哲(以下簡稱李):
首先想請您就一個基本問題做一些解釋。最近這些年,大家越來越多地用“文獻”來界定您和諸多同行的工作,但在早些時候,大家包括您自己都愛稱呼自己是“史料工作者”。那么根據您具體的工作經驗,這兩個詞的區(qū)別到底在哪里?劉福春(以下簡稱劉):
其實“史料”和“文獻”這兩個詞一直在用,它們的區(qū)別一定是有的。從理論層面,好像也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我可能更想講的是這樣一個過程,特別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進文學所那時開始的一個變化。這不是一個理論層面的問題,而應有一個時間線索的梳理。其實最早的時候不是叫“史料”,而是叫“資料”。那個時候做這樣(研究)的一些人,大概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稱呼,就是“搞資料兒的”。在“文革”那個時候還有一個東西叫“材料”,“材料”跟“資料”好像又不一樣,“資料”有點中性,“材料”好像是有意在做某個人的“材料”,這個說法當然是不太好的。我到所里工作的時候,“材料”的說法一般不會用了,當時更多使用了“資料”這個說法。比如說那個時候像咱們研究室老的一代,他們就不大說“史料”,說自己是“搞資料兒的”,包括咱們做的那套《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也是用“資料”的說法,而幾乎沒有用“史料”。我想后來顯然是覺得這個稱呼有點太輕了,就更多使用了“史料”的說法,像馬良春他們出書,都用“史料”取代了“資料”。到八十年代后期,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這個學會在最初成立時以研究現代文學的人為主,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1988年10月在上海召開了首屆“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那次會議人還是挺多的,像臺灣的秦賢次等都來了,還有香港的學者。“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這個名字現在大多數人都叫不好,“史料學學會”是個有點別扭的稱呼,在“史料”后面又加了一個“學”,好像如果不加這個“學”,就覺得它的理論成分不是很高,我覺得這跟我們工作的方法和自信心還是有一點關系。最近這些年,“文獻”的說法更加流行了。我為申請國家社科重點項目去查了一下,發(fā)現那里面的題目已經很少用“資料”了,“史料”偶爾也有一點,但是更多的是“文獻”。我覺得從“史料”到“文獻”的變化當然可以從理論層面來進行辨析,但更多還是一個實踐問題,跟大家對這項工作的重視度以及我們自己的“自信”有點關系。現在,我當然覺得“文獻”比“史料”更加正規(guī),或者說更加完整龐大一些。史料嘛,它就好像更小一點。這是我的一個感覺,從理論的層面上我沒有更多的想法。李:
這個太有意思了,也牽涉到很多特別重要的學科史和學術史問題,也很值得從歷史和理論層面再做一些辨析。劉:
我覺得做史料也好,做文獻也好,大部分都還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一個學科成熟,它確實是需要理論方面的一些思考和建設,但是我覺得可能更多的還是一個操作層面,即具體怎么來做的問題。所以我常常說我更像一個廚師,但是這些年逼得你不斷要闡釋一些什么美食理論。我可能會把菜做得還可以,或者做得很專業(yè),但是你要讓我在理論上說得那么清楚,或者要從什么營養(yǎng)學方面再說出一些話,那就說不上來。我寫的好多所謂“理論”文章都是跟我實踐有關的感想,我覺得它缺少一個在理論層面上對這個學科的系統思考,這本身就是我的不足。李:
“史料”“資料”和“材料”的問題,是否跟七八十年代之間中國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狀況的變化有關?這些詞背后是否對應著當時人們一些特殊的心態(tài)和感覺?比如“資料”在當時就常常和“情報”連用……劉:
你講的這個讓我忽然想起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臺灣做資料、做史料的這些人都來大陸交流了。記得九十年代初,來了一位臺灣的詩人,見面當然談一些詩歌的問題,沒想到他說自己對臺灣那些搞資料的人特別討厭,原因是他們搞得太細致了。我當時很驚訝,搞資料肯定是越細越好啊,但那位詩人說那些搞資料的太氣人了,他們連哪個詩人哪個作家是黨員都寫得清清楚楚,這不給國民黨提供情報嗎?李:
沿著您剛才說的線索再提一個問題吧。從“資料”到“史料”再到“文獻”的名稱變化,是否也伴隨著我們這個學科不斷“規(guī)范”的過程?劉:
我覺得這個跟一個學科的成熟或者叫獨立還是有關系的。因為過去做材料、資料,還是一個附屬的關系。后來稱呼雖然變成“史料”,但還是會附屬到“闡釋”或理論研究的后面。但我覺得,史料和文獻工作更多關系到求真求實的問題,它還是應該和理論闡釋區(qū)分開來,它們各有各的目標和方法。李:
史料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總是占有一個位置,一般研究者不可能不利用史料工作者的“成果”,但大家對史料的態(tài)度在各個時期卻有很大的不同。作為資深的史料工作者,您對這種態(tài)度上的變化是否也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劉:
我覺得變化最大的還是發(fā)生在最近這些年,大家對史料工作的整個評價變高了。當然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國家社科基金,這樣一個傾向性的東西不能不說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我看了一下國家社科基金里的項目,特別是重點項目,很多題目都是“整理與研究”,與“史料”相關的似乎更容易申請成功。但你看那些題目,“整理”后邊還是要帶一個“與研究”的尾巴。所以我就想問,如果只是做一個“史料整理”,能申請到基金嗎?其實對我們來說,“整理”本來就是“研究”,沒有“研究”又談什么“整理”,所以大家還是沒有做出很好的區(qū)分。李:
史料整理工作的從屬性應該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吧。劉:
是的。比如我們常常說“資料熱”或者“史料熱”,其實最熱的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時候咱們文學所(主要是現代文學研究室)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就是一個國家級的社科項目,當時各個高校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好多都參與了工作,在當時影響是非常大的。不過仔細看就會發(fā)現,很多研究資料還是作為“副產品”出來的。比如有學者要撰寫《冰心傳》,前期要收集資料,所以捎帶著編出了《冰心資料研究》。就是說,他們的資料工作從緣起、觀念和具體操作上都是服從于“闡釋”的。所以我為什么總是在考慮學科的獨立問題,因為這里邊確確實實有這樣的問題。雖然大家都做了,做了那么多,但是真正把心思都放到這上邊的人并不是很多。李:
您覺得史料文獻工作從屬性問題是什么原因呢?劉:
一是大家對“史料”有一個評價,好多研究者心態(tài)上覺得你本來就是服從于研究的,而且你們這些人只能是給我們“做資料”的;二是在成果體現上,成果出來的時候,我們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評價標準會帶來很大的問題,這個跟“古代”學科是完全不一樣的。剛才提到的“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成立最開始還是以“現當代”為主的,后來“古代”的逐漸加入進來了,到后來開會的時候,“現當代”就成了一小撮了。這里有一個不均衡的問題,人家有專門的古籍所,資金充裕,也有自己的評價標準,跟人家相比,我們現當代做史料的這些人包括我們的成果,我覺得在評價上肯定是不夠的。另外反過來講,也不能不承認,我們所做的這些成果,跟“古代”的相比,專業(yè)性還是差一些,這里確確實實有一個學科建設的問題。李:
您剛提到社科基金偏重于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然后一下子出來這么多的題目和成果。但也正如您所說的,我們確實是水平不如人家古典文獻,那么我們要怎樣提高我們的水平?其實是需要更多的人能投入進來,你東西出來了,然后在大家的評價之中再提高規(guī)范的要求。所以恐怕還是要呼吁,應該承認史料的整理或者說文獻本身的價值,這其實是我們提高水平的一個前提。劉:
成果的評價問題確實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確實就是專業(yè)性的問題。史料文獻工作現在一下熱了,很多人在做,它仿佛忽然變成了一個非常容易操作的東西。但是就我見到的一些成果來說,真不能說是專業(yè)的。大家都熱心來做,這當然是好事,但是不是你只要想做就能做,我覺得這可能不是那么簡單的問題。比如說我見到有一些還比較大型的東西,從文獻的專業(yè)角度來看,還是非常成問題的。李:
您能圍繞這個問題從經驗層面具體談談嗎?劉:
比如近些年出的比較大的那些影印的(資料),我當然覺得非常有用,總比沒有強。但如果從專業(yè)上考慮,就應該有更高的要求。比如我想做一個關于詩歌的影印資料,那我就必須對詩歌有專業(yè)的了解,我得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版本,這個版本我在影印時必須找到放進去,而不是說現在我能找到什么就往里塞。再比如,當時的一些出版物后邊有好多廣告,但我曾見到一套影印資料,居然把廣告都刪了。還有就是封面。很多影印資料會把封面弄得非常小,就像咱們在網上看的那樣,幾乎讓你看不到封面。我跟李怡老師也在做影印資料,我費勁比較大的就是找封面,因為封面殘缺得太厲害了。我找到的書如果缺封面,我會盡量去很多圖書館找,把那個封面補上,因為我覺得那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才能把資料作為一個“整體”來表現。還有這幾年去世的作家,對他們的相關資料也在整理,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從專業(yè)上來考慮,還是有很多問題。有的資料編輯者介紹作家去世的消息,只說來自新華社,來自《文藝報》,但《文藝報》哪月哪日登出來的,都不清楚。這些其實非常重要,作協認為非常重要的作家,那是第二天或者當天就能見報的,但如果他們認為不是重要的作家,就會扎堆(報道),集體發(fā)一些,或者發(fā)的位置不顯眼,等等,這些都是“很專業(yè)”的信息,如果以后有人研究的話,能根據這個看出當時對這個作家的評價。我覺得要讓更多的人關心這個,讓真正做的人能夠成為一個專業(yè)人士,往專業(yè)上做。現在這個東西忽然時髦起來了,大家一哄而上在做,這種做法我覺得可能對于文獻的建設未必很有利。李:
您談到當下資料整理工作的專業(yè)性問題。您能結合自己的經驗說說史料文獻工作完整具體的過程嗎?尤其是在過去,不只要動手翻書,還要全國各地去跑圖書館,“動手動腳找材料”,這跟今天數字化時代的專業(yè)性有很大區(qū)別吧?劉:
那個時候確確實實要“動手動腳”,只動手還不行,必須動腳,就是你說的“跑圖書館”。我在做新詩集目錄的時候,跑了五十多家圖書館,也看了一些個人的藏書。那個時候大家做得還是比較辛苦,每一條資料那都是從報刊里邊翻出來的。那時候可以看原書刊,但是報紙只有縮微膠片,看那個其實是挺費勁的。要坐到那兒一個上午,一卷一卷對著看,有的時候看過了又倒回去。那時候沒有電子文檔,全部是手工勞動,你要去跑。李:
那時候找材料難度最大的是什么呢?劉:
難的就是人家不給你看。當時好多圖書館的公共性還不夠,基本上是拒絕給你看,所以我還記得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個時候咱們所里有一個北大的借書證,因為咱們所前身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雖然分開了,但是咱們還有一個證。那個證所里好像只有一個,但是你要去的話,你可以拿著那個證去,你可以跟北大的師生一樣憑證看書。我記得當時去他們那里借詩集抄寫目錄,由于一次借閱的冊數有限,只能是管理員從庫里取出幾本詩集,抄完了,再去找她取。有的詩集里邊根本沒有幾首詩,那時候詩集也薄啊,一會就抄完了。管理員當時就非常憤怒,說:“你這么反復地拿呀,自己進去找!”那是我遇到的讓我最開心的一次“憤怒”。他們的書庫像咱們圖書館,一進去就發(fā)現了好多在別處發(fā)現不了的東西。所以后來我經常盼著什么時候她再“憤怒”一次,但實際上也就只讓我進去那么一回。不讓看歸不讓看,但一旦親自看到,你能接觸到原始文獻還是會有很大的好處。前些天四川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開了一個“70—80年代校園詩歌群落學術研討會”,同時辦了一個展覽,我拿出了一些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原始的非正式詩歌出版物。我問參會的學生:“你們看復印的和原始的刊物有什么樣的不同?”他們好像回答不出來。其實文獻是否“原始”不僅僅是清楚不清楚的問題,還關系到對那個時代的感受。
李:
能再具體說一說嗎?劉:
比如那天,詩人鄧翔拿來一本1983年的《第三代人》,這個刊物很重要,因為跟所謂“第三代”有關系。但如果你把它電子化了或者重新影印了,你就不知道它原來是什么樣了。當然,你能看出來它是個油印的,但是你很難感受它當時是一個多么“艱苦”的東西。鄧翔當時沒有錢,他用的紙張都是非常薄的,油印只能單面印,雙面印就透了。所以那個紙你一拿過來,放到手里邊,你就感覺你面對的就是那樣一個時代。如果現在把它影印了,重新出版了,那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了。還有,那個時候它為什么小本為什么大本都是很重要的信息,但現在如果重版了,開本大小也會有一些改變,那重要的信息就流失了。再比如,你看抗戰(zhàn)時候的文獻,拿來的時候會發(fā)現它就是土紙,一摸都輕飄飄的,是不是?所以這些感覺現在從網上看是很難再有了。李:
但我們現在確實進入數字化時代了,搜索引擎、數據庫確實在研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您對這些怎么看呢?劉:
怎么能更好地利用數字化,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問題。現在很多所謂網絡詩歌或者網絡文學,還只是把紙質的“搬”到網上去,這種機械的“搬”其實會出現很多錯誤。有的是不大認識繁體字,把字弄錯了;還有就是把從右向左的書名弄反了,就永遠查不到了。除了這些錯誤之外,這種“搬”也沒有充分利用網絡的特性,它跟網絡特性的關系也沒那么緊密。其實我和四川大學的同事也在思考,如何利用網絡的優(yōu)勢,而不是簡單地把我們現在的文本“搬”到網上去。比如將一首詩放在網上,只要我點擊這首詩,就能出現與這首詩相關的各種信息,朗誦的錄音,相關的影像資料,包括關于它的評論等等,都能充分顯示出來。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現代文學文獻學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不僅僅意味著我們的整理對象是現代文學,也意味著我們的整理方法也應該是“現代的”,能夠不斷地更新。所以文獻的數字化,其實還是一個專業(yè)性問題。好多做文獻數據庫的公司都不是很專業(yè),他們會請一些沒有經驗的年青人,給文獻分類時分得亂七八糟,好多書都找不到了。再比如文獻錄入,其實也是非常專業(yè)的問題。在李怡老師的重大項目里,我負責做詩刊目錄,我就跟大家說,目錄呈現并不是簡單地把目錄復制下來,因為一本書或一個雜志的目錄和它的正文常常是有區(qū)別的——有的目錄有正文沒有,有的正文有目錄沒有。再比如詩歌刊物中有的詩歌是組詩,它在目錄里邊呈現的只是組詩的題目,但這組詩究竟包括了哪些詩,目錄里是顯現不出來的。還有“詩四首”“外二首”之類,也是如此。但現在很多人做的時候,就簡單地把目錄頁復制一下,只要沒有錯誤,能把繁體字都認識清楚了,就算“專業(yè)”了,實際上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李:
我感覺您強調的專業(yè)性,其實已經超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范疇了,文獻的“專業(yè)”反倒給我們提出了許多“跨學科”和“跨專業(yè)”的要求。所以再提一個小的問題:作為一個文獻的使用者和研究者,我們怎么能夠讓文字文獻的數字化保留更多我們紙質文本的歷史性,或者說,那些紙質文本的社會性包括它的物質性,怎么能夠更好地在網上呈現出來?有沒有可能防止那些東西被模糊掉,影響到研究者對文獻本身的認識?劉:
我覺得首先要考慮的還是完整性,在關注某個特定文本的時候,也不應忽略和它相關的信息。比如某一首詩,它所發(fā)表的報刊我要關注,但從文獻學的眼光來看,我要知道它是放在頭條還是放在末尾,是否是補白,還要看和它相關的這一版里還有誰的東西,甚至也不能忽視它前面和后面的相關部分。這在五六十年代會非常明顯,比如某個詩人的某首詩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當你翻看前面的時候看到頭版有黨中央的聲明,那么兩者就可能是有關聯的。有段時間我特別想讀《人民日報》,但那個時候讀原報不方便,就在網上看,開始覺得也挺好,但后來就不讀了。為什么?因為那時候網上的《人民日報》相當于只是一個“選本”,一篇一篇地看,我想知道同一版都發(fā)了什么就很難了。但現在就有技術了,有的網站可以把條目單獨拿出來放大,能夠看到整版的版樣,這其實是可以做到的。所以電子資源怎么能對文獻完整呈現是第一位的,此后才能討論如何更豐富、更立體地呈現,但第一步現在都很難,“完整”這一塊都沒有做到,所以我們的專業(yè)之路還是很長的。李:
我自己感覺,您的文獻整理工作有一條非常核心的準則,即追求完整性,對材料應收盡收,最大限度保存歷史原貌。這條準則說起來很樸素,但一旦著手去做又有很大的挑戰(zhàn)性。而且相比“現代文學文獻”,您最近文章討論的“當代文學文獻”可能更會遭遇這一挑戰(zhàn)。在“當代”的情境之下,所有的“文獻”并沒有成型,而且處于不斷變動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所以當我們對它做整理工作時,“全”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必須要有所選擇,而且無論如何也會有一些選擇的標準。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全”的理想追求和“選”的現實標準之間,是否會存在張力?您作為史料文獻工作者,又如何在具體操作中處理這些問題?劉:
我覺得作為一個文獻工作者應該是求“全”的。但是我非常清楚,我根本不可能“全”,而只能向“全”努力。我覺得文獻工作盡量不要去“選”。我在做“編年史”的時候,難度最大的就是選擇問題。有人說“文學史”應該是越來越薄,但“薄”也應該建立在“厚”的基礎上,或者說“全”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你怎么“選”都是有問題的。這里面可能有向度的不同,寫“史”的話當然要有選擇,不可能把那么多東西都放進去,但是作為文獻的話,我覺得第一要完整,即求“全”。但實際上這只能是一個理想,從根本上是做不到的。李:
比方說您做新詩文獻,肯定是以應收盡收為準,這可以說是追求“全”。但把“詩”從眾多的文學作品中拎出來,或者說把“新詩”從眾多的詩歌作品中拎出來,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為是另一個層面的“選”呢?劉:
就拿我做的“編年史”和“詩集目錄”來說吧,這就體現了兩種不同的工作原則。“編年史”雖然有文獻的意義,但是它的目標還是做一個“史”,這就要有選擇,如果沒有選擇的話,我沒有辦法把它做出來。但選擇非常困難,首先就是文獻不全的困難,比如說詩刊,詩刊出了多少種,每一種出了多少期,這些都不清楚,我想盡量把它做清楚。在實際工作中,在做“編年史”的時候,主要還是一個選擇問題。這“選擇”有兩個方面的困難:一個就是我曾講過的,我常常擔心由于我的選擇遮蔽了書刊的原貌,又害怕因為我的疏忽遺漏了可能最有文學史意義的事件。這畢竟是一個“編年史”,而不是一個“敘述史”。比如一本詩刊,因為你一“選”就可能把一個刊物“選”得面目全非了。假設我的選擇是“對”的,一個很爛的刊物,它可能只發(fā)過兩首好詩,都被我選進來了。但人家看我的“編年史”里面對這個刊物的記錄,就會覺得這刊物厲害啊,水平這么高,可實際上它就那么兩首好詩,那就等于說我的選擇就把刊物的原貌遮蔽了。還有一個困難是因為我的選擇可能會漏掉很多更有文學史意義的東西。所以我的“編年史”在處理刊物時用了兩種方式,先是不“選”,刊物推出的頭條我一定要記錄,盡量地保留一點原貌,然后再有我的一點發(fā)現和選擇。所以嚴格地講,“編年史”不是一個文獻的著作。
實際上我更感興趣的是我做的“詩集目錄”,當初叫《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詩歌卷》。這個書目原本是有注的,出版的時候因為要與其他卷體例統一,所以把大量的注都給刪掉了,有點可惜。詩歌卷跟其他卷最大的不同,就是那里邊有大量的注。注的是什么?就是我將目錄與正文進行了對校,把二者的不同處都注了出來。還有詩集的各種缺項,比如有的沒有時間,就要根據其他資料補充。當時為什么我會跟那些詩人通信那么多,好多都是在確定這些問題。詩集沒有時間,請詩人大致回憶一下,根據詩人反饋回來的信息,我就在下面加一個注釋。我認為“詩集目錄”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那里邊沒有我的選擇,我見到的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比如目錄是有序的,正文沒有,我會注上“所見本未見序”。“詩集目錄”不用我來選擇,它收了什么詩,我一點選擇都沒有,也自然沒有選擇的痛苦,我覺得這才是文獻。我個人更喜歡“詩集目錄”,但是沒辦法,好多人都對這些東西評價不高,總覺得是“編”出來的。
李:
您在那篇討論當代文學文獻的文章中也提及了特殊文獻的問題,在我們的研究中,這些材料的使用是否有些需要注意的方面?劉:
這些特殊文獻,還是要看你在哪個方面使用,總的來說,那個時代留下來的文獻,我們必須要經過一些辨別。傳統文獻學有辨?zhèn)危敶墨I可能無法直接稱之為辨?zhèn)危俏矣X得還是需要辨析,你直接拿來作為“信史”肯定有問題。我覺得這里有兩個層面,一個是當初公開的一些文件,這些文獻就不用多說了,我覺得我們大家都經歷了,都知道這些文件不能直接使用。還有一個就是現在發(fā)現的大批檔案材料,這肯定有助于我們的研究,但不加辨析也是有問題的。比如說檢討文獻,檢討的動機和過程都很復雜,比如有的人就是要不斷地檢討,一次檢討不合格,就得再檢討,越來越上綱上線,有的要檢討好長時間。還有就是揭發(fā)文件,揭發(fā)者的心態(tài)也完全不一樣,有的混混過關,有的是想把個人的“私貨”也夾雜進來。這些都是非常復雜的問題。這里還牽扯到一些其他問題,如版權的問題等。古典文獻做李白、杜甫的資料,很多隱私啊、小道消息啊只要可靠都可以用,但我們在使用現當代文獻時很多就會受到版權限制,版權所有人不準你用。很多當代作家的問題,我們沒法說等到版權失效了再來做,我們等不起,但一旦要用,就會涉及版權以及倫理問題。如果材料涉及好多個人隱私,是不是都能拿到研究層面直接使用?其他關聯的問題還有很多,我覺得都需要大家認真討論。當我們用當代文獻去敘述歷史的時候,問題可能會更多。我做“編年史”做到最后的時候,最不敢用的一個詞就是“真實”,越做我覺得離真實越遠。我雖然用了大量的所謂第一手資料,我想要達到的目的是把一個已經被簡單化的歷史重新還原,還原出它的豐富性,但是能夠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心里邊也沒底,我不認為那些東西全部是真實的。
除了“文本”之外,還要跟“人”有大量的接觸。這是現代文獻與古代文獻的一個不同。這有利于我們的文獻收集,但也會遇到一些問題。比如有一位詩人,我當時找他的詩集,找來找去找到一本,但看他當時出版的關于自己的介紹,他有好幾本詩集。我給他寫信,他也告訴我他有什么詩集,可還是找不到。因為畢竟是老先生,我也不好意思問得太直接,就寫信給他問詩集的出版社,他回答說:“我從來沒有說我出版過那些詩集呀?我只是說我有我自己編的詩集。”也還有另一種情況,詩集已經出版,但詩人自己卻忘了。我最近在《新文學史料》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談馬加的兩本詩集。我當時問過他,他說,“我告訴你吧,詩集根本就沒有出出來”,還告訴我沒有出的原因是如何如何,但后來我跟他說,我在圖書館見到了他的詩集,他聽了又很高興,還讓我?guī)椭陀 ?/p>
總之,我覺得這些所謂的歷史文獻,包括檔案,公開的不公開的東西,都必須要辨析。此外還涉及史料文獻工作中的“拾遺補缺”問題,有些問題需要討論,比如現在網絡上有的是不是還要去補,是補網上有而全集沒有的東西,還是補網上沒有的東西,等等。
李:
這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在當下究竟應該怎么界定“佚文”?劉:
這個問題很復雜,鼠標一動就能找到的東西,是不是還叫佚文?另外,全集里沒有的也不能直接稱之為佚文。比如卞之琳,他的好多東西文集里都沒有,因為在編的時候,他自己說他那些東西都不要。還有,當你找到一篇文集或全集中沒有的詩文,要確認為某個作家或詩人的佚文是需要辨析的。當初我編《牛漢詩文集》的時候就找到一首詩,署名為“谷風”。那個時候牛漢用“谷風”的筆名寫了很多詩,但這一首讀起來就不大像他的東西。后來我就問他,他連看都沒看,直接說“我不可能在那種刊物上發(fā)”。因此今天如果只是按照筆名去找佚文,可能會有很多的問題。“拾遺補缺”,這是一個非常需要功夫的工作,并不是簡單的工作。而且現在有一些這類的工作是從小到小,我希望能從小到大,從一個小的發(fā)現引申出大一些的問題,當然不能說必須就是宏大的問題,但總要大一些,這當然有難度。現在“文獻”這塊有點熱,但我覺得我們做文獻和做史料的人自己要有一些反省。我們現在做文獻的條件還是比過去好得多,應該努力有一個從“拾遺補缺”往“系統整理”的邁進。并不是說“拾遺補缺”不需要,但我覺得更需要的還是系統地整理,把那文獻做得更大一些。
當然,也不能說越大越好,“大”本身也應該有標準。我們現在做得太容易,常聽人說“在某某方面積累了幾百萬字的資料”。在這方面我還算個專家,我想說,幾百萬字太容易了,帶著學生就能做,用鼠標點出幾百萬字并不算困難的事。但重要的是,在網絡之外,你究竟又增加了百分之多少的新東西。哪怕增加10%,就很可以了。但現在大家不管這個,好像幾百萬字就了不得了,可這幾百萬字都是大家能找到的。我覺得這里應該有一個標準。
李:
當代文學文獻工作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文獻整理工作的對象并不是現成的文獻,而是正在生成過程中的“文獻”。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劉:
首先還是要強調文獻工作的眼光,尤其是包容度,就是說把這些東西先留下來,不要急著做價值判斷, 如果過于強調價值判斷,就等于是在做“選本”,這會傷害我們以后的研究。好多工作可能是“前無古人”的,前面沒有人做而我們做了。但我們還應該重視那些“后無來者”的東西,如果你現在不做,或者說現在沒有一個文獻學的眼光,你就永遠把它失去了。好些東西,你當時認識不到它的價值,后來再找那就費勁了。比如當時可能一個訪談就能解決的問題,但時間一旦過去就不可能那么簡單了。其實訪談也是很需要專業(yè)性的。現在訪談也常常被當作最容易操作的東西,常常有人拿著一個訪談提綱,就“放之四海而皆準”了。跟人家說你談談你的學術經歷,連人家做什么都不知道就訪上了。這還是一個專業(yè)性的問題,我要訪談,我就必須對訪談對象有深入了解,而且能找出最關鍵的別人訪不出來的問題。我最近整理謝冕老師的東西,他被訪談過好多次,但不少人連謝老師是什么樣的人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很有名,寫過《在新的崛起面前》,其他的也沒有深挖,也挖不出來,所以做出來的東西大都是千篇一律,不痛不癢的。李:
當代文獻的工作確實和古典文獻有所不同。劉:
做當代文獻,其實要求更高。古典文獻當然非常難,需要進行歷史考古,而當代文獻既要考古,又要同步追蹤。這時候真的不能簡單做價值判斷,要有更寬容的態(tài)度,盡最大可能把文獻保留下來,經驗也好,教訓也好,都是如此。比如我的書目,已經做得夠包容了吧,收錄的標準是只要“成書”就收,我也不必選擇,詩寫得怎樣我也不看,主要看版權頁就好。但實際上還是會有遺憾。比如說當時對油印的書刊,我就沒有重視,只有北島等幾個詩人的油印詩集放進去了。而現在做這個課題,我才發(fā)現油印太豐富了,而且這些東西現在“搶救”就有點晚了。如果20年前有這個意識,會有更豐富的收藏。我覺得這真的需要一個文獻工作者有更專業(yè)的眼光,或者是更包容的心態(tài)。不能只是“選”,我真的最怕選,看到選本就頭大,因為你選就遮蔽了好多東西,而且這選本會讓別人上當。李:
我們那會兒上學寫論文的時候,老師就要求注釋一定要引用原刊,實際上已經有很多整理出來的東西了,但是你不能用那些東西,你一定要用原刊,如果用別人整理好的本子,就說明你沒有用功。這是讀書時候的一個狀態(tài),但是不是也反映出對那些整理出來的資料的不信任?劉:
很多東西確實是有問題的。如果說真正有一個高度專業(yè)性的資料集,為什么不能用呢?為什么你要去重復勞動?但是關鍵的問題就在于我們是否專業(yè),是否值得信賴。李:
這個問題在網絡上電子資源上可能會更加嚴重,讀秀電子書中有些書的版權頁和封面都會出現不統一。劉:
知網上也有一些錯誤。刊物有季刊、月刊,還有上半月刊、下半月刊,期數的標法不完全一樣。比如《詩刊》,有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雖然一年實際上是出刊了24期,但期數是2020年12月號上半月刊和2020年12月號下半月刊。在知網上我見到是把期數順序地排了下來,《詩刊》2020年12月號下半月刊成了2020年第24期。李:
這就引申出一個關于何為原始材料的問題,您剛才說自己當年到圖書館看原始材料,其中可能包括某本詩集的初版本或初刊本等等,但今天這些東西可能被數字化到讀秀或大成老舊期刊之類的網站上,那還算不算原始資料呢?還是說它們應該算另外一個“版本”?劉:
有些特別的研究,如果你不看真正的原始資料,可能就不會意識到,比如我剛才說的紙張和印刷等問題。我覺得你剛說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電子資源做得不夠專業(yè),如果真正專業(yè)的話,我覺得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原始資料。問題是專業(yè)性不夠。張秀中有一本詩集叫《清晨》,這本詩集缺少封面和版權頁,網上有的數據庫也不查工具書,簡單地依據該書代序確定書名是“月下的三封信”,導致很多人查《清晨》時根本就查不到。有不少的書都沒有原汁原味地把原始文獻呈現出來,比如書的版權頁有時候在前,有時候在后,但在數據庫里就把它們全弄到前面,或許是認為這些東西都不重要。所以我覺得現當代文獻應該更專業(yè)些,更可信些,它提供的東西應該做到讓研究者直接進行閱讀。但現在不行,研究者直接用往往會上當。李:
您剛才談到的很多都是具體經驗層面的東西,但它其實也涉及很多理論性問題,但僅僅用特定的理論去整理這些經驗肯定會簡化,那應該如何去處理復雜經驗和理論之間的張力問題?劉:
這些經驗確實要上升到理論問題,我們剛才主要圍繞文獻問題來談,但這些問題其實不只是文獻,還是中國文學的經驗問題。我們的文獻和美國的文獻應該是有不同的,比如,很難想象他們會像我們一樣有那么多關于檢討、揭發(fā)的文獻。所以他們的理論肯定不能全部解決我們的問題,這些理論可能會刺激我們,也會給我們提供更多的視野和方法,但真正把中國經驗說明白,真的還是要靠我們自己。李: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現代文學的史料文獻工作既缺乏獨立性和專業(yè)性,實際上也沒法直接視為歷史研究,“史料”本身畢竟不能等同于“歷史”。劉:
對,我們處理的這些文獻,還有人認為這不是文獻。而對這些文獻怎么處理,怎么打開,我們真正能“進去”,同時又不被它們所左右,這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我在閱讀的時候就發(fā)現,只要仔細辨析,每次讀都會有一些新的感受。最近我就讀了一些從前讀過的材料,但感覺好像跟沒讀過似的,因為站的角度不一樣了。比如我的“編年史”,有人說最大的一個功績就是做了30年,其實我覺得做了30年也是最大的問題。30年前我的眼光是什么眼光?30年后我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樣了。李:
感覺值得展開的問題越來越多,但限于時間關系,我們今天就先聊到這里吧。非常感謝劉老師,也很期待以后有機會繼續(xù)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