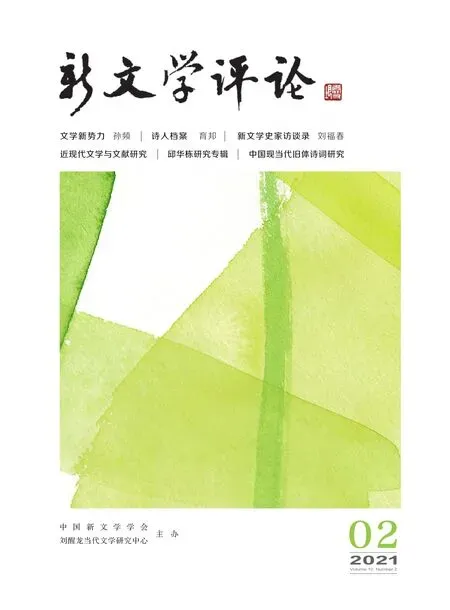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飛越真理與存在的爭辯”
——趙汗青對話育邦
2021-11-11 23:51:35趙汗青
新文學評論 2021年2期
□ 趙汗青 育 邦
趙汗青:
您的詩歌似乎有著兩種相對立的氣質,正如您一次演講的主題——鮮花與塵埃。讀者能感知到的還有“生長與死寂”,“純凈與污濁”,“微笑與鮮血”等;詩作中既有對純粹的渴望,孩童般強烈的好奇心,又有蒼老的,憂郁、哀傷的吟唱,伴隨強烈的毀滅感;在無聲的黑暗中孕育著一股“爆裂”的力量,形成悖論美。挑選一句詩來概括就是:“微弱的悖論/引導你走向自己。”(《薄伽梵說》)這樣的句子在詩集《伐桐》中隨處可見:“每一生都有一個死去的童年/我們從那個男孩的死亡中誕生。”(《無題》)“水冢……飄來歌聲/蕨類植物展翅飛翔/我們在黑暗中毀琴,斷弦。”(《與仁波切夜游錦溪》)“蕉下的蝴蝶,在死亡中受孕。”(《云中鳥》)“料峭春風中/死亡之燈熠熠生輝。”(《夜訪七曲山大廟》)讀者被引領著進入一個奇異的,充滿矛盾和迷思的世界,如《迷樓》一詩所言:“留下了瓊花、謎語和一連串非確定性王國。”這個文學的私人花園兼具西方現代主義的荒誕感與東方哲思中樸素辯證的美感。這應該和您的閱讀偏好、審美趣味有關?育 邦:
是的。我試圖在世界的微弱悖論中抵達某種詩歌美學。悖論,不確定性,荒誕,歷史循環等,不過是我們看到的世界的某一個側面。在各種氣息交互的文本中,我們依然圍繞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而書寫。我們的思辨為了一種洞察、一種警醒,為了發出樸素和諧的聲調,即便其本質是尖銳的。談到讀書對于寫作的影響,這可以寫成一本書。簡要地說,我認為我的閱讀與寫作的關系可以用以下幾位導師的話來表達:1. 好讀書,不求甚解。(陶淵明)
2.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杜甫)
3. 搜盡奇峰打草稿。(石濤)
4. 事實是每一位作家創造了他自己的先驅者。(博爾赫斯)
5. 偉大導師的作品是環繞我們升起而又落下的太陽。(維特根斯坦)
趙汗青:
在繼承古典性的同時,賦予詩作強烈的現代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這絕非是將古體詩轉譯成白話那樣的簡易工程,而是涉及了新詩創作最核心的秘密。“他若無其事,砍下那棵青桐”(《伐桐》)看似是東方典故,卻不盡然。中國傳統意象雖十分明晰、鮮活,但象征較為單一,可“伐桐”卻有著西方詩歌意象的奇崛性,隱喻與象征的豐富性。您是如何經營此類隱喻和象征的?育 邦:
其實,我沒有刻意地去“經營”。它們是自然生發的,富有生命的。但在寫作的時候,我還是有意識挖掘我們日常生活中、平常世界中可能產生獨特“詩歌形象”的意象。古與今,中與外,生活與想象,日常經驗和閱讀經驗……它們之間不再有明確的邊界。伐桐,這一意象,你也許以為是從我的腦海里臆想出來的,是想象力催生的結果。但事實是,有一次我去山中游玩,正遇到一幫人在清理一個風景怡人、三面環山的山洼子,而這個平坦的山洼子中間有很多亭亭而立的青桐。他們正在砍伐這些青桐。青桐就是我們古人常說的“梧桐”,就是《詩經》中“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中的那棵樹,它站在歷史與文化的深處,站在中國人深層次的民族文化基因之中。“孤桐北窗外”,它是孤獨而高潔的。“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它自身又是散發出淡淡憂傷的“呼愁”。也許讀者總能看到更多。詩歌意象的構建,既是作者主動為之的“發現”,也是世界給予寫作者的“恩賜”。也可以說,作者的選擇與意象的降臨,是一個“雙向遴選”的過程。趙汗青:
在我看來,您的意象群像是被嚴格管控和篩選出來的。作品中相對較少出現直觀上的現代意象,如“鐵路”“高樓”“工廠”“手機”等。您更多使用的是“河流”“云影”“蝴蝶”“湖石”“慕雪”……同時加了一些限定,使傳統意象得到進一步挖掘和開發,使看似古典的意象具備強烈的現代性,諸如“焚毀的星辰”“迷惘的琴弦”“暴動的花朵”“誤入塵世的白鸛”等。李商隱對待意象的方式和他那個時代的詩人不太相同,讓我們產生了他是個現代人的錯覺。當然他的現代性與真正的現代精神又是大不相同的。您怎么看待自己詩歌意象群的構建對自身創作風格的影響,以及詩人的意象群與其所處時代之間的關系?育 邦:
你說我作品中“意象群像是被嚴格管控和篩選出來的”,嚇得我一身冷汗,因為我從來沒有思考過“管控和篩選”,但是文本呈現不可避免地展示了這種微妙的景觀。至于你所說的古典意象的現代性,我覺得是必然的。在某些方面,我們與所有的古人、所有的外國人都有著相近或相似的洞見與情感,但表達方式上,作為一名當代中國詩人,你自身就攜帶著中國人與現代性這兩種本質屬性。你讀李商隱,包括更多的偉大詩人,他們身上都有一種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卓越品質。詩人的意象群如一滴水,能夠成為觀照其所在時代的鏡像;如一粒塵埃,也包含著時代的混沌和幽暗。一個個意象,也許就是詩人在其時代走過的一個個渡口。進一步說,詩人需從時代的日常情境中躍升出屬于他自己同時也屬于其時代的“異境”,如我的詩中表述的那樣,“我有別于我自己”。趙汗青:
智性與感性的平衡問題一直是個充滿爭議性的文學話題。詩人有時也被粗暴地劃分為藝術家式的詩人和知識分子式的詩人。您說過自己對知識分子和傳統文人的敬仰來自學生時代一位代課老師的影響。《伐桐》正如一座古典與現代交織的迷宮,入口看似敞亮,一不小心卻會迷失其中。這恰恰像是您童年時在萬花筒中看到的“一個立體的迷幻世界”。在迷宮中讀者偶然也會走入里爾克、佩索阿、博爾赫斯、齊奧朗、普魯斯特、卡爾維諾、喬伊斯等作家的遺跡。在《伐桐》的部分詩篇中,我們偶爾會看到一些較為抽象的表述,如“疾病的隱喻”“時間的暴君”“道德之軸”“真理與存在的爭辯”等。這類經過了現代思想編碼的短語,有時需要破譯才能被大眾讀者理解,詩人使用起來有一定風險,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育 邦:
也許,我們需要某種平衡。正如我在《鮮花與塵埃》主旨演講中提到的那樣:鮮花與塵埃要達成和解與平衡,它們既是一種對抗的關系,同時也是一種和諧共生的關系,是愛與恨的交織,也是生與死的現實存在。但我們試圖通過蜿蜒曲折的詩歌小徑走向無限廣闊的世界之時,智性與感性之間是否需要平衡,古典與現代之間還有無分野,抽象而危險的剃刀是否會危及詩歌的命運,我覺得這些問題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呈現”我們眼中的世界。我們需要“飛越真理與存在的爭辯”。這兩日,我讀到詩人呂德安的一句話,“每一首詩都應該有其形象,能令人聯想到生活”,深以為然。為了表達,我們需要攻破漢語中陳詞濫調的堡壘,戳破那些無病呻吟、歲月靜好的假面。而從修辭上說,我的詩歌正如耿占春老師所言的那樣,“在現象與隱喻、感知與象征之間尋求著平衡”。趙汗青:
福樓拜說:“我不過是一條文學蜥蜴。我相信,一名作家,他不應該有過多的欲求,他能夠‘取暖度日’就足夠了。”您很認可這一說法,也曾寫道:“一名作家一旦要進行創作,他是‘棄世而獨立’。”個體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在技術上可以造假,尤其對于年輕詩人而言,這一誘惑巨大。部分作家和世界的關系持續緊張,恰如策蘭所言“對抗著人世的/分秒”;另有一些作家也許會與世界達成某種短暫的和解。您作品中既有嚴酷的對抗性,如同一場“體內的戰爭”,又有某種超越性。這些詩作背后隱約站著一個超然的迷思者,又或是一個隱逸的反抗者。也許對世界的妥協和超越只是一個作家為了到達所處時代更高的文明程度而向下兼容的過程。可否談一談在閱讀與寫作這個層面上,您和世界的關系經歷過哪些階段,或仍在進行何種修煉?育 邦:
我在2000年左右,寫過一個文論叫《對抗之路》。在文中,我寫道:“寫作者跟現存世界是對立的。他們的對立方式隱匿而沉默,從不惹人注目。……這種對立必將走向對抗。對抗是正常的,沒有對抗就沒有個人的位置。假如對抗徹底消失,那么藝術也將丟失它應有的位置。對于個人來說,想在對抗消失的情況下從事藝術創作也是不可能的。在對抗中,個人才可能取得位置。”那時我只是個二十幾歲的毛頭小伙子,但即便到今天,我依然覺得它沒有修正的必要。卡夫卡的道路是對抗之路,他與存在于他身邊的世界和秩序一直是抗爭著的,藝術或者說文學寫作是他對抗外部荒誕世界的唯一武器,他別無選擇。雖然在此期間,他極度渴望實現藝術與現實的統一,甚至他個人與外部世界有過短暫的統一,但這種統一也是轉瞬即逝的,表面和形式上的。加繆寫作《西西福斯神話》就是他以無比的勇氣面對死亡和荒誕作出的抗爭。他對這一行為的巨大意義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寫道:“反抗貫穿著生存的始終,恢復了生存的偉大。對于一個目光開闊的人來說,最美的景象莫過于智力和一種超越他的現實之間的搏斗……”我們就要“在人間”進行摔打、錘煉、鍛淬,處處惹塵埃,如巴別爾一樣楔入生活的深處,而不是隱居在山中,沉溺在書齋中。塵埃就是我們面對的外部世界,既是風花雪月,也是日出月落,是屈辱,也是喜悅,是淚水,更是荒誕,是希冀,亦是絕望……是人世種種的煩惱,是大千世界的存在真相。我們來此世界,并不是要成為一個得道高僧,成為一個位列仙班的人。我們生來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成為一個人。我覺得只有處處惹塵埃,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這就是我們與世界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