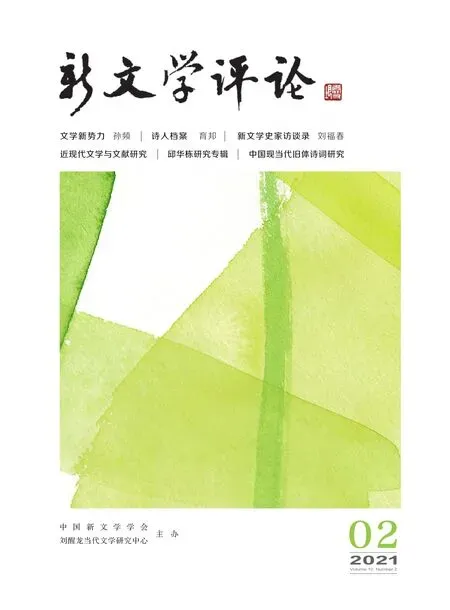主持人語
□ 張清華 王士強
育邦的詩集《伐桐》中,其個人簡介是這樣的:“1976年生,現居南京,幻想文學愛好者、山水愛好者,從事詩歌、小說、文論的寫作。”簡介并不長,內容卻很豐富,尤其是“幻想文學愛好者”與“山水愛好者”這兩種身份頗值得重視,可以作為理解詩人、作家育邦的重要入口和關鍵詞。迄今,育邦已出版詩集《體內的戰爭》《憶故人》《伐桐》,小說集《再見,甲殼蟲》《少年游》,文學隨筆集《潛行者》《附庸風雅》《從喬伊斯到馬爾克斯》等,在多個領域均有建樹,并且都達到了較高的水準。在這樣的基礎上重新觀照“幻想文學愛好者”和“山水愛好者”這兩個標簽,確有深意存焉。育邦的文學不是簡單地反映現實、為現實服務的文學,而是一種經過深度加工、處理、變形、提升、重構的“幻想文學”,他與時代生活并非親密無間(或者擁抱或者摒棄,或者勾肩搭背或者劍拔弩張,其實質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共通的),而是葆有充分距離的,他與此時此地的都市生活、現代境遇頗有些格格不入,是一位有類隱士的“山水”愛好者。他不是現實、現世生活的簡單的(因而也是形而上的)歌頌者或批判者,而更多的是一位觀察者、思考者,他的詩歌所表達的不是表面化的情緒、立場、姿態,而是更為內在、糾纏的現代經驗,是包含了書齋氣、經卷氣、士大夫氣、知識分子氣的復雜言說。在“六朝古都”的南京,育邦的詩學追求也體現出一定的貴族氣息、精英立場,他的詩歌具有唯美、頹廢、典雅、高曠、淡遠等多重特質。在當前這樣一個急躁的、消費化的時代語境中,這樣的寫作無疑只能是小眾的甚至不合時宜的,不過,惟此,也正凸顯出其價值。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育邦的創作是封閉的、窄狹的,實際上他的創作是深具開放性、對話性、當代性的,他深諳藝術上的辯證法。在創作談《我的詩歌札記》中育邦有這樣的夫子自道:“一方面,詩歌來自無處不在的生活經驗、不斷上涌的回憶、行走的足跡、想象甚至夢境;另一方面,還要求它不停地偏離生命航道,探尋那些晦暗的地帶,進行所謂超越的活動——試圖擺脫重力的白日夢。”他的詩歌既有對實然生活的反映與回應,又有對應然生活的想象與追慕,它不是單向度的突進,而是多角度、多層面的磋商,具有一種“綜合”的特質:經驗與超驗,介入與超拔,大地與天空,憂傷與冥想,狂放與紀律,淡泊與沉痛,言說與沉默,世故與天真,神性品質與人間情懷……他的文字將多重因素融混在一起,經發酵、沉淀,郁結于胸而千回百轉、不吐不快,是深層人格的形象轉化,正如他自己所說,“詩是蒙上復雜色彩的自傳”。這樣的“自傳”,屬于詩人自己,同時也極具普遍性和涵蓋能力,屬于“無限的少數人”。
由此,育邦成為一個“秘密詩人”,或者一個懷抱“秘密”的詩人。詩歌即是他的秘密,他行走于獨己的、幽秘的小徑,而又連接眾生、天下,他身有利刃而又心懷悲憫,至冷酷,至溫柔!他所選擇的詩歌道路不可能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更不可能引起消費的狂歡,但卻是清醒、睿智、有效的。他以拒絕一個時代而真正進入了時代、表達了時代,真正的詩人,當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