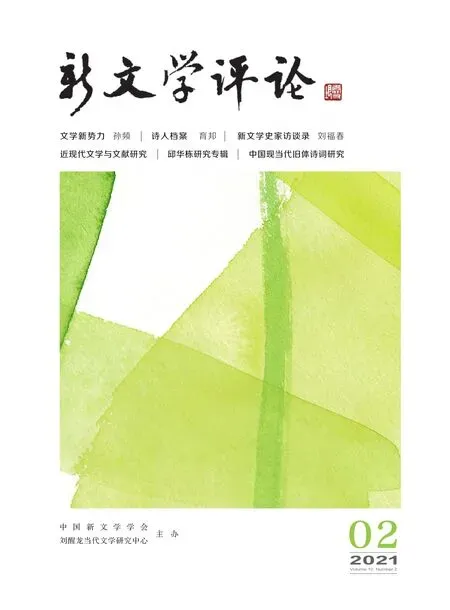主持人語
□ 劉芳坤
至今仍清晰記得孫頻跟我說的第一句話:“你終于來了!”那是九年前我們相識的情景,彼時我剛博士畢業回到家鄉,參加的第一個活動就是她的作品研討會。我和孫頻年齡相仿,她的老家交城縣距離省城很近,但是非得是在某個特定時刻,通過文學這一特定中介,我們產生了“終于相識”的眼神交匯。直到最近,我還在思考著這種“終于”:80后一代人分享集體記憶,但是,每一個人卻存在區隔,我們的靈魂深處無時不渴念著“終于”的情景,這恰恰寓意在孫頻幾乎所有小說的結尾——靈魂終于解脫,與你終于相遇。
從50后到70后作家都不曾擁有這樣的機遇,而80后的文學實踐和成名過早,似乎讓我們的文學比任何一代人都“與青春同行”。我甚至至今在課堂上還會驕傲地告訴學生:在我大一時,同代作家就涌現出來了,但是你們現在沒有代言人。然而在我們跨入中年之際,那些新銳的、弄潮兒式的“殘酷青春”卻成為反諷。80后文學真正負載起我們的時代約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也就是自2009年孫頻發表處女作《姐妹》起的十年。我第一次讀到的孫頻的小說是《鵲橋渡》,主人公是一對母女,在母親身患絕癥的逼迫下,“豁出去不嫁”的縣城大齡女青年終于和生活妥協了。小說寫“她終究是個絕緣體”,我登時震顫,因為即使在自己生活的周圍又有多少絕緣體呢!后來讀了孫頻的《醉長安》《祛魅》《凌波渡》等篇章,我就開始跟周圍的朋友打聽這個作家是誰。我其實早就該想到,這是我的同代人,因為這些小說的憐憫像把很多人的內心一起清空了,它似乎隔岸觀火,然而那倒出來的卻是自己的血肉。
如果說批評家的第一直覺是就著作品談論小說的本質,面對孫頻的創作,我卻最想談論“女人是什么”或“我是什么”,不是說她的創作直指性別經驗,而是“終于”有個人寫出了“我”與這世界的關系,把“我”的經驗悲壯地釋放了出來,那是《自由故》中決心退學,用自由反抗學術吞噬的女博士呂明月,那是《祛魅》中走不出日常生活魅影的縣城文學愛好者李林燕,那是《一萬種黎明》中被無數個追尋的黎明所擁抱的山莊主人張銀枝。2014年夏天到2015年秋天是我和孫頻來往最為密切的一年,孫頻是一個在創作時可以敞開交流的作家,那一段時間我們談了很多,比如經驗、細節、語言,當然談得最多的還是關于轉型和縱深。我們深諳小說中發自“我”疼痛的經驗,然而在真實表達、快意釋放的同時,我們是否可以將其放置在歷史和時代的洪流之中?我們即歷史,那是我們,但卻不僅僅是我們。此后,孫頻不僅擴大了自己閱讀的范圍,而且多次回到故鄉交城去尋找答案。接著,她考上研究生,待到畢業前夕,她的小說就愈發“厚”了起來。
本次專欄的四篇文章均圍繞孫頻小說的“變”與“不變”展開,四位學者不同角度的論證為我們帶來在80后代際意義之外,孫頻創作的“恒常”或者說“經典”內涵。馬婧和閆東方的論文從文學史的縱深發現立論,分別從零余者的形象體系和女性寫作四十年的話語體系出發討論孫頻小說創作的意義。艾翔和張艷花的論文則分別從《我們騎鯨而去》和《天體之詩》兩部作品出發,探討孫頻“轉型”的突破。四篇論文從不同角度達到了一個共識:孫頻的創作不斷從自身經驗中攫取精神寶藏,其敘事逐漸向歷史縱深拓展。
伍爾夫曾不無失望地談道,百年以來作家的寫作之路不過是朝著不同的方向沖擊,一條運動軌跡卻大體構成了周而復始的圓形。一代人也許從來也不會站在有利的高度,我們一直在地平線上,淹沒于擁擠的人群,任由塵土迷離雙眼。而孫頻的創作也許最終還在這一序列當中,但我對她仍存在“嫉妒”——是對一個幸福的戰士的嫉妒。作品的經典性最終會由文學史家定奪,但哪怕是在走向歷史塵埃的孫頻也留下了倔強的姿勢,這種姿勢足以激勵我。我甚至經常如此感嘆:由張愛玲的“不徹底”到孫頻的酷裂決絕,竟是如此漫長而激烈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