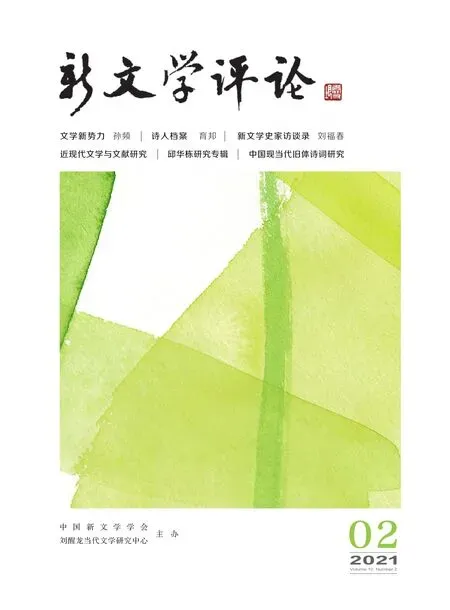唯有大海與摯愛永存
□ 孫 頻
我是一個小時候沒怎么見過水的北方人,在黃土高原上,河流是罕見的,更不用說湖泊與大海,以至于小時候見到澆地的水渠,都會把它當成河流,幻想著能從里面釣出一條魚來,任何有水的地方都能讓我流連忘返一陣子。因為缺水,沒有人會養鵝,所以我直到十五六歲才第一次見到了真正的鵝。直到現在,無論在哪里,我只要看到有水龍頭在滴水,就會像強迫癥一樣過去使勁擰緊。
人越是缺少什么就越是會幻想什么,所以可以想象我當年在黃土高原上對大海的各種幻想,我甚至幻想過在鯨魚的嘴里搭個房子,點支蠟燭,橫渡大海。它對于我來說,神秘、遙遠,完全是異域。多年之后我終于見到了大海,一開始是好奇而敬畏的,敬畏它的巨大與包容,敬畏它居然能孕育出像藍鯨這么龐大的動物,敬畏它的斑斕與壯美。尤其是在滿月的晚上,月光鋪滿整個大海,整個海面閃著銀光,水天之間的界限消失了,天地縫合于一處,而人在其中是如此渺小,又是如此震撼,讓再卑微的靈魂都生出些莊嚴之感。
時間久了,便生出枯燥感來,會覺得浩渺無際的大海其實與沙漠有相似之處,深陷其中時都會生出絕望感與很深的孤寂感。時間再久一些,便會發現那種獨屬于大海的海洋文明,過于悠久,過于龐大,以至于想到它們的時候,覺得它們就像那些巨大的史前巨獸正一步一步向我走來,光是它們投下的陰影便足以讓我震懾不已,但它們又輕盈得像是一種幻象。
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皆始于大海,最早的魚類爬上陸地,慢慢進化為最早的猿類,又慢慢進化為最早的人類。人類和萬物的祖先都來自大海,我想,這可能就是人類面對大海時會不由得產生敬畏的原因,好像那是自己的故鄉。作為一個普通人活在這個世上,雖然每日消遁于眾生之間,卻還是有諸多困惑與苦痛,那些苦痛是那么渺小,卻又真實地啃噬著人的神經。再加上生活過于真實瑣碎,巨大的重力不斷拖著人下墜,使我想避開一些太過具體現實、太貼地行走的素材,雖然能力和目力都有限,但起碼可以把目光投向更渺遠一些的地方,被更大更遠的東西所牽引。如同一個人被月光的磁場所籠罩,即使外觀上什么變化都沒有發生,在內心深處,在意識的某個角落里,卻總有什么東西和從前不同了,也讓一個凡俗的普通人(比如像我這樣的)產生了片刻的飛翔感與莊重感。
《我們騎鯨而去》中寫海島不是因為我熟悉海島,相反,我對海島太不了解了,也因此對它太好奇了。海島有著與大陸完全不同的生態,還有著最獨特的海島文化,像島民一樣寫出一座島的細微肌理非我所長,也不是我的關注點所在。海島對于我來說,更是一個抽象的存在,所以我在一個中篇小說里,盡可能多地把世界各地形態各異的小島濃縮于一處,讓所有這些島變成了一座島,它并不是具體存在的,只是我想象中的一座島。在我的想象與理解中,它已經從一座島的肉身里長出了更多的涵義與象征,已經長出了帶有文化屬性的魂靈。每一座島都有它獨特的氣質,但所有的島都放在一起,就會生出一種極其絢爛的效果,像追光燈照耀的舞臺,小島變成了世界劇場,變成了最考驗人性的實驗室。這得歸功于小島本身的環境和條件,它太小了,孤懸于大海之上,四周茫茫皆海水,海島上的資源又是極其有限的,包括食物和淡水,然后就是可怕的會把人逼瘋的孤獨,遠離人類和人類的一切勾心斗角、自相殘殺,享受著酷刑一般的自由。沒有人比海島上的人更想念人類,不是想念某一個人,是想念人類。孤獨讓塵埃般的個體忽然與天體般龐大的人類真正有了臍帶,也讓一個從不思考自由為何物的人第一次開始思考到底什么是自由。海島其實能給人一種重生的機會,當然前提是,能活著離開海島。也許,沒有絕境就不足以有重生。
在這幾年的寫作中,因為時常自感渺小脆弱與笨拙,所以不由得開始去向往一些更宏闊的東西,也許是因為從這些宏闊的存在里,人能汲取到能量,能去平衡自己的世俗感。有時候想想人類的進化會覺得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最早的祖先從大海里爬出來,漸漸長出四肢,漸漸直立行走,漸漸變成了今天的我們,想想歷史上那么多的國家朝代與政權更迭都已經化作云煙,連一絲痕跡都沒有留下,而今天的我們,尚能思考的我們,也必然有一天匯入這云煙當中,我們在人類的文明進程當中,只是一滴水。但是我們本身就屬于文明的一部分,我們的存在就是文明。那無論最后如何消逝,我們都曾有過絢爛的一瞬間。這也許便是個人的意義所在。
在海島這個劇場上,陸陸續續有人登場,又陸陸續續有人退場,有人出生,有人死亡,有人哭泣,有人歡笑,人性的戲劇從不曾間斷也不可能間斷。在我想象的這座海島上,有生命力強大到野蠻的人,可以睥睨世間所有的苦難,可以在荒無人煙的海島上為自己種出希望;有與世隔絕多年卻仍然保留著最后風骨的藝術家,仍然會選擇為自己保留最后的尊嚴;有猶疑在世俗間的思想者,想遠離人類的紛爭,又無比眷戀著人類。有希望者終會在大海深處建立自己的王國,而有尊嚴者在絢爛慈悲的大海中最終騎鯨而去。
無論世事如何變幻,無論文明如何進退,最后我們會發現,滄海桑田,唯一能留下的也許只有大海和摯愛,那些最真誠的最血肉相連的人類情感,它們會與時間一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