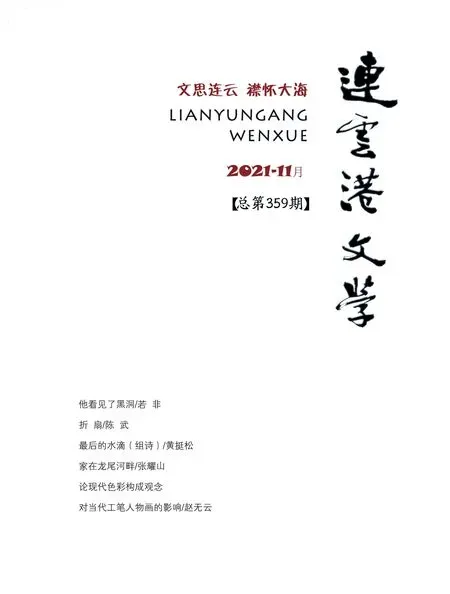鄉村秋天的交響曲(組章)
王壟
立秋之歌
時在八月,“夏”依然占據著季節的主角,那個叫“秋”的演員,還遠遠地立在候鏡的行列,一俟風吹草動,便儼然粉墨登場。
雨是常見的道具,雷聲陣陣,不知是為夏天喝倒彩,還是要為秋日加把勁。所有的果實都開始爭著飽滿,一粒粒、一枚枚、一顆顆,都可以做歲月的勛章。
母親的芝麻花開得正恰到好處,仿佛幸福的生活也在節節拔高。黃豆也忙著結莢,知了的叫聲似乎變成了“加油,加油!”
七夕的神話往往就在左右,中元節的紙錢,讓一個千古不滅的主題,加深了濃濃的鄉愁。人節也好,鬼節也罷,經過夏日淬火的靈魂,必將在秋季找到精神的歸宿。
菱角在水中與時間較勁,要趕在中秋大戲到來之前隆重獻演。荷花與荷葉,像處于青春妙齡。蓮子悄無聲息地孕育著農歷的情話,雪白雪白的藕在淤泥中傳遞著唯美的祝福。
路邊的石榴,慢慢在羞紅了半邊小臉。一頁初識秋意的楓葉,像一種符號,暗示秋天就在不遠的眼前。
瓜果飄香,總是最喜人的味道。所謂的“啃秋”,被西瓜甜蜜成上風。還有更多更好的豐收,等待秋熟分派主打的角色。
青綠的稻田里,蛙聲總像在朗讀一首經典的詩篇。新建的風能發電大風車,傲然在村莊周圍,如同得道的高僧,對春去秋來、寒來暑往,熟視無睹,或者保持特有的淡定。
就借“秋”這個字,暫先掃去盛夏的燥熱吧!貼在心坎上的故鄉,企盼長長的絲瓜,像綠色的鐘擺,搖晃出時光悠長、生命悠然。
處暑之歌
我知道,處暑的“處”有躲藏、終止之意。但我卻夢想使之成為處理的“處”,用一切的修辭,把夏天的暑熱“處理”干凈。
然而,暑氣尚未消退,涼爽還顯得金貴。蟬在忘乎所以地叫著,它們從不計算未來的日子還剩余多少時光。蒼蠅和蚊蟲,永遠都是最討厭的角色。從這個角度出發,真希望來一場強勁的秋風,將一切“害人精”統統消滅。
母親的芋頭,在陽光下搖曳著一把把隱士般的蒲扇。黃豆地里的蟈蟈和蟋蟀,沒日沒夜地吟唱著耕種的快樂。菱角與荷藕,匆忙顯現成熟的誘惑。芡實盤上落著的小水雞,與一只紅紅的蜻蜓交換著季節的秘密。
南瓜花總是帶著星星的模樣,粉黃粉黃的花心間,似乎哪一刻也不會少了蜜蜂、蝴蝶的身影。芝麻花旁若無人地晃動著潔白的小鈴鐺,牽牛花用一朵朵藍色的小喇叭,吹奏著久違的鄉村民歌。
絲瓜長長地掛著,像一個個特別的感嘆號,催促著美麗的秋色早一點粉墨登場。稻田里正是一片遼闊的青青,那種舒服的綠色,讓人每個毛孔都感到無比的通透。豐收的渴望在蛙聲的音樂會上傳播,嫩嫩的玉米棒頭在紫色的穗須下,竟有著少女一樣的羞澀。
地火有時讓人懷疑季節更替的誠意,類似于七月的滋味只在早早晚晚有所藏匿。城市里的詩人已經開始書寫傷秋的詩句,其實鄉下的處暑與暮夏并無太多的差異。不到田間地頭的人,就會看著書本上的“雁”字望文生義。
希望和等待,是現在唯一要做的事情。沉甸甸的秋果,懸于母親香香的夢中。在老家,一場聲勢浩大的收獲,終會鋪展在日新月異的畫冊之上。屏息凝神,側耳細聽,能聽到不一樣果實發出一樣的歡唱。我伸出遠離勞動已久的手指,竟然觸摸到了處暑以前或者以后的果粒。
白露之歌
“露從今夜白”、“白露為霜”……白露啊白露,這是一個多么詩意的名字。仿佛來自《詩經》,又仿佛來自老家口口相傳的諺語。
目不識丁的母親,從來都說不出那么多文雅的詞句。“白露兩邊菜”是老人家每年此刻掛在嘴邊的老生常談,種青菜、種油菜、種蘿卜……無須暗示的節氣,總有樸素的哲學和真理。
二三十度的氣溫,還依然司空見慣。鄉親們也會納悶:如今的白露,還有多少秋天的樣子?但草尖上的露水倒是真的晶瑩著季節的心事,黎明時分的狗尾巴草,耷拉著小腦袋,像在閉目沉思。
韭菜花狀如落在綠叢中的繁星,六朵小而純潔的花瓣,正切合用白露的“白”作為姓名。黃瓜、豇豆還在近似瘋狂地結著果實,好像要把對歲月的情意在白露時分表達得淋漓盡致。
水稻在拼命地拔節、抽穗和灌漿,喜陽的植物總喜歡陽光普照,偶爾的陣雨和雷雨,讓人誤以為還在夏天。穿著夏布單衣的母親,在小菜園勞動的間隙,也愿意聽一聽蟬兒最后的齊聲共鳴。
扁豆花如同大地的眼睛,眨一眨,都會變幻出美妙的風景。石榴、柿子、葡萄、冬棗……也像大自然的恩惠凝結而成的另一種“露”啊,帶著香、帶著甜、帶著彩,誓將里下河平原的日子點綴成甘露、蜜露。
中秋的燈籠就要紅了,遍地的桂花等待完成一年里最美情感的銜接。明月像一輪秤盤,能量得出靈魂的重量。一滴銀露一樣的眼淚落在游子的鍵盤上:只要我還能寫詩,我對母親的承諾,就一定要在“蒹葭蒼蒼”的時節,完完全全、圓圓滿滿地兌現。
秋分之歌
抑或是草木的末日,抑或是豐收正高潮迭起。萬物不懂得平分秋色,唯有汗水和希望,互不虧欠。
稻子在田野上喧囂,紛落的葉片如同天空拍痛的手掌。野草尚不足有燃燒的成色,除非有人想象霜降過后,五谷豐登,幸福在大地之上熊熊燃燒的模樣。
夕陽與夜色平起平坐,互為欣賞。最后的稻草人,凝望著落日,戀戀不舍這秋日的輝煌。一年僅此一天,我們總有理由,抱團取暖,欣喜若狂。
路邊的小野菊正黃得耀眼,漸成頹勢的蟬鳴,被故鄉的燈火和月光依次敲打在耳邊。此刻的風景似乎有點文不對題,或者蟈蟈的訴說言不由衷。綠色依然積重難返,仿佛眼前的秋分,早已舊貌換新顏。
狗尾巴草還在搖頭晃腦,老家并未為暫行告退的那一小部分不安與激動。秋高氣爽把秋分的“分”,拔高成得分的“分”。風和日麗、天藍水碧、鳥語花香的家園,的確值得打一個碩大無朋的贊。
湖面寂靜得像一塊玻璃鏡子,點水的小蜻蜓竟忍心輕輕將它打碎。紅蓼無須苦苦地掙扎,就能對薄涼和輕霜視而不見。蘆葦戴了一頭銀發,就像在水一方的伊人,披了紗巾,比月亮還要楚楚動人。蒲棒兒緊了緊瘦削的身子,準備裹住越來越重的寒冷。
季節真的被秋風分開了嗎?大螃蟹的爪子癢了,九月的酒,叫誰愿意寡欲清心?
請把我分到一條思親的河流上去吧,人間的秋色可以飲盡,真情的浪花豈能枯竭?突然想起秋草下深埋的父親,能否抓住太陽的最后一絲熱度。而天空越發低垂,母親日益衰老,真不希望有光的日子太短,美好的秋意不被時光拿走一分一毫。
這小小的秋分之歌就要結尾,剩下的感恩,引領我們向前,收獲一些傳世的永恒。
寒露之歌
寒露在寒露的時節,還沒有半點冷的樣子。大地的性格變了,節氣的姓名無法更新。
重陽附近的生活,依然火熱。金色的豐收已經在望,一如詩歌正將欣欣向榮。
秋風的確有諸多不合時宜的念頭,一切的果實,卻無視薄涼的掃興,自顧自地黃,自顧自地大,自顧自地甜。
蟬鳴和蟈蟈的叫聲,竟堅持不知疲倦,仿佛鄉村的歌手,在吟唱著草根的秋天。蚊蠅已經一天天見少,每一聲細雨,都能反襯秋高氣爽的歡欣。
稻子的一生只向土壤低頭,遼闊的沉默不是無語,而是把更豐腴的希望藏在心底。
此刻的藍天,更像是騰空的糧倉,十月的鄉村也有夏日的躁動。農民的身份越發金貴了,越來越叫人羨慕,越羨慕就越容易不寒而栗。
農歷九月的月亮,不比中秋月更耐得住寂寞和冷清。草葉上晶瑩剔透的露水,交代了歲月的心事,以及夢境的精妙。
霜,其實是個十分鄉土的意象。古詩里的那個詞,在漸黃的蘆葦、漸白的蘆花上,連識字不多的父老鄉親,竟也耳熟能詳。
白發如霜,相思如霜。深夜的小寒氣,常常激起沖天的火焰。
殘荷在白露之下保持未減的激情,落葉如同一群背著行囊的游子,重新回到生我養我的故地。收獲的榮耀驚世駭俗,而唯有團圓的幸福,才能抵御霜降之前的蕭瑟與寂寥。
陽光折斷了一泓秋水,關于愛的記憶仍鮮活在腦海。順著皇歷,我走進了母親的秋天,不忍心讓每一朵小花擅自枯萎。萬物的退場請勿從寒露開始,大地裸露的內心,恰似我對故鄉和母親的祝愿。
寒露之歌,是我敬奉的一絲光熱。我不愿褻瀆冬天的到來,我慶幸在這個時節,還能抖落一身的塵埃,在有母親生活的故土上,滿眼含淚,詩興大發。
霜降之歌
重陽附近,霜降來襲。
稻穗已經金黃,但每一串都仍在田間使勁地“秀”著,如同待嫁的少女,要把最美的身體留給迷人的秋夜。霜的白,是這個季節最好的陪襯。泛黃的銀杏葉間,累累白果,曾是農歷九月最誘人的饋贈。
父親生前手植的桂花樹,已經成為老屋邊最香的“景點”。母親不忍使之掉落一粒小小的花瓣,那是世上最細微的承載或顛覆。小村之中,彌漫著那奇異的味道,就像懷念與追思,早已深入骨髓。
山芋藤還在忘我地綠著,而新挖出土的紅薯,卻陸續被曬成山芋干、制成山芋粉。河水還沒有些許落差的意思,也許輕易空缺或流失的,只是少年人日漸淡薄的鄉愁和鄉戀。
“清霜醉楓葉,淡月隱蘆花。”紅葉漸顯,蘆絮始白,里下河平原的深秋,從天而降的多是胎記般的風物與景色。“最憐秋滿疏籬外,帶雨斜開扁豆花。”一場意外的秋雨,讓最后的扁豆花臣服于滿架的秋風。而扁豆燒仔雞的美味,讓人對母親的手藝終生貪婪。
“秋冬的蔬菜賽羊肉”,在老家,絕不是一句夸張的言語。母親新種的黑菜、香菜、菠菜和蘿卜,在經霜之后,更顯得嫵媚和妖嬈。那一種純天然的蠱惑,能讓遠方的游子夢里的江山掀起漩渦。
菊是必需的樂器,以大地為弦奏出纏綿悱惻的旋律,呼喚梅們一道奔向濃霜重雪的冬天。火紅的辣椒在屋檐下抒情,佛手瓜像戀舊的智者或聽禪的高僧,端坐于秋陽下可貴的綠蔭。
該收的就要收了,該種的也得種了。霜無雪寒,霜只是驚飛了守時的大雁。狗尾巴草搖晃著西風的利劍,我想起不識字的母親卻說過“地底下的種子也有春天”。霜已降,雪尚遠。祈禱重陽前后的人,都有一顆不老、敬老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