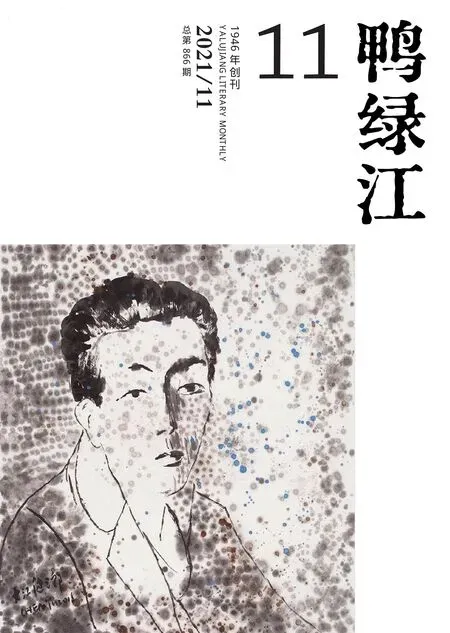以數(shù)學(xué)老師的方式(短篇)
海東升
1
“不信拿不下他們。”
那老師從屋子里出來,啪地甩手關(guān)上房門。老婆在門里嚇了一跳:“你這是給誰臉子看呢?別拿不下人家,還得找人修門。”
那老師此時(shí)根本沒聽到老婆說的話。此時(shí)的那老師就好像站在易水河畔的荊軻,大有壯士一去不復(fù)還的架勢(shì)。
他開始打量自己腳前的樓梯。每一段是十四級(jí)——作為一個(gè)初中數(shù)學(xué)老師,在這之前,他還真不知道自己家的樓梯是多少級(jí)。只是這次打算去樓上,他才一個(gè)一個(gè)地仔細(xì)數(shù)數(shù)。
14×2×3=84,他在心里列出算式。這和他去過的北鎮(zhèn)青巖寺的臺(tái)階沒有可比性。青巖寺的臺(tái)階1000×2=2000。如果不是兒子高考,那老師也不會(huì)去三百多里地以外去拜見文殊菩薩。
拜神比拜人簡(jiǎn)單。因?yàn)槲氖馄兴_就在青巖寺山頂上,你只要帶著虔誠的心去拜,他就在你的頭上。但人不行,你明明知道樓上的三家就在你的頭上,但你不一定能拜到,或者說,你就是拜到了,也不一定靈驗(yàn)。
想到這兒,那老師剛剛邁上臺(tái)階的腳又退了下來。
那老師想抽煙,但摸摸自己身上的幾個(gè)口袋,除了手機(jī)和幾張手紙,什么都沒有。他想回家去取煙,但一想家里也一定沒有,就是有幾盒待客的煙,老婆也一定藏起來了。因?yàn)槔掀挪幌胱屇抢蠋煶闊煛?/p>
那老師在樓梯前憋得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回家,使不得;上樓,也不知道怎么和那三家說。平常在學(xué)校里、在課堂上出口成章,滔滔不絕的優(yōu)秀老師,在眼下的困境中,真是進(jìn)退兩難。
好在樓上傳來一聲門響,鼓起了那老師的勇氣。他提提褲子,系緊了褲腰帶,甩甩大背頭。這是那老師每次遇到大事,決定出擊的規(guī)定動(dòng)作。
當(dāng)當(dāng)。那老師在兩次猶豫之后,敲響了四樓的房門。但過了兩三分鐘,里面絲毫沒有開門的動(dòng)靜。老齊應(yīng)該在家啊?他是一個(gè)退休在家賦閑的人,那老師平時(shí)沒事下樓的時(shí)候,幾乎都能和他碰上,不是在樓道里,就是在樓下,有時(shí)也會(huì)在樓口。
是在看電視,還是歲數(shù)大了耳朵背?那老師又敲了三下。靜等三十秒,里面有開二道門的響動(dòng)。那老師好像做了壞事的學(xué)生,站在辦公室的門前,不知道結(jié)局如何,也不知道死相是不是會(huì)很難看。
“嘎吱——”看來老齊家的門也和自己家的門一樣,缺油了。那老師在房門推開的一瞬間,想和老齊說,他家的門該上油了。但話還沒出口,他的舌頭就縮了回來。開門的不是老齊,是一個(gè)戴眼鏡的臉色不算白的小個(gè)子女人,三十多歲,那老師記不起是老齊的女兒還是他的兒媳婦。就在那老師拿不準(zhǔn)的時(shí)候,她的后面還冒出一個(gè)和女人個(gè)頭差不多的胖小子。
“你找誰?”那個(gè)不算白的女人問他。
“你爸在嗎?”那老師覺得這個(gè)回答沒有瑕疵。
“在啊,你是誰啊?”這個(gè)不算白的女人警惕性才上來。
那老師說:“啊,我是三樓的,我姓那,你爸認(rèn)識(shí)我。”那個(gè)女人退回去,喊里面的那個(gè)爸。
老齊走出來,穿著花格子的睡衣,顯得比穿制服的時(shí)候要瘦一圈,眼袋也比平時(shí)腫大,沒戴帽子,白發(fā)很多,在燈光下閃著銀光。門里的老齊和門外的那老師都愣住了,就好像經(jīng)常碰到但又接觸不多的人,真正站到一起,還真是既熟悉又陌生。
那老師剛要張口,門里的老齊卻打斷了他剛要出口的話。“孩子可真沒跑。”這是老齊四年來第一次和那老師說這么多字的話。
那老師一下子蒙了,不知道老齊是真的離題萬里,還是有意回避。但緊張之中的那老師是善于調(diào)整的。他經(jīng)歷過各種尷尬場(chǎng)面,老齊的開場(chǎng)白讓他瞬間冷靜下來,一下子讓時(shí)間回到四年前。那也是差不多這個(gè)時(shí)間,也是在這個(gè)門口,老齊也是穿著睡衣,但肯定不是這件花格子。那時(shí)的那老師實(shí)在是忍無可忍,上樓和老齊說他的兩個(gè)孩子從早上五點(diǎn)多開始,就咚咚咚地在臥室和客廳里來回跑,讓心臟不好的老婆坐立不安的事。老齊說的兩次都是四個(gè)字:孩子沒跑。
那老師笑了,仔細(xì)打量那個(gè)女人身后站著的胖小子。說:“長這么大了?還有一個(gè)呢?沒來?”老齊感到莫名其妙。
“都過去多少年了,你還記得那件事?”那老師也記得盡管他去上樓找過一次,老婆也上樓去找過一次,但樓上老齊的孫子和外孫子,只是比平時(shí)少跑了一點(diǎn),還是雷聲依舊。那老師兩口子不找了,老齊再碰到他們,卻少了過去的笑容,好像是不認(rèn)識(shí)的路人,頭不抬眼不睜了。這讓那老師開始重新認(rèn)識(shí)打裝修那時(shí)就打招呼的老齊。但那老師和老婆還是像原來那樣,遇到老齊的時(shí)候,該打招呼還是打招呼,盡管老齊帶搭不理的。但近年來情況似乎有所好轉(zhuǎn),老齊開始有了過去的笑容,或回答或點(diǎn)頭,但從來沒說過今天這么多字的話。
“那是啥事?”老齊問。
“昨天晚上我家人上來問過了。”
“哦。”老齊好像有點(diǎn)不好意思,“我想起來了,通下水道的事。”
“對(duì)。”那老師覺得老齊并不糊涂。因?yàn)橛泻芏鄽q數(shù)大的人對(duì)眼前的事情會(huì)忘,他們總是記得過去的事情,尤其是對(duì)自己刺激大的事情。自己的老婆就是這樣,現(xiàn)在的事情說過就忘,但總是對(duì)過去婆婆待她不好的事情記憶猶新。但老齊不是女人,過去還是在機(jī)關(guān)工作的人,不應(yīng)該只記得過去的事情,而不記得昨天晚上剛剛發(fā)生的事情。其實(shí)應(yīng)該是那老師記得傷害他的事情,而不應(yīng)該是傷害別人的老齊。或許老齊認(rèn)為自己做的沒有一點(diǎn)錯(cuò)誤吧?
“其實(shí),你老婆就應(yīng)該直說,她繞著圈子說,我過后才想明白。”
那老師心里笑了。這是老婆的說話特點(diǎn),從來都是婉轉(zhuǎn),總是覺得她一說,別人也應(yīng)該理解她說的意思,但人的文化程度不同,理解能力不一樣,怎么能都明白你的意思?也可能是老婆覺得第一次去找人家,不知道怎么表達(dá)罷了。但昨天晚上老婆回家后,反應(yīng)的可不是這話。老婆說老齊態(tài)度惡劣,說“我還做飯呢”,說著就關(guān)上了房門。
這個(gè)老齊,果然是人鬼兩面啊!和昨天晚上老婆說的態(tài)度冰火兩重天。也許是他真的沒理解老婆的話,還是給那老師一個(gè)男人的面子?那老師說不準(zhǔn)老齊的心理,但這兩天不同的態(tài)度,說明老齊和原來有了些許改變,這應(yīng)該是配合的態(tài)度。
“你接著找通下水的,完事算賬,我保證掏。”
老齊的認(rèn)識(shí)又是一個(gè)明顯的提高。那老師沒想到會(huì)這么輕而易舉,他原先是做好最壞打算的,現(xiàn)在老齊站到了自己一邊,這就是四分之二。那老師開始拉攏老齊,齊叔,跟我上去做個(gè)伴兒,和五樓、六樓的商量商量?那老師記得這不是第一次叫老齊為叔,只是后來老齊不懂事,那老師就只打招呼,而不叫他叔了。
面對(duì)那老師的得寸進(jìn)尺,老齊顯然沒想給面子。
“我不去,你自己去說,他們不認(rèn)可,我再上去,要是他們把咱們倆都給卷下來,這事就不好辦了。”
那老師想想也對(duì)。還是蹲過機(jī)關(guān)的老齊考慮得周全,做事留有余地。他能這么說,開始替自己考慮,就說明老齊是認(rèn)可這件事的,或者說他這個(gè)一直生活在城里的人就知道這樣的事情應(yīng)該這么做,但卻不愿意提醒而已。或許是自私,還有可能是接觸不多,關(guān)系還沒到這個(gè)份上。
那老師想給老齊一根煙,作為回報(bào),但摸摸自己的口袋,卻空空如也。他怕老齊看出尷尬,就沖老齊笑了笑,匆匆離開。
那老師是帶著四分之二的勝利心情走上五樓的。據(jù)昨天晚上老婆的反應(yīng),五樓的兩口子歲數(shù)不大,四十左右的年紀(jì),態(tài)度還算可以,說一次兩次行,再多了,他們也不掏了。這是中間的力量,看形勢(shì),看風(fēng)向,有了態(tài)度惡劣的老齊的轉(zhuǎn)變,他們自然會(huì)向那老師一邊傾斜,所以,那老師站在五樓的門口,還算信心滿滿。
“當(dāng),當(dāng)。”那老師心情輕松地敲門。等了兩三分鐘,屋里沒有動(dòng)靜,再敲,還是沒有動(dòng)靜。從時(shí)間上來看,早已過了下班的時(shí)間,那就是在外面應(yīng)酬,或是去雙方父母那里吃飯。但那老師對(duì)五樓的不在,還不是太放在心里,因?yàn)樽蛱焱砩先思矣性挘蔷偷扔谑桥浜希扔诖饝?yīng)了。
最難對(duì)付的看來是六樓。據(jù)老婆說,六樓的那個(gè)男人態(tài)度比老齊還惡劣,三十多歲,教養(yǎng)很差(樓道里的門幾乎都是他拽壞的),罵罵咧咧,非要那老師的老婆拿出方案來,他看過合理,才考慮是否掏錢。從這個(gè)說法上來看,那老師覺得這個(gè)人或許是研究院的,也可能是某個(gè)局管基建的。那老師針對(duì)他制訂了方案,該怎么說怎么辦,才能讓這個(gè)自以為是、自以為權(quán)威的家伙無話可說,他心里有數(shù)。
但沒想到的是,開門的不是老婆說的那個(gè)男人,是一個(gè)長得并不好看的年輕女人。她眼眉上挑,眼神很刁,說話嘴角一撇一撇的,給人的感覺有點(diǎn)傲慢的樣子。那老師覺得這個(gè)女人應(yīng)該是這家的女主,便問:“你老公在家嗎?”
“我老公不在家,你是誰啊?”
那老師說:“我是三樓的那木拉,昨天晚上,我家人來過。”
“哦。那個(gè)老太太是你老婆?”這句話從那個(gè)小女人的嘴角一撇一撇地說出來,那老師感覺很不舒服。盡管他們樓上樓下可能擦肩而過,可能從來都沒有刻意關(guān)注過對(duì)方,但從年紀(jì)來看,這個(gè)女人的年紀(jì)應(yīng)該和自己兒子的年紀(jì)相差無幾,你可以不敬重我,但對(duì)于快六十歲的人來說,尤其是聽?wèi)T了老師好的那老師來說,就好像一根細(xì)小的魚刺卡在喉嚨里,讓他咽不下去,也說不出話來。那老師開始用老師的審視的目光來看眼前這個(gè)傲慢的小女人。她穿著胸口開得很大的背心,露出不算白的乳溝。這個(gè)小女人可能也看出了那老師的不悅,或許是女性自我的防范意識(shí),她忽然向后面退了退,一手扶著二道門的把手,好像如果那老師再往前靠近,她就會(huì)一個(gè)甩手,把那老師關(guān)在門外。
“你看啥?你個(gè)老不正經(jīng)。”
那老師沒想到這個(gè)小女人會(huì)這么想。他只是想看看上一句話是怎么從一個(gè)比自己小將近三十歲的年輕人嘴里蹦出來的,沒想到這個(gè)小女人把自己審視的眼光看成是淫邪的念頭,那老師真是感到了莫名的侮辱。他把身子向后退了退,生氣地說:“孩子,你怎么能這樣看我,我一個(gè)都快六十歲的人,可能比你父親年紀(jì)都大,你這樣說,簡(jiǎn)直是對(duì)我人格的侮辱。”
那個(gè)小女人看起來并不生氣,嘴角仍然一撇一撇地說:“你們這個(gè)年齡的男人最有危險(xiǎn)性。”
那老師忍著怒火,說:“愿聞其詳。”
“說不行,有時(shí)候還真行。說行,多數(shù)時(shí)候還真的不行……”
2
那老師是今天早晨從六十多公里外的小鎮(zhèn)趕回市里的。
昨天上午老婆給他打電話,說廚房的下水管反水了,她和孫女沒法做飯了。那老師讓她打樓道小廣告上的電話,花了一百五,暫時(shí)不反水了。可誰知道到了傍晚,水槽子里的臟水又上來了,不長時(shí)間又下去了,老婆讓他趕緊請(qǐng)假回來,她都不知道怎么應(yīng)付了。
看天時(shí)已晚,那老師就打同事給他的另一個(gè)人的號(hào)碼,可王師傅不來,說是一二樓飯店在改造的時(shí)候把觀察口都給封上了,根本看不到下面在哪兒堵了,讓那老師另找別人。看來這個(gè)王師傅對(duì)自己樓下的情況十分了解。
從自己家的下水口疏通,說是沒堵,樓下的觀察口又被封到了裝修的墻里,那老師覺得僅憑自己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gè)大事了,他才讓老婆晚上上樓,去和那三家通報(bào)事情的嚴(yán)重。可沒想到樓上的三家竟然是這個(gè)態(tài)度,那老師才在憋屈了一個(gè)白天后,晚上接著上樓。
但白天的那老師也沒閑著,在想辦法自衛(wèi)。
既然人家王師傅不來,昨天找的李師傅又沒修好,總不能讓自己家變成幾家的臟水井吧?住在市里的表弟說:“你再給李師傅打電話,在下面通通,實(shí)在不行讓他給你在連接管上做個(gè)帽兒,干脆擰上算了,大伙一起憋,癤子早晚能出頭。”
李師傅在做熱熔的時(shí)候,那老師還是半信半疑:“那蓋子能擰住?你要知道,水往上走,壓力就會(huì)越來越大,弄不好,還要從我這里冒出來。”
李師傅說:“沒事,這管子不粗,蓋子拱不開。你放心,我頭幾天在小高層那給一家做的,也是三樓,你猜猜怎么樣?沒幾天,八樓的都張羅上了,不掏錢,往上憋唄,用不了幾天,都出頭。”
那天中午,送走李師傅,回來上樓的時(shí)候,碰上下樓的老齊。
“通了?”老齊問。
“還不行。”
“給錢了?”
“又是二百。”
“沒通,你給他啥錢?”
“我也不能讓人家白干活兒不是。”
“那錢,你自己掏,我們可不花……”
3
“當(dāng),當(dāng)!”早起在客廳的老婆喊剛剛起床的那老師。那老師走到門前,說:“沒人敲門啊?是不是你聽錯(cuò)了?”
老婆對(duì)自己的聽力始終是懷疑的,和那老師一起聽聽,還真的沒有聲音。那真是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老婆搖搖頭,似乎對(duì)自己的聽力真的無可奈何。那老師也搖搖凌亂的大背頭,對(duì)老婆一大早晨的一驚一乍感到莫名其妙。
他前腳剛邁進(jìn)衛(wèi)生間,“當(dāng),當(dāng)!”后面的門真的響了兩聲。那老師盡管也快到六十了,但身體的各個(gè)器官都很正常,除了打麻將輸錢是毛病,還真的沒有其他的毛病。那老師把邁進(jìn)衛(wèi)生間的一只腳抽回來,轉(zhuǎn)過身,心想,這兩天都是別人家的門響,那是老婆敲的,自己敲的,沒想到今天一大早晨,還有人敲自己家的門,不會(huì)是表弟吧?但揭開貓眼的一瞬間,那老師就感覺自己的判斷錯(cuò)了,表弟的眼袋沒有這么大,額頭的皺紋也沒有這么多。
老齊。四樓的老齊。那老師悄悄走到茶幾旁,說:“是老齊。”老婆說:“怎么是他?”
那老師說:“怎么不可能是他?”老婆敲敲自己的腦袋,微微地笑了。昨天,李師傅臨走的時(shí)候說,你在這兒住,你就擰下來,你不在這兒里住,你就給它擰上。自己家廚房不反水就行了唄,早晚四樓的會(huì)主動(dòng)找你。
沒想到李師傅還真見多識(shí)廣。
小孫女住在北臥,也被外面的敲門聲弄醒了,她悄悄地對(duì)爺爺說,昨天下半夜她就看到四樓陽臺(tái)廚房的燈亮著,是不是水反到老齊家去了。
還真有這個(gè)可能。
那老師拉開門,站在外面的果然是老齊,眼袋看起來比前幾天還要大,眼睛里面還有發(fā)紅的血絲。
“齊叔,昨天晚上沒睡好?”那老師問。
老齊揉揉眼睛,所答非所問:“真的沒通?”
“有時(shí)候通,有時(shí)候不通。”
那就是沒通。老齊沒用那老師讓,邊說邊往屋里走。
那老師猜想,老齊的廚房昨天晚上肯定反水了。他生怕老齊看到橫管上擰著的那個(gè)帽兒,就用眼睛示意廚房里的老婆。老婆心領(lǐng)神會(huì),用身子假裝一碰開著的柜門,柜門還真配合,一點(diǎn)沒言語,悄悄地關(guān)上了。
“那老師,”老齊第一次這么叫,“都別置氣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擰上了,昨天晚上整了兩回水,你家要是通了,能反到四樓?”
那老師偷偷地看看老婆,又看看孫女,孫女朝老齊那兒擠咕眼睛,他們?nèi)谌硕荚谘劬锿低档匦Α?/p>
4
老齊和那老師在樓下等李師傅。
“李師傅手藝咋樣?”
那老師說:“上下都通了,但還是反水,不知道那鐵鏈子通到哪兒去了。25米,咱們這樓到樓下,哪有25米,是不是下面的管子折了?”
“不能。”老齊說,“你是不是整錯(cuò)了?你是不是沒找對(duì)臟水井?”
樓下一共是六個(gè)臟水井。
老齊和那老師站在地上掂量著這幾個(gè)臟水井。老齊問:“你昨天通的是哪個(gè)?”
那老師用腳直指前面的臟水井。老齊看看,說:“東面的是不是五六單元的?”
那老師在附近找到一把鐵鍬,挖開最東面的那個(gè),里面也是四五個(gè)粗細(xì)不等的管子,但里面沒水,管子里也沒有水流出來,和昨天李師傅打開時(shí)一樣,顯得口干舌燥的樣子。“李師傅說這個(gè)應(yīng)該不是咱們單元的,但五六單元能用一個(gè)臟水井嗎?”那老師反問老齊。
老齊說:“還應(yīng)該有一個(gè)在得天下火鍋的前面。”老齊又讓那老師挖開第二個(gè),也就是昨天李師傅干活兒的這個(gè)。這個(gè)里面還是有水,但不是很深,水面上有四個(gè)粗細(xì)不等的管子。
老齊指著第二個(gè)臟水井說:“你昨天通的哪根管?”
那老師說下面這個(gè)。下面交叉著兩個(gè)細(xì)管。李師傅說應(yīng)該是下面那個(gè)。現(xiàn)在看來,上面那個(gè)正對(duì)著那老師的廚房,老齊認(rèn)為這個(gè)是。
那老師說:“李師傅昨天沒通開,今天不一定來。”就問老齊有熟悉的人沒有。老齊說:“我哪有?樓道里不是有電話嗎?”那老師說:“那就是李師傅的電話。”老齊說:“你再給他打,昨天整的那個(gè)不對(duì)。”那老師說:“齊叔,你萬一整錯(cuò)了,不還是白花錢?”
老齊說:“你這幾天花了多少錢?”那老師說:“前天疏通上面花一百五,昨天上下疏通花了二百,一共三百五。”接管子錢那老師沒說。
“不能錯(cuò)。”老齊指著地面上的一條土棱子說,“沒錯(cuò)。你看那條線,是物業(yè)還有的時(shí)候,宋經(jīng)理領(lǐng)人挖的。這根管子,就是咱們四單元西戶的。你再給李師傅打電話,咱們給他錢,他不能不來,就說他昨天整得不對(duì)。”
還真如老齊所說,李師傅還真的來了。但按照老齊說的那根管子通了二十多米,讓四樓三樓同時(shí)往下面放水,卻沒在這根管子里出來,都在那老師家的廚房里出來了。看來老齊說的還是不對(duì)。那就怪了,老齊和那老師在計(jì)算從家里到臟水井的距離,怎么也超不過25米,那么這真有可能就像李師傅說的那樣,管子可能在一樓拐彎的地方折了,或者是一樓在施工的時(shí)候把管子壓癟了,還有一個(gè)可能是疏通的時(shí)候,鐵鏈子前面的鉆頭把拐彎的地方鉆壞了,水管子里的水是在往土里滲。
那可就不是幾百塊錢的事了。
李師傅說:“這挖開可不簡(jiǎn)單,因?yàn)楣諒澋牡胤皆谝粯堑睦哮啘思业牡匕宕u能讓你挖?那就是五千也下不來啊。”
老齊和那老師都嚇住了,彼此看看,不知所措。這幾百塊錢四家分擔(dān),人家都不愿意掏,這五千塊錢,那更是說不通的,那這個(gè)樓就買瞎了。對(duì)那老師來說,如果這種情況放在幾年前,還好說,他和這些常住人口靠得起。但現(xiàn)在不行,遠(yuǎn)在深圳的兒子把孩子送回來,讓孩子在前面的小學(xué)上學(xué)。孫女都已經(jīng)開學(xué)一個(gè)星期了,廚房反水,做不了飯,這才是那老師頭疼的大事。
那老師看看老齊,老齊沒看他,問李師傅多少錢。
李師傅說:“沒通開,你就給我個(gè)工錢吧,五十。”老齊從上衣口袋里拿出二百塊錢,說:“你剛才說的那個(gè)你熟悉的人干土建的,三千怎么樣?”李師傅說:“我問問,看他這個(gè)價(jià)干不干。”說著,摘下手套,摸出電話。可就在電話撥通的工夫,老齊的手卻按住了李師傅嘟嘟響的電話,把二百塊錢塞給李師傅,說:“不用了。”
不用了?李師傅和那老師一樣,都是一臉茫然。
李師傅走了。那老師說:“你怎么也給他二百?”其實(shí)那老師在老齊拿出二百塊錢的時(shí)候,他曾悄悄地提醒過他,他也以為老齊是想討好李師傅,讓他往下壓土建的錢,沒想到老齊既不讓李師傅去找人,也沒說自己另外找,卻把完整的通下水的錢都給了,老齊這是賣的什么藥?
老齊看著茫然的那老師說:“咱不用他,離譜。但保不準(zhǔn)啥時(shí)候還興許用他,找他,一定痛快。”看來老齊做事,什么時(shí)候都留有余地。
“咱六樓的那個(gè)是個(gè)小包工頭,就是干土建的,我晚上上去問問他三千干不干。”老齊說。
5
第二天早上九點(diǎn)多鐘,老齊給那老師打電話,讓那老師下來。那老師說:“你在哪兒?”老齊說在樓下。那老師走到二樓平臺(tái)上,往下一看,底下站著老齊。老齊的旁邊站著一輛三輪車,一個(gè)老頭從車廂里跳下來,從里面往下卸東西。那老師以為是干活兒的工具,但仔細(xì)一看,卻是通下水道的機(jī)器,比李師傅的小,還比李師傅的破。老齊這是怎么了?不是找六樓的破土嗎?怎么又找來一個(gè)通下水的?
那老師一邊往下走,一邊看著從駕駛室出來的一個(gè)穿軍大衣的男人和老齊說話。
這是石師傅。老齊向走到跟前的那老師介紹眼前的這個(gè)男人。這個(gè)男人的個(gè)子不高,兩個(gè)門牙卻很突出。那老師感覺和他在街上看過的一個(gè)崩爆米花的人很像,就覺得老齊是不是把一個(gè)多面手給找來了,現(xiàn)在在城里混飯吃的全才多的是,看來老齊的眼光比自己也強(qiáng)不了多少,就像昨天他愣說對(duì)著自己家廚房的那根管子是,結(jié)果根本不是。所以,那老師只是禮貌性地和石師傅點(diǎn)點(diǎn)頭,就把老齊叫到一邊。老齊說:“六樓那個(gè)家伙更黑,我昨天就托人打聽了。我愁了半宿,忽然想起來,我和物業(yè)的宋經(jīng)理很熟。你不知道吧?我過去是咱們這個(gè)樓的樓長,經(jīng)常和物業(yè)打交道。我就想咱們給他倆錢,他打發(fā)幾個(gè)工人給咱們干活兒,盡管現(xiàn)在物業(yè)把咱們這個(gè)樓給甩出來了,但物業(yè)應(yīng)該有咱們這個(gè)樓的布局圖,下面的管子怎么走的,一看就一清二楚。我早早地去找宋經(jīng)理,他說不用大動(dòng)干戈,管子不一定壞,是咱們沒看對(duì),他就把過去經(jīng)常給咱們小區(qū)通下水的石師傅給我找來了。”
說話的工夫,石師傅已經(jīng)調(diào)好了機(jī)器,那個(gè)老頭用洋鎬撬開第三個(gè)井蓋。石師傅說:“你們誰都沒我了解你們這個(gè)樓的情況,你們這幾天整得不對(duì),下水井你不能看著是不是對(duì)著你家的廚房,應(yīng)該看哪個(gè)井對(duì)著你們家衛(wèi)生間。”那老師和老齊一看,三號(hào)井果然對(duì)著自己家的衛(wèi)生間。
“那井里的哪根管子是我們這個(gè)西戶的?”老齊問石師傅。那老師也往井里看,這個(gè)井里的臟水比昨天的那個(gè)井多很多,臟水的上面還浮著一層結(jié)實(shí)的糞便。緊貼著糞便的一根粗管子和一根細(xì)管子上下交叉。石師傅說:“這兩個(gè)都不是。粗的是絕活肉餅的,細(xì)的是三單元東戶的,我前幾天才給他們通過。”
“那我們的呢?”那老師絕望地問。
石師傅拿著一根粗管子在糞水里找,一下子對(duì)準(zhǔn)一個(gè)看不見的地方,說:“你們的在這里,也是細(xì)管子。”老齊和那老師不信,都覺得眼見為虛。石師傅讓他們也拿著粗管子去碰,果然在東南方向,水下二十厘米左右的地方有剮碰。
石師傅仿佛賣油翁在世,就是這個(gè)樓的活地圖。老齊說:“你找的那個(gè)李師傅是哪兒的家?”那老師說:“好像是外地的,剛干這活兒時(shí)間不長。”老齊笑了:“一個(gè)生手,咱們白花錢。”石師傅抱怨說:“我真不知道你們現(xiàn)在自治的樓長是怎么想的,我一年一萬五,抽臟水井通下水,她都不讓我干,卻兩萬塊錢包給張老四,你們看看,都看不到管子了,還不給抽,井里的糞塊都快堵上了,也不給掏,這干的叫啥活兒?”
老齊說:“張老四不給通下水。”
“那你們傻啊?把她擼了得了。”石師傅顯然很氣憤。
這個(gè)石師傅說的果真不假。幾分鐘,十五米鐵鏈子就沒影了,停機(jī),再抽出來,除了掛著一些頭發(fā),還真沒有其他的東西,讓四樓三樓同時(shí)往下倒水,果然在臟水里開始冒泡泡,接著形成擴(kuò)散的水波紋。
這真是見了鬼了。是李師傅一竅不通裝神弄鬼,還是把25米的鐵鏈子通到別人家去了?那老師真是無語了。
石師傅說:“看來沒堵死。一般上面都沒事,主要是下面拐彎的地方容易堵。”
老齊開始掏兜,那老師以為他要給工錢,就趕忙掏出二百塊錢。但老齊掏出的是煙。他給石師傅點(diǎn)煙,說,歪嘴子和尚念不了正經(jīng),往后咱們就找石師傅。那老師感覺這話好像不是針對(duì)李師傅,倒是針對(duì)自己說的。
石師傅抽煙。看著那老師遞錢,問老齊,不是你們家啊?老齊說,我們這個(gè)單元四家的。石師傅說,那我就收二百了。他沖著那老師說:“我和老齊熟,今后常年用我,我一回收一百。經(jīng)常往里邊倒點(diǎn)火堿水,試著用幾天,不好使再給我電話。”
6
用了一個(gè)星期,那老師覺得幾家應(yīng)該開個(gè)小會(huì),所以事先讓孫女在那三家的門上貼了通知,晚上七點(diǎn)在六樓開個(gè)碰頭會(huì),可以各家出代表,也可以兩口子都參加,把有關(guān)的事情通報(bào)一下。老齊也覺得很有必要,這不單單是收錢的事。
到會(huì)的一共是七個(gè)人,只有老齊的老伴兒沒參加。老齊說:“一共花了幾百?”
那老師說:“一共四次,總共七百。”
“四次?不是三次嗎?”老齊感覺那老師在訛人。
那老師說:“第一次是在兩個(gè)月前。我在老家,我老婆在深圳給兒子看孩子。老鴨湯的老板給我打電話,說是他家二樓的棚頂洇濕了,是不是我家的廚房漏水了?我一聽就蒙了,我一年幾乎不在這兒住,自來水都關(guān)了,什么地方來的水?我給我表弟打電話,他來了一看,是廚房的下水管反水了,從水槽子里淌出來了,地板上都是臟水。我問那個(gè)老板嚴(yán)重不嚴(yán)重,需要不需要賠償。人家那個(gè)老板很開通,說不嚴(yán)重,就是嚴(yán)重,樓上樓下地住著,也不能讓你賠。我就納悶了,我記得十年前買樓的時(shí)候,老鴨湯在一樓,二樓是住戶,怎么二樓也變成他家的了?看來他家的生意整得挺紅火。我挺感動(dòng),讓表弟找了通下水的,花了一百五,在我家往下面通通,還真沒事了。誰知道才過了兩個(gè)月,又反水了?我老婆又花了一百五,還是沒弄通。我也找不到別人,又找了那個(gè)李師傅,他沒有經(jīng)驗(yàn),我也是外行,沒成功,前面那三百算是交學(xué)費(fèi)了。剩下的四百,齊叔掏二百,我掏二百,我們四家均攤。”那老師的老婆用眼睛掐了他一下,但那老師一點(diǎn)都沒有理會(huì)。
老齊說:“那老師,我那是逗笑話,我那天說,沒打通給他啥錢,你自己掏啊,你別當(dāng)真。一是一,二是二,你們兩家說是不?”
五樓的女人說:“我那天就說過,我們不懂,掏一百也好,二百也好,這次我們都掏,但回?cái)?shù)多了,我們也不掏,我們一個(gè)星期也做不了幾頓飯。”
“那是。”六樓的女人仍然嘴角上翹著說,“我們也是,反正反水,也到不了五樓、六樓。”看來她也想找個(gè)盟友。
那老師老婆說:“如果你們說都沒怎么做飯,那我們算算,我們這幾家誰在這兒常住?”
“從打買樓,有十年了吧?”那老師老婆說,“我們?cè)谶@兒住過的時(shí)間沒有半年,根本就沒怎么做飯,每次都是開會(huì)路過,進(jìn)來看一下。你們?nèi)艺l都比我們住的時(shí)間長,但我們也沒有想到,剛買樓的時(shí)候,我們也覺得只有一二樓才能堵,可這么些年,人們都有經(jīng)驗(yàn)了,一二樓的都自己另外裝下水管了,我們?nèi)龢且幌伦幼兂闪艘粯恰K裕铝耍秃孟袷俏覀內(nèi)龢堑氖隆!?/p>
那老師說:“說實(shí)在的,遇到這樣的事我們真的鬧心。不找你們吧,我們覺得心里憋屈;找你們吧,我們又感覺好像做了虧心事。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們?nèi)易∪龢牵銈兪亲约禾湍兀€是按照常規(guī)出牌?”
“反正一時(shí)半會(huì)兒也上不來,我們過一天算兩晌。”六樓的女人接茬說。
“那我們就互相憋?”那老師反問。
“憋就憋。我們高,我們不怕。”六樓的女人看來不怕事大。
那老師覺得這兩個(gè)年輕人就好像自己班級(jí)里刁蠻的女學(xué)生,明明知道自己理虧,卻總是極力狡辯。這種情況下,打不得,罵不得,就得掰包子讓他們看餡兒,才能心服口服。他壓住怒火,說:“我先不跟你們?nèi)リ瘛O滤軟]堵的時(shí)候,我也沒看它長得什么樣,但這幾天我一看,它長得挺瘦。你們說說,它的腰圍是多少?”
那兩個(gè)女人就好像沒注意聽課的學(xué)生,一時(shí)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問題。
老老少少的幾個(gè)人都不言語。
那老師說:“我量了一下,直徑六十毫米。我們各家房子的舉架是多少米?”
有人說三米,也有人說二點(diǎn)七米。老齊說:“二點(diǎn)七米,我自己裝修的,記得沒錯(cuò)。”幾個(gè)年輕人都不知道自己家的房子舉架是多少米。
那老師看年輕人不言語,就又說:“長二點(diǎn)七米,直徑六十毫米,這個(gè)管子的容積是多少?”
幾個(gè)年輕人更不說話了,面對(duì)老師提出的問題,他們不知道怎么算。那老師說:“我不需要你們回答,但你們想想,我們做一回飯,洗菜,淘米,要倒多少水?那個(gè)管子你們?nèi)彝碌梗貌涣硕嚅L時(shí)間,就會(huì)灌滿二點(diǎn)七米。容積我們不說,就說長度,從我家算,幾個(gè)兩米七到你們幾家?”這個(gè)問題好像讓幾個(gè)年輕人心動(dòng)了,默默地看著那老師。
“我看還是別置氣了,我們住戶碰到一起,也是緣分。”老齊看局勢(shì)僵化,打著圓場(chǎng),“跟你們說實(shí)話吧,我原先也覺得四樓沒事,也說了許多難聽的話,結(jié)果那老師把下面堵上了,一個(gè)晚上就憋到我家了。廚房一冒水,我才覺得不是相互置氣那么簡(jiǎn)單,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在平房里住可以,在樓房里住,那還真不是一家的事了。”
那老師順勢(shì)說:“過去你們也都住過平房吧?”幾家都說是。那老師說:“那個(gè)時(shí)候,就是我們住一趟房,也是各掃門前雪,是幾個(gè)獨(dú)立的個(gè)體。那個(gè)時(shí)候我們是平行的關(guān)系,但現(xiàn)在不行,我們是什么關(guān)系?”那老師的職業(yè)病犯了,好像在課堂上講課,又開始了啟發(fā)式。
“垂直關(guān)系。”五樓的男生說。
“對(duì)。”那老師說,“你說的很對(duì)。”其他幾個(gè)人也覺得是這么回事,沒人反駁。那老師說,那個(gè)時(shí)候一家一個(gè)臟水井,別人家堵了,我們可以不管,但現(xiàn)在卻是兩根管子連著我們四家,好在我們的衛(wèi)生間還沒堵,那要是反水,更是讓人反胃的事。”
看著身邊的幾個(gè)人沒人反對(duì),那老師開始教誨了:“所以說,我們并不是沒有關(guān)聯(lián)的人,按照現(xiàn)在的說法,我們四家就是一個(gè)命運(yùn)共同體。你們不知道聽說沒有,有個(gè)小區(qū)有個(gè)單元,互相斗氣,一共十層,下水都憋到八層了;還有的小區(qū)因?yàn)椴惶湾X,都鬧上了法庭。我覺得我們幾家不應(yīng)該是這個(gè)覺悟,你們說對(duì)不?”
“不能那樣。”老齊帶頭說。
五樓的男生說:“您是老師吧?”
那老師說:”我們兩口子都是老師。”
“就你們老師能說。”六樓的撇嘴女人冷不丁冒出一句。
那老師老婆的眼睛一下子變大了,那老師往身邊拽拽老婆,說:“你說的不完全對(duì),我們老師在課堂上能說,但在社會(huì)上卻真的不會(huì)說,生活經(jīng)驗(yàn)少,常常發(fā)傻。我跟你們說,我一點(diǎn)都不撒謊,如果不是堵的回?cái)?shù)多,城里的老戶不說,我還真的沒想到這個(gè)下水管是咱們四家的事,你說我們傻不傻?我買了十年的樓,在這兒沒住過半年,你們往下倒,我找?guī)煾担屹I單,你們要是換成我,你們是不是也會(huì)傻到現(xiàn)在?如果老鴨湯的老板不好說話,讓我賠個(gè)幾千,你們說,我冤不冤?”
五樓的女人說:“過去我們有物業(yè),打個(gè)電話就有人干了,現(xiàn)在不行了,啥事都得自己張羅。”
那老師說:“那個(gè)時(shí)候有物業(yè),我們幾家好像沒有關(guān)聯(lián),那真是‘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可現(xiàn)在物業(yè)沒了,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五樓的女人說:“老師您是數(shù)學(xué)老師,還是語文老師?”
那老師說:“我是數(shù)學(xué)老師里語文最好的。”那個(gè)女人撲哧一聲笑了。她的男人說:“我冒昧地問一下,老師您姓那?是滿族嗎?”
“不是。”
“您的名字?”
“那木拉。蒙語,秋天的意思。”
五樓的男生很興奮,說:“是咱們市那個(gè)有名的大作家?”
那老師說:“不大,沒到一米八。”
“我經(jīng)常看您的作品,我們認(rèn)識(shí)一下,我也是市政府搞文字的。”說著,向前,和那老師握手。
“我們真是有眼不識(shí)金鑲玉,大作家就在咱們單元。”五樓的女人說。
“我哪有你們說的有名,就是一個(gè)寫作文的數(shù)學(xué)老師。”
“您太幽默了,周日我們聚聚。”五樓的男生發(fā)出邀請(qǐng)。
“好。”那老師給予回應(yīng),“沒有物業(yè),我們就得自己自治,我有的時(shí)候聽到你們使勁拽單元門,真的很心疼,為什么不用鑰匙?這一百塊錢都覺得心疼,那單元門壞掉了,你們都愿意掏嗎?”
“我可沒拽。”五樓的女人說,“我還掃過幾回樓道呢,也不知道誰,總是扔煙頭,再讓我看著,就罰他掃樓梯。”
那老師說:“我看見過你在晚上掃樓梯。單元門的燈,我花錢安上了,你們要再使勁拽門,估計(jì)那燈還得壞。”
老齊說:“都注意點(diǎn)。能再讓物業(yè)接收咱,那就省事了。”
那老師說:“有物業(yè)的時(shí)候,有的人挑刺,不交物業(yè)費(fèi),我聽說咱們這個(gè)樓,情況最嚴(yán)重。不瞞你們說,我今年被選上政協(xié)委員了,我可以和社區(qū)聯(lián)系聯(lián)系。”
“那可太好了,你趕緊聯(lián)系。”老齊說。
“不過也不一定那么快。”那老師回應(yīng)說。
看四樓和五樓的都站到那老師的一邊了,六樓的女人說:“我們想通了,也掏,我們都沒有啥文化,也不會(huì)說話,我向老師道歉了。”
那老師說:“沒事,時(shí)間長了,我們就知道誰的脾氣秉性了。見面不說話可以,但啥時(shí)候都得明理。”
老齊說:“那咱們就每家二百,也不能讓那老師吃虧啊!”
“不行啊。我說話算數(shù)。前面那三百,算我的,剩下的四百,四家均攤,還省得出零數(shù)。”那老師不依不饒。
“那怎么行?”五樓的男女說。
“我說行就行。這次就是我多掏,往后大家均攤。”那老師說著虛擬地扇了自己一個(gè)嘴巴,“我可不希望有以后啊!”
看見大家僵持,老齊說:“那既然那老師大度,我們就占點(diǎn)便宜,一家一百。”
“是現(xiàn)金還是微信轉(zhuǎn)賬?”有人問。
那老師說:“我看咱們也建個(gè)群,往后聯(lián)系方便,都要實(shí)名制,寫上電話。”
“我保留意見。錢,我可以給,但,話我也得說。”六樓的男人在長時(shí)間沉默后爆發(fā)了。
“你說啥呢?”六樓的女人沖自己的男人瞪眼睛。
“我沒喝酒。我跟你們說,你們這么整,不是長久之計(jì),治標(biāo)不治本,我們應(yīng)該研究一個(gè)方案,徹底解決這個(gè)問題。”
那老師說:“不到萬不得已,我們還是疏通。大動(dòng)干戈,那麻煩事可就多了,一樓二樓的飯店是不是讓你扒墻刨地板,都是一個(gè)未知數(shù)。再說,我們找對(duì)了人,各家再注意點(diǎn),哪能總堵呢?”
老齊說:“我知道你是包活兒干這個(gè)的,可也不是現(xiàn)在,將來實(shí)在壞了,小子,那個(gè)時(shí)候你再制訂方案,我們保證沒有二話。”
7
第二天早晨,老婆買早點(diǎn)上來,氣哼哼地把包子、豆腐腦扔到桌子上。那老師問怎么了。
“憋氣。搬家。”
那老師看到老婆的眼睛里汪著淚花,就一邊抽紙巾,一邊說:“小點(diǎn)聲,孩子還沒醒呢,說說,到底咋回事?”
老婆擦干眼淚說:“上樓的時(shí)候,碰到六樓的兩口子,我和他們打招呼,這兩個(gè)人不回話也就算了,卻對(duì)著我吐吐沫。這幫人,素質(zhì)真差。”
那老師說:“也別這么說。咱們和人家接觸得少,時(shí)間長了,就能發(fā)現(xiàn)他們的優(yōu)點(diǎn)。”
“就你心大,你班主任沒當(dāng)夠啊,還想當(dāng)什么單元長?”
那老師笑了:“沒當(dāng)夠,你知道我在學(xué)校是善于帶亂班的。再有一年半,把這個(gè)班級(jí)帶到畢業(yè),我就退休了,我還得帶這個(gè)社會(huì)班。”
老婆說:“我看你是帶班成癮了?我在這兒待不慣,還是想回農(nóng)村,回到草原,省得憋氣。”
“那孫女不念書了?農(nóng)村有農(nóng)村的憋氣事,城里有城里的煩惱。你退休了,要開啟城市的新生活,總是要碰到新的人,發(fā)生新的事。”
“可這也太點(diǎn)兒背了吧,剛想長期住,就遇到這樣的壞事,我看著他們就心里別扭。”
那老師說:“我的包老師,你這個(gè)多年的思品老師,怎么當(dāng)?shù)模客诵萘耍磫栴}也應(yīng)該有點(diǎn)哲學(xué)思維嘛……這怎么都是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