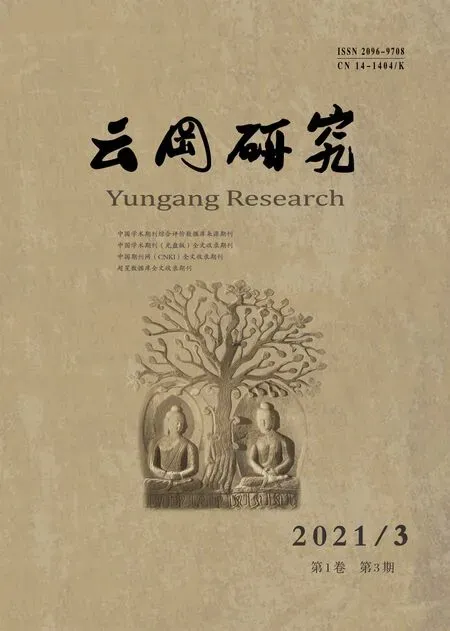從墓葬壁畫看遼金西京大同的社會生活
王利霞
(大同市博物館,山西大同037009)
907年,以耶律阿保機為首的契丹族在我國東北地區建立起大遼國,與后來的北宋、西夏形成三足鼎立的割據政權。立國以后,遼太祖率領部眾南征北戰、開疆擴土,擁有了廣闊領土。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以后唐節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求援契丹之際,不費吹灰之力獲取了肥沃的燕云十六州地區,其中云州即為大同。由此,契丹不僅占據了廣袤的農業地區,增強了經濟實力,而且打開了南下中原,直入北宋腹地的屏障,這是遼國與北宋能夠形成長期對立局勢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1044年,為了加強邊防守衛,遼興宗升云州為西京大同府,自此大同成為遼五京之一,為遼國西南地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1125年金滅遼,承襲遼制,仍作大同為西京。大同作為遼金西京近兩百余年,經濟繁榮、文化昌盛,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區域特征造就了該地區風格迥異的人文生活,這在大同地區遼金墓葬中出土的壁畫內容中表現的尤為突出。近年來,大同地區出土了數十座遼金壁畫墓,題材眾多、內容豐富,本文以這些壁畫內容為研究對象,從中探索遼金時期大同地區的社會生活概況。
一、大同地區的遼金壁畫墓概況
就目前的考古發掘資料來看,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大同地區發掘、清理了50余座遼金墓葬,其中壁畫墓20座,分別為遼代17座,金代3座,主要分布在大同北郊、西南郊及南郊地區,尤以西南郊居多,是遼金時期的主要墓葬區。為方便研究與閱讀,筆者將大同地區遼金壁畫墓的相關信息作了簡單整理(見表1),并以此對壁畫中所體現出來的服飾、飲食、勞作、娛樂、出行等生活信息加以提煉分析并作對比性研究。

表1 大同地區遼金壁畫墓

大同十里鋪M27[3]墓門兩側守門侍女圖西壁出行圖北壁侍者圖東壁生活圖墓門兩側守門侍女圖西壁出行圖北壁侍者圖東壁生活圖大同十里鋪M28[3]西壁出行圖、飲宴圖北壁繪圍欄東壁牽馬圖、飲宴圖大同新添堡M29[3]大同南關M2[6]墓門兩側人物圖西壁生活圖東壁備膳圖遼代墓門兩側守門侍官圖西壁牽馬圖、牧群圖東壁動物圖(牛、2只動物)大同南郊五法村遼墓[6]大同周家店遼墓[6]甬道兩側門神圖墓門西側收財帛圖墓門東側燈擎侍女圖西壁侍女圖北壁守門侍官圖、待客圖東壁守門侍婢圖、備膳圖大同和平社M45[7]西壁出行圖北壁侍奉圖東壁飲宴備膳圖大同東風里遼墓[8]墓門兩側守門侍者圖西壁出行圖、農耕圖北壁起居圖東壁侍酒散樂圖、吉祥圖大同云中大學M1[9]南壁守門侍者圖西壁備膳圖北壁侍奉圖金代大同云中大學M2[9]南壁守門侍者圖西壁宴飲圖北壁侍奉圖東壁備膳圖大同金代徐龜墓[10]西壁散樂侍酒圖北壁侍奉圖東壁侍女圖
從目前大同地區出土的遼金壁畫墓來分析,遼代壁畫墓占比較多,20座遼金壁畫墓中有17座為遼代壁畫墓,占比85%,這一方面凸顯了遼代大同地區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揭示了遼金時期該地區豐富多彩的人文生活,而這在題材眾多、內容豐富的壁畫上表現的淋漓盡致。從表1可知,壁畫內容以人物侍奉圖居多,其次為宴飲、出行等場景,另有少量的農耕及勞作的畫面。盡管與遼金腹地相比,大同地區的壁畫不論是從內容的表現形式,亦或是畫面的表現題材上來看,都略低一籌,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該地區的壁畫又有明顯特點。首先,壁畫人物形象以具有鮮明唐宋風格的漢人為主,契丹或女真人物形象較少,目前僅有大同市機車廠遼墓、東風里遼墓以及南郊云大1號和2號金墓中出現了頭梳髡發的侍從人物形象,這與遼上京、中京墓葬壁畫出現較多的契丹隨從不同。這一現象表明,盡管大同為遼金西京轄區,是遼金政權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由于歷史淵源及地緣關系,該地區歷來受中原文化影響頗深。其次,壁畫題材承襲唐宋舊俗,以人物侍奉、宴飲為主,而在大同遼代的壁畫中又有這樣的特點,即早期無出行圖,晚期有出行圖但無歸來圖,同時在早期至晚期的遼墓墓室正壁也不見墓主人形象,更沒有遼腹地常見的狩獵場景,這與遼上京和中京地區的遼墓壁畫形成鮮明對比。而遼中晚期出現的農耕圖、勞作圖以及牧群或放牧的場景,揭示了大同地區獨特的生活勞作習俗。由此來看,遼金西京大同無論是從人物形象、衣著服飾,還是宴飲文化、出行勞作都有其獨特之處。
二、壁畫中的生活習俗
古人認為:人雖死,靈魂不滅,于是便有了對長眠之地的裝飾或隨葬器物的常伴,而這些又恰恰是現實生活世界的反映,豐富的壁畫內容既寄托了逝者步入靈界的美好愿望,又展示其生前生活休閑的場景,是研究古人生活習俗的重要實物資料。
(一)服飾特征
遼代服飾有民族之分,有國服和漢服之別,國服指的是契丹服飾,早期以野獸和牲畜的皮毛制成,建國以后,伴隨著疆域的開拓及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毛麻紡織品及絲綢之類愈加增多,《遼史·儀衛志》記載:“太宗制中國,紫銀之鼠,羅綺之筐,麋載而至。纖麗耎毳,被土綢木。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國制,南班漢制,各從其便焉。”[11](卷56,P905)從上述的文獻記載中,我們可以一窺當時服飾風貌,而近些年大量的考古發掘及墓葬壁畫的出土,使人們對遼代服飾有了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那么,作為遼金西京大同,當時人們的衣著服飾又有何特征呢?
男服。以圓領、寬袖(窄袖)長袍為主,內搭中單,亦有翻領、斜領長袍。以袖子的特征來看,大同地區遼代早期壁畫中的男服以寬袖居多,如遼景宗乾亨四年(982年)的許從赟夫婦壁畫墓中的墓門東側男侍官圖、北壁守門侍官圖,皆“身著圓領寬袖長袍,腰束帶,足蹬黑履。”[2]與許從赟墓墓室結構相似、繪畫風格相同,同屬于遼代早期的周家店遼墓中的男性侍從同樣身著圓領寬袖長袍,如墓室西側的“書房行文圖”,桌子后方的兩位男子,一人身著淡藍色圓領寬袖長袍,雙手叉于胸前,兩臂之間橫置著一根長尺;另一人則身著深藍色圓領寬袖長袍,束黑色腰帶,左手捧一賬冊,右手執筆,躬身作記錄狀(圖1)。[6]在墓室正壁的“守門侍官圖”中,兩位侍從皆著紫褐色圓領寬袖長袍,同樣在墓室西北角的“待客圖”中的侍者均身穿圓領寬袖長袍。這種服飾具有典型的中原漢人服飾特征,說明遼代早期,大同地區的文化特征以中原為主,契丹因素浸潤甚微。遼晚期及金代壁畫墓中的男性侍從的服飾多為窄袖長袍,內著中單。大同市東風里遼墓為典型的遼晚期墓葬,墓室西壁“出行圖”的馭者與隨從身著圓領窄袖長袍,北壁“起居圖”中的三位男性侍從,除一人著右衽窄袖衫外,其余兩人均身穿淺灰色圓領窄袖長袍,內著中單,腰系軟帶。此外,在墓室東壁的“侍酒散樂圖”中的五位中年男性侍從,皆身著藍色、紅色或淡黃色圓領窄袖長袍,內著白色或綠色的中單,腰間系黑色或黃色軟帶(圖2)。[8]在云大1號和2號金墓壁畫中,所有的男性侍從均身著圓領窄袖長袍,腰系帶。而這種服飾在遼上京、中京地區的壁畫中十分常見,說明遼中晚期大同地區受契丹文化影響頗深。

圖1 紙箱廠遼墓“書房行文圖”中的男服形象(寬袖)

圖2 東風里遼墓“侍酒散樂圖”中的男服形象(窄袖)
女服。多上著襦衫,下著長裙,極少著交領寬袖掩腳長裙。如和平社M45號遼墓北壁壁畫,畫面正中繪三扇轉角屏風,屏風兩側各繪一侍女,均上身穿青灰色寬袖襦衫,下身著米黃色長裙。而在西環路1號遼墓西壁,侍女上身著粉紅色寬袖衫,內著中單,下身穿青色長裙。同樣,在許從赟夫婦壁畫墓墓門兩側的侍女圖、東壁的守門侍婢圖、東北角及西北角的侍女形象均身穿寬袖襦服,淺色長裙(圖3)。與這些侍女服飾不同的是,周家店遼墓中侍女均著寬袖掩腳長裙,如墓室東北角的“備膳圖”中,畫面左側的兩位侍女頭梳高髻,身著交領寬袖掩腳長裙,或雙手捧盤,或站立交談;畫面右側的一侍女身著交領寬袖掩腳長裙,雙手捧一桃形食品。[6]由此來看,遼金時期大同地區的女性服飾以裙裝為主,通常上為衫,下為裙。就特點而言,與上述男性服飾相同,遼早期襦衫的袖子寬廣,具有明顯的唐傭遺風,遼晚期及金代襦衫的袖子窄而小(圖4),呈現出少數民族服飾特征。

圖3 許從赟墓中的女服 (寬袖)

圖4 東風里遼墓中的女服 (窄袖)
冠飾。以幞頭為主,有無腳、展角(又稱硬角)、軟角之分。大同站東金代徐龜墓墓室東壁的三位男性侍從均戴無腳幞頭,留八字胡,作策馬行進狀。而在云大1號金墓東壁的“備宴圖”、西壁的“宴飲圖”以及2號金墓的“備宴圖”中所有的男性侍從皆戴無腳幞頭。周家店遼墓的“待客圖”、“收財帛圖”以及許從赟夫婦壁畫墓墓門東側的“侍官圖”(圖5)、臥虎灣4號遼墓西壁的“宴飲圖”中的侍從均頭戴展角黑色幞頭。軟角幞頭相對于展角(即硬角,兩端平直)幞頭而言,兩端展自然下垂,行動時有飄逸之感(圖6),頗受文人及士官喜愛。如周家店遼墓北壁的“守門侍官圖”,兩位侍官身著圓領寬袖長袍,頭戴黑色軟角幞頭,叉手面向朱紅大門而立。除幞頭以外,亦有氈帽、東坡巾、軟巾、草帽、斗笠等。在臥虎灣4號遼墓西壁的“宴飲圖”中,有的頭戴黑色軟巾,有的戴漁翁式草帽,而在東壁的“宴飲圖”中,有的則戴東坡巾。

圖5 硬腳幞頭

圖6 軟腳幞頭
鞋靴。以靴居多,由皮革或氈制成,可保暖御寒,如東風里遼墓墓室南壁的老者身著黃色圓領長袍,腳穿黑靴,而在東壁的“侍酒散樂圖”中的五位中年男性侍均腳穿黑色長筒靴(圖2)。此外,還有布鞋、麻鞋、草鞋(圖8)等。大同機車廠遼墓南壁侍從,“上身穿圓領粉紅色長袍,下身著緊口長褲,腳穿黑白相間布鞋,兩手攏于袖內”。[1]而在許從赟夫婦墓所有的侍從中,除女性侍者長裙掩腳看不出鞋靴外,男性侍從多著黑履(鞋),東壁的守門侍者則著草鞋。由此可見,遼金時期大同地區人們的鞋子式樣較多。
(二)飲食文化
關于飲食,筆者在《從墓葬壁畫看遼金大同地區飲食文化》做過詳細解讀,就大同地區目前所發掘出土的遼金壁畫墓而言,除人物侍奉圖外,備飲、備食、宴飲等場景較多。遼代早期,大同地區的墓葬壁畫尚未形成固定布局,四壁以人物圖為主,宴飲或出行場景較少,典型代表便是許從赟夫婦壁畫墓。到了遼代中晚期,則主要以人物圖、備宴圖、出行圖為主,并由此形成了固定的區域裝飾內容。通常墓室北壁繪人物圖或侍寢圖(與遼上京和中京地區墓室北壁通常會出現墓主人形象不同的是,大同地區遼代壁畫墓正壁隱去了墓主人形象,只出現花卉、屏風以及侍者等表現生活的場景),墓室西壁繪出行圖或出行準備圖(也有在西壁同時繪出行和宴飲兩種不同場景,如臥虎灣遼墓群),東壁則一般繪宴飲或備膳圖,南壁繪侍者或門神形象。到了金代,壁畫裝飾內容發生了明顯的區別,西壁以盛大的宴飲散樂場景取代了出行圖像,東壁、北壁與南壁延續遼代繪畫內容,仍以備膳、侍宴及人物侍奉圖為主。也就是說遼金時期宴飲或備膳圖在墓葬壁畫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大同地區的飲食壁畫中并未出現遼金腹地常見的烹飪或煮肉的場景,卻有放牧及農民勞作的畫面,這說明當時該地區的肉類食物并不像遼上京或中京地區被普遍食用,由于糧食作物豐富,相應的農產品才是該地區主要的食用品種,而這在壁畫中亦有突出表現。
主食。《遼史·禮志二》記載:“大臣敬酒,皇帝飲酒。契丹通,漢人贊,……贊各就坐,行酒肴、茶膳、饅頭畢。從人出水飯畢,臣僚皆起”[11](卷50,P843-844)。同時《事物紀原》又載:“古之饅頭有餡,用豬、羊肉之以面,像人頭。”[12](卷9,P333)這里所記的“饅頭”應與現今的包子相似,在壁畫中也常見這類食物。如大同市南郊云大1號金墓的宴飲圖,在畫面中央的長方形高桌上放置一透明紗罩,紗罩下又放著數個白色圓形食物,筆者猜測應是饅頭或包子一類的面食品。此外,在南郊云大2號金墓的宴飲圖中亦有類似的場景,畫面中共八位男侍,左起第二人手端一大圓盤,盤內盛放著六個白色桃形食物,第四人雙手捧著一蓋有紗罩的器皿,紗罩內又放置六個白色帶褶圓形食物。可以肯定是,這兩位侍從手中端著的食物應是饅頭或包子之類的面食。在侍從前方的高桌上又放著一個較大的紗罩,內有數個大小不等、涂著黃色或紅色的圓形食物,可能為點心一類的面食。除此外,還有餅、餅餌、艾糕之類的面食品,不過這些在大同地區的壁畫中鮮少出現,但出土的隨葬器物可以證實這類食物的存在,尤其面餅應是西京地區重要的面食品種。該地區的遼代許從赟夫婦墓及云大1號金墓、2號金墓都出土了鐵質鏊盤。《正字通》中記載:“鏊,今烙餅平鍋約餅鏊,亦約烙鍋鏊”,[13](P2483)由此來看,鏊盤應為古代烙餅的一種工具,其做法是先將鏊置于爐火之上,再將搟好的面餅放置于鏊面上,待餅烙好鏟出,面餅形狀類似于現在新疆地區常食用的馕。因此,鏊盤在大同地區的遼金墓葬中都有出現,充分反映出面餅是該地區重要的食物之一。
飲品。以酒和茶為主。大同地區農作物種類豐富,為釀酒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故有“蔬菜果實、稻粱之類糜不畢出”,而西京大同“礬麹尤盈”。這里的“麹”凡指酒,說明該地區釀酒業十分繁榮,而在該地區遼金墓葬壁畫中的備膳圖、宴飲圖、備飲圖出現的飲酒場面以及器型不同、式樣豐富的酒具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如大同站東金代徐龜墓西壁的“散樂侍酒圖”,畫面中的方形高桌上放置著一曲沿盆、數件蓮瓣形盞、荷葉形盞以及一套注子及注碗,在高桌下方的一長方形矮桌上,放置著兩件帶底座且封口的黑色梅瓶。壁畫左側侍女雙手捧著一淺藍色橄欖形瓶,正側身往曲沿盆內倒酒;右側的兩位侍女,一人雙手托著一帶溫碗的注壺,另一人雙手捧一方盤,盤內放著一荷葉形盞,似作斟酒之狀,畫面形象生動、富有意境(圖7)。[10]同樣在大同東風里遼墓的“侍酒散樂圖”以及云大金墓群的“備膳圖”、“宴飲圖”中也有類似的場景。此外,隨葬器物中還出土了大量的梅瓶、雞腿瓶、注壺以及盞、盅等典型酒具。由此說明,大同地區飲酒之風十分盛行。除酒外,飲茶也是遼人重要的風尚,如墓葬壁畫中出現的茶盞及執壺等,皆為典型的飲茶器具。

圖7 徐龜墓西壁的“散樂侍酒圖”中酒具組合及食物
(三)出行勞作
從表1可知,關于出行場景主要集中在大同地區的遼代墓葬,尤其是遼晚期墓葬,如臥虎灣遼墓群、西環路遼墓群、和平社遼墓群以及東風里遼墓,這些墓葬的墓室西壁皆繪出行或出行準備圖,為大同地區遼墓“程式化”特點之一。金代以后承襲唐宋舊制,墓室西壁不在呈現出行場面,而是代之以盛大的“散樂侍酒”場景。因此,我們這里所介紹的出行特征主要以遼代為主。
大同地區遼早期的出行場景通常由人物或牧人牽馬或放牧形象出現,如大同機車廠遼墓墓室西壁的出行準備圖,畫面中既沒有車馬,也沒有遼晚期常見的駝及駝車,單以兩位出行人物表現意境。畫中男性侍從(南側題記“牛哥”)寬額粗眉、高鼻闊目,身著圓領灰色寬袖長袍,雙手捧著一醬紅色包袱。女性侍從(北側題記“大喜子”)寬額彎眉、面部渾圓,身著紅黃色寬袖掩腳長袍,雙手捧著一敞口壺與牛哥站立,似在耳語。[1]通過這樣一組人物畫面以及題記中的人物稱謂來表現其意欲出行的場景。同樣為遼早期墓葬的五法村遼墓的出行圖則是另外一番情景。在該墓的墓室西壁分別繪有“牽馬圖”和“牧群圖”,牽馬人頭戴冠帽,身著紅色圓領窄袖衫,腰系帶,腳蹬皂靴,左手執轡,右手掌鞭,站立于馬旁,仿佛在等待主人騎馬出行。在這一畫面的左側又繪馬群及羊群,它們或互相追逐,或低頭吃草,呈現出一番別有韻味的草原風情。由此來看,大同地區遼早期壁畫墓的出行畫面并沒有形成固定的繪畫內容,即使是屬遼早期偏晚的五法村遼墓出現的牽馬出行的場景依然相對簡約,而遼上京、中京以及該地區遼晚期壁畫墓常見的駱駝或者駝車(典型的游牧民族的墓葬壁畫內容)并未出現。盡管牧馬、牧羊、牧牛及出行場景的出現,反映了遼代大同地區亦農亦牧的經濟形態,揭示了自后晉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后,大同地區所呈現出的契丹化傾向,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傾向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所呈現出的特點并不鮮明。歷經半個世紀的文化浸潤,大同地區的契丹化傾向愈發明顯,表現在出行畫面上,則是形成了固定的繪畫內容(畫面通常由人物、馬、駝及駝車構成)(圖8),出現了與遼上京壁畫相似的駝及駝車。與遼上京相比,大同地區遼晚期的出行圖又呈現出這樣的特點。首先,出行人物(馭者及隨從)通常為頭戴裹巾,身著窄袖袍的漢人形象,頭梳髡發的契丹人物并未出現。其次,除東風里遼墓的出行場景畫幅較大、內容豐富外,其它墓葬的出行畫面較為簡單,如和平社45號遼墓,只在墓室西壁一角繪出鞍馬、駱駝及馭者。盡管這樣簡約的畫面與遼上京大幅的出行場景無可比擬,但遼北地常見的駱駝和駝車在這里依然出現,說明契丹文化已經滲透到該地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墓葬習俗。

圖8 東風里遼墓西壁“出行圖”(局部)
西京大同是典型的農耕區,農業經濟發達,但墓葬壁畫中關于農耕勞作的場景極為少見,目前僅有東風里遼墓西壁所繪的“農耕圖”,畫面由勞作的人物、耕牛以及農具構成,上方繪出起伏的山峰與植物,中間繪四位農民田間勞動的場景,左起第一位頭戴氈帽、右手拿鋤,左手抬至額頭似在擦汗;第二位頭戴斗笠,上身赤裸,下桌短褲,雙手握鋤,作鋤田狀;第三位為送飯女,上著襦衫,下穿長裙,肩扛兩端挑有罐的扁擔;第四位頭戴氈帽,身著短袍,手扶牛拉的耬車,作播種之態(圖9)。[8]而在畫面的下方又繪著顆粒飽滿的谷穗,周邊點綴背月方孔錢及銀鋌,寓意五谷豐登、生活富足。由上述內容可知,大同地區的壁畫既有農耕勞作的場景,又有牧羊、牧馬及駝車出行的畫面,深刻反映出遼代大同地區獨特的文化面貌。

圖9 東風里遼墓“農耕圖”(局部)
(四)娛樂活動
據文獻記載,遼國境內的娛樂活動豐富,包括音樂、舞蹈、雜技及游戲等項目,在遼上京的壁畫中出現了“蹴鞠”這樣的體育活動,但大同地區的遼金壁畫墓中并未出現類似畫面,而是以散樂形式出現的宴樂活動為主。散樂包括歌舞、俳優、角觝等,遼太宗天顯四年(929年)正月,皇帝宴請群臣及外國使節,便“觀俳優、角觝戲”。此外,在民間的重要活動諸如婚嫁儀式、宴請賓客等,除行酒外,還有歌舞、奏樂、雜劇等,散樂器有蕭、琵琶、拍板、大鼓等。在大同南郊云大1號金墓的西壁的宴飲圖中就有這樣的場景,畫面中共七名侍者,其中四人,一人身著綠袍,雙手握笙作吹奏之狀,另一人身著紅色長袍,雙手拿著一拍板表演,第三人身著紅褐色袍,左右手各執一樂器(左手樂器形似圓筒狀,右手樂器上扁下圓,中間系帶,形似木鏟),最后一人雙手握笛(圖10)。[9]此外,金代徐龜墓西壁的侍酒散樂圖亦有古箏、觱篥、笛子、拍板等樂器,在臥虎灣2號遼墓東壁的樂官圖中既有吹排簫、豎笛、橫笛、笙的場景,又有彈琵琶、擊拍板、敲大鼓、打腰鼓、敲方響的畫面。這些壁畫中的散樂情形表現了遼金大同地區一般士族生活中的宴飲娛樂活動中散樂的配置以及樂器組合的形式等,為研究該地區生活習俗、娛樂文化等內容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圖10 云大1號金墓西壁“宴飲圖”
結語
正如上文所述,盡管大同地區為遼金兩朝重要的都城之一,但是前期受中原文化影響頗深,以致于服飾、飲食、娛樂等生活習俗及喪葬風俗具有明顯的唐宋風格,這與遼上京、中京等地的契丹化特征形成鮮明對比。到遼中晚期,由于長期的人員往來及文化浸潤,該地區的契丹化特征表現得越發明顯,服飾方面不論是男裝還是女裝,衣袖均變的窄小,與遼北地的服飾特征基本相似。如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壁畫中的宴飲圖,桌旁站立著一男性侍者,身穿窄袖黃色長袍,腰間系帶,出行圖中的備馬者(男性)同樣身著圓領窄袖長袍,女性侍者身著直領窄袖藍色長衫,腰間系帶,下著絳地裙。[14]這類穿著服飾與中晚期遼墓中的男女侍從的著裝基本相同。此外,出行場景汲取了遼腹地的繪畫元素,出現了駱駝及駝車等,說明遼代中晚期大同地區受契丹文化影響較深。由于歷史及地理之故,該地區的文化生活呈現出獨特的地域特色。壁畫中既有表現農耕生活的勞作場景,又有游牧生活的牧群畫面,揭示了遼金西京大同亦農亦牧的經濟形態,這樣的經濟模式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飲食、服飾等等。總之,該地區的生活習俗既傳承了中原文化特征,又吸收了北方草原民族風俗,從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活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