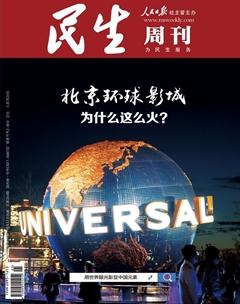蘆詠莉:讓學生更有“彈性”

北京第二實驗小學校長? 蘆詠莉
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13年后,蘆詠莉從高校的講壇上走下來,進入了小學的課堂。這一轉身,已然10年。
在這10年里,蘆詠莉從北京第二實驗小學的教師到校長,每個角色都充滿挑戰(zhàn),但她越走越從容。她將多年的理論積累運用到學校的教學管理中,而學校的教育實踐也讓她有新的發(fā)現和心得。
在學校的每一天,忙碌是常態(tài)。記者見到蘆詠莉時已經是下午,她坦言自己忙得有些“暈乎”了,但還是很開心地分享起學生們的日常照片和視頻,“我這兒的孩子特別好玩。”
作為發(fā)展與教育心理學專家,面對小學六年的教育,蘆詠莉提出要讓學生有一副健壯的身體、一顆發(fā)達的頭腦、一個遠大的夢想。在她看來,學生的身心健康重于一切,心理健康教育不只是心理教師的事,而是全校的事,貫穿在學校的各項工作中。
蘆詠莉關注學生的心理成長,希望學生能有“彈性”,不僅是心理的彈性,還包括思維的彈性,這樣才能適應將來的生活,應對漫漫人生路上的各種挑戰(zhàn)。
建立新的依戀關系
對每一所小學來說,一年級的新生入學都是“大事”,新生入學適應是否順利,直接影響后續(xù)教學工作的開展。
小學適應中最難的是什么?很多人認為是知識學習的適應,于是早早地讓孩子上課外培訓班,學習拼音、數學等知識。
但在蘆詠莉看來,學業(yè)適應并不難,難的是建立新的依戀關系。入學適應其實是孩子邁出家門,走入校園開展集體生活的時候,尋找新的依戀對象的過程。這個依戀對象如果尋找得好,他就會建立新的安全感,進而去學習和探索。
“孩子進入學校,也是進入一個新的探索環(huán)境,他需要很好的師生關系,很好的同伴關系,這樣他去探索這個世界就會變得很自在,他就不會在這里感到擰巴。”蘆詠莉說。
據她觀察,在小學中,不愿意上學,厭學或者學習有困難的學生中,至少有一半是因為人際關系不好,跟老師關系不好,或者跟同學關系不好,不喜歡校園,沒有辦法建立這種重要的依戀關系。
蘆詠莉告訴《民生周刊》記者,這種童年依戀開始是來自家庭成員,一層一層發(fā)展到生命中的重要他人,而這種依戀也分為三種類型,即安全型、回避型、焦慮矛盾型,其中最理想的是安全型的依戀。
“我們并不是要讓學生離不開老師,離不開學校,而是為了讓學生能更好地獨立生活。”蘆詠莉說。
她把建立這種安全型依戀的過程比喻為放風箏,有時候要緊一緊,有時候要等一等,有時候要松一松。“松的時候就是要認可學生,給他自主的空間,但也要對他所做的探索給出邊界,當他闖出邊界的時候要適時制止,這樣他才會知道要在一個安全的范圍內去闖。不過學生肯定會不斷犯錯,我們要制止的是具體行為,而不是探索的精神。”
只有建立了安全的依戀關系,教育才能更好地進行下去。蘆詠莉記得,學校曾有過一名學生是孤獨癥患兒,他到學校后總是不說話,老師們只能拉著他的手,帶著他一點一點地學,同時也要求所有的同學不歧視他、嘲笑他或者欺負他。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沒有一個老師放棄過這個學生。蘆詠莉常在校門口值班,剛開始這個孩子看到她扭頭就走,慢慢地會走到她面前圍著她轉一圈,然后高高興興地走了,再后來會專門跑到她跟前,湊到她眼前,對她笑一笑。
“他越來越認可老師,越來越喜歡老師,這需要花很長的時間,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但是只要堅持,就能做到。”蘆詠莉很欣慰,最后這個孩子到了畢業(yè)考試的時候,也能考到七八十分,順利地畢業(yè)了。
“彈性”的訓練
“看,小鐵腿呀。”“臭球簍子。”……在北京第二實驗小學的操場上,常有這樣“不友好”的呼聲。對學生跳繩動作太僵了,足球踢偏了等,旁邊的老師并不只是喊“加油”,還會“喝倒彩”。
“老師有時候是故意這樣喊的,我們就是要給學生們一點挫折。”蘆詠莉笑著說,“平時訓練的時候加一點心理上的鍛煉,到了真正比賽的時候,場上有各種各樣的觀眾,但他們會專注于運動本身,任何外界的聲音都聽不到,就算聽到了也不會受影響。”
其實在生活中也是這樣,蘆詠莉從來不要求學習環(huán)境特別安靜,反而認為對環(huán)境要求太高會讓人走向強迫癥。
“在心理的彈性中,最重要的是對成敗的理解。”蘆詠莉指出,人追求的是最后的英雄,在這個過程中會有起起伏伏,都很正常,沒有人一輩子都是對的,也沒有人一輩子都在贏。
她經常告訴學生,要把成敗看成暫時的贏、暫時的輸,有這種彈性,才有更多機會。即便放棄了,還有另一條路,怎么樣都行。
她要求學生能適應多元與變化,學會包容,有心理彈性。學校每個年級都有一些自閉、多動、抽動或者閱讀障礙的孩子,老師們都要求學生不要用異樣的眼光去看待他們,要接納他們,就像接納別人眼睛有大小、個子有高矮一樣。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蘆詠莉希望學生們在小學就能明白這一點,形成多角度的思維。學校也非常關注學生思維彈性的訓練,用各種方式讓學生知道,看待事物不止有一種視角,解決問題也不止有一種方法。
“二外”育人
“校長,什么是博愛?”一個二年級的學生對學校外墻上貼的校訓發(fā)出了疑問。
“你覺得呢?”蘆詠莉慣常地反問。“博愛是愛每個人嗎?”這個學生再問。在得到肯定的答復之后,他又慎重地問:“包括壞人嗎?”
“包括!”蘆詠莉很肯定地回答。學生大驚失色,“為什么要愛壞人?”
“那什么叫壞人?怎樣是愛壞人?”蘆詠莉還是繼續(xù)發(fā)問。這個學生認為,愛壞人就是幫助壞人干壞事。但蘆詠莉告訴他,愛壞人是制止壞人干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