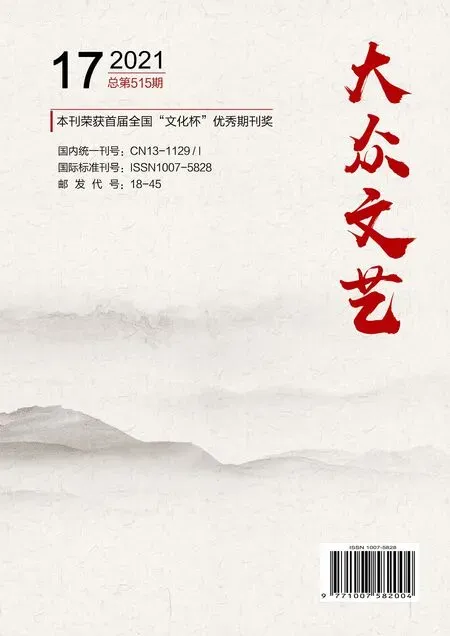古希臘陶瓶畫中的體育運動項目探究*
薛 芬 宋長江
(1.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藝術設計學院,江蘇南京 210000;2.河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河南新鄉 453000)
古希臘是世界體育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其體育運動反映了人類對自我潛能的開發,對勝利的渴望以及對和平的向往。體育運動在豐富古希臘集體生活的同時,也成為希臘藝術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在雕刻與繪畫中多有體現,陶瓶畫便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古希臘的陶瓶畫經歷了東方風格、黑繪風格和紅繪風格的演變,后兩者中,以體育運動為題材的作品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對于體育題材陶瓶畫的研究,過去多停留在藝術與美學的角度,較少從體育運動及背后的社會問題來進行闡釋。本文從體育與藝術的起源談起,進而論述體育題材陶瓶畫對于古希臘奧運會的記錄,起到了圖像證史的作用,最后落腳在對體育題材陶瓶畫所蘊含的藝術性探討上,挖掘陶瓶畫作為裝飾畫之外的價值,還原其真實歷史面貌。
一、古希臘體育與繪畫完美結合的歷史淵藪
在古希臘的儀式中,希臘人用形體的運動來體現力與美,傳達著崇奉與感恩。希臘人熱衷于競技,在此情況下,古代奧運會誕生了。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始自公元前776年,之后每四年一次,起到了停止戰爭,促進和平的功能。奧運會是群體公開性活動,公共的情感正是奧運會得以形成的基礎,也是古代繪畫創作的重要前提。英國劍橋學派學者哈里森在《古代藝術與儀式》一書中明確闡發其觀點:“能夠轉變儀式的并非個人的和私己的情感,而是公共情感,即由整體社區所共同體驗并公開表現的情感。”[1]在希臘人看來,體育運動能挖掘人體最大的潛力,體現人體本真之美。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講道:“希臘人首先鍛煉他們自己的身材為美麗的形態,然后把它表現在大理石和繪畫中間。”[2]也就是說,希臘人把體育當成一種藝術技巧,雕鑿著軀體,將其打造成藝術品。由此不難看到,在希臘人那里,體育就是藝術。于此,體育與藝術的最佳結合點就呼之欲出了。
希臘人認為美是終極目標,它展現出構成希臘哲學中的一些基本立場。在藝術源于模仿的觀念下,這些體育運動大量出現在陶瓶畫中,黑繪式《擲鐵餅者》就是典型一例。該作品畫面展現了運動員比例完美、結構精確的強健身體,它是陶瓶畫繁盛時期的代表作之一。在陶瓶畫中,體現出了體育與藝術的完美融合,體育為陶瓶畫表現生命提供了模仿的范本,陶瓶繪畫將體育精神展現為可見形象。可以說,古希臘體育與藝術相輔相成,共生共榮。
二、儀式與展演:陶瓶畫中的體育運動歷史記錄
(一)古希臘奧運會的內容展示
在我國傳統畫論里,早有“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畫”的經典論述,肯定了繪畫的文獻價值。今天的學者在考察古希臘的體育運動時,陶瓶畫為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佐證材料。毫不夸張地說,陶瓶畫形象地記錄了古代奧運會,從開始的儀式,到中間的各種比賽項目,再到最后的綬獎,每個環節都有表現。《繪有圣火傳遞儀式的紅像陶瓶》記錄了奧運會火炬傳遞的儀式。畫面里有三個運動員,后面一個雙腿錯開,呈奔跑狀,左手握有火炬,并將其傳遞給前面的一個運動員。第二位,也就是中間的運動員,回首伸右手去接火炬,左臂與左腿呈待跑姿態,整個畫面生動地描繪了火炬在運動員之間傳遞的瞬間。希羅多德的《歷史》就對圣火傳遞有所記錄,但相比這幅陶瓶畫的形象描繪,文字則相形見絀。
(二)競技體育項目的內容展示
陶瓶畫對于體育比賽項目的記錄也頗為詳盡。它們形象地記錄了比賽的場景,還原古希臘運動會的狀況,同時也能讓今人看到同樣的運動項目在古今之間的差別。如《英俊少年跳遠運動員》中少年頭戴橄欖枝環,低頭彎腰,雙手拿啞鈴狀器械,左手啞鈴一端觸地,右手啞鈴提于腰間,雙腳微開。以今天的視角來看,跳遠時手持啞鈴類重物,一定有礙雙臂的擺動與助力,對于彈跳的遠度,只能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但是,陶瓶畫的形象不會撒謊,古代奧運會中的跳遠運動員在起跳時,需要手持啞鈴狀器具,至于能否助跳,當時的希臘人必然是持肯定意見的。
古希臘女性也要進行體育運動,有單獨的女性運動會,奧運會里也有如賽馬等個別項目允許女性參加。《女子摔跤》陶瓶很好地展示了女性運動的一面,五個人中間兩人為女性運動員,留有長發,其中一女性為白色,其他均為黑色,黑白的強烈對比,能將兩人的摔跤動作表現得更為清晰。
通常認為,古希臘運動員必然個個體形健壯勻稱、瀟灑俊美,但拳擊運動員卻并不如此,其體型肥大,且有大肚腩特征,《大肚腩拳擊手》展示了希臘運動員的另一面。古希臘的拳擊運動員和今天的拳擊運動員在體型上有明顯出入,今天即使是重量型的拳擊運動員,在肌肉發達的基礎上也需體型勻稱,鮮有大肚腩者。而陶瓶畫中的大肚腩拳擊手,在記錄體育運動的同時,似乎也突破了希臘人固有的審美準則,不禁令人贊嘆不已。另有《勻速賽跑》《手持鐵餅的競技者》《賽跑》《搏擊》等等,不一而足。
(三)競技比賽儀式的展演
在記錄比賽授獎方面,《勝利綬帶》可以算較佳一例。畫面共5個人,分為兩組。左面一組兩人,一個著衣男子正在給一個運動員配授綬帶,有點類似于今天的頒發獎牌。右邊一組三人,兩著衣男子在互送禮物,而最右一男子手持小禮品,作猶豫不決狀。第二組似乎與第一組是不同場景,第二組中間的年輕男子應該就是第一組的運動員。有人推測,這是另外一種授獎形式。筆者在此闕疑,可以肯定的是,該陶瓶畫內容的確是一場授獎儀式。
以今天的藝術眼光看來,陶瓶畫是一種藝術創造,其中必不可少地帶有畫師的主觀表達,其對體育運動的記錄有多少真實,又有多少虛構,好像不可考證。但若時刻謹記希臘人“藝術是對自然的模仿”之理念,想必陶瓶畫中即使有畫師的主觀發揮,應該也不會過多。對陶瓶畫中的體育運動進行解讀,必然帶有時代的有色眼鏡,這是闡釋與實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如彼得?伯克說:“圖像可以讓我們更加生動地‘想象’過去。”[3]無論如何,陶瓶畫的存在,確實能生動地向世人展示古代希臘的體育運動,更能激發起對古人的敬重之心。或許,這正是體育運動題材陶瓶畫的歷史價值之所在。
三、從公共到私密:古希臘體育的社會性發展
古希臘的體育運動,并不是源于閑暇與娛樂,而是承擔著相應的責任與義務。體育運動所帶來的健美身材,是希臘人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公民自由的外在表現。在軍事意義方面,體育訓練對內可以和諧民眾,對外可以抗擊敵人,從而保證安全。作為愛智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也說:“每個市民決不能成為體育的門外漢,應該具有最堅實的身體條件。”[4]這在斯巴達城邦尤為突出,其公民從出生就開始從事強負荷的體育與軍事訓練,恪守保衛城邦的職責。
無論體育承擔的是何種責任與義務,都屬于希臘人的公共空間活動。關于公共空間,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認為,“這個公共空間,……跨越了個人和家庭界線,是公眾聚眾場合,公眾在這里對公共權威或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作出自由的、理性的評判。”[5]希臘的公共空間為體育運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而體育活動的公共性促進著古希臘民眾的凝聚力。相似的是,藝術創造在一定意義上同樣是公共空間活動,因為古希臘時期藝術家的創作活動,表達的是一種群體性生活,或者說,自我的表達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否則便會被趕出柏拉圖的“理想國”。因而,“對于希臘人來說,圖像不僅僅是簡單的再現,它是一種社會性的事實。”[6]如雕像與壁畫,它們不是私人擁有的對象,而被置于公共空間。相對于雕像的公共性,陶瓶畫則較為私密,從陶瓶的用途來看,可說明這一點,伍德福德在其《古希臘羅馬藝術》中,將陶瓶的用途總結有四:作為盛具、作為飲具、用于擺設、作為禮器,這基本肯定了其日常生活用品的屬性,主要在家庭內部使用。顯而易見的是,畫有體育運動題材的陶瓶畫,將體育運動從公共活動空間滲透到了希臘人的私密性生活空間,它起到了鏈接性作用。
有人說,希臘的體育與藝術是自由的象征,但若看到,連私密性的家庭空間也被諸如體育、傳說等繪畫所代表的形式侵占時,恐怕此自由要打些折扣。不管怎么說,體育題材的陶瓶畫在無形之中推動了這種自由,以藝術的形式宣揚著希臘的審美。
四、結語
陶瓶畫中表現的大量體育運動,起到了圖像證史的作用,為今人對古代奧運會的研究與想象提供了巨大空間。作為裝飾性藝術,無論是體育題材,還是其他題材,都是為了滿足人們審美的需求。不過,看似集審美與自由為一體的體育題材陶瓶畫,并沒有逃脫科林伍德所說的藝術行列。其成功之處在于,在表征其社會性時,體育題材陶瓶畫不是強迫性的灌輸,而是讓人在審美的感知中,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并深深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