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死與愛死——《文城》的悲劇書寫
馬璐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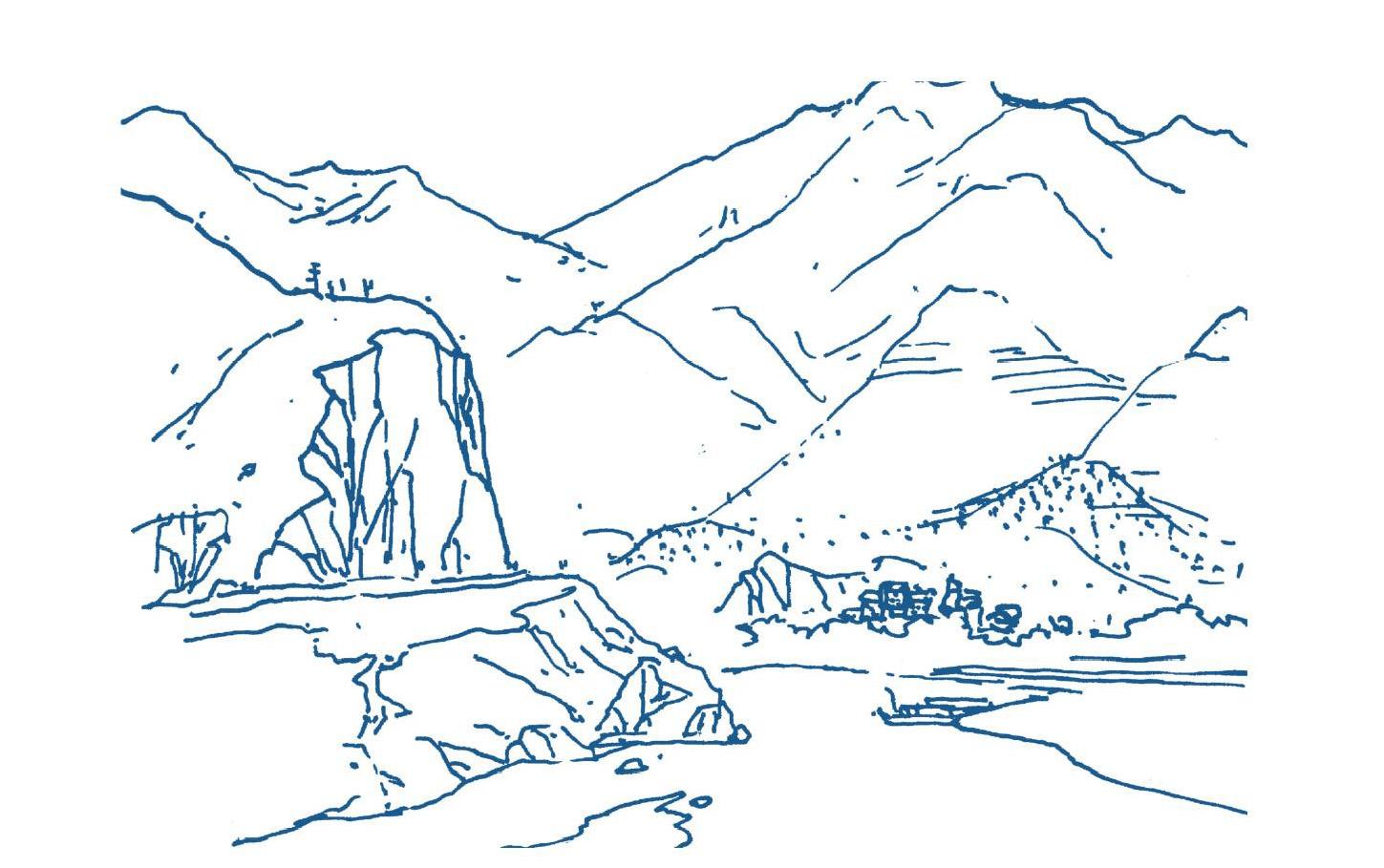
《文城》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匪禍橫行的大背景之中,亂世天然就具備著一種恐怖、肅殺的氛圍,其圖景構成動輒是大場面的人群,軍隊、匪徒、平民們,一旦形成了群體匯聚而成的全景圖,那么個人的渺小就更加被凸顯出來,個人的生命便成了最脆弱、最易損害的東西,當這樣一幅圖景展現在眼前時,死亡已經被濃厚的亂世氛圍沖淡了——我們可以預料到必然的死亡。死亡主題在余華的作品中并不罕見,而《文城》則將兩種悲劇形式——弱者的死亡與強者的死亡,置于了同一個敘事空間之中,“正文”與“補”,兩個部分,兩種腔調的聲音同置,使得小美的悲劇在歷史的大敘述面前更加動人。
清末民初之時,中國的社會環境處于大的變動之中,革命、戰爭紛至沓來,那是一個需要“英雄”的時代,民族國家話語被置于高處,在此,文學的邏輯與歷史的邏輯巧妙地重合了起來,對歷史的思考、想象與呈現代表著當代作家的藝術價值判定以及審美取向。在時代洪流之中,“人”是最渺小的,也是最易被遮蔽的,人們自然而然地將眼光放在時代的變遷這一宏大命題之上,只有宏闊的筆觸才能將動蕩不安的大時代容納進去,這樣的時代需要有力度的文學。
而《文城》的正文部分無疑就是群像式英雄悲劇的大敘述,本文的基調是肅殺、悲壯的,以亂世中的死亡為底色,濃墨重筆渲染出的一幕幕死亡圖景少了此前余華慣寫的悲哀、荒誕,但因獨具時代特征的殺身成仁的英雄主義精神以及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俠氣,其帶來的震撼感與沖擊力絲毫未受減損。就如那十八個壯烈犧牲的民團兵士,他們沒有被葬在西山,顧益民把他們葬在城隍閣前的空地上,他要百姓們記得是誰保衛了溪鎮,他們的死值得立碑做傳。
我想把林祥福的死稱為“赴死”。在決定前去贖回顧益民的時候,女兒的樣子突然浮現在了林祥福面前,這仿佛是什么預示,此去兇險萬分,要做好必死的決心,然后他想到了陳永良,他輕聲說,“我去”,這時,他決定赴死。在臨行前,他寫好了三封信,他寫“葉落該歸根,人故當還鄉”,他知道此去兇多吉少,所以寫下信,他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當然,我相信他是期待著希望著自己可以活著回來的,所以才又把這句話給涂黑。他去翠萍那里吃了最后一頓晚飯,這是他給自己的告別儀式。在臨行前,他不斷想起自己的女兒,在去往匪窩的船上,他回憶了自己的一生。余華在這里給了林祥福的死亡以長長的鋪墊,這個鋪墊不僅讓讀者隱隱猜測到他的結局,這種延宕強化了林祥福本人對自己前路的預知,即便知曉前路但他仍舊要去“趕赴”即將到來的死亡。
亞里士多德的悲劇觀立足于嚴肅與宏大,旨在嚴肅而不在悲,他認為“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凈化(Katharsis)”,“卡塔西斯(Katharsis)”即要求對于接受者情感的克制,可以說,古希臘的悲劇多是一種英雄悲劇,是悲壯的,而悲壯則是嚴肅的、是震撼的。
“死亡”天然可以與“悲劇”劃等號嗎?赴死是悲壯的,是知前有猛虎偏向虎山去的精神,是我們民族中為義而殺身成仁的赴死精神,是中國自古以來傳承的氣節,英雄的死值得立碑做傳。永遠被人們銘記與無人所知的螻蟻的死亡相比,有意義的死亡是悲劇嗎?
如果林祥福的死、獨耳民團的死,是英雄的死,是“赴死”,那么小美的死,則是小人物的死亡,是“受死”。當小美攜著她無法擺脫的宿命登場,如同螻蟻般的命運似乎怎么也無法被稱為悲壯,她是個平凡人,是生活的弱者,甚至她的死無人在意,可就是這樣的小人物,卻代表著歷史中千千萬萬同樣的境遇。
于悲壯而言,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而當我們審視現代悲劇美學,其基調更大程度落腳于對于不幸者所遭受苦難的“哀嘆”。在“補”的部分,小美的悲劇以哀柔的前調登場,她的死亡并不悲壯,其故事也是綿綿地開展,似乎沒有那樣劈面給出的強大力量,但卻余味悠長。若說正文部分的英雄悲劇具有著悲劇的力度,那么小美的命運悲劇則真正具有藝術上的美學韻味。更深入地讀下去,小美的故事站在人類的經驗立場上,是具有哲思意味的女性命運寫照。
小美是《文城》中的靈魂,她支撐起了整個故事,卻遲遲隱而不現,在“正文”部分中,并沒有正面寫到小美,她藏在這段歷史背后,卻難以讓人們忽略。小美是一個小人物,她的死亡沒有意義,她跪在雪地里,同許多人凍死在一起,是她們之中的一員,葬在終日不見陽光的西山北坡。那里不見陽光,當然也不見人的目光,螻蟻一樣的死去,無人在意,沈家的祖墳再無親人會去祭奠(林祥福曾離她們很近,但他們永遠地錯過了),這不是一種孤獨,而是無人在意的悲哀。林祥福的死,獨耳民團的死,是英雄的死,是強者的死,如果將他們的死稱為赴死,那么小美的死,則是弱者的死,是受死——是被動的,是巧合的,是猝不及防的,甚至是沒有意義的。而她的死亡恰恰正因為這種“無意義”而具備了悲劇的美學價值。
主流的歷史敘述,是從社會歷史結構中生發的“大敘述”,尤其是在一個長的時間維度中、在一個大的空間維度中,其原本就存在著一個總體。但兼顧總體的敘述必然是簡略的,是散點展開的,于是,在時代洪流之中,“人”也是最渺小的、最易被遮蔽的。無論在文學上發展進程中還是歷史上,“人”的發現幾乎都是“人” 經歷漫長的壓制、摧殘之后的被重提,都與人的解放相連,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潮流一起構成了新時期“人的解放”的重要內容。20世紀早期,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提出了“人的文學”概念,標志著近代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人”的覺醒,標志著“人”作為“個人”而不是“群體中的人”被肯定。《文城》是一個筆觸宏闊卻又精細的典型文本,余華在鋪展統觀全局式的“大敘述”之時,也將隱微的人性以及命運書寫聚焦于小美身上。小說的敘事方式是作家歷史觀的反映,也是對世界、社會、人生的認識方式,代表著一個作家的整體性歷史觀。而在這一敘述空間中,歷史這一整體毫無疑問被深入地細化到了人生之中,余華將散點式的大敘述收束起來,聚焦在“人”身上,他的文字在呼吁著“被歷史淹沒的人”。這是余華展現時代的一種獨特的歷史視野,也是他書寫時代的一種獨特的方式。
此外,小美代表了男權話語之下的“美”的標準,在文本的語境中,她是一個可以在普遍意義上被稱為“美的象征”的女人。她的美不光在于外表,還在于其本身的順從、賢惠、繁育這些作為一個“好妻子”的特質。在男權話語中,她可以被稱為是一個好女人。面容美麗,性格順從,盡到了其應盡的義務。因為這種“美”,她的悲劇才更讓人惋惜。
在男權話語之下,好女人/壞女人的判定標準與好人/壞人的判定并不一致。偷竊可以是好人與壞人的判定標準,而在文中,好女人與壞女人的判定標準則是“偷穿花衣服”。為什么小美欺騙了林祥福,還偷走了林祥福家傳的金條,仍然可以被認為是“美”呢?林祥福在她回來時,為了說服自己,是這樣為她辯解的:“雖然你把我家一半的金條偷走了,一根也沒有帶回來,但是你沒有把我的孩子生在野地里,你把我的孩子帶回來了。”“你也沒有狠心到把金條全偷走,你留下的比偷走的還多點。”林祥福為她辯護是為了肯定她的人格嗎?我想不是的,只是作為一個令人喜愛的女人,作為妻子這一身份,她最終還是回來了,她堅定地要把林祥福的骨肉送回來,包括后來轉胎,希望給林家生一個男孩,這些“好女人”的特質足以掩蓋對于人格是否高尚的要求。林祥福原諒了她,原諒的不是她的偷竊與出走,而是作為一個“所屬物”最終的回歸。或者說,小美她并不被要求作為一個個體的人應達成的品質,她所被要求的,都只是作為“妻子”該有的品行。所以她的人格不需高尚,而作為一個“妻子”,她本無什么錯誤,甚至無論怎樣看,都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妻子。故而,林祥福對她的諒解是順理成章的。
《文城》總體的時間觀實際上并非是循環式的,而是站在一個較大的歷史維度面前的線性時間觀,但其將宏大的歷史與尋常的生活放在同一個敘事時空之中,一個作為前景,一個隱為后景,正是這一前一后的敘述空間展開中,小美的命運悲劇漸漸清晰,這種代代相因的宿命卻不自覺地浮出了文本。循環論并非是現代話語體系中的時間觀念,分分合合是一個自古而然的循環,是中國傳統敘事的時間觀念,諸如從無到有再到無的《紅樓夢》,從石頭偶遇一僧一道開始,再有賈寶玉隨一僧一道離家結束,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再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國演義》,這一根據歷史寫就的小說從現實層面證明了循環論的哲學。這種循環論的觀念更貼近于自然,不僅是人生,即便是時代、社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納入循環當中的。于是這一時間觀念在文學話語中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一種哲學思考,個人的命運在這種循環的哲學之下就多了一層宿命感,更加突出了悲劇的美的力度。
當我們把眼光聚焦到站在小美背后的那個女人時,小美命運的無力與停滯也就凸顯了出來。十歲的小美以童養媳的身份進入了沈家,從此,教育、塑造她的人是她未來的婆婆,可以說,是婆婆造就了一個男人喜愛的好女人。“婆婆隱約看見了過去尚在閨中的自己。小美干凈整潔、不茍言笑、勤儉持家。”婆婆隱約看到了過去的自己,那么是否也曾經有一個女人——那個將婆婆塑造成如今這個樣子的女人,也曾經看著年輕的婆婆,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呢?正是由小美為圓心,構成了具有代際意味的循環的時間觀。小美的兩次“盜竊”、兩次婚姻、她的出走以及回到文城,這種空間感上的閉環將其背后隱藏著的時間環給連接了起來。從哲學范疇來看,循環的時間注定是虛無的、是悲觀的,身處其中的生命個體,必定也陷入陳陳相因的宿命之中。小美與婆婆這同一家族中兩代女人的承繼,似乎構成了女性的代際承繼的隱喻,女性長久以來被規訓的、被要求的“道德”的傳承,而時代似乎停滯在了這樣的承繼之中,也被消解在了這一悲觀的敘述之下——陷入循環是生命本身難以掙脫的悲劇。
小美的人生就如同她的死亡一樣,是受死,也是受活,無論是活著還是死去都是被支配被操縱的。她的悲劇是她的命運,是她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刻就已經帶有的“原罪”。

